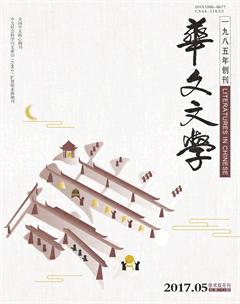微信與華文文學的跨語境傳播及相關(guān)問題
顏敏
摘 要:微信既是華文文學跨語境傳播的新形式,也是華文文學跨語境生存的新空間。首先,通過個人微信號,公眾號、微信社群等多種途徑,華文文學在微信中的跨語境傳播變得頻繁而便捷,時空距離和文化差異趨向模糊。其次,面對微信中凸顯新聞性和交往性的華文文學作品,“離散、邊緣和混雜”等以往的詩學話語需重新定位。第三,微信傳播敞開了華文文學發(fā)展所面臨的如新聞性與文學性的矛盾、交往性與文學性的沖突、經(jīng)典意識的弱化等新問題。或許,在我們的時代,華文文學的價值還在于作為交往媒介融通整個華語世界,故而如何定位與發(fā)展作為“次文學”樣態(tài)的華文文學將成為我們要面對的重要問題。
關(guān)鍵詞:微信;華文文學;跨語境傳播
中圖分類號:I0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0677(2017)5-0036-07
1980年代以來,“華文文學”逐漸替代漢語文學成為語種文學的總稱①,從現(xiàn)實情況來看,它隱含了將中國大陸文學“包括在外”的視野,即指向以中國大陸文學為參照,在大陸文學之外,以華文為表達工具的文學存在②。因歷史經(jīng)驗、社會制度、區(qū)位文化等的不同,華文文學在區(qū)域間的流播具有跨語境性;但正是跨語境傳播的過程和經(jīng)驗,激活了這一概念的內(nèi)在活力,確立了其現(xiàn)實意義——限于單一區(qū)域得來的狹隘思路與理論觀點遭遇挑戰(zhàn)。可以說,華文文學這一文學景觀本身就是跨語境傳播的結(jié)果,具有流動性和過程性,考察華文文學跨語境傳播的歷史與現(xiàn)狀,現(xiàn)象與規(guī)律,對理解其存在狀態(tài)與詩學特性具有重要意義。
媒介不是中介、也不只是信息,而是構(gòu)成了文學賴以存在的場域或語境,新的傳播媒介,不僅是新的傳播方式,也提供了考究文學存在樣態(tài)的新路徑和新語境。從華文文學跨語境傳播的媒介變化情況來看,自1980年代以來,經(jīng)歷了以紙質(zhì)媒介為主到影視網(wǎng)絡等電子媒介全面介入的復雜過程,近幾年來手機移動網(wǎng)絡也成為重要的傳播媒介。其中,微信的崛起值得關(guān)注。微信是騰訊公司推出的一款互聯(lián)網(wǎng)交友軟件,自2011年進入市場以來,短短五年多時間內(nèi),用戶已有6億多人,逐漸成為移動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生活方式的象征,為文學提供了一個全新的生長基地。微信所具有的時空跨越性為華文文學的跨語境傳播提供了契機,催生了眾多新的現(xiàn)象與問題,故本文嘗試以微信為主要陣地,探討移動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華文文學跨語境傳播的現(xiàn)象及相關(guān)問題。
一、微信與華文文學跨語境傳播的新形式
微信是社交軟件,卻給文學留下了一定空間,文學以特定形式在各種微信形式中被推出。一是個人微信號。在這個人人都是寫手的時代,個人微信號推出了大量的原創(chuàng)作品,也轉(zhuǎn)發(fā)了大量心靈雞湯式的文學養(yǎng)料。其中,作家、學者和編輯的個人微信號是帶有鮮明文學印記的主打傳播載體。二是微信公眾號,由文學刊物、文學組織、文化公司推出的各類公眾號,有目的、有規(guī)律地推出帶有鮮明特色的文學作品與文學信息,成為文學傳播的集中箱。三是微信社群。由文學組織、學術(shù)團體、師生群、高校文學院工作群等組成的社群,活躍著眾多專業(yè)或準專業(yè)的文學愛好者,眾聲喧嘩,可謂文學傳播的交響樂團。華文文學的跨語境傳播,也主要依靠這三類微信形式進行。
(一)個人微信號:作者、學者和編者的互動網(wǎng)絡
微信雖是中國大陸推出的一款媒介平臺,但因它和手機操作平臺的完美融合,已被世界各地華人廣泛使用③。近幾年來,分散在不同區(qū)域的華文作家、研究者和各類文學刊物、出版社的編輯開始陸續(xù)申請個人微信號,并通過朋友圈產(chǎn)生互動,他們及時發(fā)布并交換有關(guān)華文文學的創(chuàng)作、評論、出版及活動信息,形成點對點,點對面、面對點等多種信息交換方式,構(gòu)成了一個可以瞬時、延時互動的跨語境傳播網(wǎng)絡。在這種具有拓展交互性質(zhì)的傳播網(wǎng)絡中,傳播的信息在數(shù)量上如滾雪球般擴容,在形態(tài)上則表現(xiàn)為重復與聚集。因而華文文學在個人微信號中的傳播,呈現(xiàn)在區(qū)域涵蓋面不斷拓展、信息流量不斷增長、信息聚焦可能性越來越高的趨勢。
個人微信號及朋友圈的交互功能使得華文文學獲得更多轉(zhuǎn)發(fā)、評論和聚焦的機會,跨語境傳播的速度和廣度得以提升。但個人微信號立足于個體生活及其社交需求基礎(chǔ)之上,并非純文學的、專業(yè)化的傳播渠道,呈現(xiàn)的信息也處在個人生活與文學信息混雜的狀態(tài)。作為聯(lián)系紐帶的華文文學,在朋友圈中存在但不常在;必要但非重要,相關(guān)評論留下人際交往的痕跡,更多隨意的點贊、簡單的應答,及時率性的回復,這造成了華文文學通過個人微信號跨語境傳播的平面感。
(二)微信公眾號:傳統(tǒng)紙媒的延續(xù)與轉(zhuǎn)化
目前,微信公眾號的類型日漸多樣化,與華文文學跨語境傳播相關(guān)的主要有以下幾類。一是由文學刊物、文化公司、出版社等推出的微信公眾號,它類似傳統(tǒng)紙媒的電子版,是宣傳、推廣、銷售文學作品的移動形式,通過定期推送作品目錄,刊發(fā)節(jié)選作品片段,發(fā)布相關(guān)出版信息,起到廣而告之的作用。其傳播思路延續(xù)傳統(tǒng)紙媒的選擇性原則,華文文學的位置及其內(nèi)部構(gòu)成并沒有發(fā)生變化。如人民文學,收獲,上海文學、花城出版社、華語文學網(wǎng)等公眾號中,海外華文文學作為微量元素,融匯在外國文學、大陸文學之中,選擇的作家作品受制于特定刊物與出版社的編輯意圖。二是由文學組織、文學社群、文學刊物推出的公眾號,它相當于同人刊物的精華版,定時推出組織成員的代表作品,發(fā)布一些文學信息。如國際華文微詩群的公眾號每周一次推出精短的同題微詩及相關(guān)的文學評論。此外,還有以公眾號形式推出的綜合性電子刊物。它也會推出一定數(shù)量的文學作品,但常作為點綴邊料存在,帶有較強的新聞化、問題化色彩,與世界各地華文紙媒處理文學的思維一致。如由北美華人主持的《世界華人周刊》公眾號推出的文學作品和文學信息便具有上述特點。
微信公眾號在處理華文文學的思維上與傳統(tǒng)紙媒相似,但增加了很多新的傳播路徑,如頻繁的超鏈接、多媒體的發(fā)布形式,互動的在線批評、贊賞的商業(yè)回饋、與電子書的互融④等,這些新形式的存在使得華文文學跨語境傳播過程成為與用戶互動、與時代融合的過程。同時,華文作家及其作品在公眾號的推出方式具有強烈的宣傳發(fā)布意識,被新聞化和信息化。endprint
(三)微信社群:集結(jié)的文學空間
微信社群是以微信維系的社團空間與組織形式,對于處于分散狀態(tài)的華文作家和研究者而言,是一種非常便捷實用的聯(lián)絡方式。目前,以華文文學為紐帶的微信社群主要有以下幾類,一類是以學術(shù)研究為紐帶的研究社群,如以導師為中心的師門群,以研究組織為中心的學會群等,另一類是以原有文學社團為基礎(chǔ)建立起來的華文作家社群,如美國洛杉磯華人作家協(xié)會的環(huán)球作家微信群。此外還有以某種創(chuàng)作現(xiàn)象或會議活動等為紐帶新建的各類創(chuàng)作社群,如國際華文微詩群、華文文學與中華文化群等。
微信社群是眾說紛紜的傳播空間,超越了點對點傳播方式的局限,使華文文學的跨語境傳播走向了立體化。理論上,無論身處于哪一區(qū)域空間,只要被允許加入特定社群,其成員就超越了本土語境,進入信息共享體之中,可以隨時發(fā)布華文文學的學術(shù)會議與活動信息,共享創(chuàng)作動向與創(chuàng)作成果,進行評論、創(chuàng)作和研究的互動對話,跨語境傳播的效應便凸顯出來了。但實際上,社群的宗旨、組合方式和成員的性質(zhì)、連接強度等都會影響文學傳播的方式與效果。一方面,成員的區(qū)域構(gòu)成越是多樣,社群宗旨越是開放,群主及主干成員的組織力度越大,跨語境傳播的可能性及其效應就越凸顯。如世界華文微詩群以微詩創(chuàng)作為紐帶,有意打破區(qū)域界線,獲得了較好的創(chuàng)作成果,形成了眾多共識⑤。另一方面,由于微信社群是相對獨立、具有一定封閉性的交流社區(qū),社群與社群之間存在傳播的距離,這就有可能造成新的保守視野,妨礙跨語境傳播的力度。如北美文學社團林立,各自組織了本地區(qū)的微信社群,但這些社群作為本地華文作家的網(wǎng)絡聚會場所,以自娛自樂為主,具有明顯的內(nèi)向性格,難以促成區(qū)域文學向外延伸發(fā)展的推動力。此外,建立在社交維度之上的微信社群,文學傳播自有限度,存在缺乏過硬的專業(yè)向度、溝通的生活化和隨意化、聊天信息的瞬時化和海量化等現(xiàn)象。
此外,個人朋友圈、微信社群和微信公眾號中偶爾出現(xiàn)的電子書鏈接,也是不容忽視的現(xiàn)象,讀者通過打開微信提供的電子書鏈接,可以獲取完整的文章或著作信息,供網(wǎng)上瀏覽或下載打印后閱讀,這種全媒體時代微信與其他媒介互動互融的形式說明,微信對華文文學的跨語境傳播,具有多面向的拓展,可能走向綜合性傳播的態(tài)勢,提出了知識產(chǎn)權(quán)保護等方面的新問題。
二、微信與華文文學的詩學新質(zhì)
通過對微信空間華文文學跨語境傳播現(xiàn)狀的簡要梳理,另一種形態(tài)的華文文學逐漸呈現(xiàn)在我們面前。它以信息化、新聞化和生活化的方式出現(xiàn)在我們的日常交往空間里。那么,這種形態(tài)的華文文學,能否用我們立足于印刷媒介而形成的詩學話語進行闡釋理解呢?在原有的論述體系中,當我們研究華文文學,特別是海外華文文學時,最常用的詩學話語有“流散、邊緣和混雜”等,這些詩學話語在面對由微信跨語境傳播所造就的華文文學景觀時,在我看來,有必要進行反思和調(diào)整。
(一)流散的中斷
以往,當我們論及華文文學時,常在聚合和流散的矛盾關(guān)系中突出“流散”現(xiàn)象及其意義,這是因為,當我們認可了華文文學這一命名時,就意味著我們的聚焦點不是指向大陸的漢語文學,而是聚焦于臺港澳暨海外的華文文學,而后者,在很長一段時間內(nèi),相對大陸文學,其作品在語言表述、思想內(nèi)蘊、形式技巧等方面都別具特色,這種由作家所在地域差異和流動經(jīng)歷而產(chǎn)生了在作品藝術(shù)上的流散性,豐富著我們對于漢語文學的審美感受,經(jīng)由反復提及和論述,逐漸上升為所謂流散(離散)美學。
流散美學是對特定時期華文創(chuàng)作的總結(jié)提煉,從傳播媒介的特點來看,這一話語流行的時期,是以紙質(zhì)媒介為主的文學傳播時代。相對電子媒介,紙質(zhì)媒介的出版、發(fā)行和流通都受時空限制,構(gòu)成了區(qū)域文學的保護墻,有利于不同區(qū)域文學保持相對穩(wěn)定的美學特性,因而某些區(qū)域的華文文學相對主流漢語文學而言就具有了流散性。進入互聯(lián)網(wǎng)特別是移動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之后,隨著地域感的消失,不同區(qū)域的文學創(chuàng)作相互影響、互相滲透,彼此難以形成懸殊的美學差異,文學由流散逐漸走向聚合。可以說,越是新的媒介,就越有利于不同區(qū)域文學的聚合。微信作為新一代社交媒介具有了更強的聚合能力,在對華文文學的跨語境傳播中,它借助強大的人際和組織傳播優(yōu)勢,打造了共同閱讀、欣賞和評論華文文學的移動平臺,不同語境的華文文學逐漸融匯成一體化的媒介景觀。雖因時間尚短,這一聚合過程對華文文學創(chuàng)作產(chǎn)生的影響不是特別清晰,但趨同效應是顯而易見的,也就是說,華文文學由流散而導致的美學多樣性可能逐漸被媒介同一性消解。
(二)邊緣的重構(gòu)與消失
“中心和邊緣的對峙”是我們以往定位區(qū)域華文文學的美學與文化價值時常借鑒的話語框架。余光中的“三個中心”也好,以王德威為代表的美國華裔學者的“華語語系文學”也好,都暗示了由地理、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延伸而來的文學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以及由此而形成的詩學話語與價值判斷。但在微信等新媒體的話語空間里,作家作品背后的地理區(qū)域空間變得無足輕重,更重視的是另一些特點——或是具有強烈的新聞性和時間性的文學現(xiàn)象,或是滿足心靈撫慰和休閑所用的雞湯式文學——。在此情境下,有關(guān)華文文學的論述即便沿用邊緣與中心的話語模式,其所指也發(fā)生了轉(zhuǎn)移,從地理區(qū)域的差異維度轉(zhuǎn)變?yōu)閰^(qū)域、作家、作品與新媒體的關(guān)系維度。
在微信之類的新媒體空間里,區(qū)域、作家、作品與新媒體的關(guān)聯(lián)方式與關(guān)聯(lián)程度將影響其在文學場域內(nèi)的位置與價值⑥。從宏觀層面來看,那些位于技術(shù)前沿的區(qū)域華文文學將更容易融入新媒體空間,從而凸顯其價值;從微觀層面來看,那些善于運用新媒體的作家或具備某些特質(zhì)能被新媒體青睞的作品,將成為中心,而那些固守傳統(tǒng)寫作范式,與新媒體無法直接關(guān)聯(lián)的作家,則逐漸被邊緣化,乃至消失。自然,新媒體背后也會有意識形態(tài)的力量,但經(jīng)由新的媒介技術(shù)的過濾與變形后,傳統(tǒng)的文化政治中心對華文文學的規(guī)訓將在形式與內(nèi)涵上有所變化。
根本的層面是,微信等新媒體的技術(shù)力量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界限鮮明的中心邊緣思維及其背后的生存模式,讓深受地理、文化局限的人們享受快速越界的快樂,最終出現(xiàn)如麥克盧漢所言之地球村的效應⑦。事實上,有關(guān)華文文學的中心與邊緣之說的背后正是中外文化碰撞沖突的生存語境,誕生于紙質(zhì)媒介時代的部分海外華文文學作品中,的確保留了這一結(jié)構(gòu)——作品中,代表西方文化的環(huán)境或個人往往處在強有力的中心位置,形成對代表中華文化的離散者的壓制,進而影響到人的命運與選擇。而微信空間里華文文學的跨語境流播現(xiàn)象,本身就體現(xiàn)了跨越文化邊界的速度和文化和解的心態(tài),其文學作品的思想內(nèi)涵與價值取向能否用“中心與邊緣”一概論之值得懷疑。在我看來,對邊緣和中心思維定勢的超越,可能成為微信時代重構(gòu)華文文學詩學話語的關(guān)鍵之一。endprint
(三)混雜的新動向
混雜也是以往我們分析華文文學創(chuàng)作時常用的詩學話語。何謂混雜?從形式層面來看,包括了創(chuàng)作手法、表達語言、審美意象的中西合璧,從思想內(nèi)涵的層面來看,則指向作品所傳遞的文化觀念、審美境界等方面的繁復化合。創(chuàng)作上的混雜現(xiàn)象,往往是創(chuàng)作主體的多重文化身份和生活體驗在文本中的自然呈現(xiàn),可以視作對華文文學審美獨特性的體現(xiàn)。從早期容閎、邱菽園到當代的白先勇、洛夫,在其創(chuàng)作中都確認了混雜的存在及其正面價值。然而隨著全球化的進程,混雜成為一種普遍的生活和文化現(xiàn)象,在文學創(chuàng)作中比比皆是。如一位中國大陸作家可能擁有豐富的港臺經(jīng)驗和海外經(jīng)驗,其創(chuàng)作既有本土色彩與關(guān)懷,又充滿了異國情調(diào)和對異文化的認可。一位美國華裔作家,可能一直居住在北京或上海,他寫的故事,或與其華裔身份和美國經(jīng)驗有關(guān),可也有著直書中國的歷史與現(xiàn)實的汪洋恣肆。
微信空間中,華文文學的混雜還可以有新的動向,主要表現(xiàn)在兩個層面。一是不同媒介話語的混雜。微信既是已有文學作品的傳播空間,又是新媒體文學的生產(chǎn)機制,涵蓋了印刷體、多媒體和手機體的等多種文學話語形式,故而微信空間的華文文學是多種媒介話語的混雜存在。二是不同代際話語的混雜。每一代作者和讀者都有不同的文本經(jīng)驗和閱讀旨趣,形成了文學話語的代際⑧差異,隨著微信群體的增加,華文文學作者與讀者的層次愈加豐富,不同代際文學話語的混雜將成為不容忽視的現(xiàn)象。對于研究者而言,這種代際混雜現(xiàn)象可謂華文文學的最新動向,它將我們的審美注意和詩學建構(gòu)從橫向比較引向了縱向探索。
三、微信與華文文學面臨的新問題
作為當前社交傳媒的代表,微信與文學的關(guān)系既體現(xiàn)了新的媒介形態(tài)對文學發(fā)展的影響;同時也具時代寓言的性質(zhì),如一面光影交替的鏡子,照出了時代文學的特征及問題。因而,通過梳理微信與華文文學跨語境傳播的關(guān)系,我們不僅獲得了反思華文文學詩學話語的契機,還發(fā)現(xiàn)了華文文學創(chuàng)作與研究所面臨的新問題。
(一)新聞性與文學性的矛盾
按照傳統(tǒng)的文學觀念,文學與新聞是有區(qū)別的,新聞強調(diào)時效性,報道事件的速度越快越好,文學雖有時代性,卻更注重作家個體審美印記對現(xiàn)實的沉淀與加工。在當下語境中,微信傳播的速度已經(jīng)超過了傳統(tǒng)媒體,讓依附其中的文學生產(chǎn)與傳播都具有新聞性,華文文學也作為一種信息化的產(chǎn)品被微信接納、傳播,由此導致其文學性的探索受到影響。
從創(chuàng)作的時間維度來看,微信上的文學可以按秒來計算其生產(chǎn)速度,刷新率極高,但不假思索、一點就發(fā)的情感表達,能否稱之為傳統(tǒng)意義上的文學?如華文微詩群上一些華文詩歌就有速度過快、沉淀不夠的特點,或緊跟時事變化而即可推出幾首,或應和同群之人而率性吟誦幾句,幾小時后就被海量信息遮蔽,消失在雜七雜八的聊天記錄里。從創(chuàng)作的內(nèi)容層面來看,多為以文學表達技巧呈現(xiàn)事件和情感故事的文本,少見嚴肅自省的創(chuàng)作。編選者用炫人耳目的標題對華文文學文本及現(xiàn)象進行肢解、變形,滿足特定的傳播目的的現(xiàn)象也屢見不鮮。如《世界華人周刊》介紹香港作家亦舒時,用了這樣的標題《她是最受追捧的言情小說大師,但她一生最大的敗筆就是愛情》。從創(chuàng)作主體來看,短期轟動效應的追求也使得很多華文寫作者在微信上的創(chuàng)作新聞化、時事化,缺乏沉淀意識;一些海外華文作家借助微信平臺,積極靠近與國內(nèi)文壇和政壇,熱衷就時事進行文學創(chuàng)作與表達,喪失了原有的流散優(yōu)勢。
(二)交往性與文學性的沖突
在傳統(tǒng)的文學觀念中,文學的主要特性是審美性,交往性倘若存在也是隱性的。但在微信這一社交媒介之中,文學所具有的交往功能及其衍生出的相關(guān)特征,已經(jīng)上升到更為重要的位置,甚至會與文學自身的審美訴求產(chǎn)生一定的沖突,對華文文學的發(fā)展產(chǎn)生了一定的影響。
從創(chuàng)作層面來看,交往空間的文學,由于重視對心靈的撫慰和沖擊,造成了雞湯型、安利體文學的流行,一些在微信空間流播的華文文學作品不是短、淺、甜,就是故弄玄虛、炫人耳目,正體現(xiàn)了交往性對華文文學的影響。誠然,對于部分游離于宏大敘事之外,重視表情達意等小我訴求的海外華文文學作品而言,微信生存可謂猶魚得水,可是否因此會喪失走向深度敘事的可能性呢?從研究層面來看,微信凸顯了更為鮮明的華文文學圈子意識。以個人交往為中心的朋友圈、以師生情誼或?qū)W會組織為紐帶的微信社群、都是自成體系的圈子,閑人未必能入,容易造成自產(chǎn)自銷、自吹自擂的文學評論機制的形成與流行,遠離嚴謹客觀的學術(shù)境界。如一些華文作家在朋友圈對自己創(chuàng)作動向的持續(xù)加貼和朋友們對其創(chuàng)作的簡單回應,造成了淺度批評的流行,對正在拓展中的華文文學研究未必有利。
(三)經(jīng)典意識的弱化
傳播原本是沉淀、提煉文學經(jīng)典的基本途徑,跨語境傳播更是特定作家作品跨越語境撒播影響的過程,華文文學的跨語境傳播也正是在選擇和過濾過程中凸顯經(jīng)典的過程。但相對傳統(tǒng)傳媒,微信是一種熱媒介⑨,熱媒介提供多感官的接觸,要求主體介入程度低,容易出現(xiàn)淺顯化、碎片化、零散化等選擇傾向,使得華文文學難以在流播過程中走向傳統(tǒng)意義上的經(jīng)典化,而是走向了浮化或輕化。⑩
從刊載層面來看,微信空間呈現(xiàn)的華文文學作品遵循的是壓縮法。為適應移動閱讀的特殊環(huán)境,也為了滿足撫慰心靈、消遣娛樂等交往功能,微信的選擇傾向于短而淺。篇幅較長的作品被刪減、更改,相關(guān)的研究文章也略去注釋,剪輯刪改。網(wǎng)絡監(jiān)管等因素的介入,還導致了某些具有深度思想力和現(xiàn)實批判精神的作品難以上傳、或傳播不久就被舉報刪除等現(xiàn)象。從接受層面來看,隨著微信更新頻率的加快、微信信息海量化發(fā)展趨勢的加劇,特定文學現(xiàn)象、文學創(chuàng)作的信息以及刊載的文學文本幾乎以秒計在刷新,難以形成強勁持續(xù)的影響。從表達形式來看,微信對文學作品的呈現(xiàn)具有與音樂、美術(shù)、視頻等多頭信息混雜發(fā)送的特點,作為語言文學的文學主體地位被挑戰(zhàn),被消解。客觀地看,如果認為“文學”應以純文字為載體,追求超越現(xiàn)實的審美意蘊,具備本雅明所言的供人瞻仰的光暈,那么,微信中的華文文學不太符合近代以來的“文學”概念,距離傳統(tǒng)意義上的經(jīng)典追求越來越遠。endprint
總體而言,以微信為代表的新媒體空間中,在對文學的選擇標準中,經(jīng)典意識并不重要,新聞價值和交往價值才是特定文本脫穎而出的依據(jù)。對于倚重手機和微信等來了解當下華文文壇的群體而言,經(jīng)典意識也在隨意、淺度的閱讀中不知不覺消失了。
結(jié)語
微信既是華文文學跨語境傳播的新形式,也是華文文學跨語境生存的新空間。在這一新的傳播形式與傳播空間中,我們發(fā)現(xiàn),以往有關(guān)華文文學的詩學話語和定位遭遇挑戰(zhàn),一些具有時代感的現(xiàn)象與問題不斷涌現(xiàn)。
首先,通過個人微信號,公眾號、微信社群等多種途徑,華文文學在微信中的跨語境傳播變得頻繁而便捷,文學背后的時空距離和文化差異趨向模糊。其次,面對微信空間中凸顯新聞性和交往性的華文文學,以往的離散、邊緣和混雜等詩學話語需要重新定位,重新理解。第三,倘若對照傳統(tǒng)的文學定義與文學發(fā)展觀念,微信中的華文文學面臨諸多新的問題,如新聞性與文學性的矛盾,交往性與文學性的沖突,經(jīng)典意識的消解等。
微信作為新媒介所具有的的普及化、大眾化特性對華文文學發(fā)展的引導作用,體現(xiàn)了新的媒介形態(tài)對華文文學所產(chǎn)生的內(nèi)在影響,它正在形塑華文文學的新形態(tài)。相對傳統(tǒng)的純文學定義,這種依附社交媒介,在承載形式上走向多媒體化、思想內(nèi)涵上走上淺顯化、表達方式走上碎片化、功能上凸顯交往性、新聞性的文學形態(tài)或可稱之為“次文學”。微信作為社交媒體所呈現(xiàn)的文學生存語境,也折射了當下整個文學生存語境的特性,在我們的時代,凸顯了交往性和新聞性等功能的“次文學”將占據(jù)越來越重要的位置。在這個意義上,華文文學的價值還在于它作為交往媒介即時融通了整個華語世界。但在較長一段時間,立足傳統(tǒng)的純文學觀,對文學發(fā)展的理想設定是出現(xiàn)大作家和經(jīng)典作品并可以經(jīng)久流傳,我們對華文文學的價值定位,也慣以經(jīng)典作家和作品來衡量區(qū)域華文文學的主次與分量。因此,作為次文學的華文文學如何定位和發(fā)展、會面臨哪些困境,與傳統(tǒng)媒介所造就的經(jīng)典文學景觀如何抗衡并存等,都將成為創(chuàng)作者與研究者要面對的重要問題。
① 世界華文文學、漢語新文學、華語語系文學等也被一些學者用來作為語種文學的總稱,但鑒于“華文文學”這一術(shù)語的歷史淵源與其學術(shù)地位,本文還是選用了“華文文學”的表述,關(guān)于這一術(shù)語的來龍去脈筆者將另有專文論述。
② 王德威在提及華語語系文學這一概念時,曾借用張愛玲的話,以“包括在外”的策略處理大陸文學的地位,我覺得這也是當前學界提及華文文學這一概念時所采取的現(xiàn)實立場,雖與王德威試圖超越中心與邊緣視角來重新定位漢語文學的立場不同,但既是現(xiàn)實情況,自不可視若罔聞,本文重在對現(xiàn)實進行總結(jié)與歸納,故據(jù)實指出。王德威相關(guān)觀點見《中文寫作的越界與回歸——談華語語系文學》《上海文學》2006年第9期。
③ 華文世界使用微信或其他手機社交媒體的情況尚無具體數(shù)據(jù),但隨著智能手機在世界內(nèi)的廣泛使用,這一群體在數(shù)量上應處在不斷上升狀態(tài)。
④ 微信公眾號有時會直接插入電子書的鏈接,提供完整的文章甚至書本的內(nèi)容,這也是當下不同媒介互融的景觀之一。
⑤ 國際華文微詩群從2014年12月3日創(chuàng)立至今,發(fā)展迅速,在筆者寫作此文之時,人數(shù)已達135人,造成了一定影響,如定期推出微信公眾號對微詩創(chuàng)作進行理論總結(jié),組織了線上線下的多項專題創(chuàng)作活動,出版了紙質(zhì)詩歌合集《華文微詩選粹》,是一個頗為成功的華文文學微信創(chuàng)作群。
⑥ 無法進入新媒體傳播語境的華文文學作家與作品,自容易被邊緣化。
⑦ 源自傳播學經(jīng)典著作《理解媒介》的觀點,見加拿大,馬歇爾麥克盧漢著,何道寬譯《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
⑧ 根絕某些社會學家的觀察,如今十年一代的概念已顯落后,代際差異縮短到五年、三年,并且總的趨勢是頻率加快,代際差異加深。
⑨ 冷熱媒介是麥克盧漢在他的傳播學經(jīng)典著作《理解媒介》一書中提出來的,根據(jù)該書的表述,冷熱媒介的區(qū)分是相對的,也是暫時的,如果一種媒介相對另一種媒介而言,主體介入程度高就是冷媒介,介入程度低就是熱媒介。新媒體的趨勢是越來越智能化、傻瓜化,故而新媒介相對舊媒介而言具有熱的特點。但麥克盧漢的學術(shù)著作具有詩化和寓言化的特點,對冷熱媒介的定義與描述并不確定,后起的研究者也有不同的闡釋,頗有爭議。不過,大家對冷熱媒介的相對性這一點是一致認可的。
⑩ 以往有關(guān)華文文學的討論,特別是海外區(qū)域華文文學的討論中,何謂華文文學經(jīng)典文本以及如何定位華文文學的經(jīng)典化過程等問題頗受關(guān)注,研究者也通過文學批評和編寫文學史、教材、作品選以及年鑒等積極介入華文文學的經(jīng)典化過程。
(責任編輯:黃潔玲)
Cross-contextual Transmissions of Literatures in
Chinese by WeChat and the Related Issues
Yan Min
Abstract: WeChat is a new way of cross-contextual communications in literatures in Chinese and also a new space for the survival of such literatures. First, through many channels, such as individual WeChat numbers, public platforms and WeChat groups, literatures in Chinese have become more frequent and instantly convenient in the cross-contextual transmissions via WeChat, obscuring the distance between time and space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Secondly, in the face of literary works in Chinese that prominently feature the newsworthy and communicatory in WeChat, the past poetics discourse, such as dispersion, margin and hybridity, need to be repositioned. Thirdly, communications by WeChat have opened up new issues, such as conflicts between the nature of news and that of literature, nature of communications and that of literature, consciousness of classics and its weakening. In our time, perhaps, the value of literatures in Chinese may lie in its use as a medium to integrate and communicate with the Chinese-language world as a whole and, for this reason, literatures written in Chinese, as a‘sub-literaturewill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for us to face.
Keywords: WeChat, literatures in Chinese, cross-contextual communications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