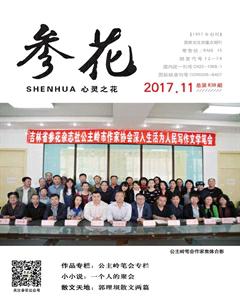論梭羅生態觀中的中國哲學文化
摘要:梭羅提出了物質簡單、精神富足的生態哲學觀,反對奢靡,對以火車和鐵路為代表的工業文明進行生態反思和批判,強調了人與自然合而為一的生態整體觀,與中國儒家的“知足常樂”思想、道家的“天人合一”和“道法自然”的哲學不謀而合。他重視自然本身的精神內涵,倡導詩意棲居回歸自然,為世界生態文化的視野提供了哲學奠基和豐富視角。
關鍵詞:生態 儒道 自然 哲學文化
中國傳統哲學思想對世界文化的影響不可估量,在多種領域、多個層面展示出其不凡魅力。梭羅倡導簡單生活觀及人與自然和諧統一的生態整體觀,揭示了生態危機的文化根源,其中也深深烙印了大量儒家與道家的中國古典哲學文化思想的印記。同時,他以走向荒野為契機,倡導詩意棲居、回歸精神家園的生態理想,為世界生態文化的視野提供了哲學奠基和豐富視角。
一、融入中國儒家思想,倡導簡單生活與精神富足的生態哲學觀
儒家向來推崇安貧樂道。孔子曾云“何陋之有”,陶淵明的田園歸耕也是儒家崇道之心的典型體現。數百年前大洋彼岸的梭羅也深諳此道,他于1845 年至1847 年,在瓦爾登湖畔的小木屋里獨自度過兩年兩月零兩天,這是他“自然生活”也是“簡單生活”生態觀的實驗。
(一)批判奢侈,梭羅否定以物質豐富為目的的生存態度
世人眼中的財富,在梭羅眼里就是“金銀的鐐銬”,他批評人們對待物質的態度,認為人們對于物質的需求更多的是出于享受和炫耀,而非生存的重要需求。比如追求時尚而購買衣服,那更多是被新奇所誘惑,對所謂“時髦”的追隨者甚至用沐猴而冠的比喻來加以諷刺。梭羅一再強調,比起衣物的破敗,個人德行的不足才是真正可恥之事,“穿在我們最外面的,常常是很薄很花巧的衣服,那只是我們的表皮,或者說,假皮膚,并不是我們的生命的一部分”(《瓦爾登湖》)。他不能容忍衣服對于“自我”的掩蓋與改變,“人消失在了衣服背后”(《瓦爾登湖》)。人性個體的存在意義屈從于膚淺的物質追求,人與人之間的本質區別變成了衣服代表的等級差別。越來越熱衷于包裝自我的人類,實質上失去的是體內越來越喪失真實的生命力。
除了衣服,另一個重要的物質象征“房屋”也是如此。“我們不再在夜間露營,我們安定在大地上,忘記了天空”。梭羅認為,人們對待房屋的態度,不是滿足于安住,而是被房子的裝飾與花哨所累,甚至成為房屋的奴隸。于是,復雜而壁壘森嚴的“房子”里居住的是人們的身體,但同時卻阻礙甚至關閉了人民與天地萬物的溝通,于是自我便逐漸迷失于物質生活的不斷豐富中。“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梭羅引用這句儒家名言,正是批評和否定終日蠅營狗茍、奔波勞碌卻忘卻自我本來面目的靈魂失落者。
(二)重歸原始,梭羅呼喚人們回歸簡單生活觀
儒家先賢曾子所說“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大學》),體現了簡單生活的方式和快樂。同樣,梭羅也認為,只要個人心境淡泊,吃最簡單的野果也能為品行提供足夠的營養。于是他大聲疾呼: “簡單,簡單,簡單吧 ……我們的生活在瑣碎之中消耗掉了。惟一的醫療辦法……一種嚴峻得更甚于斯巴達人的簡單的生活,并提高生活的目標。”(《瓦爾登湖》),他也勇敢地自我實踐了這種簡單生活觀,他來到瓦爾登湖邊筑造小木屋,他與禽獸為鄰,他獨立生活了兩年多時光,記錄自己的所見所聞所感,探尋簡單生活的本質意義。他的思想被稱為超驗主義,而這一切的確在一定程度上證明:活得簡單、更簡單,拋開物質的羅網,是可以找回自我的真正存在的。
“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這是梭羅倡導簡單哲學觀的同時,結合中國儒家思想所提出的精神富足的生態觀。 “衣服可以賣掉,但要保留你的思想……中國、印度、波斯和希臘的古哲學家都是一個類型的人物,外表生活再窮沒有,而內心生活再富不過”(《瓦爾登湖》)。在梭羅的思想中,德行與智慧才是最重要的個人財富。“德不孤,必有鄰”,他有意無意中曲解孔子有德之人必有同道的原意,而強化德行對個人存在的意義——一個人如果內有德涵,那么便永不孤獨,實現這種精神富足、永不孤獨的方式,有與自然萬物的寬容融洽,也有先賢們以足跡為證的閱讀,他認為,“書本是世界的珍寶”,獨處、閱讀,足以為人類個體提供廣大的視野與廣袤的內涵,在精神的寧靜平和中,善與美自然顯現,并且成就簡單生活的最豐富收獲。他希望摒除“人性”而恢復“獸性”,及摒除虛幻的物質財富而重歸“與禽獸為鄰”的清醒自我。
二、呼應中國道家思想,倡導天人合一的生態整體觀
何以真正實現簡單生活,回歸自我?梭羅最重要的生態觀就是號召人類返歸自然,重建人與世界的關系。梭羅對于荒野自然的親昵與膜拜,對20世紀以來生態文化和環境主義運動產生了極顯著的影響。
學者郭建良曾撰文探析梭羅與中國道家思想的相似性。老子所說“獨立而不改”,似乎也正是梭羅的遺世而獨立的自然探索之道。梭羅從生態整體觀的宏觀視角確認了人與自然的同根性關系。在梭羅的荒野生活里,“每一支小小松針都富于同情心地脹大起來,成了我的朋友。”他的自然觀,奇妙地同古老東方“天人合一”與“道法自然”的哲學觀念相應和著。梭羅常常將自然萬物視為同類,認為自然萬物才“最接近自己的血統”。從先民開始,人與自然絕非劍拔弩張、生死對立,人與生物、山水就是和諧一體的關系。梭羅謳歌人類古代與野生動物和諧相處的生態理想,對于大自然中的鳥獸蟲魚,是一種極親近的態度——山雀會飛落到“我”懷抱的木柴上、潛水鳥會嘲笑愚蠢的獵人、野鹿會好奇地凝望近在咫尺的“我”,遠離喧囂的瓦爾登湖“太陽,風雨,夏天,冬天——大自然的不可描寫的純潔和恩惠,永遠提供這么多的健康,這么多的快樂……難道我不該與土地息息相通嗎?我自己不也是一部分綠葉與青菜的泥土嗎?”(《瓦爾登湖》)他在瓦爾登湖的荒野棲居的兩年里,和自然中的其他生物取得了生存的平等,組成了一個寧靜而富有生命力的生態系統。
與生趣盎然的自然生態系統相比,工業化文明下的現代社會則是“有病的”存在,“社會總是有病的,最好的社會病得最重。”(《瓦爾登湖》),梭羅極其抵觸以火車、鐵路為象征的機械化和工業化,他以強烈的字眼批判那些侵蝕田園農舍的鐵路,“這惡魔似的鐵馬,那裂破人耳的鼓膜的聲音已經全鄉鎮都聽得到了,它已經用骯臟的腳步使清泉的水混濁了!”(《瓦爾登湖》)鐵軌對叢林的毀壞,喧囂和煙霧對自然生物的折磨,梭羅批判工業化進程是以金錢和利益至上而戕害人類自然心靈的野蠻惡行。
所以,正如“道法自然”“萬物歸一”的中國古典哲學思辨,梭羅也堅持認為,自然是有生命的,也是有人格的,自然和人的精神是相通的,決不能疏遠自然,甚至肆意破壞自然界的生態系統,順其自然本質上成為宇宙運行和人類生存的最高法則,只有遠離工業文明污染的瓦爾登湖畔富有詩意的荒野式棲居才能拯救日益被破壞的社會生態。
總而言之,梭羅生態觀中蘊含著深刻而豐富的中國哲學文化內涵。精神的詩意棲居,也被梭羅認為是人類真正重要的追求,返璞歸真、回歸自然正是實現詩意棲居、重新發現生存的唯一途徑。他倡導簡單生活,號召人們回歸自然,以精神生態的詩意建構對抗日益嚴重的生態危機,這種強調人與自然合而為一的生態整體觀,與中國儒家的“知足常樂”思想、道家的“天人合一”和“道法自然”的哲學文化不謀而合。
參考文獻:
[1][美]HD梭羅.瓦爾登湖[M].徐遲,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 .
[2]楊麗.走向一種純樸的自然情懷———《瓦爾登湖》的生態整體主義思想解讀[J].南陽理工學院學報,2013(01).
[3] 張巖,孫立言.詩意棲居與精神守望:梭羅《瓦爾登湖》生態思想論析[J].南華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06).
[4] 王焱.論梭羅超驗主義的自然書寫[J].文學與文化,2014(04).
[5] 楊靖. “疾病的隱喻”:梭羅論健康與自然[J]. 外國文學評論,2015(01).
(作者簡介:韓彬,女,碩士,山東理工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講師,研究方向:文學理論研究)(責任編輯 劉月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