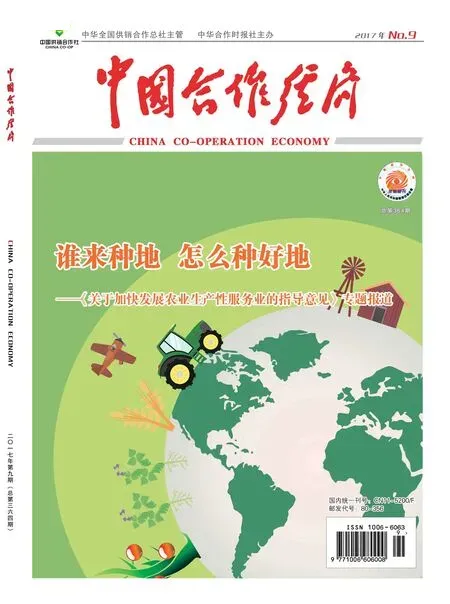從東方理性復興的角度看習近平“三農”戰略思想
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社會學系副教授 何慧麗
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社會學系研究生 王 輝
從東方理性復興的角度看習近平“三農”戰略思想
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社會學系副教授 何慧麗
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社會學系研究生 王 輝
未來很長一段時期,如何在中國的地域范圍內推進現代化、工業化、城市化的同時,又要保持農村近7億留守群體的就業與增收、農村社會的良性治理、農村生態資源環境的可持續發展?相較于對外轉嫁成本的西方工業化發展道路而言,這是習近平治國方略的一個東方式的基本命題。
習近平“三農”戰略思想,具有東方理性復興的宏觀歷史意義
習近平一直對解決“三農”問題關懷備至。早在2006年,習近平任浙江省委書記時就在溫州倡導嘗試了“三位一體”的新型農民合作方式,即以農民專業合作社為基礎、以供銷合作社為依托、以信用合作社為后盾的“三位一體”服務聯合體建設,在鄉村各個層面整合成大農協,增強為農服務的科技、流通、金融三重功能的做法。有學者總結了以之為主的有關習近平“三農”思想的一系列提法,稱為習近平“三農”戰略思想。“三位一體”的新型農民合作,需要自下而上的大農協的合作體系建設與自上而下的大農政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相輔相成,既提高行政效能,又降低合作成本,這樣從組織制度創新上解決小農經濟適應市場經濟的問題,從制度保障上根本解決“三農”問題。它體現了中國領導人要實現的幾代農民夢,即從家庭承包責任制的第一個飛躍,跨進到大規模、多層次的農村合作制的第二次飛躍。
以“三位一體”新型農民合作為組織制度創新舉措的習近平“三農”戰略思想,結合當前的歷史宏觀大勢,具有在政治經濟層面上的東方理性復興之意義。為分析方便,把東方文明的政治經濟傳統稱為東方理性,把西方文明的政治經濟傳統稱為西方理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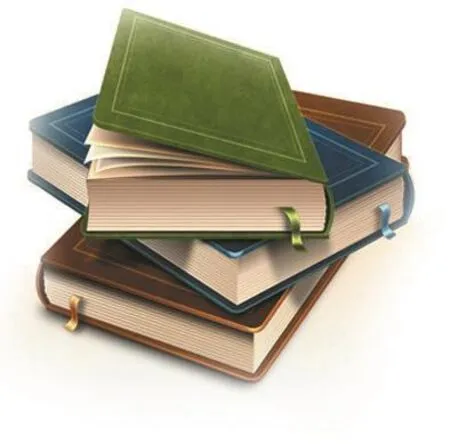
中國近現代史上現代化制度變遷與“三農”問題之間的矛盾關系,本質上是西方理性擴張、東方理性漸縮以及導致東方問題加劇之間的伴生性關系。中國人地關系緊張的“內生性結構變量”和國家追求工業化、現代化的“宏觀制度變遷”,是百年中國農民、農業、農村問題的根源。誰緩解或者解決好了這個現代化制度變遷與“三農”問題的矛盾關系,既可保證現代化從“三農”中汲取資源,同時又可以某種組織制度形態保證“三農”問題不至于導致危及到社會和政權穩定及現代化、工業化本身。
建國后以中央政府主導的工業化,改革開放后則路徑依賴地形成了以地方政府主導尤其是東南沿海發達地區的工業化進程。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的農村“家庭承包制”,其實是一種形成制度改變的交易:政府為了進一步主導改革開放時期的工業化、現代化進程,從不景氣的農業退出,其實質是部分恢復了傳統的小農經濟。在資本下鄉和工業化、城市化發展中,庇護小農經濟的傳統村社理性日益遭致瓦解,小農經濟日益成為原子化狀態,表現為資金、土地、勞動力等方面的分散性、細碎化、兼業化,它很難抵御自然風險和市場風險,也很難成為當前國家農業戰略安全、生態文明建設和新農村建設的主體性力量。
盡管西方理性的擴張加劇了東方式的現代性問題及“三農”問題的伴生,但是它又高度依賴東方理性對其致貧致亂致污效應的軟著陸和化解。中國之所以在建國后的現代化工業化進程中基本上沒有遭受大的社會性動蕩危機,實是因為每當產業資本在城市發生危機的時候都會把代價向鄉土社會轉嫁。如果不能做到新農村建設的實際效果,而是把農村摧毀,危機軟著陸的載體就不存在了。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之所以陷入危機跳不出來,原因就在于沒有像中國這樣有一個個無數次接受危機代價并使其在城市得以軟著陸的農村。以史為鑒,著眼于百年來現代化制度變遷與“三農”問題辯證關系的歷史宏觀規律,通過發育新型農民合作組織制度的關鍵舉措,以農民增收和農村經濟發展為核心任務,努力維持鄉土社會的可持續性;寄望于維持好經濟危機階段軟著陸的機會和條件,包括提供糧食安全、生態安全和民生安全的軟著陸條件,使農村作為現代化的要素蓄水池和危機消納器,擺脫百年來現代化制度變遷與“三農”問題加重的歷史性規律循環,這些才是習近平“三農”思想的戰略意圖所在。
東方理性復興在貫徹習近平“三農”戰略思想中的兩個著力點
任何組織制度創新,都是處于一定的歷史條件和具體場域之中的,任何人的“三農”戰略思想若想持久,則必要溯源;若要可持續,則必要滋潤根本。習近平欲通過“三位一位”的新型農民合作組織制度創新的辦法,以制度創新為載體,解決具有戰略高度的“三農”問題。“三位一體”,既是組織制度層面的,同時也是思想文化層面的。在此強調頗具有東方理性復興內涵的兩個方面:
復興“村社理性”,是基礎性載體和目標
無論多么豐富的“三位一體”內容,都會把加強“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的“統”的經營體制作為基礎性任務和使命。在傳統信用社、供銷社系統與農民專業合作社各自為營的大環境下,亟需探索小農經濟的村社層面統一經營體制在現實中得以完善和穩定的好辦法——從村莊層面發育適度規模性的綜合農民合作,嘗試以經濟合作為基礎的村莊整體建設與各涉農部門服務及外部市場長效對接的可能性。這一擔當需要借助既有基層組織制度——村“兩委”的體制內和自治體之雙重優勢。這也是第二次飛躍的應有之義。
對于大多數普通村莊的發展前途而言,顯然,不只是夯實村級層面農村基本經濟制度的“統合”功能,而是復興村社理性。這個村社理性,普遍意義上而言,即一種村社群體理性,指中國人數千年聚居于村落,祖祖輩輩共享村落邊界內的以土地、水和山場為主的資源,形成了能夠“內部化”收益互補并降低外部風險的小農村社文化共同體,其中的經濟理性,是一種“內部化”機制,即以村社為邊界、以平均地權為內容的財產均沾以及存在農戶和村社的兩級地權,這種統分結合的土地產權是小農村社體制的經濟基礎,也是維系村社內部治理秩序的關鍵機制;同時,中國農村缺乏超越性信仰,小農村社因而成為再造農民人生價值和生命意義的基本場域。以“村社理性”為實踐原則的發展模式能夠使村社共同體成為應對“資本下鄉”的保護機制,村社共同體利益能夠最大化地得以保持。
復興村社理性是有效落實“三位一體”新型合作機制的必要基礎。在村社理性遭瓦解的情況下,無論是什么下鄉,都會遭遇小農困境,形成“精英俘獲”機制,縣鄉層面上的“三位一體”也因缺乏基礎性載體而功能失效。在高度緊張的人地關系矛盾和無法突破不平等的國際分工體系的情況下,面對國內外政治經濟緊縮周期的正確選擇,是提倡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的民生主義,這是個東方式命題和解決辦法。亟需從村莊層面增強“統”的功能,復興村社理性,鞏固統分結合的小農村社制度。
政黨理性的自覺,是習近平“三農”戰略思想得以貫徹的組織保障
“三位一體”的合作組織制度得以落實,關鍵在于政黨理性在自上而下的大農政主導作用和整合作用的自覺發揚。
制度設計是重要的,但制度的執行取決于人,取決于其所依靠的行動者或者踐行者所持的理念和文化。制度決定論是有它的局限性的,只能是持理念、在行動的組織者,組織者的思想建設問題很重要。習近平主張,各級政府要指導和幫助農民成立自治組織,實行農民的自我保護,但是在一些地方推廣“三位一體”合作組織,遇到的最大阻力來自涉農部門本身,涉農部門各有利益、各自為政,難以起到對大農協的主導作用。這個問題如何解決呢?是要靠深化改革,然而只有建立在政黨理性自覺之上的制度深化改革才能成功,否則很難以制度層次突破制度局限性,也許解決了舊有問題,但會帶來更多的新問題。
習近平曾提出,博大精深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根基。牢固的核心價值觀,都有其固有的根本。不忘本來才能開辟未來,善于繼承才能更好創新。中國共產黨具有馬克思主義和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的雙重性格,其所繼承的中國本土的優秀傳統政治理念的那重性格,即從先人那兒傳承下來的價值理念和道德規范,那種“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的優秀政治精神元素,正是在千年本土政治中所傳承的東方理性,它與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的中國人的民族特質、價值觀念、生活方式、行為規范相切合,它是實事求是的,是經世致用的。中國共產黨惟有從東方理性中汲取政黨自覺的元素,則可以避免西方政黨政治的制度性、權利性缺陷,在制度困境中以德治國,以德行政。
習近平的“三農”戰略思想,其“三位一體”新型農民合作組織制度創新的長效貫徹實施,亟需一支以東方理性為自覺修養的黨政干部隊伍,從道德的層面內在的生發出各種實事求是、因地制宜的“法”和“術”出來,否則,制度組織創新缺乏真正自覺的執行主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