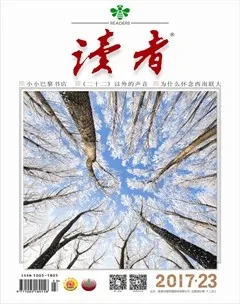卡夫卡的“愛人”和“罪人”
麥家
她有一雙纖細的手。她有一頭烏黑濃密的秀發。她的笑容純真迷人。她的嗓音“有表演的天賦”。她的名字叫多拉·迪阿曼特。1923年7月,為疾病所擾的卡夫卡來到地處波羅的海的米里茨里鎮,住進一個猶太人度假村。有一天,卡夫卡經過廚房,看見一個姑娘正忙著殺魚,他似乎有所觸動,不滿地說:“多么纖細的一雙手,可干的活又是多么殘忍!”
他們就這樣相識了。
當時多拉是這個度假村里的廚房傭工,之前她還在柏林一所猶太人孤兒院當過小裁縫。這給人一種感覺,好像多拉是一個為生計所迫的難民。其實,她出身于一個有名望的猶太人家庭,只是因為年輕和對父母保守觀念的不滿,才離家出走,浪跡四方。與此同時,卡夫卡卻因為日益嚴重的結核病,四處就醫、療養。就這樣,兩個人像兩粒沙子一樣,在這個度假村里邂逅。是偶然的,又是命定的。此時,卡夫卡的生命只剩下11個月。但就在這短暫的時間里,卡夫卡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溫暖和愛。對此,卡夫卡“幸福而誠懇”地告訴我們:這都是多拉給予的。
從一定意義上說,卡夫卡和多拉都是“父母意志的棄兒”,精神上的流浪者,同時又都是“文學的寄生者”。兩人剛相識,多拉就用希伯來語為卡夫卡朗讀了《葉塞尼亞》,讓卡夫卡“一天都沉浸在美好的遐想中”。他們很快相愛,并在柏林租房同居,“過著真正愉快的家庭生活”。在去世前的一個月,卡夫卡正式向多拉求婚。但隨后迎接他們的不是婚禮,而是卡夫卡的葬禮。因為沒有舉行婚禮,多拉似乎也無權擁有愛人的葬禮。但她還是執意出現在卡夫卡的葬禮上,在一片冷嘲和責備的目光中,“哭得死去活來”。多拉的哭聲讓卡夫卡的親人們震驚,致使他們都不敢放聲而哭,好像只有這樣才能貶低多拉哭泣的價值。可以說,在卡夫卡入葬之際,他只聽到一個人的哭聲,就是多拉的。這幾乎就是卡夫卡一生的象征:這世界,只有多拉短暫而真誠地溫暖過他。
想起卡夫卡,我們總覺得人世對他不公,他給我們留下如此珍貴的文學遺產,但他的一生,每一天、每一夜,都是在極度受傷和凄涼之中度過的。多拉的出現,讓我們感覺上天多少還了欠卡夫卡的一點債。但同時,多拉也欠下了我們一筆債:她曾經在卡夫卡的授意下,親手燒毀了卡夫卡大量的手稿,沒有燒毀的,她又沒有及時公之于世,而是私自珍藏,以致后來被蓋世太保糟蹋掉。親自燒毀和私自珍藏,都是出于愛,但她對卡夫卡的愛,構成的是一種難以救贖的“罪”。卡夫卡總是讓我們感到無所適從,感到“存在的荒謬”,這真是沒辦法的。 (心香一瓣摘自浙江文藝出版社《人生中途》一書,李曉林圖)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