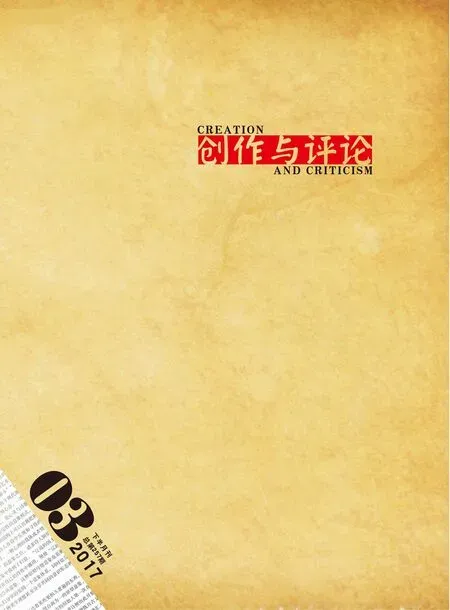文學(xué)批評(píng)的可能性
——吳曉東訪談錄
○唐偉
文學(xué)批評(píng)的可能性——吳曉東訪談錄
○唐偉
一、“興趣”的生成與“專業(yè)”的自覺(jué)
唐偉:吳老師,您好,早就有跟您做一次訪談的想法,正好這次借《創(chuàng)作與評(píng)論》“評(píng)論百家”欄目策劃一期您的研究專輯的機(jī)會(huì),我想就文學(xué)研究和文學(xué)批評(píng)的一些問(wèn)題向您請(qǐng)教。《創(chuàng)作與評(píng)論》主要關(guān)注當(dāng)代文學(xué)的創(chuàng)作和評(píng)論,結(jié)合刊物的旨趣和我個(gè)人的經(jīng)歷,所以我們這次的話題,可能主要會(huì)圍繞當(dāng)代文學(xué)的創(chuàng)作及批評(píng)來(lái)展開(kāi)。梳理您見(jiàn)刊的論文,我發(fā)現(xiàn)您早期的寫(xiě)作,像1986年發(fā)表在《讀書(shū)》上的《需要再探討》 《“現(xiàn)代主義”的反動(dòng)》,以及1987年寫(xiě)的評(píng)北島的一篇論文,均以當(dāng)代文學(xué)思潮或作家為研究對(duì)象。能不能先請(qǐng)您簡(jiǎn)要回顧一下您當(dāng)代文學(xué)的興趣生成和批評(píng)歷程?
吳曉東:好的。讀本科期間,我確實(shí)是對(duì)中國(guó)當(dāng)代文學(xué)感興趣。原因主要有兩個(gè):一是當(dāng)時(shí)的中國(guó)當(dāng)代文壇特別活躍,我1984年入大學(xué)的時(shí)候,文壇流行的正是讓我們感到振奮的“新詩(shī)潮”和“尋根文學(xué)”。那時(shí)讀王安憶、韓少功、鄭義,讀張承志的《北方的河》 《黑駿馬》等被命名為“尋根”的作品對(duì)我影響非常大。在我看來(lái),“尋根文學(xué)”在今天可以說(shuō)是已經(jīng)經(jīng)典化了的當(dāng)代文學(xué)。當(dāng)然,同樣經(jīng)典化的,還有以“朦朧詩(shī)”為代表的“新詩(shī)潮”——無(wú)論是從政治姿態(tài)上,還是從美學(xué)批判或詩(shī)歌藝術(shù)角度來(lái)說(shuō),以北島、顧城為代表的“朦朧詩(shī)”,今天無(wú)疑也可以載入經(jīng)典文學(xué)的史冊(cè)。這些在今天看來(lái)已經(jīng)經(jīng)典化了的當(dāng)代作家作品,當(dāng)年影響了我們一代中文系學(xué)生。
唐偉:那時(shí)正是上世紀(jì)八十年代中期。
吳曉東:對(duì),正是上世紀(jì)八十年代中期。雖然從寫(xiě)作發(fā)生的角度說(shuō),北島等人的詩(shī)歌創(chuàng)作時(shí)間其實(shí)很早,但對(duì)大學(xué)生日常閱讀構(gòu)成真正影響的,還是在八十年代中期。八十年代中期的當(dāng)代文學(xué),迎來(lái)了它真正的收獲期,從文學(xué)形態(tài)上講,遠(yuǎn)比此前所謂的“傷痕文學(xué)”“反思文學(xué)”“改革文學(xué)”等歷史階段要豐富。
我對(duì)中國(guó)當(dāng)代文學(xué)感興趣的另一個(gè)原因是,我們本科二年級(jí)上學(xué)期的專業(yè)必修課——當(dāng)代文學(xué),是由洪子誠(chéng)老師給我們講授的。通過(guò)洪老師獨(dú)具反思力的,同時(shí)兼具他個(gè)人審美感悟力的講授,我對(duì)當(dāng)代文學(xué)的興趣更濃厚了。我還記得給洪老師的那門課提交的作業(yè),寫(xiě)的是關(guān)于史鐵生的小說(shuō)《我的遙遠(yuǎn)的清平灣》的一篇評(píng)論。同樣也是因?yàn)閷?duì)當(dāng)代文學(xué)的興趣,那個(gè)學(xué)期我還選了一門關(guān)于當(dāng)代詩(shī)歌的課,課程作業(yè)最后寫(xiě)的是北島,后來(lái)這篇作業(yè)經(jīng)修改整理以《走向冬天》為題發(fā)表在1987年第1期的《讀書(shū)》雜志上。
唐偉:您后來(lái)的追溯,好像是把評(píng)北島的這篇《走向冬天——北島的心靈歷程》視為您的第一篇發(fā)表論文,但在此之前,您還發(fā)表過(guò)兩篇商榷性的短論。
吳曉東:那兩篇文章,也是跟當(dāng)時(shí)的文學(xué)思潮有關(guān)。《需要再探討》是對(duì)當(dāng)時(shí)何新的《當(dāng)代文學(xué)中的荒謬感與多余者》一文的商榷性回應(yīng),這篇文章是想就何文所說(shuō)的當(dāng)代文學(xué)中的“荒謬感”與“多余者”,表達(dá)我個(gè)人的理解,某種意義上也算是為當(dāng)時(shí)的現(xiàn)代主義文學(xué)思潮做一點(diǎn)辯護(hù);《“現(xiàn)代主義”的反動(dòng)》則是在讀了1986年《讀書(shū)》第3期上的《后現(xiàn)代主義:商品化和文化擴(kuò)張》一文后,感到當(dāng)時(shí)批評(píng)界對(duì)“后現(xiàn)代主義”的文化特征、審美心理及價(jià)值取向有了一個(gè)大致把握的同時(shí),有些問(wèn)題還有待再深入思考,其實(shí)仍是站在現(xiàn)代主義文學(xué)的立場(chǎng),來(lái)反思所謂的后現(xiàn)代主義的種種問(wèn)題。正是因?yàn)閷?duì)當(dāng)代文學(xué)的濃厚興趣,所以本科畢業(yè)時(shí),我是想跟洪老師讀當(dāng)代文學(xué)專業(yè)的研究生,但不湊巧,那一年正好他停招。后來(lái)我跟錢理群老師讀了現(xiàn)代文學(xué)。但即便是讀現(xiàn)代文學(xué),我對(duì)當(dāng)代文學(xué)的興趣也一直在持續(xù)。讀研的時(shí)候也寫(xiě)過(guò)當(dāng)代批評(píng)的文章,1989年評(píng)海子之死的文字《詩(shī)人之死》就是在研一完成的,這篇文章后來(lái)發(fā)表在《文學(xué)評(píng)論》上,也算是我讀研之后的一次文學(xué)批評(píng)練筆。
唐偉:有意思的是,1993年,在您讀現(xiàn)代文學(xué)博士研究生的時(shí)候,您還發(fā)表了一篇《當(dāng)代文學(xué)的話語(yǔ)和秩序》,在我看來(lái),這是一篇很有抱負(fù)和分量的批評(píng)文章,這篇文章所涉及的當(dāng)代文學(xué)創(chuàng)作及批評(píng)的諸多問(wèn)題,非常有前瞻性。比如您當(dāng)時(shí)有這樣的判斷,“當(dāng)代文學(xué)在瀕臨世紀(jì)末的今天達(dá)到了一種從未有過(guò)的豐富局面”,“先鋒派文學(xué)的媚俗趨勢(shì),新寫(xiě)實(shí)主義的庸庸碌碌以及王朔式作品的市井氣,都示出世紀(jì)末中國(guó)文化現(xiàn)狀的世俗化傾向”,類似這樣的觀點(diǎn),今天看來(lái)仍具有啟發(fā)意義。您能否回憶一下這篇文章的寫(xiě)作背景及過(guò)程?
吳曉東:這篇文章是在1990年代初所謂的歷史轉(zhuǎn)型和文化轉(zhuǎn)型之后,我個(gè)人不太滿足當(dāng)代文學(xué)反思意識(shí)和歷史意識(shí)的喪失,想從總體上梳理檢討一下當(dāng)代文學(xué)面臨的問(wèn)題。在我看來(lái),當(dāng)時(shí)當(dāng)代文學(xué)面臨的主要問(wèn)題,是受虛無(wú)主義思潮浸潤(rùn)較深——從文化思潮上看,后現(xiàn)代主義文化思潮,表現(xiàn)出了消解一切的苗頭。當(dāng)時(shí)我的觀察是,1980年代文學(xué)那種介入現(xiàn)實(shí)的雄心抱負(fù),到1990年代之后,有很大改變,作家們表現(xiàn)宏大歷史的激情以及批評(píng)家們的介入現(xiàn)實(shí)的激情,都在衰減。隨著當(dāng)代文學(xué)這種文化反思能力的喪失,平面化、世俗化的風(fēng)潮開(kāi)始甚囂塵上。比如之前的先鋒文學(xué),到1990年代已喪失了它的先鋒性,開(kāi)始和世俗文化合流,表現(xiàn)出某種消解先鋒性的媚俗性來(lái)。因此,對(duì)當(dāng)代文學(xué)流露出的虛無(wú)主義及后現(xiàn)代主義等種種思潮傾向,我覺(jué)得有必要重新檢視。今天看來(lái),當(dāng)年的那種批評(píng)可能有點(diǎn)偏激,因?yàn)閺臍v史發(fā)展的取向來(lái)看,世俗文化恰恰代表了中國(guó)歷史文化走向了一個(gè)新的階段和面向,有它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如果再用1980年代啟蒙主義的眼光來(lái)看待問(wèn)題,必然存在一定的偏頗。今天回過(guò)頭來(lái)反思,還有一點(diǎn)想強(qiáng)調(diào)的是,以往那種宏大而整體性的判斷,在今天這樣一個(gè)現(xiàn)實(shí)世界,是否還可能?或是否還有效?換句話說(shuō),在今天的歷史階段,再對(duì)生活現(xiàn)實(shí)或文學(xué)現(xiàn)狀進(jìn)行全稱判斷或總體把握,我更愿意持一種審慎的態(tài)度。“現(xiàn)實(shí)”這個(gè)概念,無(wú)疑是文學(xué)批評(píng)中一個(gè)核心關(guān)鍵詞。但今天的現(xiàn)實(shí),已很難用一種總體方案來(lái)概括了,今天的世界,已大不同于以往的現(xiàn)實(shí)主義所說(shuō)的那種現(xiàn)實(shí)了。這就像劉慈欣的科幻小說(shuō)《三體》所構(gòu)造的那種多維的宇宙世界,你看過(guò)《三體》沒(méi)有?
唐偉:沒(méi)看過(guò)。
吳曉東:我建議你找來(lái)看看,在《三體》中,劉慈欣用科幻小說(shuō)的形式,試圖去定義一種新的多維的“現(xiàn)實(shí)”,而多維的“現(xiàn)實(shí)”,不同于我們以前理解的那種多元的“現(xiàn)實(shí)”。我們今天所處的“現(xiàn)實(shí)”,就有點(diǎn)類似于劉慈欣所說(shuō)的那種多維“現(xiàn)實(shí)”,就是說(shuō),不同維度的“現(xiàn)實(shí)”之間或許永遠(yuǎn)都不會(huì)發(fā)生交集。因此,我們今天對(duì)“現(xiàn)實(shí)”的看法,也必需有所調(diào)整。相比較于作家介入現(xiàn)實(shí)的能力而言,我現(xiàn)在更看重的,是作家想象未來(lái)可能性的能力,或者說(shuō)作家處理歷史和現(xiàn)實(shí)的遠(yuǎn)景的想象力和創(chuàng)造力。未來(lái)跟現(xiàn)實(shí)不能做完全的切割,換句話說(shuō),對(duì)未來(lái)的想象,仍有賴于對(duì)現(xiàn)實(shí)的理解,而對(duì)現(xiàn)實(shí)的解釋或把握本身,即已蘊(yùn)含著某種未來(lái)指向,這就是“現(xiàn)實(shí)”與“未來(lái)”的辯證法。
唐偉:縱觀您1980年代到1990年代初的思考聚焦,感覺(jué)您1980年代的學(xué)術(shù)起步,包含了您極富雄心的學(xué)術(shù)抱負(fù)——用趙園老師的那句話,“起點(diǎn)處的選擇,對(duì)一個(gè)學(xué)人有可能意義重大”。我們看到,您這一時(shí)期樹(shù)立的學(xué)者形象,跟您后來(lái)在現(xiàn)代文學(xué)研究和《從卡夫卡到昆德拉》中塑造的那個(gè)為人所熟知的退守書(shū)齋的學(xué)者形象,有很大不同。這并不是說(shuō),您后來(lái)的專業(yè)轉(zhuǎn)向,放棄了最初的種種抱負(fù),而是引而不發(fā)地隱藏在了您的思考和寫(xiě)作中。是否可以說(shuō),正是因?yàn)橛性缙谀鷮?duì)當(dāng)代文學(xué)和文化的種種熱切思考作為基礎(chǔ),才促生出您后來(lái)關(guān)于“文學(xué)性”的相關(guān)思考?
吳曉東:有道理。1980年代,我們那一代人基本上都是受“現(xiàn)代主義”的滋養(yǎng)和哺育,我們?cè)?980年代積累的文化判斷、審美資源和文化想象以及意識(shí)形態(tài)訴求等,進(jìn)入1990年代之后,既有一個(gè)自我消化轉(zhuǎn)化的過(guò)程,同時(shí)也有一個(gè)反思揚(yáng)棄的過(guò)程。如果說(shuō)“現(xiàn)代主義”“先鋒性”構(gòu)成了1980年代文學(xué)的一種核心的文化驅(qū)動(dòng)力和美學(xué)驅(qū)動(dòng)力——從“尋根文學(xué)”到“先鋒文學(xué)”,我們都可以看出這種征兆來(lái),那么,到了1990年代,在商業(yè)大潮的沖擊下,1980年代的文學(xué)與文化資源,則面臨解體耗盡的危險(xiǎn)。進(jìn)入1990年代,我個(gè)人在消化“現(xiàn)代主義”資源的同時(shí),也在消化1980年代的文學(xué)文化積淀,具體的表現(xiàn),就是對(duì)西方20世紀(jì)現(xiàn)代主義文學(xué)的閱讀,當(dāng)年留校后不久,我還開(kāi)了一門外國(guó)文學(xué)的選修課,后來(lái)整理出課堂講稿,即三聯(lián)書(shū)店出版的《從卡夫卡到昆德拉》——這某種意義上也算是我個(gè)人對(duì)“1980年代”的一種“告別”。所謂的“告別”,就是因?yàn)楝F(xiàn)代主義到1990年代之后,轉(zhuǎn)變?yōu)榱讼庖磺械摹昂蟋F(xiàn)代主義”。換句話說(shuō),在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沖擊下,盡管世俗主義甚囂塵上,但還是剩下來(lái)很多精神資源。這些遺留下來(lái)的思想內(nèi)核,就像你說(shuō)的是“引而不發(fā)”,它變成了一種歷史潛流,這其中就包括了我對(duì)“文學(xué)性”的思考。
唐偉:1993年的那篇文章之后,一直到2001年,這段時(shí)間好像沒(méi)見(jiàn)您寫(xiě)過(guò)專門的當(dāng)代批評(píng)文章。
吳曉東:1994年博士畢業(yè)之后,我留在中文系現(xiàn)代文學(xué)教研室工作,自己好像由此獲得了一種“專業(yè)”意識(shí)——因?yàn)楸贝笾形南担F(xiàn)代文學(xué)和當(dāng)代文學(xué)是兩個(gè)教研室。我自己的主業(yè)是現(xiàn)代文學(xué)研究,從此基本上算是回歸“本行”。但對(duì)當(dāng)代文學(xué)的閱讀和關(guān)注,其實(shí)一直也沒(méi)有間斷,因?yàn)楸M管具體研究轉(zhuǎn)向了現(xiàn)代文學(xué),但畢竟身處中國(guó)文學(xué)的當(dāng)代場(chǎng)域之中,當(dāng)代文學(xué)創(chuàng)生了新的作品或有影響力的思潮,我還是保持同步關(guān)注。雖然沒(méi)再寫(xiě)過(guò)專門的批評(píng)研究文章,但對(duì)當(dāng)代文學(xué)的興趣,依舊在持續(xù)。尤其是我個(gè)人比較喜歡當(dāng)代作家張承志,一直想寫(xiě)篇談張承志的文章。在我看來(lái),在新世紀(jì)之后,世俗主義繼續(xù)高歌猛進(jìn),而張承志的自我堅(jiān)持,不與世俗同流的決絕,以及主動(dòng)邊緣的姿態(tài),我一直覺(jué)得其中可能對(duì)當(dāng)代文壇有某種啟示意義。所以2001年,我在《讀書(shū)》上發(fā)表了一篇談張承志的文章。
唐偉:那篇文章的題目就叫《姿態(tài)的意義》。
吳曉東:對(duì)。在這篇文章中,我想指出,盡管也許不大會(huì)有太多的人去追尋張承志,但他那種遠(yuǎn)離文壇喧囂、不與世俗同流的決絕姿態(tài),在我看來(lái)的確很可貴,具有一種“姿態(tài)的意義”。
唐偉:但在世紀(jì)之交,相對(duì)于那些紅極一時(shí)的小說(shuō)家們,張承志并不是那么熱。
吳曉東:或者說(shuō)就是邊緣的。
唐偉:避開(kāi)當(dāng)代文壇的“熱點(diǎn)”,選擇相對(duì)“邊緣”的研究對(duì)象,這種“邊緣”的選擇,是否包含了您的某種批評(píng)旨趣在里?
吳曉東:我覺(jué)得既是我個(gè)人的閱讀興趣,也是我主動(dòng)選擇的姿態(tài)。如前所述,我的主要研究領(lǐng)域是現(xiàn)代文學(xué)。對(duì)當(dāng)代文學(xué),我是一個(gè)邊緣的“局外人”,但這種“邊緣”的“局外人”姿態(tài),從某種意義上說(shuō),又可能具有某種優(yōu)勢(shì)。換句話說(shuō),從“邊緣”矚望“中心”,或許能獲得一種超然的距離,因而更能看清一些東西。當(dāng)然,我不是自詡自己就一定看清了當(dāng)代文壇中心所激蕩的時(shí)代主潮。只是說(shuō),保持這樣一種“局外人”冷靜觀察的態(tài)度,或許能有某種“旁觀者清”的意外收獲。欣賞張承志,也正是欣賞他的那種主動(dòng)邊緣的姿態(tài)。但“邊緣”不見(jiàn)得不重要,更不是說(shuō)沒(méi)有意義——“邊緣”的意義,或許是當(dāng)時(shí)身處中心的人所體會(huì)不到的。而今穿越更漫長(zhǎng)的歷史時(shí)光回頭看,我在2001年選擇張承志作為重拾當(dāng)代文學(xué)批評(píng)的言說(shuō)對(duì)象,可以說(shuō)是一種作家姿態(tài)和我個(gè)人批評(píng)立場(chǎng)的雙重“邊緣性”的契合。
二、新的世紀(jì):批評(píng)的再出發(fā)
唐偉:我注意到,進(jìn)入新世紀(jì),在《姿態(tài)的意義》之后,您對(duì)當(dāng)代文學(xué)創(chuàng)作和批評(píng)的關(guān)注,不再僅止于“旁觀者”的角色,而是再度參與到當(dāng)代批評(píng)的實(shí)踐中來(lái)。2003年,在跟薛毅老師的一個(gè)對(duì)話中,您用了很大篇幅談當(dāng)代文學(xué),比如談到余華,您認(rèn)為余華在寫(xiě)出《活著》 《許三觀賣血記》之后才堪稱一個(gè)真正出色的作家,因?yàn)檫@兩部作品“回到了人,回到了人在歷史中的境遇”。同年,在清華大學(xué)的一個(gè)會(huì)議上,您有一個(gè)發(fā)言,后來(lái)以《文學(xué)批評(píng)的危機(jī)》為題整理發(fā)表在《文學(xué)評(píng)論》上。相對(duì)于《當(dāng)代文學(xué)的話語(yǔ)和秩序》對(duì)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批評(píng),《文學(xué)批評(píng)的危機(jī)》則表達(dá)了您對(duì)文學(xué)批評(píng)現(xiàn)狀的不滿。這篇文章立場(chǎng)鮮明,言辭犀利,稱“1990年代以來(lái)的批評(píng)界已日漸墮落為名利場(chǎng),匱缺最基本的批評(píng)品格”。那今天看來(lái),不知您當(dāng)年的判斷是否有所調(diào)整或變化?
吳曉東:現(xiàn)在看來(lái),那篇文章的觀點(diǎn)多少有點(diǎn)激烈,主要原因,可能是自己“置身事外”,好像由此獲得了一種天然的批評(píng)和審視的權(quán)利,自己并不屬于“批評(píng)危機(jī)”的一部分。這種批評(píng)姿態(tài)可能有點(diǎn)高蹈,過(guò)于道德化。但當(dāng)時(shí),確實(shí)覺(jué)得當(dāng)代文學(xué)批評(píng)的現(xiàn)狀比較堪憂,我在那篇文章中提到的文學(xué)批評(píng)初露端倪的某些現(xiàn)象,比如說(shuō)“不是所有的批評(píng)家在今天都有足夠的勇氣和力量去抗拒權(quán)力與金錢的威逼和誘惑”,發(fā)展到今天,某種程度上已愈演愈烈。所謂文學(xué)批評(píng)的“危機(jī)狀態(tài)”,即是指1990年代以來(lái)的文學(xué)批評(píng),在某種意義上失去了批評(píng)的目的性,或者說(shuō)是批評(píng)喪失了其應(yīng)有的功能,即批評(píng)功能和目的的雙重喪失。如此一來(lái),當(dāng)作家寫(xiě)出一篇值得從文學(xué)性、學(xué)理價(jià)值等意義上進(jìn)行批評(píng)的作品的時(shí)候,作家看到的要么是“相濡以沫”的鼓吹文字,作家上進(jìn)的可能性在批評(píng)的意義上可能會(huì)因此止步;要么是黨同伐異的批判,這又很可能會(huì)讓作家產(chǎn)生一種適得其反的應(yīng)激反應(yīng)。總之,如果文壇有分量的作品出來(lái)之后,批評(píng)界卻無(wú)法貢獻(xiàn)出與作品相稱的真正批評(píng)文章來(lái),沒(méi)有文學(xué)批評(píng)相應(yīng)的跟進(jìn),那么作家也就弄不太清楚自己的作品的位置,也就難以意識(shí)到自身的問(wèn)題,整個(gè)當(dāng)代文學(xué)創(chuàng)作與批評(píng)的關(guān)系,就不再是一個(gè)良性的循環(huán)——借用魯迅當(dāng)年的說(shuō)法,“捧殺”和“棒殺”都不是批評(píng)的良性狀態(tài),就此說(shuō)來(lái),我們今天所需要的,仍舊是魯迅當(dāng)年所大力倡導(dǎo)的“文明批評(píng)”與“社會(huì)批評(píng)”。
唐偉:今天看來(lái),那篇文章事實(shí)上還敏銳地預(yù)見(jiàn)到了當(dāng)代批評(píng)界“圈子化”的現(xiàn)象。由此引出我們下一個(gè)話題,即今天已成批評(píng)主流的“學(xué)院批評(píng)”,如今的“學(xué)院批評(píng)”某種意義上可能成了一種制度化的“圈子”。您當(dāng)時(shí)就指出過(guò),“批評(píng)家學(xué)院化是90年代最顯著的現(xiàn)象之一”,作為當(dāng)年較早關(guān)注“學(xué)院批評(píng)”的學(xué)者,不知道您對(duì)當(dāng)下的“學(xué)院批評(píng)”怎么看?
吳曉東:“學(xué)院批評(píng)”分兩種,一種是真正站在學(xué)院的立場(chǎng),從學(xué)理自足性和文化自足性出發(fā)——這其實(shí)也是現(xiàn)代文學(xué)的一個(gè)傳統(tǒng),現(xiàn)代文學(xué)產(chǎn)生了很多“學(xué)院批評(píng)家”,從這個(gè)意義上說(shuō),當(dāng)今的某些“學(xué)院批評(píng)”,某種程度上也繼承著這一現(xiàn)代傳統(tǒng)。此外,他們還從西方的“學(xué)院批評(píng)”那里獲得了一種姿態(tài)和立場(chǎng)的互證,這一類的“學(xué)院批評(píng)”是應(yīng)當(dāng)肯定的。當(dāng)然,這類“學(xué)院批評(píng)”,也有它的問(wèn)題,比如說(shuō),容易囿于自己的視域局限,有時(shí)會(huì)自說(shuō)自話,可能會(huì)走向一種僵化的封閉,很難與社會(huì)歷史互補(bǔ)互動(dòng)。還有另外一種“學(xué)院批評(píng)”,這主要是指今天大多數(shù)在大學(xué)任職、任教的批評(píng)家們,對(duì)于這一批評(píng)家群體,我們今天往往也冠以“學(xué)院批評(píng)”的名號(hào),但實(shí)際上這種“學(xué)院批評(píng)”,有一部分構(gòu)成的就是一種圈子化的生產(chǎn),這些“學(xué)院批評(píng)”家們,往往有一批同道中人或作家朋友,他們心照不宣地形成一種“利益共同體”。因?yàn)閷W(xué)院批評(píng)家是現(xiàn)在批評(píng)家的主體,因此很多作家在出新作之后,往往也需要請(qǐng)學(xué)院的批評(píng)家們來(lái)捧場(chǎng)——當(dāng)然,這也并不排除有客觀公正的文學(xué)批評(píng)的存在。所以,對(duì)“學(xué)院批評(píng)”,我們需要做具體的區(qū)分和辨析。
三、“距離感”的追求:批評(píng)的“研究形態(tài)”
唐偉:在我看來(lái),您為數(shù)不多的當(dāng)代文學(xué)批評(píng)文章,每篇都很精彩。比如,評(píng)閻連科《受活》的《中國(guó)文學(xué)中的鄉(xiāng)土烏托邦及其幻滅》,我在中國(guó)知網(wǎng)上以“受活”和“閻連科”為主題詞進(jìn)行檢索,在搜到的近250篇評(píng)論文章中,您這篇在下載次數(shù)上排第一,被引用率則排第四,僅次于從發(fā)表時(shí)間上先于您的閻連科的訪談和另一篇評(píng)論。具有典范意義的一個(gè)最新文本,是您2012年評(píng)《鳳凰》的長(zhǎng)文,這篇評(píng)論被林建法選入《2012年度最佳文學(xué)批評(píng)》,即是明證。我首先感興趣的是這篇文章的寫(xiě)作歷程,我注意到,您在文末標(biāo)明的寫(xiě)作時(shí)間是“2012年7月5日二稿,9月10日三稿于京北上地以東”,也就是說(shuō),不算第一稿成型的時(shí)間,光第二稿到第三稿就歷經(jīng)三個(gè)月之久,這種批評(píng)的寫(xiě)作周期好像也跟當(dāng)代批評(píng)不太一樣。
吳曉東:《“搭建一個(gè)古甕般的思想廢墟”——評(píng)歐陽(yáng)江河的〈鳳凰〉》全文有3萬(wàn)多字,從最初的寫(xiě)作到成稿發(fā)表,其實(shí)歷經(jīng)了好幾年的時(shí)間。歐陽(yáng)江河的長(zhǎng)詩(shī)《鳳凰》,在他寫(xiě)到第四稿的時(shí)候,最初是李陀先生轉(zhuǎn)發(fā)給我。拿到詩(shī)稿后,我曾經(jīng)組織我的學(xué)生們進(jìn)行過(guò)一次專門的討論,有的學(xué)生提出了很好的意見(jiàn),比如李國(guó)華討論時(shí)就說(shuō):既然是談“鳳凰”,為什么不談郭沫若的“鳳凰涅槃”?我們關(guān)于《鳳凰》的討論稿后來(lái)發(fā)表在《今天》雜志上,而《鳳凰》最終的定稿,也一定程度上吸收了這些意見(jiàn)。《鳳凰》在香港出單行本的時(shí)候,李陀老師希望我寫(xiě)一篇相對(duì)充實(shí)一點(diǎn)的評(píng)論,這就是牛津大學(xué)出版社出版的《鳳凰》,前面有李陀的序,正文是歐陽(yáng)江河的長(zhǎng)詩(shī),后面是我的那篇評(píng)論。這篇文章的“寫(xiě)作周期”確實(shí)有點(diǎn)長(zhǎng)。就我個(gè)人的當(dāng)代批評(píng)而言,我可能更傾向于一種“有距離”的批評(píng),而不是做那種即興的判斷,急于對(duì)作品進(jìn)行定位。這種“距離”,既是時(shí)間上的距離,也是人際關(guān)系的距離。換句話說(shuō),“距離”越遠(yuǎn),批評(píng)或許越經(jīng)得起考驗(yàn)。那篇關(guān)于北島的《從政治的詩(shī)學(xué)到詩(shī)學(xué)的政治》的寫(xiě)作,前后也達(dá)3年之久,我去日本講學(xué)之前,就開(kāi)始準(zhǔn)備和搜集材料,直到在日本呆了兩年回來(lái)之后才最終完稿。保持或追求這種適當(dāng)?shù)摹熬嚯x感”,也是想從學(xué)理的意義上,讓自己的評(píng)價(jià)相對(duì)更為客觀。
唐偉:正是這種“距離感”,使我感覺(jué)您的文學(xué)批評(píng)好像是以一種研究的路子在做批評(píng)。
吳曉東:也許有道理。
唐偉:但當(dāng)代批評(píng)好像也回避不了那種“近距離”的即興、即時(shí)的批評(píng)。這或許是當(dāng)代文學(xué)之“當(dāng)代”的應(yīng)有之義?
吳曉東:我覺(jué)得那種即興即時(shí)的批評(píng),永遠(yuǎn)是需要的。新的作品出來(lái)后,作家們想馬上看到批評(píng)界的評(píng)價(jià)和反應(yīng),這很正常。各種當(dāng)代批評(píng)雜志,也需要這種即時(shí)的反饋。但除此之外,也許還可以有另外一種批評(píng),就是我前面說(shuō)到的,“拉開(kāi)一定距離的批評(píng)”。時(shí)間距離拉長(zhǎng)一點(diǎn),歷史感相對(duì)來(lái)說(shuō)也許會(huì)增強(qiáng),也才能夠積淀以至生成較為超越的判斷和學(xué)理。
唐偉:這種“距離感”的獲得,是不是更能讓您從整體的意義上來(lái)把握一部作品?我發(fā)現(xiàn)您對(duì)作品的解讀,往往先是一種全局式的總體評(píng)判,然后才是總體判斷之下的意象分析、細(xì)節(jié)發(fā)現(xiàn)、修辭細(xì)讀。
吳曉東:這里可能存在一個(gè)閱讀和批評(píng)操作的“程序倒置”問(wèn)題,即文本的閱讀,一般是從細(xì)部入手,進(jìn)而達(dá)到一種整體意義的把握;而批評(píng)寫(xiě)作,則是反過(guò)來(lái),先把閱讀得來(lái)的總體判斷置于文前,進(jìn)而在總體觀照下,再展開(kāi)文本分析。這樣的批評(píng)類似于一種學(xué)術(shù)研究,相對(duì)來(lái)說(shuō)需要花更多的時(shí)間和精力。比如你剛才提到我評(píng)閻連科《受活》的那篇《中國(guó)文學(xué)中的鄉(xiāng)土烏托邦及其幻滅》,在這篇文章中,我是把《受活》置于整個(gè)中國(guó)烏托邦敘事的歷史脈絡(luò)中來(lái)考察的,當(dāng)然,世界文學(xué)的烏托邦敘事也必然被納入進(jìn)來(lái)。我寫(xiě)這篇文章的一點(diǎn)心得是,如果沒(méi)有這樣一種雙重的“烏托邦”反思性背景,那么《受活》內(nèi)在生成的一種歷史視野,或像我說(shuō)的,小說(shuō)指向未來(lái)敘事的那種想象力或者說(shuō)想象力的匱缺,可能就無(wú)法被洞見(jiàn)。換句話說(shuō),就“烏托邦”存在的未來(lái)指向而言,閻連科在處理當(dāng)下現(xiàn)實(shí)問(wèn)題、處理當(dāng)下烏托邦的可能性,甚至是處理“中國(guó)文化向何處去”這類大問(wèn)題的時(shí)候,《受活》中就暴露出了某種欠缺和不足,具體說(shuō)來(lái),作家否定了來(lái)自西方的兩種烏托邦:共產(chǎn)主義烏托邦和商品經(jīng)濟(jì)的消費(fèi)烏托邦,也最終否定了傳統(tǒng)的鄉(xiāng)土烏托邦。《受活》中的反烏托邦因素,意味著在當(dāng)今的中國(guó)社會(huì)建立烏托邦形態(tài)的不可能。閻連科其實(shí)面臨的是當(dāng)代文化理想和社會(huì)理想的缺席狀態(tài),他不得不回到傳統(tǒng)鄉(xiāng)土文化的烏托邦去尋找理想生存方式和形態(tài),這種向后的追溯,恰恰反映了中國(guó)當(dāng)代文化的自我創(chuàng)造力和更新力的薄弱。中國(guó)小說(shuō)缺乏的往往是歷史觀的圖景。這不是寫(xiě)作功力的問(wèn)題,而是恰恰根源于我們今天的文化現(xiàn)狀。如果說(shuō)一個(gè)作家需要對(duì)時(shí)代負(fù)責(zé),那么作家真正要負(fù)責(zé)的,還是我們的文化現(xiàn)狀。
四、批評(píng)的理論介入:文本和理論的相互打開(kāi)
唐偉:剛才您談到“烏托邦”,包括《“搭建一個(gè)古甕般的思想廢墟”——評(píng)歐陽(yáng)江河的〈鳳凰〉》也用到“史詩(shī)”的分析框架,我發(fā)現(xiàn),在您的批評(píng)文章中,多用到一些西方理論,這牽涉到這些年批評(píng)界經(jīng)常談到的一個(gè)問(wèn)題,即大家都注意到了當(dāng)代批評(píng)對(duì)理論的濫用、誤用現(xiàn)象。在我看來(lái),當(dāng)代批評(píng)界所謂的“理論過(guò)剩”,并不是說(shuō)對(duì)理論的占有已經(jīng)多充分、多透徹,恰恰相反,我認(rèn)為這或許是一種理論的“泡沫化”,即對(duì)理論的運(yùn)用,流于囫圇吞棗式的消化,是一種機(jī)械式的生搬硬套,效用十分有限,因此大家才感到不滿。也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我覺(jué)得在您的批評(píng)文章中,理論介入的方式大不一樣,您的文章讓人感覺(jué),那些理論是從文本內(nèi)部邏輯衍生而來(lái)的,也就是說(shuō)非此不可,非此不能把握文本總體。
吳曉東:很多批評(píng)家喜歡用理論,理論在批評(píng)研究實(shí)踐中的運(yùn)用,真正用得好的,在我看來(lái)大概有這樣三個(gè)層次:一是貼切,二是有效,三是升華。貼切和有效即是說(shuō),作家創(chuàng)作的動(dòng)因、文本內(nèi)在的結(jié)構(gòu)等文學(xué)內(nèi)部圖景,可以通過(guò)理論的方法得以揭示出來(lái)。理論用得好,這些效果都會(huì)顯現(xiàn)。相反,如果不借助某些理論工具,對(duì)文學(xué)文本的分析,則容易流于一種印象式的感受,或碎片式的觀感,作品本身的深度或厚度,可能就容易遮蔽。就我自己對(duì)《受活》和《鳳凰》的批評(píng)實(shí)踐而言,無(wú)論是“烏托邦”理論,還是“史詩(shī)”的概念,首先是內(nèi)在于文本自身的脈絡(luò)之中的,即小說(shuō)家和詩(shī)人本來(lái)就有一種“烏托邦”和“史詩(shī)”的沖動(dòng),且在文本中有效地實(shí)現(xiàn)了這樣一種訴求,唯有在這樣的文本前提下,“烏托邦”或“史詩(shī)”理論的介入,才能行之有效,才能真正揭示出文本的內(nèi)在結(jié)構(gòu)和圖景。
唐偉:就是說(shuō)文本自身存在著這樣一種邀約或召喚?
吳曉東:對(duì),首先是這樣。比如“烏托邦”,我們既可以從正面烏托邦角度來(lái)切入,但同時(shí)《受活》又呈現(xiàn)出某種反烏托邦的面向,也可以從反烏托邦的角度來(lái)言說(shuō),這正是這部小說(shuō)的復(fù)雜性所在。像《中國(guó)文學(xué)中的鄉(xiāng)土烏托邦及其幻滅》試圖指出的,閻連科在反思烏托邦的過(guò)程中,暴露出了歷史感的欠缺,這表現(xiàn)為他在處理社會(huì)主義和共產(chǎn)主義實(shí)踐時(shí),有簡(jiǎn)單化之嫌。更值得討論的問(wèn)題是,閻連科營(yíng)造的烏托邦具有中國(guó)本土性,是向后看的,這是有意識(shí)或者無(wú)意識(shí)地向傳統(tǒng)文化尋求依據(jù)和資源的結(jié)果。關(guān)于用“史詩(shī)”來(lái)評(píng)價(jià)定位《鳳凰》,也是這樣。首先是這首長(zhǎng)詩(shī)本身即有史詩(shī)性的宏大追求,這點(diǎn)從詩(shī)的題目上也能看出來(lái)。歐陽(yáng)江河試圖借《鳳凰》來(lái)重述神話,或者說(shuō)在思考一種史詩(shī)的可能性。但《鳳凰》的復(fù)雜性在于,我們處在這樣一個(gè)非神話、非史詩(shī)的時(shí)代,我們對(duì)史詩(shī)的借用,基本都是在比喻的意義上來(lái)使用的。所以,就此來(lái)說(shuō),《鳳凰》的寫(xiě)作本身,就是反史詩(shī)的,或者說(shuō)本身就是一個(gè)悖論。
唐偉:原話叫“探索了一種開(kāi)放性的史詩(shī)理念,重塑了史詩(shī)范疇,借以創(chuàng)造一種足以兼容當(dāng)代生活的新詩(shī)形式。”
吳曉東:沒(méi)錯(cuò),這是詩(shī)人的追求。但詩(shī)人的這一追求,需要我們準(zhǔn)確地把它概括呈現(xiàn)出來(lái)。在《“搭建一個(gè)古甕般的思想廢墟”——評(píng)歐陽(yáng)江河的〈鳳凰〉》中,我通過(guò)《鳳凰》試圖揭示還原歐陽(yáng)江河的“史詩(shī)”訴求的同時(shí),也想指出,在一個(gè)非史詩(shī)的時(shí)代來(lái)書(shū)寫(xiě)史詩(shī),這本身就與我們的時(shí)代之間存在著一種張力或矛盾——這一點(diǎn),詩(shī)人在《鳳凰》中是自覺(jué)到了的,那么,作為批評(píng)家,也應(yīng)該對(duì)詩(shī)人的這種自覺(jué)有所回應(yīng)。換句話說(shuō),我們絕不能簡(jiǎn)單地把一個(gè)既有的“史詩(shī)”分析框架,機(jī)械地套用在《鳳凰》上,那樣實(shí)際上是對(duì)文本的粗暴架空。《“搭建一個(gè)古甕般的思想廢墟”——評(píng)歐陽(yáng)江河的〈鳳凰〉》一文正是想通過(guò)這樣一部有史詩(shī)追求的作品,以“史詩(shī)”理論的有效介入,在打開(kāi)文本內(nèi)在圖景的同時(shí),又能反思“史詩(shī)”作為一個(gè)理論范疇的邊界和有效性。
唐偉:您這么一說(shuō),我感覺(jué)理論在批評(píng)中的運(yùn)用,是不是一種“雙重的打開(kāi)”?即一方面理論打開(kāi)了文本的內(nèi)景,另一方面,文本也豐富或者說(shuō)擴(kuò)展了理論的內(nèi)涵和外延。
吳曉東:說(shuō)得好,是一種“雙重打開(kāi)”。我在指導(dǎo)學(xué)生論文寫(xiě)作的過(guò)程中,經(jīng)常遭遇學(xué)生追問(wèn)如何運(yùn)用理論的問(wèn)題,而關(guān)于如何運(yùn)用理論,我一直強(qiáng)調(diào)這樣一種意向,即在文學(xué)研究文學(xué)批評(píng)實(shí)踐中,能在何種程度上去充實(shí)、糾正或者說(shuō)反思理論,并最終使這個(gè)理論獲得一種可能的拓展。我們這里講“理論”,一般是指西方理論,而西方的理論或具體到文學(xué)理論,大多是源自西方的社會(huì)歷史現(xiàn)實(shí)或文學(xué)、文化的歷史現(xiàn)實(shí),作為中國(guó)學(xué)者,我們?cè)谶\(yùn)用這些文學(xué)理論來(lái)讀解中國(guó)的文學(xué)作品時(shí),肯定不能直接拿來(lái)搬用。換句話說(shuō),既然理論跨越時(shí)空,旅行到你這里,那難免會(huì)有一定程度的變形,因此,你在使用這種理論的時(shí)候,就得承擔(dān)起一種使理論進(jìn)一步生長(zhǎng)可能性的責(zé)任,即在你中國(guó)化的研究語(yǔ)境中,能把西方的理論有所化用,并觸及到了它的邊界和有效性,這才是在文學(xué)研究與批評(píng)的實(shí)踐中運(yùn)用理論的一種理想狀態(tài),也是理論運(yùn)用的最高境界。
唐偉:這種對(duì)理論的征用,我感覺(jué)難度太大了。
吳曉東:這對(duì)批評(píng)者的功力,確實(shí)要求較高。好的批評(píng),首先得有一種準(zhǔn)確敏銳的藝術(shù)感受,即基于對(duì)文學(xué)作品的貼切直覺(jué),其次才是作為方法工具的理論的有效介入,這兩方面缺一不可。而理論或者說(shuō)文學(xué)理論,并不是固定的機(jī)械的灰色存在,它同樣是一種思考積累的過(guò)程和結(jié)果。或者說(shuō),理論是你在長(zhǎng)期閱讀思考理論文本的過(guò)程中,化為你自己的思維甚至是情感和血肉的那部分“剩余”,它需要在你自己學(xué)術(shù)生命中不斷生長(zhǎng)生成,這其實(shí)也是理論真正的歸宿。
五、批評(píng)的“有效性”:同義反復(fù)的“淺繪”或結(jié)構(gòu)呈現(xiàn)的“深描”
唐偉:您剛才談到批評(píng)中理論介入的有效性問(wèn)題,雖然文學(xué)批評(píng)沒(méi)有絕對(duì)的一定之規(guī),但我想大致還是存在一個(gè)批評(píng)“有效性”的問(wèn)題吧。在您看來(lái),何為一種有效的文學(xué)批評(píng)?
吳曉東:有效的文學(xué)批評(píng),其“有效”主要是針對(duì)作家和文本而言的。就文本闡釋來(lái)說(shuō),有效的文學(xué)批評(píng),不能僅僅流于一種同義反復(fù),就是說(shuō),不能只用一種看似學(xué)術(shù)化的術(shù)語(yǔ),復(fù)述一下情節(jié),概括一下內(nèi)容(盡管這也是必要的),對(duì)文本進(jìn)行一番包裝式的“轉(zhuǎn)譯”。有效的文學(xué)批評(píng),主要看批評(píng)家能否超越文本的表層現(xiàn)象,揭示出作品中并未直觀表現(xiàn)出來(lái)的有意識(shí)的東西,甚至是作家的無(wú)意識(shí)。換句話說(shuō),批評(píng)的有效性,可能需要批評(píng)家站在一個(gè)高于作家創(chuàng)作的角度,從更深的層次去挖掘、深描文本內(nèi)在結(jié)構(gòu)性的東西。比如在《從政治的詩(shī)學(xué)到詩(shī)學(xué)的政治》那篇文章中,我前后用了三四年的時(shí)間,原因就在于,我對(duì)北島后期特別是流亡時(shí)期的創(chuàng)作有一種“深描”的打算,試圖挖掘出他這一時(shí)期詩(shī)歌中存在的主體的復(fù)雜性,即流亡的主體、漂泊的生涯、鏡像的自我。這種“主體性”,不是從北島詩(shī)歌意象的表面就能捕捉得到的,而是一種內(nèi)在的結(jié)構(gòu)性東西。結(jié)構(gòu)呈現(xiàn)的“深描”,不是就詩(shī)歌進(jìn)行語(yǔ)句修辭意義的整理,不是流于文本內(nèi)容的抄錄、概括以及術(shù)語(yǔ)的“轉(zhuǎn)譯”,而是對(duì)文本深度結(jié)構(gòu)的有效打開(kāi)——這種結(jié)構(gòu)既是文本所依附的意識(shí)形態(tài)結(jié)構(gòu),也是作家所處的社會(huì)文化結(jié)構(gòu)和政治歷史結(jié)構(gòu)。
唐偉:借用您“深描”的說(shuō)法,我覺(jué)得我們今天的文學(xué)批評(píng),好像更多是一種同義反復(fù)的“淺繪”。也是從這個(gè)意義上說(shuō),我們今天對(duì)文學(xué)批評(píng)的不滿,原因倒還不在于說(shuō)文學(xué)批評(píng)喪失了介入現(xiàn)實(shí)的發(fā)言能力,而恰恰是在文本解讀的有效性上,很多批評(píng)沒(méi)能揭示出文本的“景深”來(lái)。
吳曉東:真正好的批評(píng),有效的批評(píng),正如我們前面說(shuō)到的,首先是尊重自己的閱讀感受,另外一方面,可以借助某些理論工具,盡可能地將這種主觀感受客觀化、學(xué)理化。換句話說(shuō),文學(xué)批評(píng)首先還是要扎實(shí)中肯,這種扎實(shí)中肯是建基于文本現(xiàn)實(shí)的一種專業(yè)學(xué)理的自足,是對(duì)作品基本面的一個(gè)大致準(zhǔn)確的總體把握——即使是你說(shuō)的“淺繪”,也必須是一種專業(yè)意義的“淺繪”,這是文學(xué)批評(píng)的最低要求。在此基礎(chǔ)上,我們才有可能談“深描”,深入到文本內(nèi)涵的深度結(jié)構(gòu)中去,亦即盡可能把文本內(nèi)部所蘊(yùn)藏的復(fù)雜豐富的東西呈現(xiàn)出來(lái),這些深層次的東西,可能是作家在創(chuàng)作時(shí)并未清楚地意識(shí)到的,而普通讀者也難以讀出來(lái)的東西。揭示出文本蘊(yùn)含的內(nèi)在結(jié)構(gòu)性深度,堪稱批評(píng)的最高要求,所謂批評(píng)的“專業(yè)”功夫,或許也即在此。
唐偉:我個(gè)人覺(jué)得,大多數(shù)批評(píng)好像忽略了您說(shuō)的“最低要求”,而又把“最高要求”想當(dāng)然化了,換句說(shuō),“淺繪”的文本分析解剖,尚未達(dá)到一個(gè)專業(yè)(文學(xué))意義的自足,就倉(cāng)促展開(kāi)了那種非文學(xué)(社會(huì)、歷史、政治等)的“深描”延伸。這或許才是今天的文學(xué)批評(píng),為什么越來(lái)越難以真正有效介入現(xiàn)實(shí)發(fā)言的原因所在。最后一個(gè)問(wèn)題,剛才在談文學(xué)批評(píng)的時(shí)候,我們也談到文學(xué)研究,那我想請(qǐng)教的是,您怎么看待文學(xué)批評(píng)和文學(xué)研究二者間的關(guān)系?
吳曉東:這取決于你自己怎么定位,你是更愿意把自己視為一個(gè)文學(xué)研究者,還是一個(gè)文學(xué)批評(píng)家。就我自己而言,我傾向于認(rèn)為自己是一個(gè)文學(xué)研究者,而文學(xué)批評(píng)算是我介入現(xiàn)實(shí)的一種“副業(yè)”,不是我職業(yè)生涯的常態(tài)。批評(píng)家不同,批評(píng)家在做批評(píng)的時(shí)候,需要敏銳而感性的即興洞見(jiàn),比如像毛尖,毛尖既是一位研究文學(xué)和影視的很出色的學(xué)者,同時(shí)也是一位非常有才情的批評(píng)家,她的一些關(guān)于電影、文學(xué)、文化現(xiàn)象的專欄形式的短論,飽含她獨(dú)具個(gè)性的批評(píng)洞見(jiàn),既受專業(yè)讀者歡迎,也深得普通讀者喜愛(ài)。但研究者和批評(píng)家這兩種身份還是有差異的,并不見(jiàn)得文學(xué)批評(píng)就比文學(xué)研究低一等級(jí)。作為現(xiàn)代文學(xué)研究者,我偶爾涉及當(dāng)代文學(xué)批評(píng),但與那種即興即時(shí)的批評(píng)不太一樣,我仰慕的是那種相對(duì)具有學(xué)理感和歷史感的批評(píng),這或許能呈現(xiàn)出跟職業(yè)批評(píng)家不太一樣的景觀來(lái)。當(dāng)然,批評(píng)有多種多樣的風(fēng)格,也不能強(qiáng)求一致。但不管是哪種風(fēng)格,套用毛澤東當(dāng)年“從群眾中來(lái),到群眾中去”的那句話,文學(xué)批評(píng)者,都應(yīng)該是“從文本中來(lái),到文本中去”。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xué)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