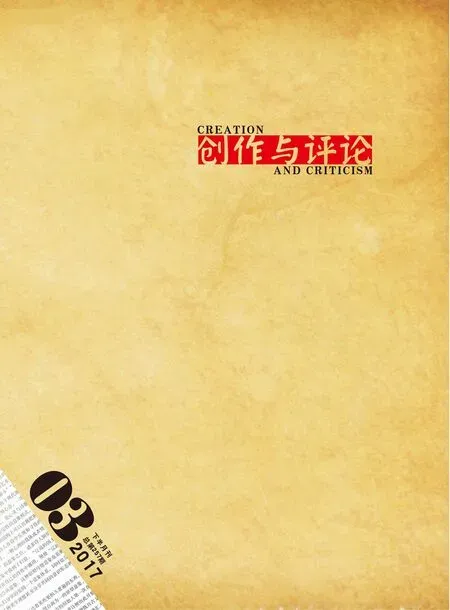時空盡頭的漫游者
——周潔茹的香港小說簡論
○邵棟
時空盡頭的漫游者——周潔茹的香港小說簡論
○邵棟
上世紀末,周潔茹作為當時“七零后”寫作的代表人物曾在大陸文壇引起過不小的轟動。而新世紀初她突然封筆赴美,杳無音訊十多年。當人們一度以為當代文學史中有關她的文字已經完結時,周潔茹如今重又從香港出發,開始了一系列帶有本地背景的創作旅途。她在2015年推出了最新隨筆集《請把我留在這時光里》,此外亦有數量可觀的作品在各種文學刊物相繼發表。她用自己實際的行動宣告著自己的歸來,并且更值得人注意的是,暌違多年的她并沒有單純重復過往的寫作經驗,而是通過新的寫作對象與寫作路徑,有意展現新的自己。
2009年移居香港的周潔茹,現在已經成為了一個香港公民,而香港也成為她如今最為重要的寫作背景。似乎理所當然的,她也已經成了一個香港作家。不過有趣的是,她卻坦白道:“作為一個香港居民,誠實地說。我對香港仍然沒有很熱愛。”甚至,她連一個香港朋友也沒有,一句粵語也不會:“……所以我的香港小說,全部發生在香港,但是主角說的都是江蘇話。”周潔茹對于香港的疏離態度大略純出于個人的生活態度,而她在寫作論述中對于作家身份和小說背景地的問題亦有意忽略:“對我來說,香港人也是人,香港小說,其實也就是人的小說。”而身份問題何嘗不是寫作政治中難以回避的大問題,她自己無不感慨:“我更愿意被稱作移居作家而不是移民作家……我肯定會被歸入移民作家,而且是香港的大陸新移民作家,我已經在盡量避免這一點了,被歸入任何一個區域。” 顯而易見的是,周潔茹對于作家身份認同并不感冒,而地域、族群的認知結構在她而言,似乎更是一種束縛。她亦曾借用顧彬(Wolfgang Kubin,)的觀點,指出作家寫作的時候,他們應該超越他們民族。
基于這樣的認識,本文無意于分析香港作為寫作對象以及香港作家作為身份對于作者創作的影響。相反,香港在周潔茹的小說中,只是一個模糊的背景,作者終歸想寫的是人。香港以及與其相關的物象、地點,不過是映照作者寫作行動的一面鏡子,投射的始終是作者本人的對于現代生活所思所想。而這種投射,亦與身份無關。或可說,周潔茹書寫的是她這段寫作空白的人生,而這段人生又恰恰與香港有關罷了。然而為了論述方便,暫且將周潔茹復出后寫作的一批與香港有關系的小說簡單稱作香港小說。
本文將著重分析周潔茹的香港小說,解讀其中獨特的時空呈現:歷史終結的時間感以及空洞的地理概念。此外,本文亦將解讀小說人物及作者離散(diaspora)的個人狀態。
一、歷史終結的時代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歷史終結與最后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中探討了一種可能的未來解讀,即歷史如果作為一個以進步為尺度的實體,那么已經過去的20世紀,當進步主義曾給人們帶來戰爭及各種災難的事實擺在面前,人們對這種進步觀念已經產生了深度的質疑。作者指出如今在世界流行的自由民主觀念將成為后冷戰時期人們普遍接受的理念,而其相伴而來的現代消費主義,更加會使生活愈加富足的人們缺乏“進步”的欲望。因而福山預言,資本主義將是人類的終極形式,歷史將會終結,即便會有事件發生,但不會再有整體性的更迭。平庸的人們將會坦然接受自己的生活,再無革命的勇氣與欲望,成為“最后之人”。
福山的議論繼承了尼采(Friedrich WilhelmNietzsche)的哲學觀念,并進一步滲透了他對人類現實與未來的深度焦慮。“受過現代教育的人滿足于閑坐于家中,對自己的心胸豁達和中庸感到慶幸。”而在相對主義的自我安慰下,崇高價值和英雄主義都將被一一消解。而歷史終結這種意識亦可以在文學中可以找到其落腳點。當后現代文學大量書寫現代人被解構的生活,細描“無聊”時,同時也是在解構價值與崇高。那些后現代文本中,常見的細碎凡庸與重復,正是現代人沒有未來,無所信仰的精神危機。“進步的展覽是對現代暫時性的拜物,永無止境的‘新奇’成為總是一樣的重復中。”
這種歷史終結意識在周潔茹的小說中是明顯的。她的香港小說中,不斷書寫那些遭遇中年危機的,無聊且平庸的香港新移民師奶。“無聊”“無所事事”“愚蠢”“婚變”似乎成為這些女人共有的標簽。《到廣州去》的靜待兒子長大的二奶,《格蕾絲》中不是在觀察鄰居就是在做夢的“我”,乃至《佐敦》中像祥林嫂一樣碎碎念自己孩子擇校問題的格蕾絲,都是這一類被自己生活困住,在可預見的時間里生活不會發生變動的現代人。這些角色好像走到了時間的死胡同里,被看不見的墻壁限制著,在生活安穩的表象之下,實際上卻有著來到歷史終結的恐慌與不安。
周潔茹在她的香港小說的創作中,對于這種精神危機有著多方面的書寫。而在她這里,最重要的被解構的崇高價值自然就是愛情。
作者自言:“我搬來香港也有七年了,意味著你應該婚變了,七年,也意味著你可以是一個永久性的香港居民了。”愛情和婚姻以及香港身份一道,成為帶有時間刻度的量表,有著各自的保質期限與兌現日期,精確而冷酷。而周潔茹筆下那些中年危機的無聊女人,亦可非常平靜地承認她們對于愛情的不信任感。小說中的格蕾絲說:“愛是錯覺,這個世界本來就是沒有愛的。”“誰都是出軌的,我們趕上了這個時代。”還是格蕾絲說的。
作者在《到廣州去》一文中設置了一個旅居香港的大陸二奶,去往廣州與自己青梅竹馬的初戀相見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她”,面對“丈夫”接二連三地添置小老婆的現實,在毫無尊重的家庭環境中,只能選擇悲觀地接受現實,不去想明天,把兒子湊大。然而這個已經對現實坦然的“蠢女人”,在再次見到自己青梅竹馬的初戀時,在對方突然說出我愛你時,還是不能自己地淪陷,如同她自己說的“我要去愛一回”。現實是“香港生活平靜,吃飯睡覺,兒子慢慢長大。”“她就是回不去了。就這么空空蕩蕩。反正也是一轉眼,什么都是瞬間。不去想明天,明天就是兒子長大。”時間無限停滯,空洞,并且按部就班。似乎一切時間的價值就在于消耗,一切都在預計中,不會發生更多改變。然而“她”的理想世界卻是另一番景象:“十五六歲的女孩,春天的晚上,后門口,桃樹下,對門的年輕人,一面,一句話,你也在這里嗎。千萬人之中遇見的人,千萬年之間的一個瞬間。”在“她”的理想的時間長河中,雖則萬年,仍然會期待一個未來的終點,一個特別的時刻會有一個人在等待著她。顯然,她無法接受歷史終結的事實,而依然在腦中構想自己的崇高價值——理想的愛情。并準備好為此奮不顧身一回。這段引用文字顯然是對張愛玲《初戀》的致敬,然而整篇小說卻是對于這篇文章的翻轉。
作者并不想寫作一個陳詞濫調的愛情故事。周潔茹極其細致不避繁瑣描寫“她”去往廣州的整個流程,遇到票販、排隊取票、換隊取票、過安檢、坐出租……在此過程中,作者不斷鋪陳女主人公的困窘和無助,排隊的漫長、余票的售罄、再換站票的反復,同時也描繪形形色色等待的迷茫的人,混亂的秩序以及毫無進展的現狀。所有的一切都展現出混沌而荒誕的一面,“等待戈多”式的阻塞與無妄。“她”手足無措,如同等待“最終審判”。而這一切紛繁的亂象,也是出軌的女主人公矛盾內心的外化。在幾經周折之后,“她”終于來到廣州,然而迎接“她”的是,不過是男人出于身體需要的求歡。雖然“她”為他給“她”夾了一筷菜而感動落淚,不過最后還是完全沒有猶豫地離開了他。
周潔茹在這篇小說中塑造了一個想要從無盡的時間空洞中解脫出來“真正愛一回”的女人,然而她的英雄主義卻被現實消解得粉碎。如果說張愛玲在《初戀》中呈現的是蠻荒現實中微小的溫存可能,周潔茹則在《到廣州去》中將這種浪漫徹底顛覆,變為一個笨女人的幼稚行為。周潔茹早期小說中也常見對于艷遇或愛情的解構,然而那些女子卻是秉性高揚青春逼人,獨立的她們可以將這種解構歸于對他者(男人、現實)的失望,而自己卻依然可以是個獨立的新女性。而周潔茹如今筆下的這些個個出軌的香港師奶,卻常常是生活的失敗者,出軌反而變成麻醉自己、逃離現實的手段。雖然她們帶著或多或少甚至自己都不愿承認的希望,但她們的失望情緒卻是指向自己的,是在在既有生活中找不到出路和未來的無奈。
所以她們出軌。她們出軌并不是全然因為愛,相反有時是因為沒有愛。《到廣州去》中現實感情干涸的“她”自不必說。《格蕾絲》里強調自己是出軌不是偷情的格蕾絲;《旺角》中完全不愛自己高智商教授丈夫的“她”。周潔茹在描繪一個歷史終結時代的同時,并不滿足于陳述事實。她亦有志于書寫一些不滿現狀,螂臂擋車的女人們。于是乎,她筆下的角色之出軌,亦染上了一種悲涼的英雄主義色彩:
我說你不是出軌了,你是還在出軌中。
是的,格蕾絲說,就是這樣的。
我能夠成為我就是因為我永遠不會說這樣的話,那你怎么辦啊,你為什么要這樣啊,你會不會覺得自己有罪啊,你以后怎么面對你的丈夫和小孩啊。
我說的是,感覺怎么樣。
格蕾絲說好極了。
于是周潔茹補充道:“格蕾絲為了家庭更是操碎了心的,不爭的現實,每次見到她,她都不是她,她是她孩子們的母親,她丈夫的妻子。這樣的女人,出軌是必然。”出軌這種行為在此獲得了一種非道德的傾向。這些出軌的女子無一不過著常人看來富裕安定的生活,然而在盡職的家庭角色之外,卻完全沒有得到與之相匹配的情感回報與“被愛”。她們空洞而匱乏的感情狀況以及與之相伴而來的不滿情緒,促使渴望被愛的她們做出越矩之態,即便她們心里清楚這樣也未必獲得了愛。然而低到塵埃里的她們即便是錯覺也不愿放過:“又沒有愛,做愛都沒做出愛來。只是維持著,到底還有點高潮。”
這些小說中并非所有的女主角都出軌。像《佐敦》里的阿珍和《尖東以東》里的陳苗苗,就是十足的老實女人。拿著單程證的阿珍得照顧癱瘓的壞脾氣丈夫,還得找工作供孩子讀書。她反復告訴自己:“還能壞到哪里去,再壞也壞不到哪里去了。”“沒有什么是會被浪費的。”;陳苗苗在婚姻破裂時,始終相信她出軌的丈夫“他自己是不想離婚的……全是我公公婆婆的主意”“只跟朋友們一起打打籃球,玩玩玩具。”她們的自我麻醉是對抗絕望的良藥,是她們不愿接受“現實即使不變壞也不會變得更好”的困境的掙扎。
周潔茹對于“都會變好的”這種歷史進化論顯然持有懷疑態度,她在冷峻地表現人們在現代社會的走投無路時,雖然有著“歷史終結”的意識,然而對于她筆下這些不甘于現實,“我要愛一回”的女性角色,依然有著同情的態度,乃至是悲憫。
或者說,這也是作者最著意表現的心理困境:明明知道現實是沒有出路,也沒有理想與崇高價值可言,但對于那些不服命運依然保有微毫希望的人們,抱有認同的態度。就比如《格蕾絲》里說著自己“不厭倦”的格蕾絲。
二、“過渡”的香港:無地彷徨
周潔茹最近創作的小說中有相當部分是以香港地名命名的,比如《《旺角》《尖東以東》以及《馬鞍山》等等。誠如前文所說,這些香港地名及其文化標識,其實在小說文本中大多沒有特別的意義,功能恰如“某地”,換言之,只是個模糊的背景和符號而已。而地理概念在周潔茹的小說一直作為城市符號的一部分,對于小說人物的漫游者(Flaneur)的身份帶有確認的作用。周潔茹在小說中常常設置“到哪里去”的命義,在這批香港小說即有《到廣州去》《到香港去》兩篇。而周潔茹自己就說道:“這是我寫作上的習慣。如果我要改換我生活的地方,我會寫一個《到哪里去》去提醒我我的方向。”周潔茹在上個世紀末就寫作過《到常州去》和《到南京去》。
《到常州去》和《到南京去》深具周潔茹早期風格的特色。《到常州去》是個現代版“何必見戴”的故事,描寫一個獨立的城市女性唐小宛從南京搭陌生男子的順風車去見常州的好友末末,忍受了一路陌生男子搭腔終于到常州的她,卻發現末末到南京去了;《到南京去》描寫的則是一個美麗頹廢的女性突然間決定離開自己的城市搭最近的一班火車去南京,與鄰座不解風情的搭訕男子之間的故事。周潔茹的早期的“到哪里去”系列中的女主角帶有很濃重的“生活在別處”的氣息,對于既有生活有著不滿和逃離的欲望。這些文藝頹廢的女性在旅途中卻常常遇到令人掃興的搭訕者,“因為男人們都沒有別的什么話可以說,他們只會說,只要你愿意,你可以做我的女朋友。可他們并不了解這個女人,他們只是看到她,她長得很美,她的身體很漂亮,她的氣質和才識都很華貴,于是他們以為這個女人優秀,應該讓她做自己的女朋友。這是多么可笑的一件事情啊。”在此,周潔茹不僅對艷遇有著犀利的解構,對于男人也有著一種不屑一顧。這些女性身上的獨立意識與自信,構成了上世紀末周潔茹對于新城市女性的想象。
閱讀這些女性故事時,讀者會感到現實生活配不上這些優秀的女人,而這些女人來去自由,想去哪里去哪里,遇見不喜歡的人便下車便走,輕松自由,而她們的自由似乎就是她們未來不致失敗的通行證,因為她們富于選擇。她們是漫游者(Flaneur),如本雅明(Walt Benjamin)所說,她們才是城市的主人,是慵懶和充滿好奇心的流浪者,洞察城市的細節,又與之疏離。但無論如何,早期“到哪里去”系列中周潔茹筆下的女性都是有著極強自尊的,并對于生活有著一種篤定的強者姿態的,即便現實不堪,依然保留自己與現實的距離。
在《到香港去》和《到廣州去》則描寫的是出一個失敗主義的,犬儒式的女性姿態。
《到香港去》里去香港只是為了給孩子買安全奶粉的張英,為了節省開銷,報了一個低價游港團。一路上忍受著各種旅游購物的脅迫,導游的冷眼,在陌生與不安的異地,時刻警醒地告誡自己“只是為了買奶粉”,在緊張的情緒下度過了旅行的天數。“一輩子都不會再去香港了。”張英的旅行的一切基礎都是以現實需求為目的,為了孩子,可以委屈自己,忍受種種異地的委屈。而“香港”這一作為地理概念的“異地”,則成為了張英實現現實世界美好的犧牲品。可以說,張英心理的預設就是她不屬于香港,若非出于現實目的,她根本不會來此,并將永不再來。張英不像周潔茹過往小說中那些四海為家,迷戀流浪的女子,相反,她傳統現實,將自己鎖死在那個相夫教子處好人際關系的小世界中。她對于“別處”是沒有好奇心和好感。她人生的目的就是過好現實生活,其他皆可犧牲。對于這種中年人的理性,從結局來看,作者是帶著微諷的同情的。而香港和張英的故鄉在小說中是完全分離的兩個地理概念,張英所持有的“不會再去香港”的態度,也代表一種心靈選擇的斷裂,是對現實的完全妥協。
《到廣州去》這個理想主義的出軌故事中,地理概念同樣有著象征意味。香港是女主人公日夜所棲的現實世界,而從來沒有去過的廣州則是“我要愛一回”的“應許之地”,代表著脫離現實的可能世界。然而當女主角一踏出關口,就顯露出與那一邊的世界極端適應不良的癥候,一切也染上了極端荒誕與混亂的色彩:來去飄忽的黃牛;永遠不會移動的隊伍;沒有人能有座位的現實;不打表的司機……“出租車的標識全都是亂的,她的高跟鞋,走到這里,又走到那里,哪里都畫著車,哪里都沒有車。”習慣了香港有條不紊的秩序的女主人公,北上之時,卻要面對一片混亂與未知的交通秩序,她的手足無措,顯然也是要奔赴一場出軌的心理外化。
當她發現自己以為的愛情只是一場性邀約,女主人公毫不猶豫選擇了離開。以為她自己所構建的理想世界已經崩塌。雖然未說,但她恐怕也和張英一樣“再不會來”了。很快女主人公穿著酒店的拖鞋又回到了火車站回香港,在深圳過關時,卻在電梯里面遇一對蠻橫的母子因小摩擦對其侮辱:“那你不要來深圳啊!年輕男人的聲音像是要炸開來,誰叫你來深圳的?滾!”女主人公還未來得及分辯,電梯門便已經關上。小說也戛然而止。在這樣的視角下,女主人公幾乎是被與她格格不入的、粗暴的“理想世界”驅逐出境了。
在這些香港小說中,女主人公已經不再自由,而這種不自由主要體現在“精神狀態”,她們也許可以旅行,但不是缺乏了“游”的精神,有了現實羈絆(張英),就是“游”的浪漫意志不堪一擊(“她”)。相比較于《到常州去》和《到南京去》中女主人公的“來去自由”,《到香港去》《到廣州去》中的女子們卻是“再不會回來”,她們主動或被動地將自己鎖死在過去的那個現實世界中。她們不僅在地理上“驅逐出境”,還變成了現實的囚徒。
回到了香港,這些新移民女性的生活也談不上美好。這種精神狀態可稱作“無地彷徨”。她們雖然來到了香港,可依然無法將香港內化為“我城”,成為城市的邊緣人。以《佐敦》為例,阿珍作為拿單程證的新移民,不會講粵語,家中有臥床的丈夫和上學的孩子,現實壓力逼著她四處尋找工作。當別的師奶跟她兜售著“教普通話”,“拉內地人保險”的時候,“阿珍只是搖搖頭,別的師奶講的話都是神話。”她沒有那樣靈活的腦子,只懂得熬日子。
如果說香港在整個大陸而言有著“包括在外”的身份的話,那么新移民在香港同樣有著“包括在外”的身份。邊緣城市的邊緣人,并且無法返回大陸(張英,“她”又何嘗不是拿了抽象的單程證),如何不是“無地彷徨”的邊緣狀態。
格蕾絲在《佐敦》中一再言及“過渡”,而阿珍也說“就是過渡。小孩要適應香港,大人也要適應香港。”可實際上,通過小說故事我們可以知道,阿珍說的“適應”其實含著“一切都會好起來”的意味,然而何其難哉。“過渡”似乎是一種許諾式的話語,會有一個更好的未來?更好的彼岸嗎?如果“過渡”是對現實殘酷的安慰語,那么“過渡”這種現代人的“既不在此,也不在彼”的生存狀態,恰如地理概念,將極難逾越。
從前后期小說的“到哪里去”寫作的比較中,我們可以看到周潔茹描寫內容的變化,如果說早期的她著意描繪超然于現實的獨立女性的姿態的話,如今的周潔茹似乎更多著墨于中年女性的精神危機和在現實中尷尬的位置。前者提出了“娜拉出走”的姿態,而后者則留下了“哪也去不了”的玄思。
周潔茹在她的香港小說中,呈現出了與過往小說不同的面貌,而時間觀念與地理意識是其中最為主要的兩個方面。一方面,作家在其小說中呈現出了一種“歷史終結”的時間意識,以此襯托人物無奈無聊對未來無望的人生狀態;另一方面,通過空間概念對小說人物的制約,作家將一種“無路可走”的人生困境,外化為地理空間的變遷,使得小說人物的處境更為真實可感。
以上兩點是周潔茹的香港小說中突然的創作意涵,同時也是區分于她過往特征的重要表現。如果說上世紀末她的創作表現的是年輕都市女性的現代感情觀與獨立意識,那么如今這些香港小說中所要表現的就是中年危機的人生況味了。這些中年女子如同被困在香港,被困在自己現有的生活范式中,并且在可期待的未來里看不到任何改善的可能。她們是時空盡頭的棄兒,也是漫游者,她們大多無所事事,但依然對于生活有著敏銳的觀察,而這對于她們自己來說,是殘酷的。
如果說香港文學常常帶上了“離散”(diaspora)的成色,反映邊緣城市香港在中原意識宰治下的個體狀態,那么,周潔茹筆下的“離散”似乎比這些創作走得更遠。她書寫了許多邊緣城市邊緣人——香港新移民的故事,這些新移民已經與大陸聯系甚微,但她們在香港的“離散”,亦是與本地人對比下的邊緣身份所決定的。
周潔茹并無意于將自己的創作馴服于一城之文學,雖然有著香港的城市背景,但她筆下的故事反映的更是現代人的精神困境,帶有普羅的意義。而她筆下的“離散”,亦是個人的“離散”,是超出政治身份的個人狀態。而作家本人并不刻意融入本土的價值取向,也應和了這種“離散”意識。
作為現代城市的漫游者,周潔茹對于香港的觀察,恰如波德萊爾對于巴黎的觀察,是帶著距離的審視,也是存著悲憫的反思。同時,亦是對于作者自身處境的多重解讀與再現。周潔茹的筆下活動的,歸根到底是現代社會下一個個異化的真實的人,誠如本雅明評價波德萊爾時所說:與其說這位寓言詩人的目光凝視著巴黎城,不如說是他凝視著異化的人。這是漫游者的凝視,他的生活方式依然為大城市的人們與日俱增的貧窮灑上一抹撫慰的光彩。漫游者仍站在大城市的邊緣,猶如站在資產階級隊伍的邊緣一樣,但是兩者都還沒有壓倒他。他在兩者中間都感到不自在。他在人群中尋找自己的避難所。
責任編輯 張韻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