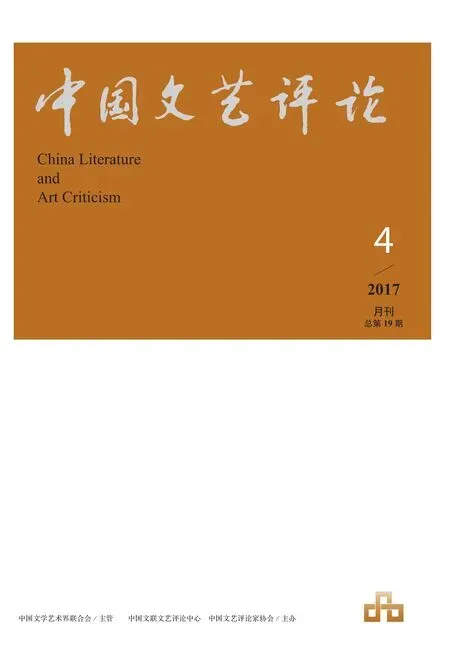新詩敘事的詩意生成及其詩學反思
楊四平
新詩敘事的詩意生成及其詩學反思
楊四平
“新詩敘事”不是該不該存在的問題,而是如何使之產生現代的中國的詩意的問題。因此,我們必須在新詩敘事所提供的歷史形象與現實影像的語境中,從它與新詩抒情、新詩議論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意境、“秘境”和事境,來思考其自由與限度的問題,進而從宏觀上構建新詩敘事理論,看看它們最終能否回應新詩發展的現實提問,并給未來新詩發展提供詩學動力。
新詩敘事 現代詩意 自由與限制
一
唯“情”是瞻,唯“情”是從,抒情獨大,制造了詩歌抒情的神話,遮蔽了敘事性詩歌與詩歌敘事性的真相。
隨著時代發展,尤其是在前現代、現代和后現代交織的多元語境里,相對主義大有取代歷史主義之勢。對詩而言,敘事與抒情,孰優孰劣、臧否分明的辯論,漸漸變得黯淡。而今,到了該將“詩歌敘事”歷史化與系統化的時候了!質言之,要將“詩歌敘事”在不同歷史時期的形態表現及風格特征加以結構性呈現。外國詩歌敘事的歷史化與系統化姑且不論,單就中國詩歌敘事的系統化來說,我們幾乎還沒有起步,畢竟我們對中國詩歌敘事的歷史化都還沒有來得及進行充分的學術梳理!筆者深知,如此龐雜的論題,非筆者一人一時能為。筆者在此先就新詩敘事如何產生詩意以及怎樣產生現代詩意的問題做一番探究。
二
敘事是一種廣義的修辭行為,既指敘事的具體運行,又指文字層面和聲音層面上的修辭格。人們往往偏重敘事的語義學價值,而忽視其語言學特征。而且,在敘事畛域里,小說這種文體長期受寵。尤其到了20世紀中葉以后,在“語言學轉向”的大體背景下,“小說修辭學”日益成為文學研究中的顯學,取得了至高無上的地位。而在詩歌領域,抒情詩長久以來被視為詩歌的正宗,其他敘事性詩體如敘事詩、史詩、劇詩、諷刺詩等則處于邊緣;而仿佛只有此類“小語種”式的詩歌門類才與敘事發生關聯;因此,敘事在詩歌家族里地位之低就可想而知了。直至本世紀初,西方才有人對此進行了深刻反思,并從19世紀以前世界文學發展史的角度,提出“世界上大部分的文學敘事都是詩歌敘事”的觀點,進而提出“建構詩歌敘事學的設想”。正是在西方敘事學和當下西方敘事性詩歌創作及其詩歌敘事研究的啟發下,近年來,國內開始有人研究古代漢詩的敘事性;同時,有些詩人也開始漸漸認識到敘事對于詩歌創作的重要作用,并自覺創作敘事性較強的詩歌。但這并不意味著,在中國詩歌史上不存在詩歌敘事。實際情況恰恰相反。從古至今,中國詩歌敘事從未停歇過。遠的不說,單就新詩而言,詩歌敘事也是邊走邊唱,形態各異,精彩紛呈。因此,我們要將古代漢詩敘事與新詩敘事作為一個整體來加以把握。
三
比較而言,我們談論新詩敘事的優長較多。比如,新詩的寫實敘事,采用線性敘述,展示已經發生的事;有時,這種寫實敘事還采取“典型性敘事”,塑造詩歌形象,彰顯宏大主題,富有寓言傳奇色彩。又如,新詩的呈現敘事,與日常敘事迥然有別,既采用意象,又利用道具或行為的細節,象征或暗示事件的此在性和本真性。再如,新詩的事態敘事,以戲劇性為手段,綜合了寫實敘事與呈現敘事之優長,能夠處理日益復雜的現代經驗。在把握了詩歌敘事學的發展大勢,新詩的三種主要敘事形態及其總體藝術特征之后,結合新詩的敘事狀況以及新世紀詩歌創作現狀,我們至少可以從以下五個方面對新詩敘事進行較為全面的詩學反思。只有當我們了解問題癥結之所在,并探明其成因,方能更好地解決詩歌敘事理論和實踐方面的突出問題,從而有效地創新與推進當下詩歌敘事。
第一,敘事與抒情、議論。新詩敘事容易陷入對事件的瑣碎描述中,造成了詩歌的通貨膨脹,因為詩人們不明白:詩歌敘事,但不泥于事。韋勒克和沃倫認為,“文學的突出特征”是“虛構性”“創造性”和“想象性”。詩歌,即便是敘事性詩歌也需如此,古今皆然,中外概莫能外。“詩者述事以寄情,事貴詳,情貴隱”。事詳情隱不僅是普通敘事性詩歌的律求,更是敘事詩的美學規則。何其芳說:“按照我們中國的傳統,敘事詩就是詠事詩。”以敘事性見長的漢樂府,就是通過省略與聚焦、呈現與凝聚,以情敘事;有時還將矛盾作為敘事推進的動力,具有行為敘事的雛形;但均因沒有“完整的敘事片斷”,只有“片斷敘事”方式,甚至連敘事語法都是臨時的;其敘事特征不像小說那樣突出,盡管有時“小說與詩歌重合”!
縱然新詩敘事是針對偽浪漫的感傷以及古典派和現代派的“不及物”提出來的;但不能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也就是說,既不能將曾經過了頭的抒情一下子降至情感冰點,也不能使曾經“不及物”的形式主義突然嘩變為僵硬的絮叨。梁啟超曾經主張“新學之詩”/“新派詩”寫實時“專用冷酷客觀”。他要求詩人不能把個人情感帶入敘述中。他認為只有這樣,才是“寫實派的正格”。對此,一直以來,質疑之聲不絕于耳。朱光潛、馮雪峰等就曾詰問過“將詩看成新聞記事”的狀況。何況世界上不可能存在純而又純的所謂的“純客觀”寫實!從“同情之理解”的歷史態度,進入歷史現場,我們完全理解梁啟超當年面對清談詩風盛行的憤懣以及由此而發出的憤激之辭。其實,我們也表示相信,梁啟超不可能犯如此低級之錯誤。它不過是一項權宜之計罷了。不止是詩歌寫實,就是小說里的寫實,也只能是仿真性敘事和典型性敘事;而且詩歌寫實還不能像小說寫實那樣以集矢式描寫人物為依歸。吳宓曾經歸納出荷馬史詩的“直敘法”和“曲敘法”。其中,“直敘法”偏向寫實敘事;而“曲敘法”類似于我們前面講到過的呈現敘事和事態敘事。總之,詩歌敘事不能自陷于對生活過程中細枝末節的展示,其實它們也可能是情感的寄寓與象征的依托。不少現代詩人在詩歌敘事過程中自覺地把寫實、激情和象征糅合起來。此外,還需要提出的是,盡管新詩敘事具有修復詩歌與社會生活關系的可能,但不能因此而將其神化,要兼顧抒情和議論對修復詩歌與現實關系的同樣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也就是說,我們要客觀理性地看待新詩敘事,不要唯敘事而敘事,不要把敘事泛化,不要將新詩敘事變成現代中國版的詩歌的“天方夜譚”,要認清敘事之外,新詩空間依然十分遼闊。尤其是,當我們評價新詩時,要力避空泛的整體性,要認清詩歌敘事只是詩人的個體選擇和詩歌態度,而不能將其視為某種普適性的詩歌標準,更不能據此妄言一切詩歌的價值和擔當;否則,既封閉了、僵化了、抽象化了、本質化了、霸王化了詩歌敘事性,也看不到詩歌敘事性與其他的詩歌特性之間的多種張力及其無限可能。20世紀90年代的“知識分子寫作”與“民間寫作”之爭,在某種程度上,就落入了這種詩歌整體性中。
有沒有文類意義上的“純”詩?如純抒情詩、純敘事詩、純智性詩?顯然,這種詩歌范本層面上的價值判斷,雖根深蒂固,但終難立足。我們只能說,一首詩不同程度地參與了所有詩的類型,而其中哪一種因素較為明顯、突出,我們就將其稱為某類詩。筆者認為,在一首詩里,如果兼有敘事、抒情和議論,且它們之間越是熔合無間,那么這首詩就越是趨于完美。據此,筆者主張,在新詩寫作中,應該把敘事與抒情、議論結合起來。首先我們要準確理解和把握詩的抒情。如果我們僅僅把抒情等同于古典的牧歌情緒,那么我們就在不知不覺中將“抒情”偷偷置換成了“抒情對象”,與此同時,還悄悄地將它們都符號化了。據此,我們需要將抒情和抒情對象再歷史化,恢復其本來面目,呈現出它們原本擁有的多樣和生機。只有這樣,抒情性就不再與敘事性風馬牛不相及,抒情性就不再是某些詩人想象中的敵人了。在寫抒情詩時,郭沫若雖然是狂飆突進地抒情,但他并沒有放棄敘事,更沒有喪失理智地走偏鋒,而是始終把情、事和理勾連在一起。不同于古代漢詩敘事,除了段位性的“形式敘事”外,大部分新詩敘事是主體性敘事,以情感為目的,事以情觀,情隨事發。“敘事中往往有詩,正如抒情不能脫離一定的事”,“抽掉了敘事,抒情即失去根基”。新詩敘事應該與抒情、議論結合起來,并最終要促使它們三者之間熔冶;如果沒有這種藝術熔冶,新詩敘事就容易犯“客觀主義”和“形式主義”的毛病。為敘事而敘事,割裂了敘事與抒情、議論之間的血脈聯系,沒有顧及敘事中詩的質素,沒有發揮詩的想象力,沒有注重詩的技巧,詩歌敘事就會蒼白無力。因此,應該把新詩中敘事與抒情、議論結合起來,先敘后抒、邊敘邊抒、敘中有抒、敘抒合一,乃至敘、抒、議“三合一”,就像白話詩剛出現不久俞平伯所期望的那樣,“說理要深透、表情要切至、敘事要靈活”,唯有如此,方能發揮詩歌以少勝多的優勢和特色。
新詩敘事、抒情和議論的關系問題并沒有就此得以解決。比如,敘抒、敘議、敘抒議,不一定總是能夠結合,正如雅俗不一定總是能夠共賞那樣!平緩敘事的內面常常涌動著不為人知的澎湃激情,這種“外冷內熱”型敘事,固然值得欣賞,但是避免出現抒情無情、敘事無事、議理無理的法寶何在?新詩難道只有抒情傳統和敘事傳統這兩個傳統嗎?是不是還有包括“議論傳統”在內的其他傳統?諸如此類懸而未決的問題值得我們更加深入細致地探究。
第二,敘事與意境、“秘境”、事境。新詩敘事在詩歌美學境界的追尋與營構上,常常因迷戀古典意境而難以舒展自己。其實,敘事是詩里的一種因子。敘事不僅是一種推動詩歌抒情和審智的修辭策略,也不僅是為了營造新詩的意境,更為主要的是以此營構一種有別于傳統抒情意境的現代事境。往深里說,敘事既是空間的,又是時間的,是空間與時間的、意義與聲音的和諧體。“一言以蔽之,詩不止是我們逼視的文字(空間),更是要我們傾聽的語音(時間)。”這是新詩敘事理應遵從的詩歌規范。在馬拉美看來,散文的語言是粗鄙而臨時的,詩歌的語言是純粹而本質的;現實與語言之間不相符,純詩中容不得現實的東西,“敘述,教育,甚至描寫這些都過時了”。顯然,在純詩論者眼中,詩是神秘的,不可解的,像謎一樣;因而,像敘事這種貌似意義明朗的東西是詩歌雜質;也就是說,純詩詩人既反對意境,又不滿事境,而追求“秘境”。像古典抒情詩人以意境否定事境那樣,純詩詩人以秘境否定意境和事境,都是形而上學思維從中作梗的結果。他們都不能用聯系和辯證的觀點來看待問題。其實,意境、事境和秘境是彼此勾連的,只不過側重點不同而已。具體到20世紀上半葉的新詩敘事而言,它們側重于事境的營構。以“紀事”為特征的寫實敘事追求明朗的事境,而呈現敘事和事態敘事追求幽深的事境。不管是哪一種詩歌敘事,不論追求的是明朗事境還是幽深事境,“每首詩都自成一種境界。無論是作者還是讀者,在心領神會一首好詩時,都必有一幅畫境或是一幕戲景”。這也牽涉到敘事與讀者的問題。漢樂府以代言和旁言的方式,不斷轉換視角,推進敘事,就是出于“為聽者計”的詩學考慮與安排。徐志摩受波德萊爾的影響很深。在《波特萊的散文詩》一文里,他將希臘神話典故中的“埃奧利亞的豎琴”演繹為“伊和靈弦琴”(The Harp Aeolian)。但是,當他在寫《再別康橋》這樣的域外題材時,他沒有使用西方文化里的“伊和靈弦琴”,而是十分靈活地回歸中國傳統文化,并在那里找到了“笙簫”來取而代之,因此就有了那句名詩“悄悄是別離的笙簫”而非“悄悄是別離的伊和靈弦琴”。徐志摩自由游走于中西文化,既要以陌生化和驚奇美滿足讀者的審美期待,又不忘顧及讀者的欣賞慣性。質言之,新詩敘事在營造事境時,在明朗與幽深之間,要適當從讀者接受的角度,綜合考慮它們的適度問題。
第三,敘事的自由與節制。新詩不同于古代漢詩最大的特點就是自由。這種自由既指形式上自由,也指精神上的自由,還指詩人個體對于語言取舍權的自由。但也正是由于這么多自由,以及新詩不懈的實驗精神,隨之伴生了無節制的瑣碎和散文化之弊端。
其實,“作詩如作文”及其寫實詩創作,并非始自五四白話新詩詩人。一些古代詩人,如同光體詩人,在1912-1919年間,創作了大量的時事詩,其中還有不少是敘事性長詩。早期新詩里有不少即興之作,但由于寫的是古典詩詞里所沒有的社會內容,就像當下的搖滾樂是一種時髦那樣,所以它們以及寫作它們的詩人受到了那個時代青年讀者的熱捧。對此,當時于賡虞沒有隨大流,反而友好提醒與理性評說道:“他們的詩作的草率,正與他們所受的歡迎相等”。這就警示人們不能對其進行拔高式評價。周作人曾經明確表示自己不喜歡沒有節制的所謂的詩歌自由,“不喜歡嘮叨的敘事,不必說嘮叨的說理”,因為這些“嘮叨”里缺少詩的“余香與回味”。詩不是信手涂鴉,而是一種美的技術,因而修辭是必不可少的。在古典中國,技術詩學淵源有自。美國漢學家宇文所安說:“從13世紀以來,批評家越來越傾向于把詩歌視為一種相對自治的活動,這種傾向集中表現在對技術詩學發生濃厚興趣:對師法前輩詩人提出質疑,開創和發展一些新的話語以談論那些純而又純的‘詩’的特性。”需要說明的是,技術詩學不等于技術主義。我們要警惕的是技術至上、唯技術而技術。新詩敘事同樣需要屬于自己的一整套技術詩學,至少要認清和處置好敘事的自由和敘事的節制之間的辯證關系,要在敘事的可能性與敘事的不可能性之間尋找新詩的敘事張力。肖開愚反躬自省道:“場所是不是太多?情節是不是左右了詩人的想象力?敘事的時候夾進去的評論是不是有點兒像無可奈何地投降?”質言之,新詩敘事的現代性、段位性和有效性的獲取,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現代詩人對自由和節制的把控。太隨意,太散漫,太雜蕪,肯定沒有詩意可言。當然,我們所說的詩意不是披著現代外衣的古典詩詞里的詩意,如廢名所說的不承擔敘事、說理,甚至抒情,而只寫自己的一點意念,一個感覺的“詩的內容”;也不是純詩意義上的西方現代詩歌里的詩意,像沈從文說的那樣“一首詩,告訴我們不是一個故事,一點感想,應當是一片霞,一園花”。我們所說的詩意,是逆反古典甜膩詩意和現代苦澀詩意的現代智性詩意。它通常經由“冷抒情”“冷敘事”和“熱敘事”而獲取。也就是說,新詩表面上的“反詩意”,并不就真的否棄了詩意,但是這些試圖通過反對甜膩詩意和苦澀詩意,委曲抵達智性詩意的簡樸方式必須要把握好“度”。申言之,樸素、冷靜、克制固然有可能產生美,但是如果過了頭,就會弄巧成拙,更顯粗糙和寒磣,此時的樸素就離感傷不遠了,或者說就是感傷和矯情了。換句話說,雖然新詩敘事的綜合力的確拓展了詩歌表達的深廣度,但是,無節制地往詩里“填料”,使詩變得難以承受如此重負。我們應該把捏好新詩敘事的自由與節制,在詩歌敘事的臨界點上給詩減負,使其擁有更大的自由、自足和自覺。
第四,建構新詩敘事理論。如何將新詩豐富的敘事經驗與古今中外普遍的敘事思想和敘事理論結合起來,尤其是從已有的新詩理論批評中抽繹和歸納新詩敘事言說,成為建構新詩敘事理論的頭等大事。我們應該避免削足適履,不能“用西方的文論術語來切割中國的文學文論,或者把中國文學文論作為西方文論話語的注腳本”,也就是說,我們要么借鑒西方敘事學理論,在新詩敘事理論與實踐的基礎上,建構具有民族特色的新詩敘事理論,評析新詩敘事實踐;要么拋開西方敘事學的緊箍咒,既遵循中國人獨有的重感悟的思維方式,又不排斥西化色彩較濃的邏輯思維,以及既保留中國敘事學原本具有的人學精神和心學色彩,又吸納西化成分較大的現代理性,從中國詩歌敘事實踐以及各種言說中,總結出一套完全屬于中國本土的敘事理論,努力找尋專屬新詩的敘述語法,并以此來解讀中國詩歌敘事實踐。盡管在這方面我們做了一些工作,也取得了相應的成績,但是比起新詩豐富的敘事實踐來,我們所做的還遠遠不夠,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當務之急,我們在向西方借鑒敘事詩學資源的同時,也應該向古代漢詩敘事理論汲取詩學資源。1919年,戴季陶在推介白居易的“社會文學”時說:“第一是平民的,第二是寫實的,無論抒情詩詠物詩,一點沒有神秘的臭味。也沒有夸大的習氣。第三是現代的,他的題材都是從當時的社會狀況上面尋出來。”已有部分詩人意識到,古代漢詩里含有現代詩人應該認真汲取的現代性。畢竟當年它們曾漂洋過海被譯介到海外,直接影響并催生了英美意象派;而正是后者又折返回來啟發了新詩的誕生和嘗試;質言之,古代漢詩對新詩構成了直接式和回返式的雙重影響。如此一來,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么現今有不少詩人向杜甫學習,向白居易學習,向《詩經》學習,向樂府學習。順此,值得提出的是,如果說早期新詩批評糾纏于新與舊之分野問題,隨后曾經長期徘徊在“外面”與“內面”之間;那么此后的新詩批評會不會轉向對敘事與抒情的討論,以促進新詩評價機制的再一次轉化?
第五,如何以筆者的此項研究回應人們對當前詩歌現狀以及未來詩歌發展之關切,我們有必要把百年新詩敘事置于“新詩的百年演變”的整體視閾中進行觀察與思索。由于篇幅所限,加上主體性突出是新詩區別于古代漢詩的重要特征,所以這里僅從百年新詩敘事主體角度來勾勒其嬗變軌跡:由晚清黃遵憲式的客觀性敘事主體、20世紀20年代郭沫若式的擴張性敘事主體、20世紀30年代何其芳式的自戀性敘事主體、20世紀40年代穆旦式的分裂性敘事主體;到20世紀50—70年代彌漫文壇的人民性敘事主體;至此,新詩的現代性敘事要么被宣講國家意志的工具性所綁架,要么被集體高漲的激情抒發所吞沒,盡管此間也有敘事實踐,但敘事理論卻乏善可陳,導致了此期新詩敘事理論與實踐的整體衰弱。進入新時期以來,新詩敘事主體開始復歸,尤其是自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以來,新詩敘事主體經歷從20世紀80年代于堅式的還原性主體到新世紀西川式“混雜性”主體的當代演進。由此,我們可以看到新詩呈現敘事對于堅式敘事寫作的影響以及新詩事態敘事對于西川式敘事的影響。當然,話也可以反過來說,于堅式和西川式的詩歌敘事分別對呈現敘事和事態敘事傳統,除了繼承之外,更多的是創新,乃至在20世紀90年代還促成了詩歌敘事性高漲。當然,對其是非功過只有交由歷史評說。
20世紀英國批評家考德威爾在談到“詩的未來”時說:“詩在技巧上達到了空前的高水準;它越來越脫離現實世界;越來越成功地堅持個人對生活的感知與個人的感受,以致完全脫離社會生活,直至先是感知然后是感覺都全然不存在了。大多數人不再讀詩,不再覺得需要詩,不再懂得詩,因為詩隨著它的技巧的發展,脫離了具體生活,而這一脫離本身無非是整個社會中類似發展情況的對應物而已。”詩脫離社會,社會報復式地、變本加厲地脫離詩。這多少有些悲觀。因為考德威爾“不成熟”地排斥現代主義,致使其只能看到問題的一方面,或者說把問題簡單化、道德化和社會化了。因為,在筆者看來,詩的“向內轉”,詩注重自身的段位性,并不一定就脫離了社會,也不必然意味著是條詩歌窄路,更不等同于詩歌死路。但是,吊詭的是,他當年下的詩的讖語,在當下中國詩界似乎得到了應驗。面對此種詩歌險境,當下中國詩人不但沒有放棄“向內轉”,反而在挖空心思地考慮如何在詩的“敘事背后”“敘事之外”大做文章,大有可為。當代著名詩人西川說:“在杜甫的敘事背后有強大的歷史感,在莎士比亞的敘事背后有上躥下跳的創造力,在但丁敘事背后有十個世紀的神學和對神學的冒犯。我們不必向偉人看齊,但我們總得在敘事之外弄點別的。”其實,新詩史上不乏這方面的探索與實踐。徐玉諾就是通過戲劇性絕境,將寫實敘事拓展為對生存境況的拷問,而且極力不使其風格化,始終保持多樣化的活力。也許唯有如此,當下詩歌才能產生敘事的詩意。它不再是單一的詩意,而是修辭的詩意、事境的詩意、秘境的詩意和意境的詩意之間的相互熔冶,是對異質因素的具有分寸感的扭結,是反常合道的意趣和理趣,是陌生化和奇特化對自動化的阻斷,是對事物內在隱秘的準確、生動而有力的詩意揭示。這種現代的敘事的詩意,也許就是新詩未來發展的著眼點和支撐點。
敘事為新詩塑造了豐富的歷史形象和生動的現實影像。筆者相信,它必將為當下詩歌乃至未來詩歌的發展繼續指示方向、提供動力。
*本文系國家社科項目“現代漢詩的敘事形態研究”(15BZW123)的階段成果和“安徽師范大學博士科研啟動金項目資助”。
楊四平:安徽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責任編輯:王筱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