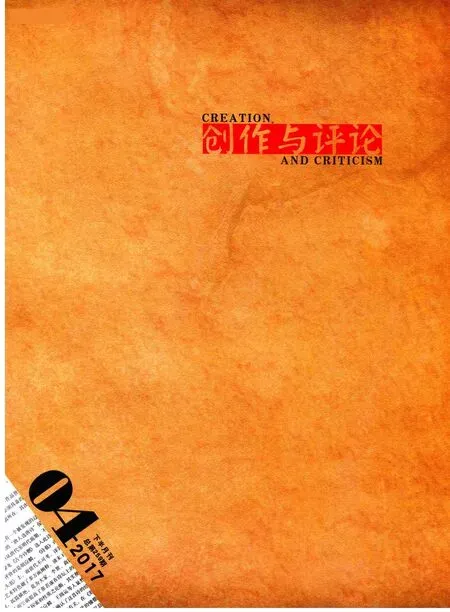人生苦難與困境突圍
——從《天堂無窯》看吳劉維的小說創作
○李 蘭
人生苦難與困境突圍——從《天堂無窯》看吳劉維的小說創作
○李 蘭
當下的中國,仍處在一個重要的轉型時期,“一個作家應該完整地去表現他自己時代的生活,應該成為他的時代和社會的代表,這是一種特殊的評價標準”。面對轉型期出現的種種社會問題,城市的繁盛與農村的凋敝,城市文明的建立與農村道德秩序的坍塌,以及由此帶來的精神文化領域的迷茫與創傷,文學的日漸“邊緣化”與“市場化”,吳劉維自1984年開始創作以來,以自己對文學的熱愛,對寫作的堅持,對當下的生存現狀與生命現實的獨特理解,持續著他一貫的寫作熱忱,除了少數幾篇散文與創作談外,吳劉維創作了一系列優秀的小說作品,從早期短篇小說《空樓》到2016年創作的《然后呢》,從長篇佳作《絕望游戲》到中篇新作《一個人的游行》。謝有順曾說,一個作家的根本使命是對人類存在境遇的深刻洞察。因而,一次成功的創作,不僅僅是判斷,它更是一種發現,一種理解,一種對存在的發現,對生命的理解。作為一個有著豐富的鄉村生活經驗的湘籍作家,吳劉維對農村現狀與底層人物生活表現了持續的關注,用不斷叩問、飽含深情的筆墨不只是呈現了農村的“貧”,也反思著農民的“困”。“商業時代的農民已經跟農耕時代的農民有著本質的區別,他們懂得用最低的成本去獲取最大的利潤”。《天堂無窯》正是吳劉維以其獨有的苦難與困境的觀照方式,對底層人物性格與命運的現實書寫,是一次用寫實手法實現對人性苦難與生存困境的突圍,滲透著作者對道德人倫、人性與命運的思考。
“我老家在山溝,要緩解生存壓力,要給孩子一個出路,二叔們別無它法,只有拼盡身家性命”,吳劉維曾提到,創作《天堂無窯》的“點”緣于他二叔跟他說的一句話,“我恨不得被砸死在窯里,拿賠償金來供細孩念書”,農村現代化進程的加速,財富積累的同時也伴隨著痛苦的增加,為了改變下一代的命運,不再過“面朝黃土背朝天”的生活,許多像“三叔”一樣的農村父母起早貪黑,省吃儉用,在艱苦的環境下死命捱著他們這一生。《天堂無窯》講述的正是生活在貧苦窯區的三叔為了供孩子順利念書,將來過上像“我”一樣在城里有份工作、有房有車的生活,自己設計布局用“命”換取“賠償金”的故事。
作者有意設置懸念,用倒敘的方式切入,開篇第一句話即“最后一次見到三叔”,為整個敘述埋下伏筆。故事一波三折,帶著種種疑問,隨著“我”的疑慮與猜測,三叔的“瞞天過海”之計漸漸清晰明朗。如果說三叔的“如愿以償”還有些許喜劇色彩,三叔最終的結局卻讓人心酸。一場戲劇化的“假死”騙局,三叔靠智慧用“假死”換來窯老板的賠款,用“作假”騙取保險公司的保險金,最后只能裝扮成撿垃圾的啞巴,遠遠看著一雙繼續求學的孩子,一個人病死垃圾站。三叔曾問及“天堂是否有窯”,“窯”原本喻示著災難與不安,也象征著苦難與死亡,但在三叔眼里,“窯”象征著財富、象征著出路——是供孩子們念書的“財富”,是改變孩子們命運的“出路”。回想起窯老板附和的話:“命是用錢買不到的,錢再多也沒有命珍貴”,三叔的這出戲唱完之后,究竟命貴?錢貴?此刻我們反而很難給出答案。農村資源的匱乏,財富分配不均,貧窮與苦難這對孿生兄弟,最終逼迫“農民不再像農民”“罪犯不再像罪犯”。
沈從文先生說:“小說要貼著人物寫”。吳劉維的小說創作,常給人一種真實、樸素的感覺。當他寫人的時候,他用扎扎實實的態度,照著人物本身來寫。《天堂無窯》中寫三叔埋頭吃米粉,“一大碗米粉連湯吞下,碗里像被清水洗過”,吃完還伸出用舌頭將嘴巴舔一圈,連說“飽了,飽了”;寫三叔等順風車,“每駛過一輛貨車,三叔都要高高揚起手臂”,“手機響了,三叔將它按掉,手機又響,三叔又按掉,手機再響,三叔再按掉”,一個節儉而又憨直的農村漢子形象躍然紙上。吳劉維用極其生動寫實的手法,盯著三叔這個人物寫,寫他的言行舉止、喜怒哀樂,三叔“熟悉窯的脾性,就像熟悉自己身上的器官”“甚至能預料到(窯上)事故發生的準確時間”。轉型期的中國農村“勤勞、肯干”仍是廣大農民的代名詞,許多在自家地里干了幾十年的莊稼漢,因常年的經驗積累,成了“老把式”“能家里手”。三叔是地地道道的農民,一生勞累艱辛,在鎮上的窯里摸爬滾打30年,因而也練就了一身好本領。然而,農村在社會利益分配上一直的弱勢地位,勤勞致富變得愈加遙不可及,精明能干也無法換來身體的康健、生命的長久。艱苦的勞作環境,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高強度勞累,吃苦耐勞的品行與頑強的生命力無法阻止疾病與死亡給農民帶來的更大威脅。作者寫三叔在窯下拼了30年,落得一身的病,但沉重的家庭負擔,三叔“似乎時刻在強忍著疼痛,臉上因扭曲變形”,只能靠著止痛藥,“一直拖著病體下窯做苦力”,最后患上骨癌,不久于人世。現實與理想的矛盾,三叔的“布局”也開始變得情有可原。作者依據充分的事實和嚴密的情理邏輯,結合寫實的手法,塑造著三叔這樣一個典型人物形象。
魯迅先生在談他開始小說創作時說,“所寫的事跡,大抵有一點見過或聽到過的緣由,但決不全用這事實,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發開去,到足以幾乎完全發表我的意思為止。人物的模特兒也一樣,沒有專用過一個人,往往嘴在浙江,臉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個拼湊起來的腳色”。吳劉維對人物的成功塑造還體現在不僅注重對不同角色不同對象的準確表達,還擅長用最簡潔的文字對作品中次要角色、“小人物”予以傳神描繪。比如他對《天堂無窯》中三嬸等幾個女性的成功塑造。“窯老板提著一個鼓鼓的包,從包里倒出一堆現金,三嬸數了兩遍,總共20扎,三嬸給我們每人發一扎,說:‘幫著數數。’我們沒一個動手,三嬸自己拆了一扎,一張一張地數,數完說:‘100張,沒錯。’又要拆數另一扎,大叔瞪大眼睛望她,三嬸的手只好縮了回去”。作者直接引用三嬸自己的語言,配以幾個動作,寥寥數筆,一個鄉下婦女的形象活脫脫地展現,尤其是后來寫三嬸面對這筆35萬元的賠償金的反應,(三嬸)被“弄得極為疲倦”,“她自顧自的一會兒愁眉苦臉,一會兒扯開嘴角陰陰地笑”,這些簡單的描寫人物神態、語言及動作的詞句,足以見出作者的寫作功底。又如小說中著墨不多的“我”母親的形象,作者寫清晨三叔剛進“我”家,母親看到三叔的行頭,原以為是給自家帶的禮,便趕緊放下手頭的活兒,接過三叔手上的蛇皮袋,說:“大老遠的,提啥東西!”得知是給三叔自己倆孩子帶的干菜,母親“喜著的臉沉了下去,隨意將蛇皮袋丟在墻腳”。這一“喜”一“沉”兩個截然相反的反應,配合“隨意”“丟在墻角”這兩個動作,母親的世俗、勢利等特征便一覽無余。此外,作品中對一平、畫師等人物的刻畫,也顯示出作者細膩、敏銳的創作品質。寫一平在三叔出事后與“我”的那番交流,表現了一平的成熟、老練,而后特意塞給畫師兩份工錢,悄聲對畫師說的話,更是印證了一平的這個特征。寫畫師的反應,先是主動打斷一平的話,然后保持一貫的笑容,將工錢小心翼翼地塞到兩重外衣的內衣口袋,一個精明厲害的畫師便活靈活現。吳劉維這種真實刻畫的素養,若不是對日常生活有著細致入微的觀察,對形形色色人物有著自己獨到的理解,恐難寫出如此惟妙惟肖的文字。
語言對于小說同樣重要,好的語言,不僅能準確傳達作者想要表達的意思,還能收到對作品的畫龍點睛之效。《天堂無窯》中的語言尤其是人物對話都極具特色。作者吳劉維“貼著語言寫”,并不時夾雜些方言俚語,讓人物變得更可信,同時也讓作品變得有趣、耐讀。寫三叔形容自己的一雙兒女,“天剛我生的還不了解?用錢比我還緊,連信息費都舍不得,嘿嘿,接我的腳!天嬌不一樣,接她娘的腳,用錢一路來大手大腳!”俗話說,“知子莫若父”,三叔總結得一點也不差,從作者的描述看來,天剛的節儉較其父三叔半斤八兩,十幾公里的路程連公交都舍不得坐,直接用走。三叔出事后“我”每次去送生活費,天剛都幫我拿主意省油費,以至于“我”只能把車遠遠停放。寫老馬借酒告訴“我”他跟三叔的“秘密”,一直遮遮掩掩的老馬,等“我”掉轉車頭,
老馬又把頭伸進來,朝我說:“我真喝多了。”
“你沒醉,蠻清醒的。”
“沒醉我會跟你說這些!”
“你說什么啦?”我裝出一臉的迷糊。
“真不記得我說什么啦?”
“不記得。只要一碰米酒,我就不記事。”
老馬這才放下心回家。
這一問一答來回幾個對話,老馬一副欲言又止、欲說還休的模樣便栩栩如生。試想,如果沒有這番對話的描寫,不僅會讓人產生疑惑,質疑老馬在作品中前后形象的一致性,連后文“我”的猜測也都無法成立,甚至有可能導致整篇小說架構的坍塌。無疑,吳劉維是一個對語言極有感覺的作家,他深諳語言對于小說的重要性,懂得如何充分運用語言,建立與讀者的聯系,獲取讀者對作品的信任。
注重細節真實,是吳劉維創作的又一特征。細節較于故事,好比零件之于機器,零件不完備,機器無法裝配完全,終究不能正常運轉。忽略細節的真實性,僅憑一己印象“想當然”、不屑做“笨功夫”就冒然下筆,不僅容易失真,甚至會釀出笑話,使讀者對作品產生懷疑,最終失去讀者的信任。一個好的作家絕對是一個“有心人”,除了在日常生活中能敏銳觀察、善于發現,還要能仔細琢磨、準確表達出那些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特征的生活細節。哪怕是一段稀疏平常的風景描寫,對事件、場景、器具的交代,都應合常理,與敘事邏輯保持一致。比如在《天堂無窯》中一共四次寫到的月亮,有回憶中兒時與三叔一起玩耍時“明朗的”月亮,有面對三叔的“死”,一平跟“我”道出困惑時“又圓又大,像是一朵開在山尖上的蘑菇”的月亮,還有三叔出事前后,對同一個月亮的兩次不同的描繪。三叔跟“我”的閑聊,看似無心、實則有意,從“月亮搖搖晃晃從云里探出頭,荷包蛋一樣粘在天鍋上”,到事后“我”再回想起當時的情景,月亮“在天邊忽隱忽現”。同樣是寫月亮,不同的情境,月亮隱含著不同的意義,兒時印象中所有的酸甜苦辣都化成美好的回憶,因而月亮是明朗透亮的,是喜悅歡欣的象征;蘑菇的唾手可奪與山尖的遙不可及,象征著人物內心的無奈與遺憾,在作者筆下,結合當時人物的心境,甚至連當時的月光都變得“慘白”。
小說是虛構的藝術,不論是《天堂無窯》,亦或是長篇小說《絕望游戲》,又或者是在新近中篇小說《一個人的游行》中,吳劉維用虛構的故事講述了一個個生活真相,訴說著人在強大的欲望與誘惑下內心的軟弱和無奈,面對苦難與困惑時的猶豫與掙扎,也展現著人性在庸常俗世中如何一點一點地被侵蝕和消融。
《絕望游戲》開篇講主人公吳谷生組織招聘,考題的內容分別對應一個人是否有積極良好的愿望、有具體運作的技巧和總攬全局的創意。作者用最簡單直接的方式,主人公的形象躍然紙上:善于思考、務實能干,喜歡簡單清凈同時又不失文人的浪漫與好自由。作者通過吳谷生這個主人公的塑造,賦予作品一種人性道義上的偉大力量,滲透著作者對生活的理解,也蘊含了作者對人性的解讀。《我岳父就這樣老了》寫岳父為了不再讓司機看出破綻,對自己從頭到腳一番“蹂躪”,連神態行為也做了一番刻意的調整,讓“我”都不禁感慨“岳父還真具有表演天賦”。簡潔明快的語言,仿佛這樣一個老頭兒就在自己跟前,幽默詼諧背后又難免生出些許憐憫與傷感。《送雪回家》中作者刻意塑造主人公陳子魚的與眾不同,意在表達作者對婚姻家庭的選擇,對傳統價值觀念的捍衛,對繁嚷現世下心靈歸宿的守護。小說中有一處寫陳子魚提出讓博士幫忙送雪尤為讓人印象深刻,博士先是“果然毫不猶豫地答應了”,但聽說帶的東西是雪,博士的反應變成“毫不猶豫地拒絕”,直笑陳子魚“做舅舅的沒有舅舅的樣子”“還玩些小孩子的把戲”,在博士看來,陳子魚的舉動不僅無聊,而且愚蠢,是一種“腦殼有毛病”的行為。《然后呢》中對子語媽訴說子語的可怕的親生父親又找到她們這一消息時的情景描繪,作者用細膩敏銳的筆觸,準確且傳神地表達了子語媽內心的極度恐懼,也寫出了作品主人公“他”(子語繼父)的憨與迂,這一看似風輕云淡的描繪,不僅合乎情理邏輯,也極為貼近人物身份。不同于以往的創作,在《一個人的游行》中,吳劉維這次調整了敘事策略,將看似兩個毫不相干的故事用交叉敘事的方式同時進行,一個題材,兩條線索,以“打倒……”為每一次敘事發聲,在一種看似冷靜、沉著的敘事姿態下,敘事者向我們講述了一個極具特色的中國式故事。小說成功地向我們傳遞了這樣一個事實:故事當然仍是現下的故事,人還是現實世界的人,只是,讀罷這樣一本小說,讀者腦海中的畫面定格到了中國歷史上某個特定時期,“打倒……”是一種口號,更是一種控訴,呼喊著這樣一種口號的人,懷著滿腔哀怨,誓不回頭地奔赴一個可能走向自我毀滅的終點,然而即便如此,這樣的故事仍舊在重復上演。卡夫卡有句名言:“不要絕望,甚至對于你并不絕望這一點也不要絕望。在似乎窮途末路之際,總會有新的力量產生,而這恰恰意味著你依舊活著”。從這個意義上來看,對于吳劉維而言,寫作就是他生命的一種表達形式,對人生境遇的敏感,生命存在的關懷,給予了吳劉維足夠的寫作勇氣,在現實面前挺身而出的力量。
很顯然,吳劉維是擅長寫實的。通過對作品中一個個典型藝術形象的精雕細刻,對日常器具的耐心打磨,對某一生活場景的細致刻畫,吳劉維以一貫務實的風格著重寫妥一種生活,并力求把這種生活落到實處。這些看似波瀾不驚的文字背后,蘊含著作者滿腔的創作熱情,映照出人生的豐富多彩,也隱射著文字背后那種難以言喻的微妙,巧妙地折射出作者對這個世界的洞察與理解。吳劉維以近乎苛責的態度,從日常生活的細微處著手,建立起屬于自己的小說王國,在這個王國中,因為理解所以悲憫,因為相信所以充滿希望,它正是吳劉維心中那個“無窯”的天堂。
注釋:
①韋勒克、沃倫著,劉象愚等譯:《文學理論》,三聯書店,1984年版,第93頁。
②⑤吳劉維:《低空飛行者》,《湖南工業大學學報》(社科版)2015年第1期。
③吳劉維:《吳劉維創作談:虛構的力量》,《中篇小說選刊》2011年增刊第三輯。
④吳劉維:《低空飛行者》,《文學界》(“吳劉維專輯”創作談)2014年第11期。
⑥魯迅:《我怎么做起小說來》,《語文教學與研究》(讀寫天地)2013年第3期。
⑦弗蘭茨·卡夫卡著,葉廷芳主編,孫龍生等譯:《卡夫卡全集》(第5卷:日記(1910-1923)),中央編譯出版社2015年版。
(作者單位:吉首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中山大學文學院)
責任編輯 張韻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