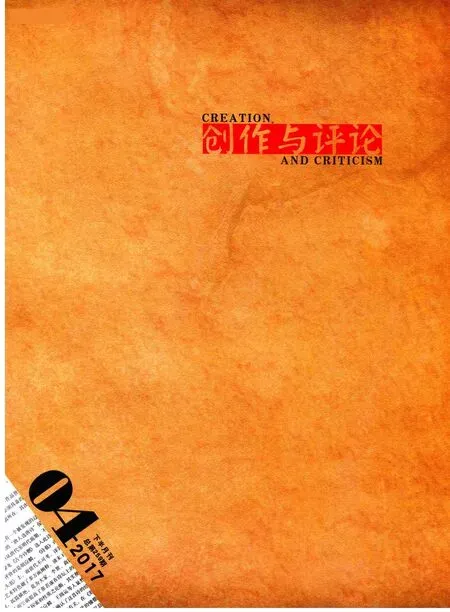廢墟與漫游者:解讀第六代導演青春敘事的一種視角
○董文暢
廢墟與漫游者:解讀第六代導演青春敘事的一種視角
○董文暢
從中國電影青春敘事的發展脈絡來看,第六代導演的“青春自傳”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掀起了第一次作者論意義上的青春片浪潮。張元、王小帥、婁燁等青年導演既是影像文本的創作主體,又是文本內部的經驗主體。他們高舉青年亞文化的旗幟,打破了革命青春電影與傷痕青春電影井然有序的元敘事,將具體的、感性的“身體”視為人存在的第一維度和與世界建立聯系的首要媒介,以私人化、邊緣化的生命感受傳遞出身處社會轉型期的焦慮、痛苦與迷茫。可以說,“感性文化”“身體美學”“殘酷物語”是第六代導演青春敘事的鮮明印記,也是國內學者分析第六代導演自傳的常見角度。然而,這些影片中“身體的在場”不僅關切著性與暴力等感官命題,更觸及到青年在都市空間內的現代性體驗問題。正是在空間敘事研究導向下,有海外電影學者以“都市一代” (urban generation) 命名第六代創作群體,認為九十年代青春電影的主要特征是對城市化所帶來的社會問題的敏感。
在某種程度上,第六代電影中的“搖滾青年”與王朔電影中的“頑主”都表明了同一種時代癥候,即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青年在意識形態神話覆滅后的精神空虛、價值錯亂與身份迷失。所不同之處在于,王朔以“言語話語”挑戰權威、顛覆秩序,第六代導演用“身體話語”沖破主流文化的身體規訓。從想象中的解構到身體力行的沖撞,我們可以看出搖滾青年比頑主的壓抑感與挫折感更加強烈,反抗性與斗爭性也更加強烈。他們對待都市文明、大眾文化的態度也少了份戲謔與調侃,多了份控訴與絕望。
“搖滾青年”的另一重身份是都市的“漫游者”。秉持著先鋒、激進的創作態度,第六代導演將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映現為斑駁、凌亂、骯臟的廢墟圖景,將個人的青春體驗言說為殘酷、扭曲、裂變的灰色記憶。一方面,都市空間的視覺符碼凝縮著商品化浪潮中東方與西方、傳統與現代的意識形態對立。另一方面,都市空間也被附著上濃重的主觀情感色彩與憂郁氣質,成為青年心理空間的延伸和精神世界的隱喻。空間質感與個體經驗兩相疊合,形成一種異質同構關系。
德國思想家瓦爾特·本雅明將歷史看作現代性完全展開的過程,并在此向度上提出了“廢墟社會”和“漫游者”的象征意象,為文化研究開啟了全新視野。“都市一代”鏡頭下“都市/青年”的想象性關系正契合了本雅明“廢墟/漫游者”的寓言式批評母題,同時也注入了中國社會城市化、現代化進程中的復雜現實與本土問題,敏銳地探入都市文明與現代人心理結構的裂縫中。影像中,青年們一刻不停的尋覓與游走恰似一場探尋自身主體性與歸屬感的“游牧”,只可惜種種努力都歸于徒勞,他們無法從光怪陸離的現代性迷宮中逃逸。在現代性震驚體驗和自我身份認同危機的交互作用下,青年們走向精神的崩潰與分裂。
一、在廢墟中探尋主體性與歸屬感
“鄉土”是中國傳統社會的深層文化結構。以血緣與地緣為紐帶的基層社會將人們緊密地固結在一起,“鄉土”就是他們世世代代的安身立命之所。鄉土性的社會結構與生存方式的背后運行著一套相對應的道德原則與倫理規范,以確保社會的穩定與正常運轉。中國的“熟人社會”區別于西方的“團體格局”,這注定了現代化進程會為中國的社會結構與人際關系帶來更劇烈的震蕩。“90年代以來中國大中小城市的硬件結構與社會纖維都經歷著陣痛性的變遷。在北京、上海、天津、廣州等地,大片民居(胡同,弄堂等)及其相關的社會空間遭到‘拆遷’的命運。取而代之的是高速公路、地鐵車站、購物中心和寫字樓。中小城市乃至大片農村地區也加入了城市化的進程。……這一破壞性極強的建設狂潮帶來了嶄新的城市輪廓線,同時也帶來了城市廢墟,及生存環境和社會關系的異化,從根本上重繪了當今中國社會的精神與物質的地形圖。”正如本雅明所說:“現代城市,其空間形式,不是讓人確立家園感,而是不斷地毀掉家園感,不是讓人的身體和空間發生體驗關系,而是讓人的身體和空間發生錯置關系。”社會結構的改變與城市空間的異化斬斷了物質與精神雙重意義上的鄉土之根,使青年一代成為飄零無著、喪失身份的離鄉者。加之陌生人所組成的現代社會缺乏傳統社會中的親切溫情,周遭皆是冷漠警惕的眼神與無法靠近的靈魂。青年們只能在身體與空間的錯置關系中展開無盡的漫游,神情焦慮、內心激憤地凝視著夢魘般的都市廢土。
就第六代導演的早期影片而言,他們熱衷于冷峻、殘酷的現實主義質感,同時慣用戲仿經典、拼貼挪用、多線敘事等后現代手法。破碎化的影像風格和敘事策略恰可呈現出“現代工業化社會中事物的破碎狀態以及與此相對應的人對事物體驗的破碎狀態”。如婁燁酷愛以晃動鏡頭呈現城市的廢棄建筑與污臟暗角,構建起上海都市景觀的另類想象。處女作《周末情人》中的一開場就是手持攝影機追蹤阿西而拍攝的長鏡頭,時明時暗的光線、狹窄冗長的樓道、悸動不安的背景音樂同時給人以躁動、逼仄與眩暈之感,有別于身處繁華都市景觀中的審美體驗。片中主角搖滾樂手、公司白領、快餐店服務員等身份雖然都具有現代特色,但經常出沒之處都是斑駁、昏暗、潮濕的場所,如張弛的搖滾樂隊常駐在一所廢棄大樓的天臺上。在極具超現實色彩的結尾處,居民樓前停著一輛加長的豪華轎車,而車旁肆意攤置著一大片異常醒目的垃圾,拼貼出一種后現代風格。《危情少女》用夢境與現實的雜糅敘事講述了一個發生在古舊洋房中的恐怖故事,斷壁殘垣和陣陣陰風為影片增添了詭異、衰敗的氛圍。《蘇州河》同樣規避了上海在主流話語和流行影像中的國際化身份,東方明珠、外灘建筑等光鮮奇觀只在偶然的攝入中閃現。“不說謊的攝影機”以不斷變化的角度、景別和迅捷凌厲的剪輯切割了都市空間,撿拾起污濁的河流、殘破的橋梁、拆毀的廠房、艷俗的酒吧等廢墟碎片,紀錄下上海在城市化進程中的另一重“敵托邦”面目。正如婁燁所說:“蘇州河自古以來是一條上海著名的骯臟的河,它構成了另一種涵義上的上海。對我來講,更赤裸,更真實。”
北京,作為與上海交相輝映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未能逃過第六代導演的廢墟美學。張元《北京雜種》和管虎《頭發亂了》中都不乏破舊的居民樓、狹窄的胡同和幽暗的地下室,鏡頭緊追搖滾青年游蕩于這些城市邊緣空間中,苦悶抑郁、漂泊無依的成長體驗與影片營造出的空間質感相吻合,捕捉著現代社會中的瞬間性、變動性與偶然性。張元的《東宮西宮》更是將鏡頭探入城市深處荒蕪的草地、腐臭的池塘、迂回的長廊和齷齪的公廁,建構起隱蔽、壓抑、密不透光的同性戀亞文化空間,映襯出一代都市青年焦灼茫然的生存境遇和貧瘠頹敗的心靈生態。
在互相忌憚、人人自危的都市生活中,漫游者以自我封閉或暴力手段來進行自我保護,同時也在持續不斷的游走中期盼著找到精神的寄托、心靈的歸屬與身份的認同。在血緣之父與精神之父的雙重缺席下,“尋找”成為第六代青春片的深層結構與恒定主題。路學長的《長大成人》中,較周青年長的紀文是一個頑主式的人物,他戀愛、打架、玩音樂的經歷對周青是種青春的啟蒙。但周青逐漸認識到紀文殘暴貪婪的本性,遂將火車司機朱赫來作為自己的精神楷模。朱赫來是保爾柯察金精神的當代化身,是一個傳統意義上的“引路人”形象。周青在后革命的時代氛圍中遙想著堅毅無懼、樂觀昂揚、勇于獻身的革命精神,并賦予它瑰麗的理想主義色彩。在多元意識形態并存、信仰缺失的年代,當王朔已經有意識地顛覆“導范者”敘事模式后,“尋找朱赫來”可以視作漫游者為了歸附傳統所做出的回光返照般的努力。
在《十七歲的單車》中,王小帥所展示的城市空間雖然不像婁燁等人那樣凌亂殘破,但關注點依然是邊緣人的生存空間與青年的漫游軌跡。在狹長的胡同、擁擠的院落或昏暗的出租屋中,由鄉鎮涌入的務工人員和城市底層市民不停游走、碰撞。農村少年小貴的山地車丟失后輾轉被城市少年小堅當作二手車買入,矛盾由此激發。對于快遞員小貴來說,單車是他得以在北京立足的謀生工具,是他融入城市秩序的物質依托和符號象征。因此,丟失單車的他將焦慮與惱怒化作偏執極端的尋找。而對于小堅來說,單車是城市青少年的時尚生活方式,是獲得群體認同的消費符碼。因此,他以青春期的敏感自尊和城市人的優越感捍衛擁有單車的權利。“尋找單車”作為電影表層的動力性敘事線索,將農村少年對物質生存、身份認同的追求,與城市青年對夸飾消費、伙伴認同的追求碰撞在一處。而這背后隱藏的,是城鄉之間經濟、文化、權力的差序格局。
二、在現代性體驗中走向崩潰與分裂
英國文化研究學者斯圖亞特·霍爾認為:“文化身份反映共同的歷史經驗和共有的文化符碼……它總是由記憶、幻想、敘事和神話建構的。文化身份就是認同的時刻,是認同或縫合的不穩定點,而這種認同或縫合是在歷史和文化的話語之內進行的。”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在話語駁雜的社會歷史語境中,青年亞文化雖然沖破了主流意識形態的鉗制與束縛,但內部缺乏一套成熟穩定的文化機制。突如其來的自由反而使青年茫然失措,青年陷入自我身份認同的困惑與危機中。無孔不入的都市文明給都市青年帶來的“震驚”體驗,加劇了他們的成長陣痛。在被抽空成“單向度的人”的過程中,現代人內心的多重維度演化、分裂出不同互相對抗、互相侵吞的人格。分裂幻象的鏡城中滋生了一種扭曲感與分裂感,導致青年走向癲狂和毀滅。
《冬春的日子》和《極度寒冷》是王小帥前期兩部極為風格化、私人化的作品,雖然相比張元、婁燁的作品少了對都市奇觀目眩神迷地呈現,但卻填補出都市青年在商品化浪潮下錯綜復雜的心靈圖式,堪稱精英知識分子與先鋒藝術家的獨白。自我意識的覺醒、自我價值的探究以及孤傲的靈魂如何在環境的重壓下扭曲是這些影片的核心主題。《冬春的日子》中,冬、春夫婦的分道揚鑣象征著精英階層的物質與精神領域存在無法彌合裂痕; 《極度寒冷》中,行為藝術家齊雷的“死亡表演”表達著藝術人士對商業經濟和庸碌世俗的反抗。當都市青年面臨著精神訴求與生存絕境的雙重圍剿,分裂與撕裂的精神之痛、身體之痛開始貫穿于冷冽殘酷的青春影像中。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影像的浮沉記載了他個體成長與精神變遷的歷程,表征了他背后的第六代導演群體對自身精神困境的了悟、掙扎、突圍與回歸的種種努力,更隱喻了時代文化語境的變遷對他們電影產生的強烈影響與制約。”
張揚《昨天》中的互文意味更加強烈,影片以多次出演第六代電影的青年演員賈宏聲的真實經歷為底本,并由賈宏聲本人及其父母出演,還原了其在戒毒過程中的日常生活與精神狀態。《周末情人》中寡言卻暴戾的青年阿西、《極度寒冷》中抑郁偏執的藝術家齊雷、《蘇州河》中不停尋找牡丹的“瘋子”馬達等多重角色在他身上重合疊映,都市空間的壓迫、內在靈魂的撕扯與服用毒品的作用使他行為乖張、精神分裂,最終沒能逃脫影像文本中的死亡讖語。在某種意義上,“賈宏聲”成為了社會文本與影像文本的互動構建起的原型符號,負載著憂郁氣質、搖滾精神、理想主義等多重話語,在都市的異托邦中因拒絕異化而走向滅亡。
與“賈宏聲”這一男性原型形象相對應的,是“魅影姊妹”這一都市女青年分裂者形象。這一概念由海外學者張真提出,“魅影姊妹是過去和當下相復合的人物形象,各自不完整卻又相互重疊。她們表現了發展過程中的不平衡性以及這種單向度的意識形態對人的摧殘,同時也借助多種方式的感官修復過程來確保社會記憶的持久性。”在王全安的《月蝕》中,女主角亞男開片就遭遇了一場車禍,同時心臟病發作,高角度鏡頭將昏迷中的她完整曝露在銀幕上。在與父親的通話中,亞男將自己犯心臟病之前的感覺形容為“像夢一樣”。這些細節都透露出孱弱的都市女性在危機四伏的社會中的不安全感與不真實感。因身體原因,亞男放棄了藝術團的工作,嫁與一位商人。在一次郊游中,她結識了業余攝影師胡小斌,并得知后者認識一位與自己一模一樣的女子佳娘。身陷平淡乏味婚姻生活的亞男逐漸對佳娘產生好奇,渴望接近、了解她。另一部采用“魅影姊妹”這一原型形象的,是婁燁的《蘇州河》。“蘇州河”恰似都市人的心靈暗流,夾帶著外界環境的污濁雜質,流速與走向都充滿著不可知性與不確定性。純真女孩牡丹因男友馬達的背叛投河自盡,民間開始流傳蘇州河中有美人魚出沒的都市傳奇。出于歉意與愛情瘋狂尋找牡丹的馬達遇到了與牡丹長相相同的美美,后者的工作是在酒吧扮演美人魚以招攬顧客。美美與馬達戀愛,并在左腿上貼上牡丹的圖案,告訴他自己就是牡丹。“美人魚”和“牡丹”的意象在兩位女子身上發生重疊。
在以上兩部影片中,無論是亞男、佳娘還是美美、牡丹,都在交錯的時空網絡和不可知的命運中共享著某種神秘莫測、充滿感性的聯系。在支離破碎的都市空間中,亞男、美美的激情與夢想被抽空,在感情中也飽受欺騙與背叛,體驗著一種深入骨髓的失落感與缺失感。在相似的外貌下,亞男覬覦佳娘雖貧窮卻充滿活力的生活,美美覬覦牡丹得到超越生死的忠貞愛情。“尋找佳娘”“尋找牡丹”正是亞男和美美為“尋覓消隱的另一半”、構建完整的自我意識所做出的努力。但現代化廢墟中拼湊不出所謂的“完整”,自我分裂是時空中回旋的宿命。此外,張元的《綠茶》則將“魅影姊妹”的二元構型統一在同一角色身上,將都市女青年的內心隱曲娓娓道來。生長于不幸家庭的童年陰影使女主角分裂出呆板木訥的“吳芳”與風情萬種的“朗朗”雙重身份,在多元自我的內部沖突中過著極具表演色彩的生活。概言之,“魅影姊妹”的人物構型反映出現代都市中的青年女性喪失了主體論意義上完滿、自足、和諧的人格狀態,淪為被多個碎片人格拼貼而成的個體。所謂的“姊妹”,其實是女性成長過程中填補自身匱乏的欲望仿像。
綜上所論,在第六代導演早期的電影作品中,“都市始終是一個大寫的他者,一份真實的恐懼,一個灰暗的身影,在這里,城市的積極性意義幾乎沒有。”從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這些影片中的廢墟社會一如波德萊爾詩中的巴黎,都是在現代文明滋養下開出的“惡之花”,都是身為漫游者的先鋒藝術家為時代寫下的癥候式寓言。第六代通過對廢墟有意味的“凝視”(gaze),構建起一套美學與哲學向度上的批判性話語:都市,作為最具象、最直觀的現代性空間表征,截斷了歷史圖景的完整性與連貫性。它使平穩運行的傳統秩序和凝聚人心的價值觀念倏然間分崩離析,散落成后工業時代的斷壁殘垣。同時,都市空間的結構性邏輯籠罩并操控了個體生活,達成了對現代人主體性的剝奪、本真狀態的遮蔽和心靈家園的摧毀。
仍需一提的是,隨著人生閱歷與藝術實踐的積淀,第六代導演的創作立場、藝術風格和對都市空間的認知與想象也逐漸發生轉變。以管虎為例,處女作《頭發亂了》中雖然流露出女主角葉彤對兒時北京胡同文化的懷念,但當她由南方返回北京后就毫不猶豫地投入青年亞文化的生存法則,在搖滾的節奏中安置青春的孤單與虛無,此片也成為了第六代導演“搖滾青春”“殘酷青春”的代表作。而在2015年上映的《老炮兒》中,管虎已經從1990年代青春文化的急先鋒轉變為胡同文化、傳統規矩的守護者,導演對北京的城市文化記憶也隱約摻雜了王朔構建起的大院文化的影子。該片以代際矛盾、階層矛盾為主線,同時帶出嶄新時代語境中的青年形象和青年問題。同樣處在青春期的叛逆與躁動中,“富二代”的橫行霸道已經與搖滾青年的放蕩不羈有所區別。片尾,不務正業的平民子弟小峰迷途知返,在胡同中開了家名為“聚義堂”的酒吧。很明顯,這象征著當代青年向父輩的歸復,在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之間達成了一種想象式、協商式的平衡。與此相應地,都市空間的審美內涵與文化邏輯也得到了重構。
注釋:
①陳旭光在《當代中國影視文化研究》中設有“電影的青年文化性”一章,他從第六代導演的電影中總結出崇尚感性文化、突出“成長”或“尋找”母題等青年文化性特點,并以從“青春萬歲”到“青春殘酷”再到“青春消費”的路徑概括中國青春電影的發展歷程。(參見陳旭光:《當代中國影視文化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286—298頁。)戴錦華在《霧中風景——中國電影文化(1978—1998)》中“初讀第六代”一章下設有“新人類與青春殘酷物語”一節,提出“他們(第六代)步入影壇的年齡與經歷,決定了他們共同熱衷于表現的是某種成長故事;準確地說,是以不同而相近的方式書寫的‘青春殘酷物語’”。同時也指出“多數第六代的影片的致命傷在于,他們尚無法在創痛中呈現盡洗矯揉造作的青春痛楚,尚無法遏制一種深切的青春自憐。”(戴錦華:《霧中風景——中國電影文化(1978—1998)》,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12-414頁。
②參見[美]張真:《親歷見證:社會轉型期的中國都市電影》,《上海大學學報》2009年第4期。.
③張真:《廢墟上的構建:新都市電影探索》,《山花》2003年第3期。
④汪民安:《身體、空間與后現代性》,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8-129頁。
⑤汪民安主編:《文化研究關鍵詞》,江蘇人民出版社年版2007年版,第324頁。
⑥婁燁訪談錄[EB/OL].時光網,http://i.mtime.com/zhangdaozhdao zheng/blog/797436/,2007-12-13/2016-10-10.
⑦轉引自王先霈,王又平主編:《文學理論批評術語匯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746頁。
⑧陳旭光、王小帥:《從〈冬春的日子〉到〈青紅〉》,《文化的蹤跡影像的激流》,昆侖出版社2003年版,第146頁。
⑨參見張真:《都市幻景、魅影姊妹和新興藝術電影的特征》,《杭州師范大學學報》2010年第4期。
⑩孫紹誼在《尋找消隱的另一半:〈蘇州河〉、〈月蝕〉和中國第六代導演》中指出:“亞男和美美的自我探究使我們想起拉康關于‘鏡像階段’的論述。這一觀念提醒我們,也許兩部影片的中心關注在于亞男和美美意識到自我‘缺乏’后而做的重新找回其“缺失”的另一半的努力。”孫紹誼:《尋找消隱的另一半:〈蘇州河〉、〈月蝕〉和中國第六代導演》,《上海大學學報》2004年第3期。
?趙立諾、龔自強:《走入城市深處的命名——從都市電影到新都市電影的嬗變》,《上海大學學報》2014年第4期。
(作者單位:中國傳媒大學電視學院)
責任編輯 孫 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