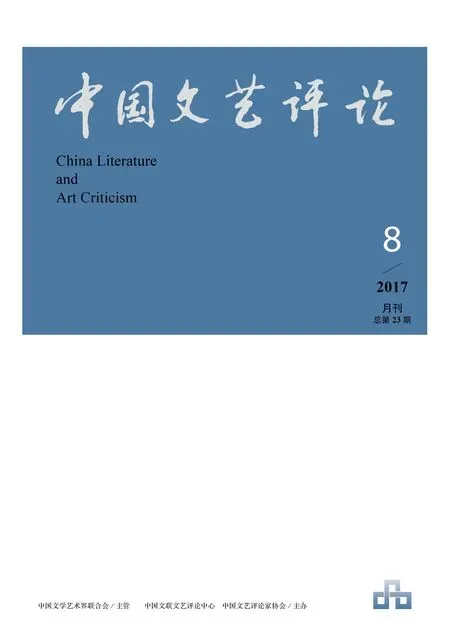文學(xué)批評(píng)的思想家原則
傅道彬
文學(xué)批評(píng)的思想家原則
傅道彬
上個(gè)世紀(jì)90年代以來文學(xué)研究漸漸表現(xiàn)出“學(xué)術(shù)凸顯,理論淡出”的傾向,缺少了問題意識(shí)和思想深度,陷入技術(shù)式的細(xì)碎枝蔓的流弊。本文以楊公驥先生的學(xué)術(shù)思想為切入點(diǎn),主張思想家原則是文學(xué)批評(píng)的第一原則,離開了理論的創(chuàng)新和指導(dǎo),所謂批評(píng)勢(shì)必成為小市民式的“擺龍門陣”。
思想家原則 楊公驥 問題意識(shí) 知識(shí)小販 理論鋒芒
楊公驥先生(1921-1989)是20世紀(jì)中國(guó)學(xué)術(shù)史上值得紀(jì)念的學(xué)者。而比起回憶他的生平,更重要的是紀(jì)念他的學(xué)術(shù),研究他的學(xué)術(shù)貢獻(xiàn),發(fā)揚(yáng)他的學(xué)術(shù)精神。把楊公驥與一般學(xué)者區(qū)分開來的是他文學(xué)批評(píng)的理論功力和他超乎眾人的思想深度。
與時(shí)下一些熱衷于以考據(jù)和資料自我標(biāo)榜的學(xué)者不同,楊公驥似乎毫不掩飾自己對(duì)理論的興趣,以思想家原則為學(xué)術(shù)的第一原則。他認(rèn)為“社會(huì)科學(xué)研究工作者應(yīng)該是追求真理的思想家。這是最高的要求,也是最低的標(biāo)準(zhǔn),否則就會(huì)跨行改業(yè)。因?yàn)椋硕徊牛词棺鲆粋€(gè)小小的思想家,甚至做一個(gè)蹩腳的思想家,也總算是個(gè)思想家,屬于思想界中人。否則,如果從事社會(huì)科學(xué)思想意識(shí)之研究而又不是思想家,那勢(shì)必變成以知識(shí)謀生的知識(shí)小販,或變成以文化牟利的文化巨商,甚至以學(xué)術(shù)趨炎附勢(shì),用學(xué)問佐奸助惡的無恥文人。立于名利場(chǎng),思維不在科學(xué)中,社會(huì)科學(xué)云乎哉?所以,不是思想家,關(guān)系非同小可也!”在楊公驥看來,思想能力是一個(gè)文學(xué)理論研究者的基本能力,文學(xué)批評(píng)必須堅(jiān)持思想家的根本原則。對(duì)于學(xué)術(shù)批評(píng)而言,思想與見識(shí)不是可有可無的,而是最重要的也是起碼的條件,即使小小的蹩腳的思想家,也強(qiáng)于只知引經(jīng)據(jù)典掉書袋子的毫無思想的冬烘先生。楊公驥提倡的思想是獨(dú)立的,自主的,科學(xué)的,毫不依附的,是蘊(yùn)藏于客觀事物中的深刻規(guī)律,是從歷史出發(fā)的實(shí)事求是的科學(xué)精神,也是毫不依傍的獨(dú)立不移的人格風(fēng)范。思想是學(xué)術(shù)的靈魂,是獨(dú)立人格的基礎(chǔ)。在學(xué)術(shù)界功利主義傾向越來越濃的今天,重溫楊先生的論述,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對(duì)一些缺少思想意義缺少問題意識(shí)的細(xì)瑣枝蔓的考證,楊公驥表現(xiàn)出一絲不屑,有一絲冷幽默。他在《從牛頓的蘋果、瓦特的水壺談到“純學(xué)術(shù)”的考證學(xué)》(《文史知識(shí)》1985年第5期)一文中,辛辣地嘲諷了那些脫離問題意識(shí)、沒有思想深度而“為考據(jù)而考據(jù)的”所謂創(chuàng)見、所謂發(fā)明。據(jù)說一個(gè)蘋果落地而引發(fā)了牛頓發(fā)現(xiàn)萬有引力定律的靈感,爐子上水壺沸騰的現(xiàn)象啟發(fā)了瓦特發(fā)明蒸汽機(jī)的思路,而有些學(xué)者不去研究萬有引力定律而熱衷于考據(jù)那個(gè)落地蘋果是紅蘋果還是青蘋果,不去思考蒸汽機(jī)的原理而耐心的尋找材料證明那個(gè)水壺是銅制的還是錫制的。按照某些學(xué)問家的考證,拿破侖身上有塊牛皮頑癬,致使其在新婚夫人瑪麗·路易莎面前自慚形穢,為了證明自己,自卑轉(zhuǎn)為自大,他才有了振長(zhǎng)策而御宇內(nèi)征服天下的壯舉;而巴爾扎克則經(jīng)營(yíng)不善,又有賭博成癖,致使其債臺(tái)高筑,為還賭債而躲進(jìn)巴黎16區(qū)的老建筑里拼命進(jìn)行《人間喜劇》的創(chuàng)作。楊公驥寫道,沿用這樣的方法,會(huì)推導(dǎo)出拿破侖肚皮上的癬疥小疾,決定了世界歷史的大格局,巴爾扎克的賭債推動(dòng)了法國(guó)文學(xué)的歷史變化。由此而來,所謂考證成了獵奇,所謂研究成了小市民擺“龍門陣”。因此楊公驥特別強(qiáng)調(diào)學(xué)術(shù)研究的理論重要性,以為“文學(xué)和其他任何意識(shí)形態(tài)一樣,沒有自己獨(dú)立的歷史,它是被社會(huì)的物質(zhì)生產(chǎn)和社會(huì)生活所派生。……只有通過對(duì)這個(gè)時(shí)代的社會(huì)實(shí)踐(歷史)的全面研究,才能對(duì)這一時(shí)代的文學(xué)作深入探討,才能逐漸得出理性認(rèn)識(shí)”。從文學(xué)發(fā)展的歷史事實(shí)出發(fā),生發(fā)出對(duì)一個(gè)民族一個(gè)時(shí)代文學(xué)的理性認(rèn)識(shí),是楊公驥學(xué)術(shù)研究的努力方向,他的學(xué)術(shù)既不是今文經(jīng)學(xué)的微言大義,也不是乾嘉學(xué)派的單純考據(jù),他的學(xué)術(shù)眼光是具有現(xiàn)代進(jìn)步意義的。
思想家原則是楊公驥堅(jiān)持的學(xué)術(shù)研究原則,也是他學(xué)術(shù)研究最有魅力的地方。學(xué)術(shù)研究中人們常犯的一個(gè)錯(cuò)誤是,偏愛自己的研究對(duì)象,夸大研究對(duì)象的歷史作用和意義。以屈原研究為例,歷史上屈原確實(shí)曾支持過聯(lián)齊抗秦的思想,以對(duì)付張儀之流秦楚和親的主張。本來楚國(guó)究竟是實(shí)行“合縱”還是“聯(lián)橫”的政治路線,是有許多復(fù)雜的歷史原因的,絕不是僅僅憑張儀的三寸不爛之舌所能左右的,也不僅僅由于楚懷王不聽信屈原的勸告那樣簡(jiǎn)單。但是在一些學(xué)者研究中,由于對(duì)屈原的偏愛有意無意地夸大了屈原的政治地位,夸大了屈原所能發(fā)揮的歷史作用,卻得出了幾近荒唐的歷史結(jié)論。對(duì)此楊先生不無揶揄地寫道:“楚懷王如果是聰明人,如果能聽信屈原的話,殺掉張儀,采取聯(lián)齊反秦的政策,同時(shí)不入武關(guān)與秦會(huì)盟,那么,楚不僅不會(huì)滅亡,甚至能滅秦和其他五國(guó),完成統(tǒng)一大業(yè)。這就是說,如果楚懷王肯采納屈原的意見,那么中國(guó)歷史將會(huì)走另一條道路,《史記》將出現(xiàn)一篇《楚本紀(jì)》”,這樣,一個(gè)重大的歷史變化就不取決于政治、軍事、經(jīng)濟(jì)的綜合歷史動(dòng)因,而取決于幾個(gè)謀臣、幾個(gè)大夫的騙術(shù)伎倆和口舌之利,按照這樣的邏輯推演,“屈原之所以失敗,歷史發(fā)展之所以‘不幸’,是由于騙子張儀收買了財(cái)迷上官大夫作內(nèi)奸,拉攏了妒婦鄭袖作幫手,共同欺騙了傻瓜楚懷王。于是乎,人們?cè)谄墼p、賄賂、嫉妒、愚蠢的支配下相成相因地創(chuàng)造了歷史,而《史記》中便出現(xiàn)了《秦本紀(jì)》。”楊先生以深刻的理論目光審視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的歷史變化,看到了隱藏于現(xiàn)象背后的歷史成因,不論是秦王的野心,還是楚王的妄想,不論是張儀的詭計(jì),還是屈原的信念,都不能成為決定秦楚興亡這一歷史“事變的最終原因”,“秦的新興、楚的衰亡并不是楚懷王性格上的弱點(diǎn)造成的;恰恰相反,正是基于秦的新經(jīng)濟(jì)制度的必然興起和楚的舊經(jīng)濟(jì)制度的必然滅亡這一歷史規(guī)律,楚懷王才不能‘福至心靈’,才讓自己的愚蠢加速了自己的失敗。顯然,戰(zhàn)國(guó)時(shí)代諸國(guó)的興亡并不是侯王的賢愚決定的。”楊先生的文學(xué)史研究固然有著豐厚的文獻(xiàn)基礎(chǔ)支撐,而奠定其在學(xué)術(shù)史上重要意義的還是他理論的犀利和思想的洞徹。
楊公驥是深受馬克思主義理論影響的學(xué)者,但是他接受馬克思主義理論不是出于一時(shí)的政治依附,而是源于深刻的理論信仰。因此他對(duì)馬克思主義不是尋章摘句的泛泛引用來裝點(diǎn)門面,也不是將馬克思主義的命題作為大棒胡亂揮舞借以嚇人,而是從科學(xué)和真理的角度深入研究與探索。從17歲讀《資本論》開始,楊公驥潛心研究馬克思的經(jīng)典著作,從而獲得了思想和方法論上的啟示。在他的著作中,看到的不是馬克思的個(gè)別語錄的征引,而是精神實(shí)質(zhì)和思想方法的圓熟的運(yùn)用。《考論古代黃河流域東北亞地區(qū)居民“冬窟夏廬”的生活方式及風(fēng)俗——民族民俗學(xué)學(xué)習(xí)札記之一》,作者依據(jù)民俗、民族史料發(fā)現(xiàn)社會(huì)歷史演變規(guī)律的學(xué)術(shù)方法,從早周時(shí)期“陶復(fù)陶穴”的建筑格局起筆,考察東北亞地區(qū)的生活習(xí)俗,進(jìn)而考證原始居民“冬窟夏廬”的普遍居住方式,從而揭示出中原文化與東北文化的歷史聯(lián)系。此文體現(xiàn)著社會(huì)存在決定社會(huì)意識(shí)這一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在學(xué)術(shù)方法上也借鑒了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guó)家的起源》論證模式,但是作者卻沒有一處生硬地引用馬克思、恩格斯的語錄,他對(duì)馬克思主義理論側(cè)重是對(duì)原理與精神的理解。
我國(guó)上古詩歌以四言二拍子結(jié)構(gòu)形式為主體,例如“斷竹/續(xù)竹,飛土/逐宍”、“伐木/丁丁,鳥鳴/嚶嚶”等,大都是上古詩歌“二拍子”結(jié)構(gòu)的經(jīng)典形式。但是人們很少將其與勞動(dòng)的節(jié)奏聯(lián)系起來,楊先生卻目光獨(dú)具,認(rèn)為詩歌的節(jié)奏與原始勞動(dòng)的韻律是一致的。勞動(dòng)動(dòng)作一般是一往一來兩個(gè)行動(dòng)組成。以打制石器為例,舉錘時(shí)用力輕而無聲,下去時(shí)力重而有聲響;音響發(fā)生于第二行動(dòng)之尾,也就是勞動(dòng)動(dòng)作節(jié)奏的二拍子之尾,所以勞動(dòng)詩大多是二節(jié)拍(四言)之尾押韻。在尋常的文學(xué)形式中,尋找出樸素勞動(dòng)生活的深刻影響。比起一般文學(xué)史“勞動(dòng)創(chuàng)造文學(xué)”的泛泛論述,楊先生的論述更根植于歷史根植于材料也根植于深厚的理論修養(yǎng),沒有良好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訓(xùn)練是很難有如此富有創(chuàng)造的學(xué)術(shù)見解的。
思想與考據(jù)并不矛盾,過人的見識(shí),應(yīng)當(dāng)依據(jù)堅(jiān)實(shí)的歷史事實(shí)和文獻(xiàn)基礎(chǔ)。楊公驥寫的許多學(xué)術(shù)論文都是經(jīng)典的考據(jù)文章,而他的考據(jù),也是思想家的考據(jù),不漫無邊際,不拖泥帶水,有著事實(shí)清楚、邏輯謹(jǐn)嚴(yán)、辯駁有力、簡(jiǎn)潔通脫的思想家考據(jù)風(fēng)格。一篇《〈商頌〉考》不足15000字,卻將《商頌》創(chuàng)作時(shí)代這樣一個(gè)聚訟紛紜的學(xué)術(shù)問題舉重若輕地解決了,成為一篇經(jīng)典的考據(jù)論文。文章首先正面列出《商頌》或作于殷商、或作于春秋宋國(guó)兩種不同意見,繼而用翔實(shí)的史料論證《商頌》不是宋襄公時(shí)期的作品,本來文章至此似乎已經(jīng)完成,而作者卻筆鋒一轉(zhuǎn),波瀾驟起,列出近代關(guān)于《商頌》是宋詩的20種意見,分八個(gè)部分,一一予以批駁,顯示出他的學(xué)術(shù)從容與自信,而最后以四種意見總結(jié)全篇,整個(gè)文章宛如一篇《商頌》學(xué)術(shù)研究史,敘述則層次清晰,資料翔實(shí),論辯則邏輯謹(jǐn)嚴(yán),要言不煩,處處閃耀著思想的靈光,成為一篇足以啟示后學(xué)的經(jīng)典的學(xué)術(shù)論文。
理論不是萬能的,思想家的危險(xiǎn)是很容易陷入學(xué)術(shù)的空洞和荒疏。楊先生早就意識(shí)到理論是一種方法,卻不是出發(fā)點(diǎn)。真正的學(xué)術(shù)精神應(yīng)該是建立在知識(shí)論證基礎(chǔ)上的,思想理論應(yīng)該是從文獻(xiàn)出發(fā)從歷史出發(fā),而不是從簡(jiǎn)單的理論概念和思想模式出發(fā)。楊先生也強(qiáng)調(diào)巨細(xì)無遺地占有第一手材料,對(duì)歷史資料要鑒定甄別。但是傳統(tǒng)的學(xué)術(shù)研究到此為止,不再前進(jìn)。而楊先生在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下,強(qiáng)調(diào)不僅僅是占有材料,甄別材料,而是在歷史現(xiàn)象中尋找聯(lián)系,尋找問題,這正是楊先生與舊學(xué)先生理論上不同的地方。他在《從牛頓的蘋果、瓦特的水壺談到“純學(xué)術(shù)”的考證學(xué)》中說:“重要的不是停止在對(duì)材料的整理和考證上,而是要在旁多雜亂的材料之間發(fā)現(xiàn)其客觀的內(nèi)在聯(lián)系,從聯(lián)系中發(fā)現(xiàn)問題,研究問題,解決問題。所謂從材料間的客觀內(nèi)在聯(lián)系中研究問題,意思就是不以自己的主觀假設(shè)作為聯(lián)系的針線,不把主觀臆斷當(dāng)成擺布材料的格局。”
真正的思想家本身應(yīng)該是學(xué)問家。《中國(guó)文學(xué)》(第一分冊(cè))體現(xiàn)著楊公驥在學(xué)術(shù)上理論性和知識(shí)性統(tǒng)一、思想家與學(xué)問家并重的風(fēng)格。以《中國(guó)原始文學(xué)》一章為例,這一章的正文部分三萬六千多字,而注釋部分則近30000字,注釋與正文這種比例在其他文學(xué)史著作中是很少見的。這是楊公驥一種獨(dú)特的學(xué)術(shù)表現(xiàn)風(fēng)格,一方面是觀點(diǎn)的流暢表達(dá),一方面是考證的翔實(shí)清晰,正文里他縱橫議論,為了不因過多引用資料而影響思想闡發(fā)的流暢,他將考據(jù)文字移至注釋中,使議論建立在科學(xué)的基礎(chǔ)上,注釋是正文的補(bǔ)充,而又自成體系,形成了《中國(guó)文學(xué)》正文與引文兩條平行而各具特色的敘述線索。
楊公驥主張的學(xué)術(shù)研究的思想家原則,對(duì)我們是有啟示意義的。1990年代以來,曾經(jīng)繁華一時(shí)的理論研究漸漸冷落,思想的鋒芒漸漸收斂,學(xué)術(shù)研究發(fā)生重要的方向性改變。從強(qiáng)烈的現(xiàn)實(shí)的使命關(guān)切,逐漸轉(zhuǎn)向歷史的傳統(tǒng)考察;以乾嘉學(xué)術(shù)為代表的樸學(xué)方法,被重新詮釋解讀;以計(jì)算機(jī)為代表的科技手段廣泛介入學(xué)術(shù)研究領(lǐng)域,使得材料搜集變得簡(jiǎn)單容易;學(xué)術(shù)更強(qiáng)調(diào)技術(shù)的規(guī)范,論證的嚴(yán)謹(jǐn)和設(shè)計(jì)路線的準(zhǔn)確清晰。這種轉(zhuǎn)向?qū)τ诩m正20世紀(jì)80年代理論的躁進(jìn),具有一定的內(nèi)在合理性,使得學(xué)術(shù)風(fēng)氣朝著沉潛務(wù)實(shí)的方向發(fā)展,但這種學(xué)術(shù)糾偏絕不能成為淡化理論、淡化思想的理由。許多場(chǎng)合一些人把學(xué)術(shù)的理論引導(dǎo)與思想闡釋描寫的相當(dāng)不堪,一提到理論一提及思想,仿佛就脫離了知識(shí)脫離了考據(jù),意味著空疏意味著淺薄。一些學(xué)者熱衷于所謂資料收集,一味炫學(xué),卻忽視了對(duì)史料的思想與理論辨識(shí)。無論何種文章,必曰考曰證,好像只有如此,才是學(xué)術(shù),才是科學(xué)。其實(shí)真正的學(xué)術(shù)失范,不僅僅是技術(shù)性的,更是思想性的理論性的。古人以見識(shí)為學(xué)術(shù)的第一要義,缺少思想性的學(xué)術(shù)研究是根本性的失范,思想蒼白的學(xué)術(shù)是不可能有影響有力量的。
技術(shù)往往會(huì)偽裝成學(xué)問,在電子技術(shù)條件下輕易實(shí)現(xiàn)的資料羅列,并不是科學(xué)意義上的引證豐富,甚至不屬于真正的閱讀。一切材料都應(yīng)該是經(jīng)過思想過濾和理論消化的,否則那只能是一堆雜亂無章的堆積物而已,用楊公驥的話說就是:“徒然的博學(xué)而形不成真識(shí)卓見,就會(huì)變成‘兩足書櫥’,或變成死背硬記囤積材料的‘知識(shí)商’。”。
現(xiàn)代學(xué)術(shù)批評(píng)應(yīng)當(dāng)是有思想力量的,是應(yīng)當(dāng)具有批判精神的。面對(duì)豐富的歷史資料,楊公驥始終保持一種警惕,以銳利的思想眼光理性地看待自己的研究對(duì)象,而不是陷入無盡的資料羅織中失去判斷力而不能自拔。他說:“文學(xué)遺產(chǎn),只能是再生產(chǎn)的思想原料,是后人的認(rèn)識(shí)對(duì)象和審美對(duì)象,而不是直接的‘消費(fèi)對(duì)象’。”無論我們?cè)鯓訜釔蹅鹘y(tǒng),懷戀古代,都應(yīng)清醒地認(rèn)識(shí)到,回憶過去卻不能回到過去,一切歷史研究都是從現(xiàn)實(shí)土壤出發(fā)的,我們只能以現(xiàn)代精神、現(xiàn)代目光審視歷史、審視一切古代歷史遺產(chǎn)。目前熱鬧的國(guó)學(xué)研究中,有種現(xiàn)象值得注意,即對(duì)傳統(tǒng)文化缺少反思缺少批判,而一味地片面地強(qiáng)調(diào)繼承強(qiáng)調(diào)吸收,這相對(duì)于“五四”精神,其實(shí)是歷史的退步。未經(jīng)批判和反思的歷史,正如未經(jīng)過濾消毒的自來水一樣是不能直接飲用的,因此應(yīng)該倡導(dǎo)批判的歷史與批判的國(guó)學(xué)。缺少理性反思的學(xué)術(shù)研究,常常表現(xiàn)出某種精神的貧血和四肢無力的癥狀,因此,在一段思想淡出的歷程之后,我們還得重新呼喚文學(xué)批評(píng)尤其是古典文學(xué)研究的理論建設(shè)。
“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楊公驥等前賢們仿佛是匆匆趕路的早行者,在前面為我們留下了探索的足跡,應(yīng)該有更多的后來人追隨他們的腳步。
傅道彬:首都師范大學(xué)文學(xué)院特聘教授
(責(zé)任編輯:吳江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