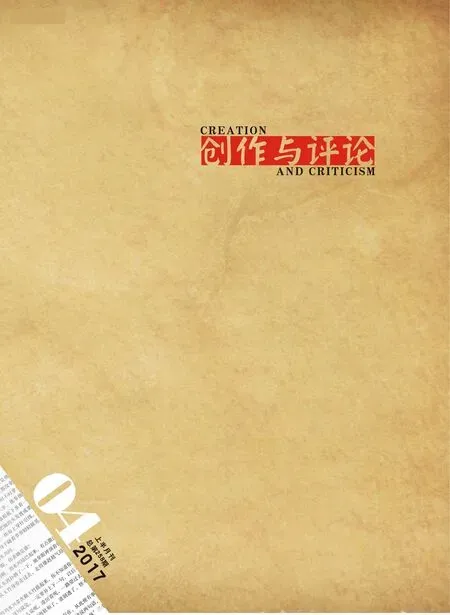生生不息(外三篇)
○管 弦
生生不息(外三篇)
○管 弦
握住那紫色芬芳
紫蘇,詩意的名字,神秘的色彩,低調而圓融,息息相扣,仿佛暮春斜陽下飄然而立的長發女子,空著盈盈玉手,等待有心之人,柔柔來握。
那么,就讓我們輕輕握住這一脈紫色的花草之手,記住她的安靜和從容,一如記住她被用作蒸魚、煮鱔、烹蝦蟹、燉老鴨等時候做佐菜的模樣兒,她用妙曼的身姿,辛溫的性味,配合著主菜,飄出溫柔清香,展示融合之美。
據說,最先發現紫蘇功效的是東漢末年醫學家華佗,他是從小水獺身上琢磨出來的
那年夏天,華佗帶著徒弟在河岸上采藥。忽然聽見河灣里嘩嘩啦啦地響,河里掀起一層層波浪。華佗仔細一看,原來是一只小水獺逮住了一條大魚。小水獺把大魚叼到岸邊,嚼食了好一陣,把大魚連鱗帶骨通通吞進肚里。一下子,它的肚皮撐得像鼓一樣了。接著,小水獺就顯得不安起來,它一會兒在水邊爬,一會兒往岸上竄,一會兒一動不動,一會兒翻滾折騰。看到這兒,華佗想,小水獺一定是吃得太多,撐得難受了。沒多久,華佗看見小水獺爬到岸的另一邊,一塊長滿茂盛紫色草兒的地方。小水獺吃了些紫色草葉兒,又爬了幾圈,就跳跳蹦蹦地回到了河邊,潛入河中,舒坦自如地游走了。
華佗明白了,是那蓬蓬勃勃的紫色草兒幫了小水獺呢。魚屬涼性,小水獺又吃得太多,傷胃傷氣,胃不和,氣不順,則身不安。紫色草兒屬溫性,能行氣寬中、益脾宣肺,治療胸腹脹滿等癥,故小水獺吃過之后就感覺舒服了。由于這草兒呈紫色,吃到腹中又很舒服,華佗就給她取名“紫舒”。華佗把紫舒加工制成丸劑、散劑,給人治病。在實踐中,華佗發現紫舒還可以治療感冒風寒、咳嗽氣喘,能解魚蟹毒。后來,大概是音近的緣故,人們又把“紫舒”喚作“紫蘇”了。
這樣的傳說讓我們看到了華佗的認真負責和細致敏銳,以及紫蘇的天然之美和天生之用。紫蘇的品質,以其葉子的正面和反面都為紫色,才是最佳。一如北宋藥物學家蘇頌所言:“以背面皆紫者佳。”明代醫藥學家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記載紫蘇時,也特別說到紫蘇的顏色,曰“其味辛,入氣分;其色紫,入血分。”故而,紫蘇能夠“解肌發表,散風寒,行氣寬中,消痰利肺,和血溫中止痛。定喘安胎,解魚蟹毒。”都旨在調理氣血。氣血和順,對于人體是非常重要的,紫蘇的安胎作用就充分體現了這一點,將紫蘇與橘皮、砂仁一同煎煮,可治妊娠嘔吐、胎動不安。
平和與沉著,是紫蘇的性情。經過烹、煮、炒、煎,紫蘇都紫色不改。即便是枯萎了,也仍然是那令人過目不忘的紫色。紫蘇的莖和葉結合得比較緊密,若是用火花輕輕煨一下紫蘇的根部,再將她陰干,那么那紫色的葉子更是難以落下了,因此,紫蘇的保存期相對較長。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就說過:“五六月連根采收,以火煨其根,陰干則經久葉不落。”
因為有著這般令人心怡的顏色,紫蘇的汁液就成了天然的色素原料。將紫蘇洗凈榨汁,滴入面食之中,可做成紫色饅頭、紫色面包、紫色餃子等風格各異的糕點。將這樣的紫色糕點擺上桌,實在是看著美、吃著香,真正綠色、安全而環保的食品啊。
將紫蘇葉洗凈,加入適量白砂糖或蜂蜜,煮成茶水喝,也是能夠理氣潤心肺的。據《本草綱目》記載,皇帝宋仁宗曾命翰林院評定湯飲,結果是紫蘇熟水第一。熟水,飲品也。也就是說,紫蘇茶在宋代的飲品中曾獲最高殊榮。當然,凡事不可過分,過量飲用,多致滑泄,滑泄又稱滑精,指夜間無夢而遺,甚至清醒時精液自動滑出的病癥,滑精是遺精的一種,是遺精發展到了較重的階段。尤其是脾胃寒人,更要注意。宋代藥物學家寇宗奭就說過:“今人朝暮飲紫蘇湯,甚無益。醫家謂芳草致豪貴之疾者,此有一焉。若脾胃寒人,多致滑泄,往往不覺。”因此,適量喝一喝紫蘇茶,輔以健脾暖胃之類溫補的小點心,才是甚好。
看那紫蘇,真像現代詩人徐志摩的那句詩“最是那一低頭的溫柔”,溫婉如水。有時,摘把紫蘇,不為食用,只是放在廚房中,那淡淡的香,也會在廚房里飄起來。溫潤的時光,便在這若有若無的淡香之中,緩緩蘊散開來。
生生不息
我總是記得和小疆一起吃生姜的日子。
小疆經常喚我一起上學、放學。在放學回家的路上,我們一邊走一邊吃點小零食。那時候物資并不豐富,大人們喜歡做一個酸水壇子,放點新鮮的生姜、蘿卜、黃瓜、刀豆、豆角、辣椒等等,泡上一段時間,再拿出來食用。有時作佐菜,在煮魚、炒雞、開湯等時候適量地放一點;有時作素菜,直接切碎,爆炒或涼拌。我們就經常把她們從壇中取出,包在小塑料袋子里,變成課余的零食。
那樣的時光,清純而絢美。我和小疆交換著這樣的零食。我們都喜歡吃生姜。用小手兒捏著生姜片兒,順著生姜的紋路,一絲一絲咬下來,含在嘴里,輕輕地吮吸,緩緩地磨碎。偶爾,兩個小女孩兒相視一笑。日子,就在那溫暖生動的味道里,靜美芳華。
生姜性味辛溫,有的人吃了她會出現熱癥,略有咽喉疼痛等癥狀。我和小疆卻沒有因為吃她而有任何的不適。可見,我們與生姜是相融和諧的。人和食物相融,便能體健身安,毒邪不侵。在那一種和諧中,食物是越發清美的,人,也越發舒暢。
據說,“嘗百草、創醫學”的神農氏也得益于生姜的排毒止痛功效。“生姜”還是他發現并命名的呢。某日,神農氏在山上采藥,誤食了一種毒蘑菇,頭暈目眩,肚子疼得像刀割一樣,吃什么藥也不止痛。很快,他暈倒在一棵樹下。不久,他卻奇跡般地慢慢蘇醒過來。他發現自己躺倒的地方有一叢尖尖葉子的青草兒,香氣濃濃的。他又細細地聞了聞,感覺身體又好了些。神農氏明白了,是這青草兒的氣味使自己蘇醒過來的。于是,他又順手拔了一兜,把青草兒的根塊也放進嘴里嚼,那味道香辣而清涼。過了一會兒,他泄瀉了一次,身體就全好了。他想,這種青草兒真是作用神奇、能夠起死回生啊,要給它取個好名字。想到自己姓姜,神農氏就把這尖葉青草兒取名為“生姜”。
這樣的傳說,讓我們進一步感受到了生姜的蓬勃生氣。生姜,不僅自己生生不息,還能用她那生動靈巧的手,拂去陰郁疼痛,讓人們身心明凈,生氣勃勃。
除了作菜和零食,生姜的用途還有很多。偶感風寒時,用生姜熬水喝;脾胃虛寒時,將生姜與紅棗加紅糖同煮吃下;寒氣瘀積時,把生姜與芍藥一同煎水喝;嘔吐氣逆時,直接嚼食生姜片或飲用生姜汁。夏天,更是可以多吃點生姜,益肺防暑。元代醫學家李杲說:“蓋夏月火旺,宜汗散之,故食姜不禁。”可見,“冬吃蘿卜夏吃姜”的說法也是有道理的。
清代醫學家吳鞠通還經常將一塊曬干的生姜用小絹袋盛裝佩帶身上,稱為佩姜,用來辟瘟疫邪氣。據傳他還使用佩姜治病呢。那天,陽光明媚。吳鞠通去郊外采藥,看見一位村婦突然昏倒在地,面色蒼白。她的丈夫在一旁,急得頓足捶胸。吳鞠通連忙過去察看并詢問病情,得知村婦已經腹瀉幾天了,是日因家中有事強撐著出門,就出現了這個狀況。吳鞠通診其脈舌,發現村婦是寒濕泄瀉,又逢日曬導致暈厥虛脫、四肢不溫。吳鞠通便取下自己帶著的佩姜,囑咐村婦的丈夫趕快用姜煎水給村婦喝。村婦的丈夫連忙照做。村婦服用姜湯后四肢漸轉溫暖,目睜神復。
所以,真如北宋政治家王安石所說,“姜能疆御百邪”。
看那生姜,微微的黃中裹著微微的白,“如列指狀”,還噙著一點兒似紅還紫的尖兒,真像宋代詩人劉子暈在《詠姜詩》中吟詠的一樣,那一份細嫩剔透,是堪比美好女子的纖纖玉指的。“新芽肌理細,映日瑩如空。恰似勻妝指,柔尖帶淺紅。”多么相宜啊。
一團明亮的火焰
大蒜,真像一團明亮的火焰。那厚厚圓圓的蒜頭子,像敦厚的在底部支撐火勢的火團兒;那微微長出的蒜苗尖,像微閃的火苗兒;而那蒜葉,就像火苗向上飄忽的招展的尾部了。大蒜,也仿佛可以生出輕煙,裊裊飛向遠方。
這樣有著火般象形的大蒜,那品性里,也有著火一樣的熱烈、果敢和堅強。她味辛性熱,可以理胃溫中、消谷下氣、消霍亂、治蠱毒、除心煩痛、除邪痹毒氣。她不僅可以內服,還可以外用。例如,有溫病頭痛的,可以用鐵杵將大蒜搗成汁液服用;有積年心痛的,可以用濃醋煮大蒜食用;被蜈蚣蛇蝎螫到的,可以將大蒜搗成汁液口服,并把和著汁液的大蒜末涂抹于患處;小兒患上白禿癥導致頭上有團團白色的,可以把大蒜切開,用蒜的切口反復揩擦患處等等。
大蒜的強大主要是她具有奇強的抗菌、消炎、排毒作用,是目前發現的天然植物中抗菌作用最強的一種,其中所含的大蒜素和硫化合物對多種致病菌如葡萄球菌、鏈球菌、傷寒、桿菌、白喉、痢疾、真菌、霍亂弧菌、病毒與原蟲等等,均有明顯的抑制或殺滅作用。大蒜還可防止心腦血管中的脂肪沉積,降低膽固醇、血液粘稠度和血糖水平,在每日都吃點生蒜的地區,因心腦血管疾病死亡的發生率明顯低于無食用生蒜習慣的地區。大蒜中的微量元素硒,通過參與血液的有氧代謝,還可以清除毒素,達到保護肝臟的目的。
大蒜的強大很早就展示出來了。傳說在三國時期,蜀漢丞相諸葛亮為征服南蠻,率百萬大軍南征,擒拿孟獲。豈料孟獲也非等閑之輩,他暗施毒計,把諸葛亮所率軍馬誘至禿龍洞。此地山嶺險峻,道路狹窄,常有毒蛇出沒,更有瘴氣彌漫。蜀兵中計進入此地后,很快就染上了瘟病,全軍面臨不戰自潰的危險。諸葛亮情知不妙,忍不住聲淚俱下:“吾受先帝之托,興復漢室,大業未成,卻臨大難,何以報答先帝之恩?”這時,一位白發老翁扶杖迎面而來,說有解救良方。諸葛亮連忙叩拜,以求解救之計。白發老翁說:“此去正西數里,有一隱士號‘萬安隱者’,其草庵前一仙草名‘韭葉蕓香’,口含一葉,則瘴氣不染,嚼碎服下,則瘴氣得除。”諸葛亮拜謝,依言而行。果然,沒有染病的士兵不再染病,染病的士兵疾病消除。諸葛亮率平安之師征服了南蠻。凱旋回朝后,他求教于一老郎中,才得知韭葉蕓香就是家喻戶曉的百合科多年生草本植物大蒜。
“韭葉蕓香”,水一般的名字,讓大蒜在剛烈之外,更多了幾分俠骨柔情。她是烹調美味佳肴的調味品,也是上好的營養品。有研究證明,大蒜的營養價值甚至超過了人參,她含有200多種有益于身體健康的物質,如蛋白質、維生素E、維生素C以及鈣、鐵、硒等微量元素。
我很喜歡吃大蒜。除了讓她成為烹魚炒肉的調味佳品,還用她來做菜。把她的嫩葉,和藠頭一塊兒切成絲,與剁碎的紅辣椒和蕪荽攪拌在一起,澆上一點鹽汁或麻油,一道紅紅火火、一清二白的涼拌菜就形成了,誘人而開胃。用大蒜來做預防疾病,更是可以隨時使用。比如,夏日里在公共游泳池中游泳歸來,可以剝幾瓣大蒜,切成蒜粒,讓她在空氣中暴露一陣,再生吃。在公共游泳池里,難免不會與身體有疾病的人接觸,或吞入池中的不潔之水,而生吃大蒜就可以防治由此而產生的疾病,增強人體免疫力。
當然,吃大蒜總是會讓嘴里有異味,哪怕按照常規祛除異味的方法諸如嚼點花生米或者泡過的茶葉,也不能徹底消除異味。所以,我一般只在晚餐時吃大蒜,吃過之后漱口,不再外出,以免讓人聞到異味。只是,有時也防不勝防。有天晚上,剛剛美美地享用完大蒜,突然有同學相約,不便推辭。我只好反復漱口外出。見到同學,盡量同她保持距離,擔心萬一有異味讓她聞到了,還很不好意思地說,我吃了大蒜呢。同學笑了,露出寬寬大大的牙齒,說,沒關系,我也吃了大蒜,我們以毒攻毒吧。
是的,吃了大蒜的人,只覺得滿口奇香,是聞不到大蒜的異味的。這樣一團強大的火焰,早就把什么異味都燒得無形了。
青青韭菜
韭菜很像草兒,青青綠綠,生生不息。
古人對于韭菜,是非常尊重的。《詩經·豳風·七月》說“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那初春二月里早早來行祭禮,獻上的是羔羊和韭菜。
“四之日”是初春二月的意思,的確,韭菜是春天的好。“春韭貴于肉,初香醉食客”,秋冬的韭菜次之,夏季的最差,“春食則香,夏食則臭”。春天的韭菜品質最佳,蛋白質、脂肪、糖、鈣、胡蘿卜素、維生素C等物質的含量最為豐富,超過許多莖葉和瓜茄類蔬菜,堪稱蔬園中的“綠色黃金”。韭菜作蔬,歷史悠久,《禮記》中就有“庶人春薦韭以卵”的記載,說明韭菜炒雞蛋早在兩千年以前即為大眾喜愛的食物。
現在有很多人食用韭菜時,比較關注她的壯陽功能。尤其是男士,在餐桌上面對韭菜時,表現可謂可圈可點,有的平靜,有的小心,有的大方。
平靜男士,也許是懵懂不知,也許是大智若愚,想吃就吃,不想吃就不吃,面不改色,心仍在跳,沒有過多言語。這算是佳境。
小心男士,似乎很詭秘,心中是很想吃的,卻又期期然不敢貿然下筷,臉上似笑非笑著,唯恐別人認為自己不行,好像有著不可告人的秘密。
的確,韭菜又名起陽草,能溫陽補腎,散血化瘀,是治療腎陽虛衰性功能低下的常用藥物,主治腰膝酸軟、陽痿早泄、小便頻數等。只是,沒必要為了所謂面子,就不吃韭菜的,要知道,功能障礙如同感冒發燒一樣,只是普通疾病,是可以治療痊愈的。不過,若是因為違背道德倫理和法律法規而染疾的,就另當別論了,那樣有可能牽涉到某些心因性疾病,那不是韭菜可以治愈的。其實,哪怕功能健全,適當吃些韭菜,也是能夠提高免疫能力,有益健康的。因為韭菜性溫,能溫中開胃、養肝益脾、行氣活血。
而小心男士卻依然猶疑并徘徊。
大方男士呢,就頗顯豪爽,拾筷端杯,做出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樣子,喊道,來來,吃吃,吃了對我們男士身體好。同時,還轉過頭對在場的女士說,你們女士就不要吃了,這是我們男人吃的。
呵,性別差異,那是沒有的。只要沒有眼疾,沒有瘡癢腫毒,沒有潮熱盜汗、五心煩熱、夜熱早涼、口燥咽干等陰虛內熱癥狀,不是兩顴紅赤、形體消瘦之人,都是可以適當吃點新鮮韭菜的。韭菜對人體有諸多好處,她含有豐富膳食纖維,可促進腸道蠕動、防止便秘、清除毒素,使皮膚清潔細膩。她可將消化道中的某些雜物如頭發、沙礫、甚至是細小金屬包裹起來,隨大便排出體外,在民間還被稱為“洗腸草”。例如,小孩子不慎誤食硬幣,可讓他將一小把用滾水焯過的韭菜整根吞下,硬幣便會被韭菜纏繞著排出體外。明代醫藥學家蘭茂撰寫的《滇南本草》也說韭菜:“滑潤腸胃中積,或食金、銀、銅器于腹內,吃之立下。”
所以,春寒料峭之時,準備一些新鮮韭菜,單獨小炒,或加入春筍,或加入黑木耳,混炒,現炒現食,那種鮮嫩美味,是很讓人享受的。更何況,還可以排毒養顏、清腸瘦身、溫補健體,女士哪能不愛呢。
而更會讓很多人眼前一亮的是,韭菜還可以治療脂肪肝。這也正如唐代醫學家孫思邈所言“韭味酸,肝病宜食之,大益人心。”可以將韭菜洗凈后,切成火柴棍一般長,再加入點滴香油、適量精鹽清炒食用。也可以做成韭菜粳米粥趁溫熱時食用,即將適量粳米淘洗后煮粥,待粥沸后,再加入適量新鮮洗凈切碎的韭菜,調入適量精鹽即可。吃點韭菜,輔以行走等持續性體育鍛煉,脂肪肝就沒了,這是多么愜意的一件事兒。
寫到這兒,想起了春秋末期思想家、教育家孔子的弟子曾晳,他在陪孔子閑坐時是這樣談論自己的人生理想的:“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那么,在細雨霏霏的初春時節,行走在風中,采下幾把韭菜,那和風、微雨、嫩綠的韭菜兒,也是一幅多么生動而和諧的圖畫啊。若人在畫中,就不妨像曾晳一樣,一路唱著歌兒回家吧。
管弦,女,大學教授,湖南省作協會員。曾在《散文百家》《文學界》《湖南文學》《佛山文藝》《翠苑》《金山》《散文選刊》《小小說》《羊城晚報》《廣州日報》等報刊雜志上發表作品。已出版文學作品集《開花的記憶》等。
責任編輯 張韻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