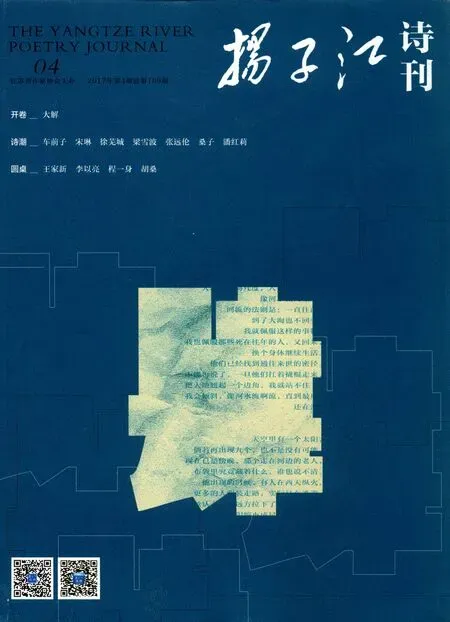傅天虹漢語新詩學的分泌與實踐
趙思運
○ 詩人研究 ○
傅天虹漢語新詩學的分泌與實踐
趙思運
中國新詩站在百年歷史的坐標上,何去何從?這是每一個詩人和文學史家急需深入思考的問題。古典與現代、中國與西方、保守與激進等二元對立的聲音仍然不斷地進行拉鋸戰。當我們把眼光凝聚到詩歌本體核心元素的時候,就又回到了詩歌常識和原點——漢詩的漢語性。關于新詩漢語性的反思、發現與探討,上世紀90年代已經開始。從鄭敏對于新詩對于傳統詩學發生斷裂的反思,到任洪淵對漢語文化詩學和多文體漢語文化哲學的探討,到姜耕玉的漢語詩性智慧說,到洛夫的跨域綜合的天涯詩學,再到新世紀傅天虹關于漢語新詩學的探索,構成了一條清晰的脈絡。作為獨異的詩人、學者、出版家和社會活動家,傅天虹經歷了大陸、香港、臺灣、澳門等不同時段,在不斷的人生漂泊歷程中,在不斷的詩學實踐的嬗變中,逐漸分泌出“漢語新詩”的概念。
傅天虹在梳理百年漢語詩歌歷程時,編撰出版《漢語新詩90年名作欣賞》和《漢語新詩90年名篇鑒賞辭典》(臺灣卷),引起了詩界關注,傅天虹遂成文《對“漢語新詩”概念的幾點思考》,闡釋了“漢語新詩”的學術準備、命名意義、可行性,并展望了漢語新詩學的區域整合與視野重建的前景。自2009年起,傅天虹就“漢語新詩”概念進行了一系列闡釋。“漢語新詩學”的詩學胚芽的生成與發育,完全帶著傅天虹的生命體征和生命溫度。這一概念既意味著為中國新詩尋找文化之根,同時也是一個“文化棄兒”的尋根。傅天虹,原名楊來順,1947年出生于南京。他尚在母腹的時候,父親就遠走香港。他還不到2歲的時候,母親又離他而去尋找父親,然后同去臺灣。傅天虹從小由外婆養大,后來考入南京師范學院讀書,上世紀70年代末才得以與父母取得聯系。傅天虹80年代初定居香港。在時任香港“中國筆會”會長的鄉叔何家驊的協助下,首開兩岸新詩溝通之先河。后來,他輾轉港澳臺和大陸,為兩岸詩歌交流做出重要貢獻。傅天虹在尋找血親之途,也是在尋找文化之源,詩學之源。“漢語新詩學”正是傅天虹尋根的最終結晶。
傅天虹的詩歌創作大致分為四個階段:六七十年代的“潛在寫作”、南京時期的“苦戀”寫作、定居香港之后的詩藝綜合寫作、漢語新詩學的凝練階段。這四個階段逐漸打開了自我、社會、文化、漢語的扇面,完成了從自我的確認、社會的反思、詩藝的歷練到文化的自覺暨詩學自覺的嬗變過程。這一過程,既是傅天虹自我生命尋根的過程,也是傅天虹詩學尋根的過程。
一、六七十年代的“潛在寫作”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傅天虹度過了漫長的流浪歲月。在流浪途中,傅天虹被一位老木匠收留,受到關愛,也隨著老木匠在四川、云南、貴州、廣西、陜西、寧夏等大半個中國顛沛流離,這種磨練使傅天虹窺視到了社會的真實面貌,開闊了胸襟。“寫詩”就是傅天虹抵抗現實的唯一武器和手段。但當時無法公布于世,只能以手抄本的形式存活。是謂“潛在寫作”。傅天虹在這一時期的寫作主要保存在手抄本《無題》(1968)、手抄本《無題二集》(1971)、手抄本《無題三集》(1974)。
傅天虹早期的詩作,雖然內容稍嫌直白,詩藝略顯單調,但卻具有那個時代所罕見的特質。我簡單比較一下傅天虹的《陰霾》和北島《結局或開始》的開頭。二者所表達的時代體驗是一致的:陰暗、壓抑、絕望、未來的不確定性。傅天虹雖然在藝術上不如北島做得立體繁復,但是他所傳遞的時代力量和個人的懷疑主義精神,在一個崇尚理想主義的空洞信仰的時代里,發出了更加真實的聲音,具有強烈的社會意義。傅天虹初步確立了樸素的人道主義和民主思想。《人》憤怒地控訴了極左力量對人的扭曲,有力地表達了傅天虹的人道主義的覺醒和個人主義的覺悟。
顛沛流離的底層人生,造就了少年詩人傅天虹的叛逆色彩。他在《我不是一個乖孩子》里就體現了“弒父”情感。這種情感態度在《問天》里呈現為振聾發聵的天問。這首詩有兩大突破:第一,傅天虹提出了“公民”概念,強調了公民意識、自我意識,具有濃厚的先覺者色彩。第二,這首詩在流行太陽崇拜的時代語境里,體現出質問太陽的“弒父情結”。他質疑刺痛眼睛以致什么也看不清的“太陽”,質疑蠻橫的太陽“如此賣弄它的強大”,而且還無情揭示了太陽的奴仆“月亮”在監聽著人間,因此,他肯定了宇宙秩序的背叛者——“那劃破夜幕的流星”。這種反抗意識也是較早的覺醒。
二、南京時期的“苦戀”寫作
如果說,第一階段的潛在寫作更多地體現了傅天虹自我命運的抒寫,那么,第二階段南京時期的“苦戀”寫作,則是對祖國和民族的苦戀。因為這一階段的詩歌基調即是由歷史深重之“苦”與詩人深摯之“戀”交織而成的“苦戀”。代表作有《苦戀曲》《母親》《酸果》《雪松之戀》《春歌》等。
《苦戀曲》抒發了一場歷經22年而無法忘卻被時代埋葬了的苦戀。這不僅是個體悲劇,更是民族之殤。《母親》描寫隔海墓陵中的媽媽無數次走進傅天虹的夢中:“三十多年了/我總渴望著/一聲門鈴/我的淚水沒有停過”。《酸果》是傅天虹的重要代表作,以扭曲的大樹上結出來的“酸果”自喻,控訴了時代風雨霜凍帶來的劫難。《賣火柴的小女孩》中那個沒有媽媽的小女孩,在某種意義上,這個小女孩就是傅天虹的另一個“自我鏡像”,表達了對自己遠去臺灣的媽媽的無限思念。
傅天虹在詩中表達了對民族未來的無限渴望。《雪松之戀》以市花的命運自喻,“我知道/你也有過被凌辱的痛苦/有過傷殘/有過厄運的侵襲/連中山陵都淹沒了的紅海洋/當然不會放過你”,“你不屈的綠/浮動在我猩紅的記憶里”。現在迎來了春天,“哪怕只犁出一點點新綠/春蠶吐絲一般的纏綿喲/似乎活著/愛,就決不會忘記”。《春歌——寫給一位會唱歌的老詩人》,一位“經過扭曲的世紀”的鄰居遭到批斗,妻子離婚,愛女夭折,但他并未沉淪,而是以充滿著“春蠶吐絲般纏綿/少女懷春般癡迷”的柔情,為時代唱一曲“苦戀”的春歌,“唱凍土里萌動的生機,/唱旭日下暖暖的春意……”他以這種動情的“戀歌”,給觀眾愛的滋潤和啟迪。
我們注意到,傅天虹這一時期的詩作,帶有那個時代的共名色彩。所謂“共名”,是指時代本身含有重大而統一的主題,知識分子思考和探索問題的材料都來自時代的主題。“共名”不但概括了時代主潮,而且可能成為作家表達自己社會見解的主要參照系。傅天虹的共名抒寫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對國家和民族的公共抒情——“苦戀”之情。引起極大影響的是《南京雜詠》組詩四首,分別寫了明孝陵、莫愁女、胭脂井、跪石羊,借物抒發歷史的巨大變遷,歷史的憂患意識是很清晰的。《跪石羊》抓住“跪”這一典型動作所蘊含的歷史深意,祈求“快起來吧,春天到了!/你身邊不遠就是長滿綠草的山坡。”蘊含了新時代人格解放的呼聲。二是在“向科學進軍”的時代號召下書寫的一批科學詩篇,開風氣之先,在很大程度上,表達的也是對國家和民族的共名抒情。三是一批具有哲理詩特點的詠物詩。
在這種共名抒寫之中,傅天虹并未像一般意義上的共名寫作那樣喪失自己的個性,而是基于個體生命感受,傳遞出一種責任擔當。他在諷刺詩《怎能叫我不開口》里,辛辣地諷刺了官僚主義的種種表現:無視下級建議和要求,揣測上級意圖,干部特權,能源浪費。甚至還會在陳腐的傳統故事里發掘嶄新的現代意識,如《月亮.女人》從傳統文化的“月亮/女人”隱喻原型出發,賦予了新時代的意義,沖破了傳統文學中“怨婦原型”的桎梏,實現了現代性價值重構。
三、定居香港之后的詩藝綜合寫作
港臺時期的傅天虹,人生歷練越來越沉雄,詩歌技藝臻于嫻熟。他的詩中洋溢對大自然、友誼、愛情的歌頌,更值得稱道的是關于香港生活的深刻描摹與諷刺。《香港組詩》《香港剪影》《磨光工人之歌》《夜香港》等均為代表作。
《香港組詩》借看更阿伯的話撕開了“血腥的利潤角逐”之下老板、舞女等各色人等的不幸生活,也借中山陵和紫金山下的回音壁,表達了對于大陸的思鄉之情。他殘酷地打開了被美麗風景遮蔽了的半張臉的陰暗,看到死海灣上“像吊桿一樣林立的/目光呆滯的/攜兒帶女的/大陸娶來的/不準上岸的/那些被看成風景的/水上新娘”。他的思想之情或許帶有一定程度的意識形態痕跡,但是他將筆觸對準了香港人的命運,刻畫了物質高度發達、精神日益貧瘠、生存日益艱難的生存圖景。《香港剪影》系列之《舞女之女》講述了母女兩代人宿命般不斷重復的悲劇命運,《天火》揭露了物質利益驅使下人性的扭曲與陰暗。
傅天虹為我們創造了不少驚人的意象和詩篇。如《夜香港》高度概括了香港人欲、物欲橫流的特質,卻又完全是詩性的處理:“夜香港/珠光寶氣/連天上斜掛的月/也閃爍/一枚銀幣的/眼神”。“斜月”與“銀幣”形似,“銀幣”與夜香港的“珠光寶氣”相諧協,舉重若輕,產生了四兩撥千斤的強大效果。與此詩的以小見大相反,他有時營造出大意境、大手筆。如《寫于香港》顯現出傅天虹卓越的想象力和概括力。香港究竟是深淵還是天堂?她接納的究竟是弱者還是強者?為讀者打開了無限遐思的詩意空間。在經歷了異地的漂泊之后,傅天虹筆下不斷地出現“云游”“浮萍”意象。他將沉痛的文字充分浸泡進自己的靈魂之海。因而,意象的經營愈加精湛。如《歸》以“破舊的歸舟”狀寫漂泊之情,以“老屋”狀寫漂泊之歸宿。結尾幾句:“此刻他握著故鄉老妻的手/久久凝視/庭前/一滴滴抓不牢樹枝的雨”,就像兩個蒙太奇鏡頭的組接,一個是“握著故鄉老妻的手”,一個是“一滴滴抓不牢樹枝的雨”,兩個鏡頭之間構成了隱喻關系。那種“相見時難別亦難”的無語凝噎的悲哀之情,沖擊著讀者的心靈。在傅天虹的筆下,不斷地出現母語文化意象。《冷艷》寫的是漳州人販賣的水仙,經過精“雕”細“刻”,切去駢生的花頭,剝掉束縛的干皮。這種古韻和冷艷,是以犧牲自然色澤和香味為代價的。這首詩與龔自珍的經典散文《病梅館記》,有異曲同工之妙。
1991年,傅天虹客居澳門以后,詩學活動遍及臺港澳和大陸,生活視野和詩學視野愈益開闊。他在沉吟中牢牢地抓住了漢語詩學的文化根系。傅天虹的詩作中密集地出現了祖國的名山大川意象,如武夷群峰、澳門觀音堂、澳門新口岸、三峽、莫愁女雕像、武侯祠、秦淮河、漓江、西湖、黃山迎客松、黃河。這是自然景觀意象,更是人文景觀意象,融合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詩學意境、佛學意境、自然意境,乃至歷史的深邃。
傅天虹的詩中,還出現了漢語文化人格符號,氤氳著傳統文化的精神。如曹雪芹、諸葛亮、鄭板橋、弘一法師。鄭板橋一生只畫蘭、竹、石,自稱“四時不謝之蘭,百節長青之竹,萬古不敗之石,千秋不變之人”。其詩書畫,世稱“三絕”。傅天虹的《讀鄭板橋的墨寶》淋漓盡致地活畫出鄭板橋的內在精神氣質:“啟開塵封的墨寶/是一行腐而不朽的神奇/脫去烏紗的揚州怪/依然活在清瘦里/瘦在蘭香/瘦在松枝/瘦在竹節”。他深知藝術之象里蘊藉的藝術家精神,在山水與心靈的耦合中,提煉出“難得糊涂”的精髓。在《讀〈紅樓夢〉》和《大觀園》中,傅天虹在透過中國文化經典《紅樓夢》,與曹雪芹進行一場文化通約,他深入到“石頭的心中”,讀懂了曹雪芹那座“金字塔”,他參透了“一個大家族/仍活在謊言之中”。可以看出,傅天虹的精神人格基因里,一直涌動著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因子。
四、漢語新詩學:母語詩學的的凝練
至此,可以看出,傅天虹在2008年編撰出版《漢語新詩90年名作選析》和《漢語新詩90年名篇鑒賞辭典》(臺灣卷),提出“漢語新詩”這一詩學概念,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因為他在長期的詩學實踐歷程中,逐漸找到詩歌的漢語脈動和漢語文化的體溫。
傅天虹的這一命名,跳出了既往詩歌史研究方法慣用的社會學政治學分析,而突進了詩歌本體元素——語言。語言既是一種表達材料,又是一種思維方式,更是一種文化范式。與以往的新詩命名相比,具有更多合理性。“白話詩”強調了創作載體白話文與文言文之間的二元對立性,“中國新詩”往往構成對境外漢語詩歌的排斥與遮蔽。“現代漢詩”相對更有學理性,但是現代漢詩與現代創作的舊體詩詞卻是包容關系,研究對象不統一。“漢語新詩”概念至少有如下幾個學術合理性:
第一,在西方詩學理論中,文體學是最高層級的范疇。在關于中國新詩的諸種概念中,“漢語新詩”則是一個最接近文體學的概念。它剝離了詩歌發展中的非文學因素,從文體的核心元素——現代漢語,來界定漢語新詩,回歸到了對文學自身的命名。
第二,傅天虹的漢語新詩學基于現代漢語的詩意組織規律,但是并不主張與文言詩詞割裂,而是看到內在的連續。他考察了臺灣漢語新詩回歸傳統的覺醒。臺灣新詩曾經注重激烈的反傳統趣味,但是上世紀60年代以來,《藍星》詩群從反傳統皈依正宗,《創世紀》《南北笛》《現代詩》中的部分詩人重新組織詩宗社,主張新詩歸宗,重返傳統。對于這種從西方現代主義晦澀風格轉向古典漢語美感,傅天虹肯定了中生代詩人的本土性、民間性和古典漢語詩學品質。也正如傅天虹《漢語新詩90年名作選析》緒論所言:“盡管漢語新詩以決絕的姿態斷裂文言母體的桎梏,但卻因漢語的內在連接性、漢語的語言信仰而形成的文化信仰,從而體現出一種承續性。”也正是由于漢語內在的綿延性與文化信仰,現代漢語對古代漢語的語法斷裂,并不能阻斷漢語母語的詩性因子的延續,因而形成了深層的漢語文化心理結構的恒穩性。這種恒穩性的文化心理結構,一方面跨越了漫長的風風雨雨政治的侵蝕而綿延不絕,另一方面,也最有可能在最深層修復已經被不同地域和族群隔離的漢民族文化共同體。
第三,漢語的文化共同體使得“漢語新詩”具有實現不同地域詩學整合的可能性。“漢語新詩學”的對象不僅僅是大陸的新詩,還包括臺灣、香港、澳門,以及其他國家地區用現代漢語創作的詩歌作品和現象。既認可了大陸漢語新詩的主體地位,又規避了“大陸中心主義”,包容了中國大陸之外的漢語新詩,實現了文化空間和地理空間的整合。正如傅天虹所言:“漢語作為一種語言,天然構成了一個無法用國族分別或政治疏隔乃至歷史斷代來加以分隔的整體形態。”這種漢語文化共同體具有民族潛意識和無意識的原型心理,傅天虹非常清醒地指出:“必須以區域整合與視野重建作為自身詩學建構的一大方向,必須破除狹隘的民族主義與政治意識形態的藩籬,不僅要注意到海峽兩岸‘和而不同’‘異中有同’的詩歌創作和詩學理論的互相參照,共同構成漢語新詩的宏觀視野;也要深入到各自豐富多彩的面貌中,探尋漢語新詩的不同態勢。”漢語新詩的命名“有助于整合漢語文化圈的地域中心主義,從而將漢語文化理解為一個沒有政治邊際的文化共同體”。這種命名并未遮蔽客觀存在的中國大陸漢語新詩的占位優勢,只是強調了漢語新詩的本體要素“漢語母語”以及漢語文化共同體的心理結構的凝聚力。
第四,傅天虹的漢語新詩學理論,從漢語母語的詩性審美方面強化了漢語新詩的本土性特質。
中國新詩自從誕生之日,白話語言與古典漢語隔斷,就開始脫離詩歌的漢語審美屬性和詩歌的本體性,而成為意識形態和社會觀念的工具。接著是上世紀30年代的戰爭環境,詩歌走向戰爭宣傳所需要的“大眾化”風格。上世紀40年代西南聯大詩群在艱苦卓絕之中使現代詩向高峰邁進,日子并不長久,很快就是50年代以來的政治清洗,文學語言轉型為蘇聯式的政論風格,政治意識形態話語全方位強勢侵入人們的日常話語和文學話語。上世紀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上半期的朦朧詩剛剛走向正軌,又遭到了第三代詩人的反叛,肆意扭曲語言,盛行的思潮是反崇高、反文化、反美學、反詩學、否定理性中心論,無限張揚自我,沒有沉下來思索漢詩何為漢詩,漢語詩歌的載體漢語以及詩歌本體被擱置。
在這種詩歌環境下,非常有必要呼吁當代漢詩的本土性。“漢語新詩”的核心命意“漢語詩性”根植于“本土性”,強調漢詩的漢語詩性智慧及漢語所承載的漢語文化體驗,乃是為漢詩新詩尋根。雖然中國新詩初受龐德的意象詩影響,但是,美國意象詩卻是深受中國古典詩歌啟發而成。西方語言學家哲學家如索緒爾(F.Saussure)、范尼洛薩(E.Fenollosa)、德里達(J. Derrida)、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深深贊嘆漢語文字的詩性功能。漢詩與西詩具有思維的同構性,而且漢語具有更加豐富的詩性智慧。
“漢語新詩”是一個新的命名,蘊含著巨大的詩學空間,它不僅僅是一個概念,更是建構“漢語新詩學”的邏輯起點。作為一種詩學體系,它的建構還需要探討漢語新詩學的內涵與外延、漢語新詩與漢語新文學的關系、漢語新詩的文化特性與詩性、漢語新詩學與傳統詩學的內在聯系與分野,等等。這個詩學建構過程對我們構成了艱苦卓絕的挑戰。
傅天虹的漢語新詩學的探討與實踐,為探討當代漢詩本土性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我之所以將傅天虹作為我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項目“當代漢詩的本土性反思與實踐”(13YJA751068)的一個重要案例,原因即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