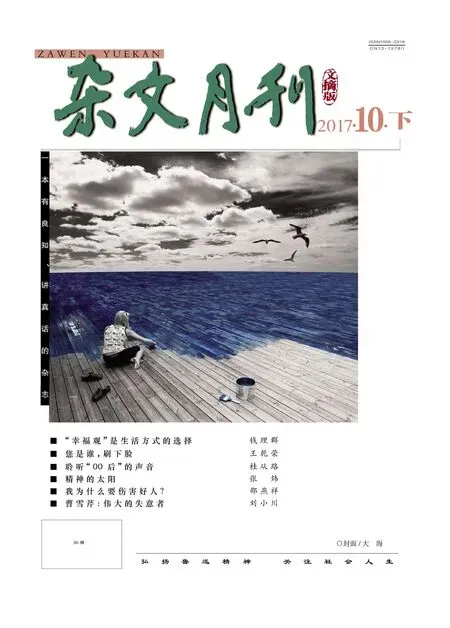十八世紀巴黎的“微笑革命”
□王兆貴
十八世紀巴黎的“微笑革命”
□王兆貴

譚詠麟有一首在歌壇深受歡迎的歌曲叫《微笑革命》。乍一聽到這樣的名字,感覺上有點小題大做了。微笑是人類內心世界的外在表達,即便是社交場合的應酬,也是一種再自然不過的表情,同革命又有什么關系呢?可是,在人類文明發展史上,微笑與革命之間確曾發生過關系。這個關系的發生,既同服務業的微笑服務無關,也與娛樂健身的微笑運動無關,而是一場于史有據的真實事件。
微笑即淺笑,既不必調動面部全部肌肉,也無需喉嚨發出聲響,只要嘴角微微上揚、眼神幽幽示意就夠了。當然,作為天性,微笑也沒什么統一模式,有人內斂一些,有人外露一些,全憑個人心性和習慣。既然笑一笑能換回十年少,又何必不茍言笑呢?但在我國古代,微笑這個表情事關重大儀軌。在古代淑女的規范中,非常講究儀容儀表的修飾與養成,特別強調“語莫掀唇”“笑不露齒”。因為咧嘴而笑會導致失態、失禮,抿嘴而笑則顯得含蓄、優雅。
原以為,笑不露齒的禮儀規范是中國獨有的,看了柯林·瓊斯的著述《微笑革命》后才發現,在十八世紀之前的西方,特別是那些有著貴族傳統的國家,對上流社會女性的要求更為苛刻,就連微笑也被視為傷風敗俗,更遑論露齒了。那時的法國,有身份、有地位的女性如果面對公眾“露齒而笑”,甚至被視作丑聞。這種情況到了十八世紀也沒有改變。法國女畫家伊麗莎白·路易斯·維杰·勒布倫夫人,一生畫過約六百幅人物肖像,色調清新,姿勢端莊,神態安詳,被后世譽為路易十六時代法國最杰出的女畫家。但在當年,卻因畫作中有露齒微笑的貴族女性形象,展出后受到了藝術評論家的強烈抨擊。那時的法國,性別歧視觀念根深蒂固,不允許婦女從事人體繪畫藝術,更不允許上流社會女性當眾露齒微笑。
1779年,勒布倫夫人應路易十六王后瑪麗·安托瓦內特之邀,入宮作畫,并因她創作的那幅王后手持玫瑰的肖像畫備受青睞。這位維也納公主出身的王后,是羅馬帝國弗蘭茨一世最小的女兒,自小受過良好的教育,追求個性,熱衷時尚,鐘愛藝術,很快就與勒布倫夫人成為閨蜜。但因她們的做派與風格不為保守人士所接受,自1783年起,關于勒布倫夫人的流言蜚語也開始到處傳揚。
面對保守社會的壓制,畫家用畫作表示了反抗。1787年,勒布倫夫人在巴黎展出了一幅懷抱年幼女兒的自畫像。在色調莊重的畫面中,女畫家神態優雅而又安詳,但因嘴角上揚,雙唇微張,牙齒清晰可見,觸怒了當時的藝術評論家,指責她作為一位有身份的女性,涉足藝術領域并公開展露微笑的繪畫有傷風化。勒布倫夫人并沒有被外界的非議所左右,仍然堅持自己的畫風,在巴黎掀起了一場“微笑革命”。同年,她為兩位侯爵夫人繪制的肖像及其1790年再次展出的自畫像中,人物表情均為露齒微笑。其實,勒布倫夫人早在1785年就曾繪制過一幅露齒微笑的油畫作品。畫像中,露齒微笑的酒神祭祀巴香特,面色紅暈,展現了飲酒微醺后的憨態。這幅畫作甫一完成,就被淹沒在評論家的口水中,斥責她表現的是一種強烈的性誘惑。
1789年10月,勒布倫夫人無法忍受突如其來的風暴所帶來的動蕩與混亂,為避瑪麗·安托瓦內特王后給自己帶來的無端牽連,不得已帶著自己心愛的女兒逃往國外,“微笑革命”就此夭折。在《微笑革命》一書中,柯林·瓊斯將勒布倫夫人露齒微笑的自畫像看作是十八世紀巴黎“微笑革命”的里程碑,認為法國對微笑的態度,反映了當時經濟、社會、文化的變遷;“微笑革命”是法國大革命的前奏,而法國大革命則反過來打斷了“微笑革命”。
勒布倫夫人流亡國外的十幾年間,不僅沒有中斷藝術生涯,反倒使其畫技得到了更為廣泛的傳揚,贏得了更多的贊譽,其作品幾乎涉及所有的歐洲宮廷。歐洲各國的皇室和貴族們,都為能得到她所畫的肖像而感到榮幸。勒布倫夫人重返巴黎后,仍然致力于肖像畫,直到晚年才放下了畫筆,全心撰寫回憶錄。
當人類跨入十九世紀之后,女性露齒微笑的行為得到了普遍認可,展示她們微笑的繪畫和攝影作品已然成為常態。勒布倫夫人的遭遇昭示人們,人類文明的每一次進步,都是思想解放的成果,其間也總伴隨著先驅們艱苦跋涉的足音。由于啟蒙運動在法國達到高潮并波及全世界,恩格斯不無贊嘆地說,十八世紀主要是法國人的世紀。在中國,笑不露齒的禮儀規范大約維持到十八世紀末,到清中期就不那么嚴格了。你看《紅樓夢》第四十回,賈府上下的女眷們,被劉姥姥逗得集體笑場,不僅前仰后合,而且情態各異。那位以個性張揚著稱的“鳳辣子”,笑起來更是沒遮攔,若不開口大笑,怎么能隔著幾道廳堂傳入內室呢?
阿爾薦自《學習時報》2017年8月11日勒布倫/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