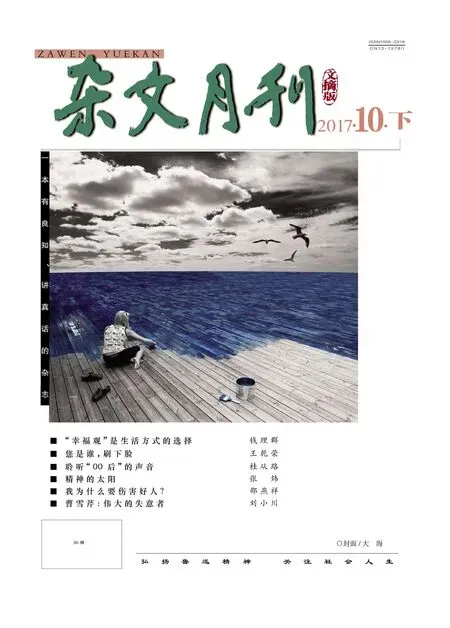曹雪芹:偉大的失意者
□劉小川
曹雪芹:偉大的失意者
□劉小川
古代寫小說是不入流的,“小說者流,蓋出于稗官野史,街談巷議”。但小說的元素在人類的洞穴時代已見端倪,形象思維淵遠而流長。《詩經》《史記》不乏場景描繪和心理刻畫。司馬遷也善于虛構細節。小說有民間的沃土,千百年強勁生長,例如書場文化在全國各地的發達。小說的不入流(封建社會),蓋因官方不屑一顧,盡管官員們私下讀得很起勁。曹雪芹寫小說的風險在于:遭人白眼,不能養家糊口。他二十歲左右成家,沒過多久妻子去世,續弦曰芳卿,家住北京的西山村落,芳卿生一子,小名叫方兒。也許她又生過女兒。家里當有其他人,比如芳卿的親人。一家好幾口,單靠曹雪芹這根頂梁柱。
曹雪芹一度做過宮廷畫師,賣過親手扎的風箏,擺過泥人攤,制作漆器、石器、玉器是一把好手,干木匠活很是利索——這個多才多藝的男人掙錢養家并不難。
他謀生的手段非常多。可是他居然寫起了小說。
曹雪芹在書寫中成為曹雪芹,換言之,他的精神偉力在方塊字搭建的殿堂中茁壯成長。“語言是存在的家。”語言的抽象功能,乃是人之為人的決定性標志。美好的女性受壓迫,群芳散盡,越是自尊自主自強,她們越是悲涼無助,男權社會霸氣橫流濁浪滔天……曹雪芹一頭扎進去,重現了時光,重構了時光。重構意味著超越。深諳此道的普魯斯特說:“唯有失而復得的樂園才是真實的樂園。”
偉大的小說寫在舊皇歷的背面,一本又一本。先生哪有余錢買稿紙。筆硯普通。舊皇歷上的宮殿漸漸金碧輝煌。回憶,回思,過去的時光黑洞般吸牢作家的目光。幾百人的喜怒哀樂奔來筆端。賈、史、王、薛四大家族的榮與衰,榮國府,寧國府,數不清的生活場景恍若夢境。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作者本意,專寫末世。”
雪芹先生身不由己了,吃與穿退居次要。藝術不可思議的魔力吸附他。表達就是生命本身。泉水要涌出來,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地熱涌出的溫泉呈噴射狀,抵達了沸點。沸點卻能表達冰點,《紅樓夢》冷熱交融,陰陽互生,聳峙為中華民族之精神奇觀。
曹雪芹年復一年在破紙上過日子,一己之身體驗著蕓蕓眾生,其樂無窮。偉大作家的一天,可比尋常人的一百天。生命首先是要由強度來衡量的。回行之思自動謀求著表達。血液分分秒秒在燃燒。尼采津津樂道的美神與酒神,每日造訪我們的小說家。

中國最杰出的小說家,是在這種困境中寫作,一寫十年。脂硯齋含淚點評:“字字看來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尋常。”《紅樓夢》從初稿到定稿,寫了五次。
中國的文化先賢多為失意者,中國的精神價值多為失意者、困頓者、堅韌不拔者所創造,歷代王公貴族與高官巨賈,罕見杰出者。此間有中華文明的特殊性,尚待仔細考查。英國哲學家羅素寫《閑散頌》,試圖證明西方的精神價值主要是由有閑的富裕階層所創造。中國顯然不是這樣。歷代豪族富商,驕奢淫逸是常態,是主流。民間有“富不過三代”的說法。家道中落,方有英才出世。
物欲橫流,精神委頓,這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鐵律。是的,鐵律。東方西方,概莫能外。物欲洶洶之輩,必定無休止地算計自然、進攻天地。人的廢掉,與大地不可逆轉的荒漠化相比,終究是一件小事。
據紅學家考證,曹雪芹圓臉,微胖。早年的山珍海味如同蘿卜小菜,打下身體厚實的底子,然而四十歲瘦成了一把骨頭。我們的曹雪芹瘦成了一把骨頭……
逝去的時光是曹雪芹的黑洞,他卻黑洞般吸引著炎黃子孫,除非中國人回望漢語經典的能力持續下降。
張朝元薦自《成都晚報》2017年8月16日周思聰/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