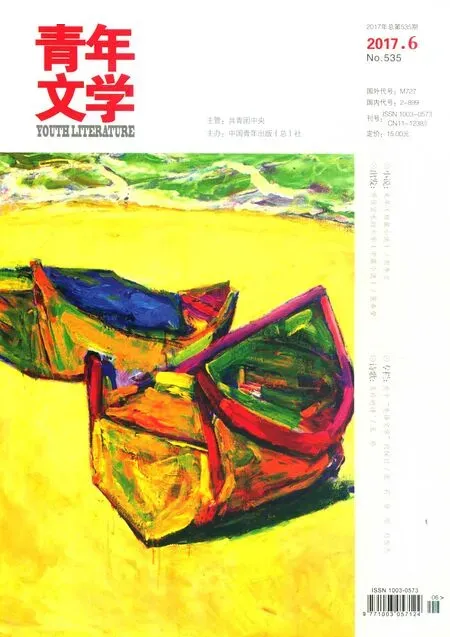【出發】
特邀欄目主持:鄭潤良
【出發】
特邀欄目主持:鄭潤良
讀過張春瑩的兩篇小說。一篇是《七一》,講一個七月一日撿來的弱智女孩,與一個老人相依為命。小說沒有大的戲劇性,但敘述節奏好,文字平淡有味,底色是溫暖的,像汪曾祺的調子。《開往宜水的火車》寫一個失去丈夫的女子與小她幾歲的列車員之間的邂逅與情感碰撞,寫得非常細膩,同樣也沒有大的事件,卻有內在的波瀾起伏。小說結尾,明亮、暢快,余味悠長,同樣讓我想到汪曾祺的小說如《受戒》,都透著人性的亮光與美感。看來,她的風格已初步形成,未來當有大成。
鄭潤良:你走上寫作之路,有受到周圍哪些人的具體影響嗎?
張春瑩:從小受我舅舅影響。我上初中起開始接觸文學名著,就是他寄放在我家的那一櫥書,打發了我很多無聊空閑的時光,并吸收了珍貴的文學養分。文學于他是業余愛好,他一直做生意,但多年保持閱讀習慣,有時去他家,他就把看過的書和雜志拿給我帶回去看。我最開始寫小說,拿去給他看,他很鼓勵我,我也蠻高興。
鄭潤良:你最近讀了什么書?
張春瑩:在看《王映霞自傳》,因為一直很喜歡郁達夫。在我心里,郁達夫不是一貫教材上的過去文人形象,他是個佯狂得可愛的文人,鮮活而真實,他有普通人身上的優點與缺點,讓我覺得他并不是個已經逝去的人。
鄭潤良:你覺得自己受到哪位作家的影響多一些?
張春瑩:外國的作家里我喜歡托爾斯泰、雨果、契訶夫等等。司湯達的《紅與黑》,有人說書里于連與德·瑞那夫人不是愛情,我認為是愛情。正因為我看到他們之間的愛與恨,被打動,我才喜歡這本書。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有一段用了很長篇幅來論述印刷術的發明導致建筑藝術的衰落,當時看到這里我很佩服雨果,他這個觀點或是說領悟,很有預見性,讓我知道作家要懂得很多。中國的作家里我偏愛古代的作家。詩詞方面,李白李商隱等人就不必說了,他們可以給人一輩子的文學養分。古典小說看得較少,喜歡《聊齋志異》,沒事時經常拿起來翻一篇看,以后去山東一定要去淄博蒲松齡的老家看看。《紅樓夢》是很喜歡的,大愛無言了,平時也看點紅學研究方面的書。現代的,錢鐘書的《圍城》是看第二遍時才覺出它的妙來,書中有很多幽默的小地方,用流行話來說就是“梗”,處處可見作者作為文人的小聰明,但是看完書后,你把這些小幽默聚起來一想,就感到這是作者的智慧。當代的,前幾年出來的《繁花》就很好,現在改編成評彈了,可惜不懂吳語,完全聽不懂,不免小憾。
鄭潤良:你什么時候在什么情況下開始了比較正式的文學創作?你覺得是什么激發了你的第一次靈感?
張春瑩:我開始寫作是在十八歲。那個年齡的人剛剛建立起自己的世界觀、價值觀,但還很淺,不穩定,而世界的多元和豐富性這時又朝你打開,因此不甘于沉默,就想有所表達。純粹是出于對文學的熱愛,還有懵懂的一腔熱情。
鄭潤良:你認為當代作家中哪些人的作品可能成為經典?
張春瑩:《塵埃落定》《白鹿原》等都是好書。成為經典的條件,是可以給各個年齡階段讀的,中學生讀《塵埃落定》和《白鹿原》受到觸動,成年后再讀這些,仍覺得好。
鄭潤良:你的小說里的那種調子讓我聯想到汪曾祺,你對汪曾祺的作品有特別的感受嗎?
張春瑩:除課本里學過《端午的鴨蛋》,以前只看過他的《受戒》和《黃油烙餅》,前幾天又看了《大淖記事》。汪曾祺的語言清新平順,有美感,他的作品深入讀者心,是他對世道人心有自己的體察與把握,然后借用小說這個藝術形式,把這些寫出來。他的文字下面有很多說不清道不明、讓人心領神會的東西,感覺他是一個特別智慧的作家。
鄭潤良:對你來說寫作意味著什么?你希望你的作品達到什么樣的效果?
張春瑩:寫作對我來說意味著表達。有話說才想寫作,如是純粹抒發個人情感,寫日記就可以了,不用寫小說。我有時想,為什么會有作家這個行當,除去別的,很基本的一點就是你文字表達的能力比別人強,多數人是用嘴說,你是用筆說,而形成文字后,它是美的,它才會被傳閱,才會被人喜歡,才會有價值。我會珍惜寫作,努力寫好每一篇小說。
鄭潤良:通常你是如何安排你的寫作和日常工作的?
張春瑩:平時要上班,只能用業余時間來寫,兩方面都協調好是有些難,但也盡力克服了。一開始寫小說時都不敢奢望能發表,更別說奢望稿費,就是憑著熱情與興趣,堅持下來了才可以得到這些。
鄭潤良:你如何看待八〇后九〇后等代際標簽,你覺得九〇后的寫作與前代作家可能有哪些不同的地方?
張春瑩:被分了類、貼了簽也是沒辦法,不過按年齡倒是比較方便歸類。我們這代人集體晚熟,從小生長在平穩安逸的環境下,外在大環境沒有給過我們什么大的沖擊和影響,因此我們的身心是比較健康的。父母那代人,很多人二十來歲已經當了爸媽,我們這代人二十五歲很多還在讀書。但是我感覺,這一代人的寫作和前代作家再怎么不同,優秀文學作品的審美與標準是不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