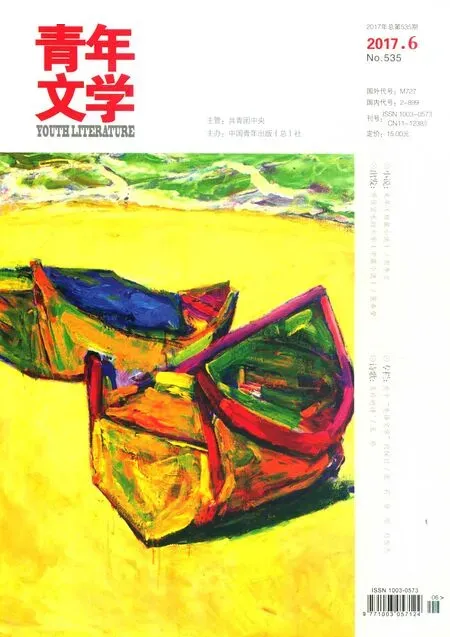先鋒文學的遺產與債務
▲徐 剛
先鋒文學的遺產與債務
▲徐 剛
從文學史書寫來看,我們一般會將馬原、莫言和殘雪視為當代先鋒小說的真正開端,認為他們分別在敘事革命、語言實驗與生存狀態三個層面展開了先鋒文學的藝術探索。具體來說,馬原的《虛構》《岡底斯的誘惑》等文本,以“元敘事”手法打破固有敘事的“似真幻覺”,用“敘事圈套”消解現實主義手法造成的真實幻覺,這在敘事革命的層面幾乎銘刻了先鋒文學的所有記憶。“我就是那個叫馬原的漢人,我寫小說,我喜歡天馬行空,我的故事多多少少有那么一點聳人聽聞。”熟悉當代文學的朋友,大概能夠輕松回想起那個自命不凡的文學天才,那個不可一世的先鋒狂徒,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文壇掀起的驚濤駭浪。這個曾經發明了獨特“敘事圈套”的“寫作的漢人”,幾乎憑一己之力,創造了彼時“純文學”的敘述神話。而在其之后,格非在《褐色鳥群》《青黃》等小說中竭力建構的敘事迷宮,則進一步將對現實的懷疑推向了極致。而在第二個層面,莫言的小說被認為“形成了個人化的神話世界與語象世界”,其感覺方式的獨特性在于“對現代漢語進行了引人注目的扭曲與違反”;緊隨其后的是孫甘露,后者在語言實驗的路途上走得更遠,《信使之函》《訪問夢境》等篇什專注于幻象構筑和詩性探索,并徹底斬斷語言與現實的指涉關系。而就第三個層面,即生存狀態而言,殘雪的《山上的小屋》等作品以丑惡的意象隱喻世界對人的壓迫,將一種個人化的感覺上升到對人的生存狀態的寓言層次;余華則發展了殘雪對人的存在的探索,《現實一種》《世事如煙》等小說以一種冷靜的筆調描寫死亡、血腥與暴力,并以此為基礎揭示人性的殘酷與存在的荒謬。
先鋒文學的這三個層面,可謂針針見血。從其歷史意識來看,它們無疑完美實現了對于過往革命現實主義文學的美學反動,這一點至關重要。現代主義文學運動,加上啟蒙史觀的歷史支援,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開啟的這股文學觀念的激烈變革,讓以現實主義為核心的文學樣式徹底失去了表現空間,取而代之的是“純文學”觀念的深入人心。現在看來,這種美學變革的歷史意義無論如何強調都不為過。先鋒的魅惑性在于激活文學的想象力,在那樣的環境之中,無疑具有激動人心的力量。而這也是我們今天重新討論先鋒文學的政治性時需要認真面對的理論前提。
盡管在短暫的輝煌之后,先鋒文學的倡導者與實踐者迅速回撤,轉向了日常生活敘事,并與這個商業時代的中產階級美學趣味合流;但不可否認,先鋒文學的藝術實驗,為此后文學觀念與技巧的變革,做了非常重要的基礎普及工作。在“純文學”觀念的燭照之下,“文學性”成為我們今天評價文學的重要尺度。而在此之中,敘事革命、語言實驗與生存狀態等層面,則是這些尺度的重要因素。先鋒文學的本土化,由此帶來的先鋒的隱匿與轉化,讓那些技巧與觀念“飛入尋常百姓家”,成為今天文學的基本表現方式。比如,我們讀到格非的《望春風》時,恐怕沒有人對小說中突然跳出來的敘事者感到詫異;而陳應松的《還魂記》則號稱“用最先鋒的形式,講好中國故事”……對于經典作家來說,先鋒文學的洗禮之后,原本高明的敘事手法已然成為家常便飯,而“純文學”的讀者更是對此見怪不怪了。
如果說敘事形式與技巧的全面更新,是先鋒文學最為重要的文學成就,那么它對年輕一代作家寫作之路的深切影響,則是我們今天評估先鋒文學遺產時的重要話題。七〇后一代寫作者中,相當多的人都是從先鋒小說的閱讀中汲取寫作靈感的。比如弋舟就曾被人認為是一位先鋒小說家,但他的小說卻是不折不扣的城市文學,他更多探討這個時代城市人的精神疾病。他討論人性的深邃,刻骨的孤獨,以及毫無來由的抑郁和同樣沒有原因的極端情感。某種程度上看,他的小說其實是與幽暗深邃的“實在界”打交道的。在他筆下,人性的真相像深淵一般讓人不寒而栗。《所有路的盡頭》寫出了人物內心的創傷、怯懦與卑微,以及“一個人一無所有的,孤獨”,彌漫其間的是歷史頹敗的滄桑感,毫無緣由的宿命感,以及無因的病態和神秘氣息。同樣深受先鋒小說影響的還有李浩,但他的小說卻顯示出與弋舟截然不同的氣質。這位喜歡琢磨小說與魔法關系的河北作家,經常自詡為魔法師或煉金術師。他操持著手里的語言,安然而自得其樂地做著虛構世界里的國王。由此來看,其小說的先鋒性一目了然,那些語言的伎倆,翻譯體的文風,可以看出從卡夫卡到昆德拉,再到卡爾維諾一脈作家的影響。在李浩那里,講什么并不是最重要的,怎么講才是生死攸關的問題。因而他的小說,即便如長篇《鏡子里的父親》,也不是通過故事情節來推動敘事;而是某種意義上的絮叨,自我的辯駁,以及更為復雜的形式追求,來組織和填充小說的內部。在他的小說里,我們可以真切地看到他與想象的讀者的較量,以及和自己的影子殊死搏斗的痕跡。
不僅是年輕作者,甚至是當年先鋒文學的“頭牌人物”馬原自己,也無法擺脫當年的寫作路數。失去了先鋒文學掩護的馬原,幾乎喪失了小說敘述的能力。“復出”后的《牛鬼蛇神》以“文革”故事開啟全篇,但作者卻完全沉浸在青春與成長的懷舊情緒之中無法自拔。此后,他相繼發表《糾纏》與《荒唐》,都試圖以更直接的方式切入當下現實。但和余華那部飽受詬病的《第七天》一樣,小說雖試圖以“正面強攻”的姿態切入現實議題,但其呈現的方式卻不能令人恭維。直到最近,《姑娘寨的帕亞馬》這部“頂禮神性云南”的作品,才讓人看到了些許希望。小說講述“我”在虛實兩種維度中探尋哈尼族祖先及其歷史傳承的故事。它在結構上雙線并行,流水賬式的散文游記中隱沒著一個匪夷所思的懸疑故事。小說不經意地切入“我”與帕亞馬的奇遇,從而引出這個原始森林中如夢如幻的世界。帕亞馬,那個腰間冒著青煙的裸體,意味著族群的起源與原始的野性。這個讓人心醉神迷的神秘男人給了“我”諸多思想的啟悟。然而,神性與世俗的分野終究讓“我”與他分道揚鑣。令人感慨的是,馬原早年獨步江湖的“敘事圈套”已然借此神性回歸。就此,這位當年的先鋒在對現實與個人記憶的徒勞之后,又重回虛構,在翻云覆雨的快意和虛張聲勢的奇跡中,領略先鋒敘事的剩余的激情。
有遺產就必然會有債務,這是我們討論先鋒文學時必須擁有的態度。先鋒文學已降,“文學性”的張揚所帶來的問題,是我們反思當下文學流弊的重要維度。最近,在一篇討論范雨素的文章中,詩人王家新提到了米沃什的《閱讀安娜·卡米恩斯卡日記》。他如此引用:“她不是一名卓越的詩人。而這才是關鍵:一個善良的人不必懂那些藝術的把戲。”這無疑是在提示我們,當面對那些矯情夸張,打磨得過于精致的“文學性”時,樸拙與單純反而成為這個時代最為珍貴和稀缺的元素。這讓我想起某個場合,一位年輕的作者坦率談到的,我們當代作家對現代/后現代的二十世紀西方文學過于沉溺,而與批判現實主義的十九世紀歐洲文學漸行漸遠,這種偏頗直接造成了當下文學的無力。我們當然不能把罪責都歸結到“先鋒文學”的頭上,但問題的產生卻也擺脫不了干系。
不過好在,先鋒文學那永遠求新求變的精神終究值得銘記。這毋寧說是文學變革的永恒命題。今天,時過境遷的“先鋒文學”依然被人看作一種自由的藝術精神,一種反叛的力量,或一個具有變革性的文學潮流。如陳曉明所言的,“先鋒性可以是作家、詩人及藝術家的精神氣質”。或者如謝有順所說的,“先鋒就是自由”。而所謂的“先鋒精神”,也被鄭重地表述為,“意味著以前衛的姿態探索存在的可能性以及與之相關的藝術的可能性,它以不避極端的態度對文學的共名狀態形成強烈的沖擊”。因此,在抽離了語詞的歷史性之后,永遠的“先鋒文學”其實就是那個帶給我們永恒之“異”的文學,這是在任何時代都值得敬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