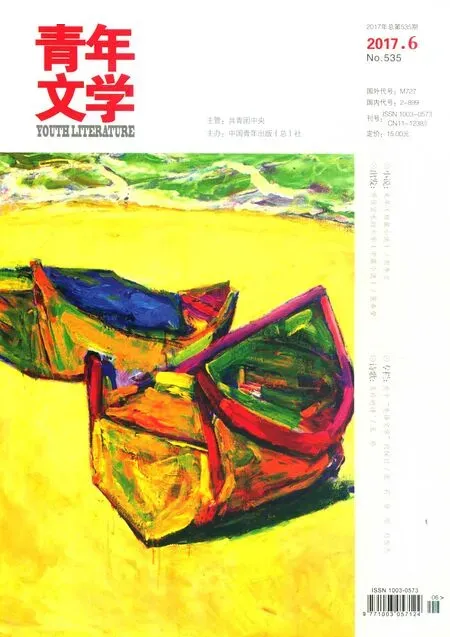我所理解的“冷想象力”
⊙ 文 / 唐 女
我所理解的“冷想象力”
⊙ 文 / 唐 女
我對溢出生活的那部分充滿好奇。
兒時,躺在外婆身邊,外婆說,有兩個鬼想靠近我們,被她趕跑了。我看著黑漆漆的夜,緊緊抱住外婆。外婆是巫。上學后,我鄙視外婆,但村里人非常喜愛她,她可以讓他們逝去的親人重新回到屋里,跟他們進行對話。那是一個奇異的空間,我一直排斥,卻無法控制撒在童年里的那些種子的蓬勃生長,無奈地看著它們開枝散葉,繁華滿冠。我對高出現實的那個世界,有了天然的親近感。
天然地,我也喜歡馬克·夏加爾天馬行空的繪畫。比如,背上站著人的公雞,在天空行走的白馬,一顆自由飛翔的頭顱……想象力空前釋放,上天入地,無所不能。一個超現實畫家,給我帶來的震撼非比尋常。跟馬爾克斯筆下騎著飛毯消失的少女、吃泥巴的女孩、長尾巴的后代一樣,跟卡夫卡的甲蟲人、老天使一樣,這些高出現實的部分把現實反照得奇光異彩——我是說想象力這塊。
有一段時間,我是這樣寫作的:睡足覺,洗漱后,空腹端坐電腦前,放適合的音樂,徹底放松,抓到第一個句子,便可把郁積于心的現實事件糅合變形,以“裸體”的形式一個個飛出來;那些奇異的句子、奇異的場景、奇異的對話,把沉重的現實提升到了半空。這個時候,整個人是亢奮的。回頭看這些作品,也是亢奮的,我沒料到會寫出這樣的東西。
但是,這樣的作品很難發表,很多朋友勸我,回到寫實路子上來,因為大家都喜歡寫實的作品。為什么只喜歡寫實的作品?我到現在也沒想明白,不過,碰壁多了,人就老實多了。寫實有寫實的好,直面現實的寫作更需要勇氣,從某些角度講,也更具感染力,只是,我再也體驗不到飛翔的感覺了。我不想寫沒有興奮點的小說,自己都興奮不起來,還寫它作甚?
我尋找契合點,在寫實的基礎上飛翔。《去勢》是第一篇這樣的作品,它在去年被《青年文學》接受了。從此,我定下基調,朝這個方向走一段看看。寫作這樣的作品,跟之前的亢奮恰好相反,情緒要降到冰點。現實很骨感,語言也冷寂,要把現實一步一步推至那個蹺蹺板上,最終讓它起飛,這是另一種想象力;與前面的“熱想象力”相對來說,它是一種“冷想象力”。我好像越來越喜歡它。
回到《影子當鋪》這篇小說,有三個點激發了我。我每天坐貫穿全城的公交車去上班,每天來回四趟。在車上,我看見街邊一座單獨的瓦房,紅門上寫著個“當”,從沒見它開過門。在車上,我聽見一個農婦說,有次漲大水,她去看在河邊養鴨子的朋友,見到她河邊的房子墻壁上趴滿了蛇,背皮都麻了。我還聽同事說,他遇到個老同事,是個退休干部,把小車停在他旁邊,一定要載他,說他不是為了賺錢,就是想出來找人說說話。這三個點在腦子發酵了一段時間,就跳出了《影子當鋪》這篇小說的靈感。
這篇小說在陳集益編輯的修改意見下,由短篇改成了中篇。說個小插曲,寫作過程中為了將情緒降至冰點,我把陳集益編輯那段修改意見一直懸浮在文檔下方,能看見的地方。當情緒高漲起來、文字出現脫離現實的想象時,我趕緊看一眼他的話,馬上又回到緊貼現實的“飛翔”狀態中。直至修改完成,才把他的話刪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