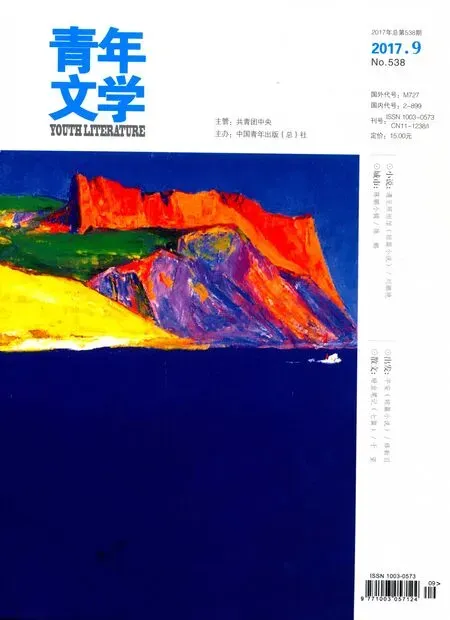我們都是受困于時代的囚鳥
——讀《刺虎》
⊙ 文 / 張艷梅
我們都是受困于時代的囚鳥——讀《刺虎》
⊙ 文 / 張艷梅
張艷梅:一九七一年出生,文學博士。現為山東理工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教授。在學術期刊發表論文近兩百篇,出版《海派市民小說與現代倫理敘事》《文化倫理視閾下的中國現當代小說研究》等著作。曾獲山東省高校優秀科研成果獎。
讀馬拉的小說,如陌上數繁星,自有其清減,亦復是妖嬈。馬拉自認為他與保羅·奧斯特、麥克尤恩這類作家更接近,喜歡精致,切口刁鉆,細致而深入。的確,無論是《未完成的肖像》《東柯三錄》《金枝》,還是《亡靈之嘆》《送釋之先生還走馬》,熱熱鬧鬧的俗世生活里,馬拉對世界有著敏感細膩的體驗,對社會人生有著清醒理性的判斷。
馮內古特說,我們都是受困于時代的“囚鳥”——既渴望逃離,又躊躇不前。讀《刺虎》,這句話反復回響起。《刺虎》以不斷疊加的視角,放大波瀾不驚的生活水面之下幽深的暗流。故事講的是普通的小城,簡陋的動物園,平凡的夫妻,俗常的日子。馬拉沒有把老虎之死寫成事先張揚的謀殺案。看虎,寫虎,是孩子眼光;殺虎,喂虎,是成人心事。一個人,一頭老虎,把幽暗的光聚焦到燃點,卻又慢慢冷卻。對于張大力而言,時光倉促,日子始終尋常,工作的怠惰,家庭的無趣,衰老的恐懼,逃逸的渴求,都沒那么尖銳。柴米油鹽,平淡的日常生活,總是按照慣性繼續向前;時代在變,張大力,張愛球,一代一代人似乎并沒有什么不同。面對老虎,被捆綁的心靈或許有著無言的共鳴,其實任何淪陷的都是隱藏的自我,一路上能夠看到的風景,是被規劃好的方向,就像那個小小的動物園。
《刺虎》刺穿虛偽的生活假象,讓熱鬧的生活呈現出漫漶的虛無和空缺。小說,當然首先是生活,然后是隱喻。刺虎,從正面看到自我,從鏡像中看到他人。馬拉借題發揮,把我們不想要的生活放大了細節給我們看。從張愛球看虎、同事們談虎、殺虎犯刺虎,到張大力喂虎;動物園、辦公室、法庭,每一次空間推進,最終都回到那個銹跡斑斑的冰冷鐵籠。無所謂生死,無所謂強弱,正如刺虎者眼里一閃而過的平靜柔和的光,死亡也不可能帶來真正的自由和尊嚴,這才是張大力最終的喟嘆。馬拉對于煙火俗世的理解,對于生命困境的體恤,既有在場感,又不乏超越性。張大力深夜里獨自與衰弱的老虎相對而坐的那個結尾,讀后令人無限傷感。一個優秀的作家,一定能夠通過關注人類自身的失敗和困惑,來揭示人性不可見的深度。上帝創造了這個世界,同時設置了很多牢籠,我們生而不自由,無法不面對充滿疑慮的道路。張大力與老虎對話,也是與自我對話。他內心那些隱秘的掙扎,大約也是整整一代人的精神鄉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