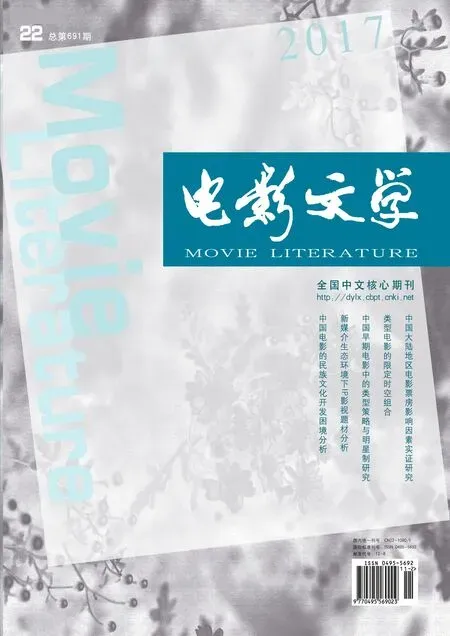《摔跤吧!爸爸》中的性別自我意識覺醒
趙 瓊
(吉林工商學院,吉林 長春 130507)
《摔跤吧!爸爸》是近年來為數不多在中國地區掀起觀影風暴的印度影片。和傳統寶萊塢出品的印度電影不同,雖然《摔跤吧!爸爸》依舊有歌舞成分,但劇情成為影片主要服務的對象。而《摔跤吧!爸爸》也擺脫了傳統寶萊塢電影中愛情電影當道的局面,試圖從親情、女性地位、印度傳統習俗、社會表現等各個方面批判式地展示印度社會的全景。《摔跤吧!爸爸》的劇情豐富,具有層次感和條理性,這一點也有別于合家歡式的寶萊塢影片。挫折引導和價值變化判斷的表達存在于整體影片之中,成為影片的主題復調。《摔跤吧!爸爸》講述了曾經前途無量的摔跤運動員馬哈維亞培養兩個女兒成為著名職業摔跤選手的故事。馬哈維亞因生計問題在放棄了職業生涯后,將為印度獲得國際獎牌的希望寄托在了尚未出生的兒子身上,可天不遂人愿,馬哈維亞的妻子一連生了四個女兒。正在他要放棄夢想之際,兩個女兒展現出了杰出的摔跤天賦,讓他幡然醒悟,就算是女孩,也能夠昂首挺胸地站在比賽場上,為了國家和她們自己贏得榮譽。 在馬哈維亞的指導下,吉塔和巴比塔開始了艱苦的訓練,兩人進步神速,很快就因為在比賽中連連獲勝而成為當地的名人。而吉塔和巴比塔與馬哈維亞之間也經歷了重重親情和價值觀念差異的考驗,父女三人最終完成了各自的夢想,為印度奪得了第一塊世界摔跤比賽的金牌。在《摔跤吧!爸爸》表達的豐富主題中,女性成長與女性的地位變遷是影片較為重要的表達主題,也具有明顯的代表性,因此本研究也基于影片《摔跤吧!爸爸》中女性自我意識表現加以分析,試圖探討在《摔跤吧!爸爸》一片中所表現的性別自我意識的覺醒。
一、女性形象的塑造與展示——吉塔和巴比塔
《摔跤吧!爸爸》的主要角色是馬哈維亞、吉塔和巴比塔,而吉塔和馬哈維亞則是主角中的主角。影片的開頭用了相當長的背景敘事引出馬哈維亞與“子承父業”式的情節。曾經是優秀摔跤運動員的馬哈維亞因為家庭貧困不得不中斷職業摔跤手的生涯,只能選擇一份文員工作養家糊口。他將為印度獲得一枚金牌的愿望寄托在了未出生的兒子身上。但是命運作弄,妻子接連生了四個女兒。這種處境和局面也暗示了馬哈維亞個人理想的破滅。因為在印度傳統中,女孩是被拒于摔跤之外的。從鏡頭中反復出現的青少年摔跤場面也可以看到,參與摔跤的選手大部分都是穿著赤裸的男性,而過肩摔等動作所需要的力量和技巧對普通女性來說也絕非易事。在這種局面下,吉塔和巴比塔的可貴性也就出現了。
她們被馬哈維亞賞識的原因來自于她們與鄰居男孩的一次打架。本應該處于劣勢的兩個女孩把男孩打得鼻青臉腫,緊接其后,兩人對打架動作的展示,讓馬哈維亞認識到“她們本身就有斗爭性。她們有戰斗的血液”。從此處就開始暗示了吉塔和巴比塔對自己性別意識與吉塔的同學的差異。她們并不被傳統禮俗所限制,認為女性只應該躲在廚房里為一家的午餐操勞。這種獨特的性別氣質也一直在影片中得以保留。在吉塔和巴比塔參加摔跤訓練時,兩人被同校的同學嘲笑:“練了摔跤之后走路都像個男人。”兩姐妹并不以此為侮辱,而是要求同學對她們保持尊重,這無疑也是人格完整和獨立的表現。換言之,吉塔和巴比塔對自己的性別認知與外加的禮規之間有很大差異,她們自身就兼具了自信和自愛兩部分,而這兩部分正是女性自我人格建構中最為重要的影響因素。
但影片中同樣細心地刻畫了她們自我的性別意識與社會力量之間的暗自較量。在兩人初學摔跤一節,她們脫掉了沙麗,換上了表哥穿的褲子和短袖衫。她們雖然沒有表現出十足的抗拒,但可以在影片后面的部分看到,她們依舊對美有著渴望和追求,對沙麗、耳環、長發依舊有著強烈的興趣。電影中并沒有刻意地從人物塑造層面抹殺了吉塔和巴比塔的女性氣質,只是從體育運動層面刻畫了兩位女性形象,從而使得人物形象更為立體。從影片的敘事層面來看,吉塔和巴比塔的形象無疑是正面的,是影片自身所提出的完美的女性形象,她們行為的偏差很快就被糾正或者是得到諒解,而她們所代表的也是導演所意欲提出的新女性的本質,吉塔和巴比塔的人物形象是影片中表現最多的,卻未必是最為飽滿的,導演為表現兩人獨特的性別氣質,刪除了兩人內心的一些表現。因而,從電影的結構分析,可得知吉塔和巴比塔的角色特點所代表的是一種女性敢于追求目標、敢于拼搏和走上社會的表現和精神,而不是具體的人。
二、女性的社會處境與傳統語境的暗示——社會環境的力量
《摔跤吧!爸爸》雖然是一部集中在馬哈維亞父女三人之間的影片,但影片也在無意之間向人們塑造了一個完整的女性人物群像,讓觀眾得以從影片中瞥見真實的印度女性社會處境。在《摔跤吧!爸爸》中女性形象主要可以分為四大類,即反抗者、服從者、受害者、社會意識表達者。
反抗者無疑是吉塔和巴比塔姐妹倆,她們不畏懼眾人的眼光,通過各自辛苦的訓練,追尋夢想,這是影片主創人員所期待的印度女性形象,卻在現實中的印度社會占據相當少的一部分。服從者在影片中則是女性群像的主體部分。吉塔和巴比塔的母親就是典型的例子。作為馬哈維亞的妻子,她的夢想也是生育一個兒子,幫助馬哈維亞繼續他未完成的金牌夢。她承擔了大部分的家務勞動,并且認為自己承擔勞動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在馬哈維亞告訴她,他想讓兩個女兒參加摔跤訓練時,她除了答應之外,幾乎沒有其他有力的反駁意見。作為一個母親,她顯然也是心疼兩個女兒的,但是女兒受傷、女兒剪頭發等細節中,她依舊尊重夫權,強忍著心痛,對兩個女兒不聞不問。這種女性形象是典型的印度式賢妻良母,在《流浪者》《瞞天誤殺記》《大地》《大篷車》等電影中屢次出現,也反映出現實中印度社會對女性的期待,他們并不需要一個有知識和理想的女性,他們需要的是一個自我奉獻的母親。受害者則是影片中毫無選擇的未成年新娘。作為吉塔和巴比塔的朋友,她的年紀不大,但是卻面臨著嫁給一個白發老翁的命運。在她與吉塔姐妹對談時,她說:“我羨慕你們還有一個‘虐待’你們的爸爸,他關心你們,而我爸爸卻只知道把我嫁出去。”作為一個女孩,小新娘的夫子自道顯然是對命運加以思考后的產物,作為一個女孩,從出生開始就意味著要在廚房幫忙,直到可以出嫁,又要到一個以前完全不認識的家里面幫忙。從小新娘的視野中可以看到,作為女性的她,顯然不是作為一個獨立的人出現的。她需要依附于丈夫、父親,自己的命運卻不能自己主宰。也正是小新娘的遭遇,讓吉塔和巴比塔認識到,她們的摔跤生涯也是她們為自己命運拼搏的生涯——在女性社會階層上升機會渺茫的印度社會中,獲得金牌、獲得勝利就是她們僅能做出的努力,是一種讓命運不被他人掌握的唯一手段。由小新娘一段所引出的則是借由社會現象引發觀眾對當代印度女性地位的思考。
影片中最為隱蔽也最為關鍵的視點,事實上來自于社會意識表達者,這些人幾乎構成了影片故事中主題的另一種復調主題。這些人既包括吉塔姐妹在學校中遇到的嘲笑兩姐妹“越來越像男人”的同學,也包括對女孩參加摔跤比賽抱有嘲弄態度的賽事組織者;既包括對兩姐妹穿上男孩衣服表達嘲弄的旁觀群眾,也包括在摔跤錦標賽上嘲弄印度的丹麥女摔跤手。他們在影片中起到的是表達大眾觀念的作用。馬哈維亞的鄰居和兄弟表達的是對女性參與摔跤運動的不理解與不支持,吉塔的同學則是從吉塔的同齡人角度表達了對吉塔姐妹這種身份選擇的焦慮和嘲弄;被吉塔和巴比塔打敗的鄰居男孩所表達的是傳統男權衰弱不堪卻依舊保有的對女性價值的終極評價權利,對印度加以嘲笑的丹麥女摔跤手則集中表達了印度民族對自我身份的焦慮和不認可。換言之,吉塔和巴比塔作為女性的身份,她們遭受到的社會壓力是男性的數倍,而擁有龐大貧困人口的發展中國家——印度,在與西方進行比拼時,同樣也作為一個弱勢的、缺少話語權的“陰性”符號出現,這種設置也讓吉塔和丹麥女選手的決賽帶有了非現實性和非指涉性的色彩,讓女性權利這一議題延伸得更遠,并且使得電影在女性和父權等主題之外,還涵蓋了更多元的解讀元素。
三、破題與立論——父親對女兒們女性地位認知的變化和發展
從劇情上說,《摔跤吧!爸爸》依舊是一部圍繞著父女三人關系發展延伸的影片,而借由此,曾經一心求子,希望子承父業的馬哈維亞對吉塔兩姐妹的態度轉變則就成為該片中女性價值體現變遷的最為重要的分析因素。首先,從馬哈維亞的個人經歷來看,他是一位因為生計所迫放棄摔跤運動的優秀運動員。影片開場,一長段男孩摔跤的蒙太奇事實上就是馬哈維亞自己所熟悉的摔跤經歷,在他的印象中,摔跤和男性的性別認知緊緊地捆綁在一起。因此,與其說馬哈維亞渴望有一個兒子,不如說馬哈維亞更渴望有一個摔跤生涯的繼承人。因此,馬哈維亞在求子無望后,對培養女兒們成為摔跤運動員則產生了十二分的渴望。從本質而言,馬哈維亞并不是一個傳統父權的維護者,他恰恰是一個反叛者,一個嘗試追夢,認為人可以實現自己理想的完整的人。但馬哈維亞的表現中依舊存在父權的因素,例如,他認為女兒蓄長發就意味著她對摔跤事業開始分心。又如他可以在不提前詢問女兒意見的情況下,就擅自決定兩個女兒日后需要參加摔跤訓練,這也是馬哈維亞所習慣的印度社會傳統。
然而,從劇情的發展可以逐漸發現馬哈維亞自身的變化,隨著吉塔兩姐妹摔跤訓練的不斷深入,他對兩姐妹的態度也出現了變化。在印度男性下廚被視為有損顏面的行為,但馬哈維亞為了能夠讓兩姐妹吃上雞肉,先是去菜場和小販討價還價,后又學習如何做飯。他本身從社會風俗秩序的維護者、遵守者,正逐漸變成一個反叛者;他從一個社會屬性上的父親,逐漸變成了一個情感上的父親。在吉塔從國家體育學院返校回家時,吉塔與馬哈維亞之間發生沖突,兩人摔跤,吉塔已經能夠勝過他了,這種身體力量的此消彼長與情感的變化讓人潸然淚下,作為傳統的強者的父親已經衰老,他關心自己的女兒,卻沒有能力再讓原本應該在他羽翼之下的女兒聽從他的意見;而原本弱小,甚至畏懼父親的女兒在獲得全國冠軍、進入體育學院之后,已經成為更強勢的一方。這種關系的轉換既奇妙地重現了馬哈維亞和吉塔之間的關系,又從另外一層面上展示了父權和女性權利力量的此消彼長。
同樣值得關注的還有原本代表著社會意識的配角態度的變化,例如,在最開始馬哈維亞提出要給吉塔和巴比塔買雞肉時,小販嘲笑道:“女孩摔跤?沒聽過。”到隨著吉塔取得的成就不斷變大,小販將吉塔的人形廣告牌不斷更替,他本人也從嘲弄和不相信變成了鼓勵、支持甚至是贊賞。原本在學校中嘲笑吉塔姐妹的同學,也隨著吉塔獲得冠軍而逐漸改變了態度,進一步認可了她們的生活方式。這種態度的變遷也更為立體地展示了吉塔和巴比塔兩人奮斗的意義,也正如影片所說,她們并不只是為了自己在戰斗,也是為了給印度千千萬萬的女性做一個榜樣,女性也有選擇自己生活和命運的權利。而影片的主題也在此升華,將影片從勵志、劇情類的類型片拔高到社會意識討論的高度,給觀影者以藝術欣賞之外的啟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