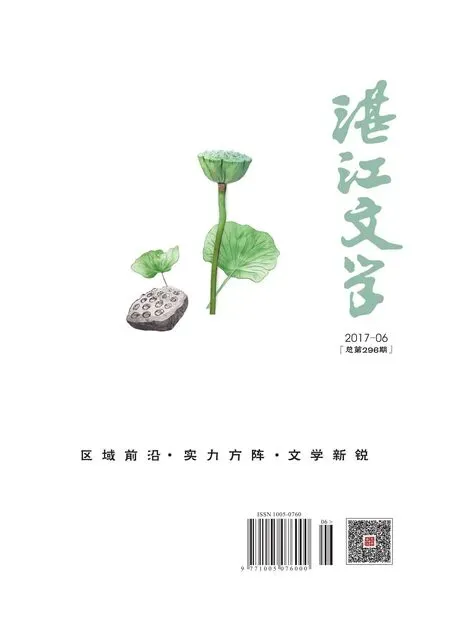送書
※ 張朝霞
送書
※ 張朝霞
擁有自己寫就的一本書,似乎激動勁還沒過,就考慮著如何送書了。
腦海里閃過曾接觸的令人尊敬的師長,暗忖對方可能也會模糊記起這書的作者,至少看到這書不會覺得太唐突。恭恭敬敬寫了請教語,簽了名,填上日期。簽名不怎樣,不是那種藝術體,還算湊合。帶著一絲期待一絲忐忑寄出去,一段時間后,斷續收到感謝的話、自謙的話,頗受寵若驚。
書本來就是讓人看的。偶爾有人問一句:“你的書,何時也給我一本呢?”立馬暗自得意:他竟然也知道我的書?然后或郵寄,或托人轉交,連同轉交的人順帶送上一本,第一時間把這本薄薄的小冊子送到對方手里。
概算了一下,如果送出的一百本書中,有百分之十被隨手翻閱過,那就有十本給人留下了粗略的印象;這十本中,如果有百分之十被好奇地看了八九成甚至通讀了,那就有一本被幸運地看完。這么一算,這書送得是值了。
我承認我也不能免俗,更多的是希望聽到贊賞的聲音。當在鎮政府工作的阿奮說:“你的書,讓人有溫暖的感覺......”在機關單位上班的小吳說:“你那次,騎著單車去看望老同學呢......”在博物館當解說員的芳芳說:“看了你的書,我覺得很多事我也經歷過,從此我也拿起筆來寫一寫。”我馬上謙虛地應答:“讓您見笑了!”內心卻是抑制不住地小小自得了一把:事務繁多的他們或蹦出文縐縐的“溫暖”,或記得其中一篇的一個小細節,甚而激發出寫作潛能,那說明送到他們手上的書,確實翻看過,并且印象還不算太差呢。
記起幾次送書的情景。
阿蘭是打電話過來索書的,之前我們一直沒見過面。要一本書,這么小的事,她說得很客氣。從電話中得知,她是一名小學教師。第二天,我拿書到了事先約好的地點,遠遠地,看到她笑吟吟地站在那兒,手里捧著一束怒放的鮮花。看到我,她把花往我懷里一放,說,第一次見面,又是向你要書來的,想來想去,一束鮮花最能代表我的心意了。這個隆重的禮節讓我措手不及。想想,似乎還從來沒人給我送過鮮花呢,因為一次送書,而享受了這個待遇。那個午后,我懷里是鮮艷欲滴的花兒,清風徐徐,兩個初次見面的人,在大樹底下暢敘良久。
丹丹是在外地打工的一個年輕女孩。在一次文藝活動中,她負責簽到。我俯身在簽到簿簽名時,看到一個穿著素色長裙的女孩,長相恬靜,站在簽到臺后,身子微微向前傾,微笑著說:“有什么需要幫助的,請隨時跟我們說。”后來聽到有人叫她“丹丹”,她急速地走過去忙活,因為走得快,裙裾飄飄,我卻注意到了她的腳一拐一拐的,只是由于長裙的遮掩,看起來不太明顯。不久后的一天,她來到我的辦公室,說要向我要一本書。那天座談中,我了解到,她一直在外地打工,上次的活動,她是回來義務幫忙的,這次趁假期過來找我。她說她的腿疾,是小時候的一次醫療事故落下的,她母親帶著她四處求醫,動了幾次大手術,終于可以自己走路了。她說這些時,很平靜,臉上閃著圣潔的光。我把書給她,送她到樓梯口,目送她匯入喧囂的人群中。
單位附近有一個快遞點。一次我去寄書,當我把寫有地址的紙條遞過去時,那個當班的小伙子接過,“刷刷刷”就填寫起來。末了,仰起頭問“姓名?”我指了指書的封面,“就按這個寫。”他現出有點夸張的表情,“這書是你寫的呀!”然后低下頭繼續填寫。店面有點暗,大包小包的物品堆得滿滿的。我走出小店,隱隱覺得他在翻著我那本準備寄出的書。第二次我再去時,特地多帶了一本。這次他“刷刷刷”填寫完地址后,徑自看著書的封面將姓名寫下。準備離開時,我把那本書拿出來,“這多出來的一本,不嫌棄的話,就送你吧。”小伙子驚喜地接過:“真給我的嗎?上次我想留著看,但不能誤了寄出的時間呀!”我輕松地走到街的對面,那個有點陰暗雜亂的快遞小店,漸漸地開闊亮堂了。
也有不亮堂的時候。
那次在辦公樓走廊,與久未謀面的他匆匆打了一照面,臨走時,急急從書柜里抽出一本書送他。他將書一卷,夾在胳膊底下告辭。許是走得匆忙,許是有急事等著處理,但看著被卷成一團縮在胳膊里的書,讓人想起受了委屈的小孩,涎著臉可憐巴巴的模樣。
那次在會場大門口,剛將書遞給他,他迅速地塞了回來:“我不要,我不看這些。”我像做賊似的趕緊把書放回包里。可能嘈雜聲中,他沒注意到我送的是我的書。浩瀚的書海,要看的東西實在太多了。家中逼仄的空間,擁擠得放不下多一本書。我別過發燙的臉,有那么一陣,坦然了。很多時候,你滿心歡喜地夸著自己的孩子,旁人也會附和著夸,但畢竟不是他的孩子,沒有你這種打心底里的喜愛是很正常的,也就是附和一下吧。
送出一本書,對方滿心歡喜地接受,就應心存感激。若送出的書在紛雜中被看完,那差不多算是知音了。
我告誡自己,別人送書時,一定記得雙手接過,真誠地說一聲“謝謝”。如果是外地寄過來的,收到后,第一時間告知對方。收到別人的書,如沒有時間,或不感興趣,或看不懂,或犯懶,起碼也要記住書名、作者,知道大概的內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