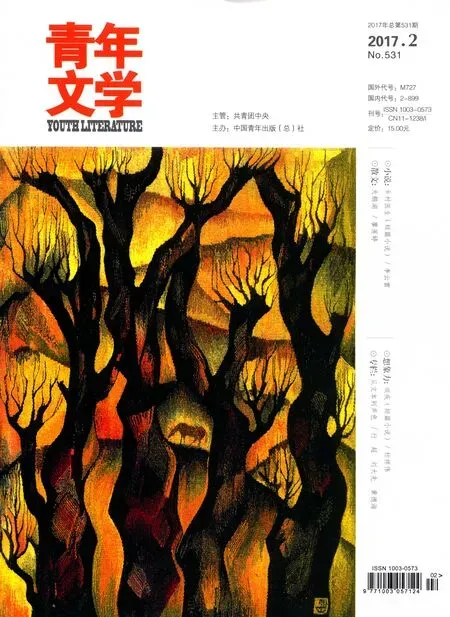另一面
⊙ 文 / 林漱硯
另一面
⊙ 文 / 林漱硯
林漱硯:一九七九年出生,浙江樂(lè)清人。作品散見(jiàn)于《芙蓉》《青年文學(xué)》《西湖》等刊,有作品被《北京文學(xué)·中篇小說(shuō)月報(bào)》轉(zhuǎn)載。
一
這個(gè)名叫嚴(yán)紫粉的女孩,坐在我面前的轉(zhuǎn)椅上,由我為她化妝。
單從臉形、五官而論的話,嚴(yán)紫粉長(zhǎng)得還算不錯(cuò),臉形嬌小,五官端正,只是鼻梁略顯扁平,光照在她臉上,一片平坦。她有一頭順直的黑色長(zhǎng)發(fā),豐茂光澤,簡(jiǎn)單地束了個(gè)黑色發(fā)圈。但她皮膚蠟黃,唇色黯淡,整個(gè)人看起來(lái)了無(wú)生機(jī)。我觸到她臉上的肌膚時(shí),像觸到了一片薄涼的冰。
嚴(yán)紫粉穿了一件淡粉色長(zhǎng)袖連衣短裙,一條黑色厚打底褲。起先,她晃動(dòng)緊繃著打底褲的雙腿進(jìn)來(lái)時(shí),我注意到,打底褲勾勒出一雙挺好看的腿形。可惜就是這身打扮,令人一眼看穿了她的底氣。嚴(yán)紫粉剛進(jìn)店時(shí),幾位打扮入時(shí)、舉止高雅的顧客,就已經(jīng)紛紛對(duì)她側(cè)目而視。
這短裙本身沒(méi)有問(wèn)題,但眼下已是仲夏,前幾天剛過(guò)端午節(jié)。那幾天,母親起早摸黑,在家里用煤氣灶燒草灰湯,包湯灰蜜棗粽。我與父母三人住一幢三百多平米的排屋,當(dāng)初房子裝修完畢,我將父母從鄉(xiāng)下連根拔起,栽進(jìn)排屋里時(shí),他們臉上就有了無(wú)所適從的神色。——住在這里,白天太陽(yáng)不猛,晚上露水不大,我們能干什么呢?父母不約而同地搓著各自粗糙的手。干什么都好,隨你們,只要不回鄉(xiāng)下種田就行,免得別人說(shuō)我不孝,我回答。兒子在城里住排屋,父母在鄉(xiāng)下住破屋,我還不被鄉(xiāng)里鄉(xiāng)親的唾沫星子給淹死?幸好父母的理想具有極其頑強(qiáng)的生命力,他們很快就在排屋里鋪開(kāi)了田園生活,在露臺(tái)上種菜,在花園里養(yǎng)雞。
當(dāng)然,這是題外話,我想說(shuō)的是,已經(jīng)過(guò)了端午節(jié)了,嚴(yán)紫粉卻還穿得如此厚實(shí)。記得端午節(jié)那天,我在吃蜜棗粽時(shí),母親說(shuō)起了鄉(xiāng)里俗語(yǔ),吃了重五粽,棉衣慢慢送,明天我可以把你的那些長(zhǎng)袖、厚被都洗了。我們家鄉(xiāng)的方言稱“端午”為“重五”。父親說(shuō),就是,我把你房里的空調(diào)洗洗,也該用起來(lái)了,你們城里比鄉(xiāng)下熱多了。父母在睿城的“心臟地帶”已經(jīng)待了兩年,還是把這里稱為“你們城里”,來(lái)自睿城“肢體末端”的地域觀念須臾無(wú)法忘懷。
再說(shuō)這黑色厚打底褲。前幾年,睿城的女人的確不論老幼都穿緊腿褲,不管是鬧市街頭,還是阡陌田間,到處晃動(dòng)著一截截或細(xì)瘦或粗壯的大腿。但是今年夏天,緊腿褲早已經(jīng)被闊到不能再闊的闊腿褲所替代,女人們又不懼老幼胖瘦,歡快而自信地甩起一片裙裾般的褲腿。說(shuō)實(shí)話,我挺喜歡女人追逐潮流,這至少說(shuō)明她們對(duì)生活還懷有熱愛(ài)之心。
大家都體悟出來(lái)了,嚴(yán)紫粉缺乏一種我們常說(shuō)的叫作“氣質(zhì)”的東西。“氣質(zhì)”是件很奇怪的事物,看不見(jiàn)、摸不著,可一旦人缺少了它,就像食物缺了鹽。依我多年的工作經(jīng)驗(yàn),我已能將嚴(yán)紫粉的家境、生活狀態(tài)猜個(gè)大概。“相由心生”這詞真可怕。
隨著化妝品的層層疊加,一張酷似王昭君的臉,漸漸浮現(xiàn)在嚴(yán)紫粉的臉上。這是她指定要變成的那個(gè)人。對(duì)于這一點(diǎn),我非常能夠理解,王昭君是舊時(shí)代的明星,有人想變成她的模樣并不奇怪。在我的“另一面”妝容館里,要我?guī)兔瘖y成古今中外各路明星的女人都有。只是,嚴(yán)紫粉看著鏡中的自己,突然睫毛一抖,眼角就滲出淚來(lái),淚水讓她的眼睛看起來(lái)?yè)渌访噪x。而這個(gè)時(shí)候,我剛好在給她畫(huà)眼線,突然滴出的淚珠讓我措手不及。
其實(shí)來(lái)我這里化妝的女人,個(gè)個(gè)都是開(kāi)心快樂(lè)、滿懷期待的。因?yàn)槲矣幸皇纸^好的化妝技巧,能讓女人的容貌連升三個(gè)等級(jí)都不止,這簡(jiǎn)直已經(jīng)成了睿城人盡皆知的事情了。因此,漸漸地,來(lái)我的妝容館化妝得提前預(yù)約,這令我看起來(lái)有點(diǎn)像醫(yī)生。“預(yù)約就診讓看病更便捷”,醫(yī)院的宣傳口號(hào)就是這么喊的。
“另一面”開(kāi)在一家商業(yè)綜合體后面的街上,交通便利,鬧中取靜。我在妝容館里擺了幾張樟木小桌、幾只圓頭圓腦的樟樹(shù)墩凳子,還有一臺(tái)意式咖啡機(jī)。每天早上,經(jīng)理藍(lán)妙芝過(guò)來(lái)上班時(shí),總是先打開(kāi)窗戶通風(fēng),給百合花澆水,然后燒開(kāi)水,煮咖啡,再把自己親手做的一些小甜點(diǎn)擺在碟子里,整個(gè)妝容館很快就漾起一股清新爽潔的香味。藍(lán)妙芝曾說(shuō)過(guò),這是妝容館最美妙的時(shí)刻,如清晨的原野一般柔和、純凈。這一切,與我在化妝界的名聲相得益彰。
我對(duì)化妝這事熟門(mén)熟路,不出十五分鐘就能完成一般的生活?yuàn)y,化個(gè)繁復(fù)的古典妝或極盡夸張的舞臺(tái)妝,也就半小時(shí)的事。但很多顧客總是不愿意踩著自己預(yù)約的時(shí)間點(diǎn)過(guò)來(lái),而是早早就到了,伸長(zhǎng)了脖子等著。她們看著其他女人化妝,一步步變得跟原先判若兩人,眼神是既羨慕又期待的。這又令我的妝容館看起來(lái)像一座衣香鬢影的醫(yī)院,她們看著我的眼神,就像患者望著醫(yī)生一樣。女人期盼自己變美,跟患者期盼自己病得醫(yī)治的心情是一樣的。只不過(guò),醫(yī)生會(huì)醫(yī)治人身體上的毛病,而我卻能醫(yī)這些女人的心病。
這些女人打扮得漂漂亮亮,多是為了參加一個(gè)讓她們感覺(jué)非常愉悅的聚會(huì):婚禮、生日派對(duì)、同學(xué)會(huì)、公司酒會(huì)等等。這個(gè)聚會(huì)能讓她們臉色紅潤(rùn)、笑靨如花,再加上我為她們私人定制的妝容,能瞬間提升她們的人脈。何況,能在我這家?jiàn)y容館接受五百元起步的化妝服務(wù)的女人,生活條件想必都還不錯(cuò)。因此,她們看起來(lái)都是快樂(lè)無(wú)憂的樣子,完全不像是有心病的人。
在等待化妝的空暇時(shí)光,顧客們喜歡三五成群地坐在一起,聊一些開(kāi)心的話題,不時(shí)發(fā)出一陣刻意壓低分貝的哄笑。這,甚至成了她們休閑聚會(huì)的另一種方式。
她們聊天的話題往往是這樣的——
我家那老公呀,心太貪,前段時(shí)間股票明明可以賺一百萬(wàn)了,就是舍不得拋,結(jié)果到現(xiàn)在只能賺五十萬(wàn)了。我本來(lái)還想換臺(tái)寶馬開(kāi)開(kāi)的,看來(lái)只能先等等了。不過(guò)也用不了幾天時(shí)間,他炒股還是有點(diǎn)水平的。
這個(gè)女人似乎是在嗔怪老公,語(yǔ)氣中卻溢出掩飾不住的驕傲來(lái)。
我的男朋友昨天向我求婚了。那時(shí)候,我們幾個(gè)同學(xué)正在酒吧喝酒,他突然帶著幾個(gè)哥們兒出現(xiàn)了,拿出一大束玫瑰花和一枚卡地亞鉆戒,單膝就跪下了。他的哥們兒齊聲喊:嫁給他,嫁給他!我完全沒(méi)有心理準(zhǔn)備,整個(gè)人都傻掉了。我的同學(xué)勸我說(shuō),看在他跪了這么久的分上,你就答應(yīng)了吧。既然大家都這么說(shuō),我只得同意了。
這個(gè)女孩子努力把那幸福到眩暈的一刻描繪得云淡風(fēng)輕,但我卻分明看到笑意在她的眉目間飛舞。
這次通過(guò)公平競(jìng)爭(zhēng),要綜合筆試、面試、就職演講等分?jǐn)?shù),才能最終確定一名人選。我的分?jǐn)?shù)排名第一,辦公室主任這位子是當(dāng)仁不讓的,我也有信心把它做好。
這位職場(chǎng)麗人語(yǔ)調(diào)平穩(wěn)、措辭簡(jiǎn)潔,自帶強(qiáng)大的氣場(chǎng),我不用看她的臉,也能感覺(jué)到上面涂滿了風(fēng)發(fā)意氣。
在等待化妝的這一刻,這幫女人如果說(shuō)有心病,那只有一個(gè)——長(zhǎng)得還不夠美。她們深切地?fù)?dān)心著自己的眼袋、皺紋、色斑、塌鼻梁、大餅?zāi)槨5齻兒芸鞎?huì)發(fā)現(xiàn)自己的擔(dān)心是多余的,任何臉部的缺陷到了我手里都不是問(wèn)題,胭脂水粉再加上我堪稱爐火純青的技藝,總是能幫她們掩蓋得恰到好處。隨著眼袋變平、皺紋變淺、皮膚變細(xì)膩、五官變立體,她們的心病瞬間就治愈了,比任何的心理疏導(dǎo)都來(lái)得管用。每當(dāng)這個(gè)時(shí)候,我就意識(shí)到自己當(dāng)初的選擇完全正確,在一次次的被認(rèn)可中,我?guī)缀蹩焱鼌s自己原來(lái)的職業(yè)了。
就這樣,我成了名副其實(shí)的女人堆里的男人。很多朋友問(wèn)我,天天跟這么多美女打交道,是不是感覺(jué)很爽?在外人看來(lái),這的確是件很“爽”的事情:每天有不同的女人朝我發(fā)嗲,嬌聲嬌氣地喊我“阿朗老師”;我可以光明正大地捧著她們光潔或粗糙的臉蛋,甚至可以居高臨下地(一般化妝時(shí),都是她們坐著,而我根據(jù)需要隨時(shí)變換身體站姿)看一眼她們從領(lǐng)口露出來(lái)的曲線。這應(yīng)該是很多男人羨慕不及的事吧。但是,每天從“另一面”出來(lái)后,我就像患上選擇性認(rèn)知障礙癥,完全意識(shí)不到地球上還有“女人”這種生物。我一般都是迅速回家,吃一碗母親煮的小餛飩,再翻翻書(shū)或聽(tīng)點(diǎn)音樂(lè),獨(dú)自消磨夜色。像我這樣長(zhǎng)得不算難看,經(jīng)營(yíng)著一家名氣十足的妝容館,每日進(jìn)賬可觀的男人卻沒(méi)有女朋友,周圍的人都表示十二分的不理解,甚至有人在背地里懷疑起我的性取向來(lái)。
你一定是個(gè)娘們兒,才會(huì)做這些娘們兒做的事,一個(gè)朋友嘲笑我說(shuō)。當(dāng)初,我放棄了那份看起來(lái)非常光鮮的工作,執(zhí)意要去學(xué)習(xí)化妝技術(shù)的時(shí)候,我的父親也這樣說(shuō):我辛辛苦苦培養(yǎng)了你,你卻去干這些娘們兒才做的事!他的臉色極其難看,烏云排山倒海般壓下來(lái)。我母親氣得當(dāng)場(chǎng)站立不穩(wěn),跌坐在地上。
即便如此,也沒(méi)能阻止我的決定。那時(shí)候,我住的小區(qū)里剛好開(kāi)著一家小小的化妝店,店里有兩個(gè)染著焦黃頭發(fā)、濃妝艷抹到面目難辨的外地女人,還有一個(gè)身形像柳枝般細(xì)長(zhǎng)、穿緊身衣瘦腿褲、一蹺蘭花指就露出十截彎曲長(zhǎng)指甲的男人。在沒(méi)有顧客的時(shí)候,他們就會(huì)在店里打情罵俏,完全忽略了從店門(mén)口經(jīng)過(guò)的路人甲、路人乙的眼睛。母親尋思著,不久的將來(lái),我也會(huì)變得跟這個(gè)男人一樣,她心里就急得要噴出一團(tuán)火來(lái)。
但母親估計(jì)錯(cuò)了,除了顧客,長(zhǎng)駐在我店里的女人只有藍(lán)妙芝一個(gè)。當(dāng)初招人手時(shí),為避瓜田李下之嫌,我本來(lái)想招個(gè)男店員,但又囿于所謂性取向的流言,便決定招一個(gè)外表實(shí)誠(chéng)、做事勤快、有責(zé)任心的已婚已育大姐。三十五歲,帶一兒一女,長(zhǎng)相平淡,言語(yǔ)不多,語(yǔ)調(diào)不高但干脆利落,藍(lán)妙芝完全符合我的要求。藍(lán)妙芝的工作時(shí)間是上午十點(diǎn)至晚上十點(diǎn),中晚餐由妝容館提供,月薪一萬(wàn)。這個(gè)工資不算低,不知是否因?yàn)檫@個(gè)原因,藍(lán)妙芝在我這邊更像一個(gè)管家,將工作做得簡(jiǎn)直無(wú)可挑剔。我跟藍(lán)妙芝,彼此配合默契。
在這樣一群熱鬧的女人當(dāng)中,除了我很少搭話外,還有藍(lán)妙芝也少言寡語(yǔ)。藍(lán)妙芝幫我打理店里的一切大小事務(wù),接預(yù)約電話、管接待、收錢,還會(huì)快速幫顧客做簡(jiǎn)單發(fā)型,往往跟妝容恰好匹配,而且是免費(fèi)服務(wù),顧客們都很喜歡她。顧客喜歡藍(lán)妙芝還有另一個(gè)原因,就是她手工制作的點(diǎn)心非常好吃,蔓越莓餅干、綠豆餅、芝士面包,裝在密封玻璃碗里,從家里帶過(guò)來(lái),供顧客品嘗。
藍(lán)妙芝應(yīng)該是個(gè)懂生活的女人,雖然衣著平常,神情卻很恬然,似籠罩著一層溫煦的陽(yáng)光。多數(shù)時(shí)候,她就安靜地坐在前臺(tái)的沙發(fā)上,以一種隔岸觀火的姿態(tài),圍觀這一群熱鬧的女人,身子慢慢地陷入沙發(fā)圈的陰影里去。但她卻又能明察秋毫,知道誰(shuí)的杯子見(jiàn)底了,誰(shuí)的妝化好了可以做頭發(fā)了,就會(huì)及時(shí)起身,周到地為顧客提供服務(wù),倒水、接電話、做頭發(fā),有條不紊,身影輕巧地穿梭著。大家很難將兩者等同起來(lái),往往會(huì)看看她,又看看前臺(tái),確定只是同一個(gè)人之后,才又繼續(xù)剛才的聊天。
于聲譽(yù)鵲起的“另一面”來(lái)說(shuō),藍(lán)妙芝一切都拿捏得剛剛好。
二
從開(kāi)店至今,在我這里化妝時(shí)哭了的人,只有嚴(yán)紫粉一個(gè)。
“嚴(yán)紫粉”這個(gè)名字是她預(yù)約登記時(shí)報(bào)上的,我感覺(jué)或許不是她的真名。不過(guò)這并不見(jiàn)得會(huì)引起我的反感。其實(shí)我這個(gè)眾多女人口稱的“阿朗老師”,也并不姓朗,連名字當(dāng)中也沒(méi)有一個(gè)“朗”字。我本名叫小強(qiáng),因?yàn)槟莻€(gè)眾所周知的原因,我極不喜歡聽(tīng)別人叫我“小強(qiáng)”,尤其當(dāng)面說(shuō)什么“打不死的小強(qiáng)”之類的話。我給自己取了個(gè)跟“小強(qiáng)”有牽強(qiáng)附會(huì)關(guān)系的名字——朗逸峰,每當(dāng)聽(tīng)別人喊我“阿朗老師”,我便覺(jué)得自己瞬間高大上起來(lái),這跟女人來(lái)“另一面”化妝是有著異曲同工之妙的。
嚴(yán)紫粉是一個(gè)人踩著預(yù)約的時(shí)間點(diǎn)過(guò)來(lái)的。單獨(dú)來(lái)我這里化妝的顧客寥寥可數(shù),加之她眼角突然滴出的淚,讓我不由得暗自忖度了一下。周圍的那些女人都太直白了,她們昨天跟誰(shuí)一起吃的飯、今天化好妝之后要去做什么、明天跟誰(shuí)有約等等話題,以及家里七大姑八大姨的細(xì)碎瑣事,只要她們認(rèn)為能夠搬出來(lái)作為談資的,都統(tǒng)統(tǒng)從她們的口中跑出來(lái),在眾朋友的唇齒間流傳。
你怎么了?我低聲問(wèn)嚴(yán)紫粉。
嚴(yán)紫粉臉上似覆蓋著一層糨糊,將整張臉龐刷得嚴(yán)嚴(yán)實(shí)實(shí),連臉上的毛孔都不曾顫動(dòng)一下。我懷疑自己說(shuō)出的話遁入了空氣,加之我本身也沒(méi)有過(guò)多探究別人內(nèi)心的欲望,便不再開(kāi)口說(shuō)話。在過(guò)去的幾年里,我做了太多這類事情,早已厭倦了。
嚴(yán)紫粉預(yù)約登記的年齡是二十五歲,但她渾身散發(fā)著病懨懨的氣息,似一株停止生長(zhǎng)的植物,讓人猜不透時(shí)間究竟靜止在哪一刻。這種不舒展的感覺(jué),令我也像渾身上下箍了個(gè)木桶。藍(lán)妙芝顯然發(fā)現(xiàn)了我的異樣,走過(guò)來(lái)附在我耳邊悄聲說(shuō),阿朗老師,下一位顧客預(yù)約的時(shí)間快到了,她說(shuō)自己要趕去參加同學(xué)會(huì),希望您快點(diǎn)幫她化一下。藍(lán)妙芝說(shuō)完,快速閃回了前臺(tái),擺出慣常的單手支腮的姿勢(shì),令人懷疑她剛才并沒(méi)有移動(dòng)過(guò)。
說(shuō)實(shí)話,我極不喜歡為嚴(yán)紫粉這樣的顧客化妝,她身上有股沉重的力量,不知不覺(jué)地拉著身邊的人往下墜。生活已經(jīng)很不易,誰(shuí)也不愿意再讓別人的煩惱來(lái)碾軋自己的靈魂,誰(shuí)都沒(méi)有這個(gè)義務(wù)。雖然大家都認(rèn)為我的“另一面”妝容館生意興隆,我儼然已是化妝界的大師級(jí)人物,算是名利雙收了。連當(dāng)初極力反對(duì)我的父母,也漸漸忘記了曾經(jīng)做出惋惜的表情。他們每天有忙不完的活兒,陽(yáng)臺(tái)上的菜要澆、餐桌上的燭臺(tái)要換精油、地下室的臺(tái)球桌要擦,在鄉(xiāng)間養(yǎng)成的習(xí)慣,讓他們一日不勞作便渾身不自在。雖然我日日早出晚歸,極少去享用這些東西,但兩位老人的手總是習(xí)慣性地在它們之間穿梭,將它們伺候得滋潤(rùn)舒適,就像在伺候我一樣。但這一切,并不代表我人生的這件睡袍比別人的華美。在夜深人靜時(shí),我也會(huì)數(shù)算華美睡袍里的虱子:比如,我總是無(wú)法愛(ài)上一個(gè)女孩子;比如,我會(huì)時(shí)常想起那個(gè)叫“靜子”的女孩,正用一雙哀怨的眼睛盯著我。
為嚴(yán)紫粉化妝的過(guò)程顯得冗長(zhǎng)而枯燥,雖然這也只是半小時(shí)的事。在工作中,枯燥與疲憊總是如影隨形,面對(duì)這位憂郁的顧客,當(dāng)年曾有過(guò)的深深的疲憊感,又緩緩升起在我心頭,但我還是堅(jiān)持為她化好了妝。
嚴(yán)紫粉屬于妝前妝后判若兩人的女孩子,這不僅僅是因?yàn)槲一瘖y技術(shù)好,也因?yàn)樗龑儆谀欠N臉部硬件好、軟件卻極差的人,我修改了她的軟件,立刻就襯托出硬件設(shè)施來(lái)了。嚴(yán)紫粉在前臺(tái)付了五百元現(xiàn)金,我聽(tīng)到藍(lán)妙芝問(wèn)她,要做頭發(fā)嗎?免費(fèi)的。前臺(tái)邊漏出一小片的寂靜。藍(lán)妙芝仍和善地對(duì)她說(shuō),下回可以刷支付寶或銀行卡,更方便。嚴(yán)紫粉仍然沒(méi)有回話,做低眉垂目狀,將玻璃門(mén)打開(kāi)一條縫,像一條瑟縮的魚(yú)一樣,從縫隙間滑了出去。她的連衣短裙被玻璃門(mén)掀起一個(gè)小角,露出了繃著打底褲的臀部。
店堂里幾位女人的目光跟著嚴(yán)紫粉飄出了門(mén)外,好半天才收回來(lái)。她們先是驚訝地互相望望,然后不約而同地表示出像模像樣的嘲諷——
這人有病吧?這都什么天氣了,還穿得這么厚?
人家打擺子,要發(fā)汗呢!
其實(shí)她長(zhǎng)得有什么好看的,還不是全靠阿朗老師的化妝嗎?
還化妝成王昭君呢,也不看看自己的氣質(zhì)配不配得上,丑人多作怪!
阿朗老師,有個(gè)女人嬌滴滴地拖長(zhǎng)了聲調(diào)道,你店里怎么會(huì)有這樣的客人嘛!
是呀,這樣的人也來(lái)你店里化妝?眾人附和道,仿佛與嚴(yán)紫粉這樣的女孩子同臺(tái)化妝,是件有辱身份的事。
她也是顧客,我望著玻璃門(mén)外那個(gè)快速飄遠(yuǎn)的身影回答道。這時(shí)候的嚴(yán)紫粉,像一只高頻率擺動(dòng)的鐘擺。
對(duì)啊,人家畢竟是付了錢的,大家都是顧客嘛,藍(lán)妙芝說(shuō)。
三
到了夜晚七點(diǎn)以后,“另一面”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這個(gè)時(shí)間點(diǎn),基本沒(méi)有人來(lái)化妝了,來(lái)我店里的,只有從宴樂(lè)場(chǎng)上退下來(lái)的女人們。
七點(diǎn)之前,在我這里化好妝的女人們已經(jīng)帶著比往常漂亮數(shù)倍的容顏,活躍在各自的戰(zhàn)場(chǎng)上,吃飯、喝酒、聚會(huì)都在如火如荼地進(jìn)行著,杯來(lái)箸往、歌舞升平。七點(diǎn)之后,她們中有一小部分人會(huì)回到我這里來(lái),卸妝。在我店里卸一次妝,統(tǒng)一收費(fèi)五百元,跟化個(gè)妝的起步價(jià)一樣。剛開(kāi)始,有人表示不解:化妝是靠技術(shù)吃飯的,還要用上各樣名牌產(chǎn)品,收費(fèi)高可以理解,但卸妝而已,怎么定那么高的價(jià)?我不言語(yǔ),一副你們愛(ài)來(lái)不來(lái)的表情。最終的結(jié)果是,但凡在我店里卸過(guò)妝的人,沒(méi)有一個(gè)認(rèn)為性價(jià)比不高的。
卸妝的女人都是單身前來(lái)的,偶爾碰到熟人,也只是淡淡地打個(gè)招呼,仿佛幾個(gè)小時(shí)前,交頭接耳、一起吃點(diǎn)心的不是她們。她們很守秩序地坐在店堂里等,不再吃東西,也不再喝水,一般都是低頭玩著手機(jī),刷朋友圈,看八卦。撕下這層漂亮的假面,用真實(shí)的面目面對(duì)熟人,大家都有難度。我審時(shí)度勢(shì),根據(jù)顧客需要,特意用磨砂玻璃隔出一個(gè)帶后門(mén)的卸妝間,顧客卸完妝后,可以直接從后門(mén)離開(kāi)。于是,幾乎所有的女人卸完妝后,都低著頭,從后門(mén)匆匆離去。
卸妝時(shí),她們臉上泛著從各種場(chǎng)合帶來(lái)的興奮之情,坐在轉(zhuǎn)椅上,任由我一點(diǎn)一點(diǎn)抹去她們姣好的妝容。這時(shí)候,我清楚地看到,她們的興奮之情一點(diǎn)一點(diǎn)褪去,隨著抬頭紋、眼袋、法令紋、色斑等等不美好的東西一一現(xiàn)身,她們的情緒陡然低落下去了。其實(shí)她們化妝前、卸妝后的容顏并未起變化,但不知道為什么,她們能開(kāi)心來(lái)化妝,卻都無(wú)法接受卸妝后的自己。難道是我為她們化的妝或者那一場(chǎng)奢華宴會(huì),讓她們?cè)趲讉€(gè)小時(shí)之內(nèi)蒼老了十幾歲?
這時(shí)候,埋在妝容下面的酸楚泛上她們心頭,她們往往會(huì)開(kāi)口述說(shuō)一些由外貌引發(fā)的話題——
阿朗老師,你看我眼袋大對(duì)不?眼袋大是因?yàn)槲宜哔|(zhì)量不好。這位顧客告訴我,她睡眠不好的原因是:結(jié)婚八年,延醫(yī)診治數(shù)年,吃過(guò)藥石無(wú)數(shù),卻始終懷不上孩子。她可以無(wú)視公婆鄙夷的目光,也可以忽略半夜嗲聲嗲氣打進(jìn)老公手機(jī)的電話,但她無(wú)法隱瞞內(nèi)心的焦慮,假如不能為夫家開(kāi)枝散葉,接下來(lái)可能要面臨一些非常棘手的問(wèn)題。這個(gè)就是夸老公即便在全線飄綠的時(shí)候,炒股還能賺五十萬(wàn)并且馬上穩(wěn)賺更多的女人。
阿朗老師,我的鼻梁看起來(lái)有點(diǎn)怪異對(duì)不?這位顧客說(shuō),那是因?yàn)樗焐橇核剑朔Q“塌鼻頭”,一直沒(méi)有追求者,后來(lái)不得已,去做了隆鼻術(shù)。豈料手術(shù)填充物出了問(wèn)題,她的鼻梁紅腫了幾個(gè)月,又去另一家正規(guī)醫(yī)院做了填充物取出術(shù)。一來(lái)二去,鼻梁看起來(lái)就非常怪異了。現(xiàn)在的未婚夫吧,其實(shí)就是個(gè)“二流子”,但派頭倒是十足,臺(tái)型扎得牢,什么卡地亞鉆戒,那不過(guò)是她自己省吃儉用攢錢買的,然后讓他轉(zhuǎn)交一下而已。這個(gè),就是滿臉幸福陶醉于男友向她求婚的女孩。
至于那個(gè)妝容高雅、談吐舉止得體的白領(lǐng)麗人,她的煩惱無(wú)疑比別人更多。不敢交男朋友,怕那個(gè)一直覬覦她,又能不動(dòng)聲色地給她帶來(lái)好處的上司冷落她;職場(chǎng)無(wú)情,人與人之間總是赤裸裸地顯出某種利益關(guān)系來(lái);花銷大,其實(shí)賺錢又不多,等等。這個(gè)時(shí)候的她,臉上浮起一片片斑點(diǎn),是我無(wú)論用何種卸妝液都無(wú)法去除的。
凡此種種,令整個(gè)妝容館里彌漫著一層名叫“焦慮”的霧霾。大家都似其中的一個(gè)大分子,飄起,連成一片,形成更大的塵埃,如一張巨大的幕,將她自己和身邊的人都覆蓋在幕布之下。大概很多人以為,能夠不費(fèi)吹灰之力窺探到別人的內(nèi)心,那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其實(shí)不然。每當(dāng)我聽(tīng)到一個(gè)人的內(nèi)心故事,下回再在眾人面前見(jiàn)到這個(gè)人時(shí),便覺(jué)得自己有了某種義務(wù),要替她做好掩護(hù)工作。這個(gè)故事便成了自己的一樁心事,像一枚釘子,扎進(jìn)了自己的心房,不用多久,內(nèi)心就千瘡百孔了。我以前做的工作就是這樣,做到后來(lái),心中積累的垃圾簡(jiǎn)直拖累得我無(wú)法邁動(dòng)腳步。我去聽(tīng)講座,做心理疏導(dǎo),參加情景劇,把幫助別人的途徑一一用了一遍,但都無(wú)法奏效。及至后來(lái)發(fā)生了“靜子事件”,我便決絕地放棄了這份工作。只是沒(méi)想到,當(dāng)上化妝師的我,居然也會(huì)陰差陽(yáng)錯(cuò)地充當(dāng)心理醫(yī)生的角色。
藍(lán)妙芝起先會(huì)在我旁邊幫忙,后來(lái)大概也是聽(tīng)多了類似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故事,而且她同為女人,還得絞盡腦汁找出幾句話來(lái)安慰對(duì)方,弄得心力交瘁。后來(lái),我在為顧客卸妝的時(shí)候,她干脆不進(jìn)來(lái)了,坐在柜臺(tái)里昏昏欲睡,一束昏黃的燈光打在她臉上。
現(xiàn)在,你們知道我為什么把卸妝的收費(fèi)定價(jià)這么高了吧?
這一次,門(mén)一推一合,進(jìn)來(lái)的是嚴(yán)紫粉。我心里暗自“咯噔”了一下,我承認(rèn)自己沒(méi)料到嚴(yán)紫粉居然會(huì)舍得花五百元錢來(lái)卸妝,我上面說(shuō)過(guò)了,她看起來(lái)并不像家境優(yōu)渥的女孩子。當(dāng)然我臉上并未起任何波瀾,她能夠排隊(duì)進(jìn)入卸妝間,藍(lán)妙芝應(yīng)該已經(jīng)把“交納卸妝費(fèi)”這類事情安排妥當(dāng)了。
嚴(yán)紫粉還是一聲不吭,這令我與她的近距離接觸顯得很尷尬。雖然平時(shí)顧客跟我鋪陳她們的故事時(shí),我都是似聽(tīng)非聽(tīng)的,但那至少有聲音在我跟顧客之間流動(dòng)。有了聲音的流動(dòng),孤男寡女會(huì)少很多尷尬。眼下,我只能自己制造一點(diǎn)流動(dòng)的聲音了。
我問(wèn)她,你住在這附近嗎?
她只應(yīng)了一聲低低的“嗯”。
你化妝成王昭君,是要參加一個(gè)古裝聚會(huì)嗎?
還是低低的一聲“嗯”。
現(xiàn)在回去有點(diǎn)遲了,路上要注意安全。
嗯。
這三聲“嗯”,一樣的分貝,一樣的腔調(diào),仿佛第二聲、第三聲只是第一聲的拷貝罷了。
我沒(méi)有了交流的欲望,不再言語(yǔ)。或許我本就沒(méi)有交流的欲望,我只是想制造一點(diǎn)流動(dòng)的聲音罷了,只是現(xiàn)在連這點(diǎn)想法也銷聲匿跡了。
嚴(yán)紫粉一直低著頭,沒(méi)有看鏡子。卸完妝后,她從后門(mén)走了,還是低著頭。嚴(yán)紫粉低著頭孤苦無(wú)依的樣子,又令我想起了靜子。——那天,我?guī)е睦韴F(tuán)隊(duì)的人,頭上頂著陽(yáng)光,臉上堆著笑,一起去那個(gè)小山村看望靜子。我以為靜子會(huì)很開(kāi)心,沒(méi)想到,她只在我闖進(jìn)她平靜生活的一剎那,抬起頭,幽怨地盯了我一眼。然后,她始終都像嚴(yán)紫粉一樣低著頭,我問(wèn)她什么,她都只是低低地回答“嗯”。
事隔三年,不知是命運(yùn)的安排,還是純屬巧合,我居然又遇見(jiàn)了一個(gè)跟靜子一樣陰郁寡言的女孩子。也許是因?yàn)閲?yán)紫粉的出現(xiàn),再加上她的出現(xiàn)又勾起了我對(duì)靜子的回憶,我今天比往常更加緘默一些。藍(lán)妙芝沒(méi)有問(wèn)我怎么了,或許她已經(jīng)猜到個(gè)大概,或許她的秉性跟我一樣,對(duì)別人的內(nèi)心世界都沒(méi)有過(guò)多好奇心。
下班時(shí)分,藍(lán)妙芝在消毒茶具、拖地板,我在翻看第二天的預(yù)約登記簿,準(zhǔn)備好可能用到的各樣物品。藍(lán)妙芝的預(yù)約登記工作做得非常到位,不僅登記了顧客的姓名、年齡、手機(jī)號(hào)、化妝時(shí)間,還會(huì)寫(xiě)上出席場(chǎng)合(這是在顧客愿意告之的情況下)、本次化妝要求等。我只要一看這個(gè)本子,便對(duì)第二天要做的工作了然于心。順便說(shuō)一句,我工作時(shí)有個(gè)非常好的習(xí)慣,就是每一樣化妝品、化妝工具,用過(guò)后就馬上回歸原位。因此,一位顧客化妝結(jié)束,第二位顧客過(guò)來(lái)時(shí),我的工作臺(tái)永遠(yuǎn)是整潔清爽的。顧客們對(duì)這一點(diǎn)非常贊許,說(shuō)這才是一家高檔次的妝容館該有的面貌。
清尾工作完畢、準(zhǔn)備工作就緒,我才像塵埃落定一般,“啪嗒”一聲將大門(mén)鎖上。老板,明天見(jiàn)。每天下班,藍(lán)妙芝都會(huì)說(shuō)這么一句。在上班時(shí)間,藍(lán)妙芝像其他顧客一樣喊我“阿朗老師”,但是下班告別時(shí),她必叫我“老板”,我到現(xiàn)在都無(wú)法適應(yīng)。我曾經(jīng)提醒過(guò)她,下班了可以叫我阿朗,甚至就算叫我“小強(qiáng)”也比叫我“老板”強(qiáng)。但她說(shuō)這是規(guī)矩,沒(méi)有規(guī)矩不成方圓。說(shuō)完這一句,她就開(kāi)著那輛二手的POLO,消失在夜幕中。
四
第二天,嚴(yán)紫粉當(dāng)然沒(méi)有過(guò)來(lái)。顧客們都在自己的小范圍內(nèi)交流著一些有趣的話題,不知有沒(méi)有人會(huì)提起“嚴(yán)紫粉”這個(gè)名字,就算有人提起,她也不過(guò)是個(gè)有趣的素材之一吧?不知為什么,我的腦海里一直有兩張臉蛋在飄浮,交織在一起,又分開(kāi)。嚴(yán)紫粉,靜子,我有時(shí)候甚至分不清到底誰(shuí)是誰(shuí),她倆雖然長(zhǎng)相迥異,但是都有一雙哀怨的眼睛。晚飯時(shí)分,我甚至翻開(kāi)預(yù)約登記簿,找到了嚴(yán)紫粉留下的號(hào)碼,看著這一串?dāng)?shù)字,我反而心悸了,重重地將本子合上。
這樣的狀態(tài)持續(xù)到一周之后的晚上。下班后,照例,藍(lán)妙芝在打掃衛(wèi)生,我在瀏覽預(yù)約登記簿。我又看到了嚴(yán)紫粉的名字,她約的是第二天的下午四點(diǎn),這一次,她要化妝成聶小倩的模樣。倩女幽魂?我暗自吃了一驚。
嚴(yán)紫粉明天要來(lái)化妝,我對(duì)藍(lán)妙芝說(shuō)。話說(shuō)出口后,我發(fā)覺(jué)自己有點(diǎn)奇怪,明天有哪些顧客要來(lái),藍(lán)妙芝比我先知道。何況嚴(yán)紫粉只是個(gè)普通顧客,我為何要特地跟藍(lán)妙芝提起她呢?
是的,要化妝成聶小倩,這女孩看起來(lái)有點(diǎn)內(nèi)向啊。藍(lán)妙芝頗為擔(dān)憂地說(shuō)。
我們都不再說(shuō)什么,默默地完成了清尾工作,直到我“啪嗒”一聲將大門(mén)上鎖。
嚴(yán)紫粉這次沒(méi)有掐著時(shí)間點(diǎn)來(lái),而是提前了半小時(shí)。她還是穿著那件淡粉色的長(zhǎng)袖連衣短裙,黑色厚打底褲,手里拎著一只紅色塑料袋。進(jìn)店后,她就從袋子里掏出一些什么東西來(lái),攥在手心里,分別在幾張樟木小桌前站了片刻,用低得幾乎聽(tīng)不到的聲音說(shuō),吃水果。然后,手一松,幾只小小的桃子放到了那幾個(gè)正談笑風(fēng)生的美女面前。
店堂里的優(yōu)雅女人顯然被嚴(yán)紫粉的舉動(dòng)搞蒙了,她們停止了交談,愣愣地看了她一下,像突然明白過(guò)來(lái)似的,帶著禮貌點(diǎn)點(diǎn)頭,互望一眼,端起各自的咖啡杯啜起咖啡來(lái)。嚴(yán)紫粉在她們桌邊站了一會(huì)兒,終于走開(kāi)了,找了個(gè)單獨(dú)的位子坐下來(lái),在與世隔絕的寂靜里,朝墻邊貼過(guò)去,貼過(guò)去。
藍(lán)妙芝拿了一碟點(diǎn)心放在嚴(yán)紫粉面前,問(wèn)她,喝咖啡,還是喝茶?
嚴(yán)紫粉客氣地說(shuō),不用,謝謝。聲音細(xì)弱得像一根窸窣彈動(dòng)的皮筋。
輪到嚴(yán)紫粉化妝時(shí),她正襟危坐在我面前的轉(zhuǎn)椅上,眼睛看向地面,整個(gè)身子微微顫抖。我讓藍(lán)妙芝拿了一件披肩給她披上,說(shuō),今天這個(gè)妝有點(diǎn)特別,怕散粉抖下來(lái)弄臟了你的衣服。
嚴(yán)紫粉這次化妝時(shí)沒(méi)有流淚,只是一對(duì)臥蠶眉始終微蹙著。這是一對(duì)人工文上去的眉毛,眉色濃黑,眉型單板,業(yè)內(nèi)人士只消一眼便可看出它們出自小作坊,出自那些只會(huì)洗洗臉、敷敷面膜便敢自稱美容整形師的人員之手,帶著雕琢過(guò)度的濃重氣息橫在她臉上。當(dāng)然,這一切都不妨礙我把她化妝成聶小倩,沒(méi)有金剛鉆不攬瓷器活兒,要是沒(méi)有兩把刷子,我的“另一面”也不會(huì)風(fēng)生水起。
嚴(yán)紫粉化好妝后,藍(lán)妙芝依慣例問(wèn)她,要做發(fā)型嗎?我剛學(xué)會(huì)做一款發(fā)髻,跟你的妝容很配。嚴(yán)紫粉搖搖頭,付過(guò)錢后,便從門(mén)縫間滑了出去。室外的熱浪從玻璃門(mén)的縫隙間撲了進(jìn)來(lái)。
嚴(yán)紫粉走了,那幾個(gè)憋悶了好久的顧客長(zhǎng)噓一口氣,立刻嘰嘰咕咕地交頭接耳起來(lái)。藍(lán)妙芝明白她們的意思,提了一只垃圾桶,將幾張桌子上的桃子撣了進(jìn)去。當(dāng)然,嚴(yán)紫粉也沒(méi)有吃藍(lán)妙芝放在她桌子上的點(diǎn)心。藍(lán)妙芝沒(méi)有表示出任何不愉快,神色安然地將點(diǎn)心倒進(jìn)了垃圾桶。
那么小的桃子,怎么吃啊?一位顧客說(shuō)。
放在塑料袋里,還直接用手拿出來(lái)放在桌子上,塑化劑、細(xì)菌一大堆,誰(shuí)敢吃!有人應(yīng)聲道。
這都什么天氣了,她還穿這么厚的衣服,該不是精神有毛病吧?
人家阿朗老師心疼她呢,還給她披披肩,怕她空調(diào)房里著涼?
女人們討論得非常熱烈,我沒(méi)有搭腔。她們當(dāng)中很多都是我的老顧客,我們彼此像老朋友一般插科打諢互不計(jì)較。藍(lán)妙芝安靜地穿過(guò)這一片聒噪聲,臉上掛著似有似無(wú)的微笑。如果換成其他女人,很可能會(huì)在此時(shí)接上話茬,狠狠地抨擊一下嚴(yán)紫粉。嚴(yán)紫粉沒(méi)有吃自己好心放在她面前的點(diǎn)心,這擺明了是不友好的表現(xiàn)。有時(shí)候,我真的挺欣賞藍(lán)妙芝,無(wú)論在怎樣紛亂的環(huán)境中,她總是能夠保持鎮(zhèn)定。
藍(lán)妙芝經(jīng)過(guò)我身邊時(shí),朝外努努嘴,示意我看外面。落地玻璃窗外,一個(gè)中年婦女剛好轉(zhuǎn)過(guò)身去,緊走幾步想追上嚴(yán)紫粉,卻不料嚴(yán)紫粉走得更快一些,她始終追不上,只得一前一后地走著。這個(gè)身形緊繃、四肢快速擺動(dòng)的嚴(yán)紫粉,跟在我店里瑟縮沉默的嚴(yán)紫粉,儼然不是同一個(gè)人。
我料定嚴(yán)紫粉晚上會(huì)來(lái)卸妝,也料定還會(huì)有故事。果然一切都如我所料,只不過(guò)故事的主角變成了下午站在玻璃窗外的中年婦女,嚴(yán)紫粉的母親。當(dāng)嚴(yán)紫粉卸完妝從后門(mén)走了的時(shí)候,她母親從我的卸妝間里冒了出來(lái)。藍(lán)妙芝歉疚地說(shuō),我沒(méi)能攔得住她。我擺擺手,表示自己可以跟嚴(yán)紫粉母親聊幾句。
她母親先是客套地感謝過(guò)我把她女兒化妝得很漂亮,然后話鋒陡轉(zhuǎn),正色道,我女兒剛參加工作,還要以工作為重,我不允許女兒化濃妝,更不同意她去參加什么化裝舞會(huì),反正跟工作無(wú)關(guān)的事情都不可以。
我愕然,還來(lái)不及發(fā)表意見(jiàn),這位母親緊接著語(yǔ)重心長(zhǎng)、苦口婆心地向我舉出了一大堆事例:我女兒之前參加過(guò)市演唱團(tuán),我用了一年時(shí)間,終于讓她放棄了唱歌這個(gè)念頭。我們是正經(jīng)人家的姑娘,我又只有這么一個(gè)孩子,在臺(tái)上扭扭唱唱的算什么事?她原來(lái)有兩個(gè)當(dāng)模特的QQ好友,我發(fā)現(xiàn)后,趁她夜里睡著了,偷偷進(jìn)她的QQ,把這兩個(gè)好友刪掉了。雖然她知道后好幾天不理我,但我認(rèn)為跟模特聊天就是不妥的,聊多了,就會(huì)生事端。她現(xiàn)在生我的氣沒(méi)關(guān)系,等她懂事了,她會(huì)感激我的。
……
嚴(yán)紫粉母親身穿一套廉價(jià)的黑色衣服,嘴巴連續(xù)一開(kāi)一合,仿佛一只老鷹正拍打著翅膀,驅(qū)趕企圖靠近她女兒的外人。說(shuō)到動(dòng)情處,她聲色哽咽,幾乎要落下淚來(lái)。真是可憐天下父母心,我腦子冒出了這句老話。我試探著跟她溝通,你這樣的管教,是不是太嚴(yán)苛了點(diǎn)呢?成年人得有自己的思想,這樣才是真正健康的人,我認(rèn)為她過(guò)點(diǎn)自己喜歡的生活并沒(méi)有錯(cuò)。
她現(xiàn)在還不懂事,當(dāng)然得由我管著她啦!我很后悔自己沒(méi)把她管好。嚴(yán)紫粉母親見(jiàn)我不肯配合她的思想教育工作,情緒非常激動(dòng),臉漲得緋紅。
我不想跟這樣的母親計(jì)較什么,便客氣地指指磨砂玻璃后面那一片隱含的世界,暗示她外面還有其他顧客,如果你不想自己的女兒成為別人的笑談,最好就此打住。嚴(yán)紫粉母親或許習(xí)慣了指揮別人的生活,所以對(duì)我的回應(yīng)表示極度不滿意,又不便于進(jìn)一步發(fā)作,只得使勁抿著嘴巴,上下嘴唇不住地顫動(dòng),憤憤然地走了。
卸妝間只是個(gè)用磨砂玻璃隔斷的相對(duì)獨(dú)立的空間,我相信我們的對(duì)話早已被在外面等候的顧客聽(tīng)得一清二楚。雖然晚上的顧客并不像白天那么多,但是只要有人聽(tīng)到了,那么就有散播出去的無(wú)限可能性。
當(dāng)藍(lán)妙芝跟我說(shuō)“老板,明天見(jiàn)”的時(shí)候,我原本已經(jīng)啟動(dòng)了汽車,卻不知為何感覺(jué)心里空空,便給家里打了個(gè)電話,又將汽車上鎖,決定去附近商業(yè)綜合體一樓的酒吧喝一杯。自從父母與我同住以來(lái),我極少有夜生活,母親聽(tīng)著話筒里震耳欲聾的音樂(lè)聲,非常擔(dān)憂地囑咐我要少喝酒、早回家。在母親眼里,再大的孩子也是孩子。
我一個(gè)人坐在角落里喝黑啤,燈光昏暗,映得酒色濃釅。有人在背后拍我的肩膀,我轉(zhuǎn)過(guò)頭,是大勇。他故意學(xué)了妝容館女顧客的口吻喊我:阿朗老師!
我淡淡一笑,你也在,一個(gè)人?
他們也在。大勇朝后擺擺手,我之前心理治療團(tuán)隊(duì)的隊(duì)友們同時(shí)走了過(guò)來(lái),學(xué)了大勇的口吻,一起揶揄地喊我:阿朗老師!
在想獨(dú)自靜靜的夜晚,我居然碰到了以前的隊(duì)友,便招呼大家過(guò)來(lái)一起坐,晚上就由我做東了。在開(kāi)“另一面”妝容館之前,我是這支團(tuán)隊(duì)的帶頭人,白天我們是別人的心靈垃圾桶,晚上我們經(jīng)常相聚酒吧,互相傾吐心中的煩懣。但這一次相聚,我已經(jīng)成了局外人,所以我們更像一群心理治療師面對(duì)一位患者。幸而他們對(duì)我很寬容,沒(méi)有追問(wèn)我過(guò)得好不好,怎么還沒(méi)找女朋友。在觥籌交錯(cuò)間,我們又談起了以前做過(guò)的案例。他們告訴我,那個(gè)因家暴而三次離家出走逃到睿城的黑龍江女人,她老公表示不再打她了,她要回老家跟家人團(tuán)聚了;那個(gè)因幼年受過(guò)侵害而不敢獨(dú)自入睡的女孩,終于能夠關(guān)上燈獨(dú)處了。這兩位女性都是我離開(kāi)心理治療團(tuán)隊(duì)后特別牽掛的人,今天聽(tīng)到她們的好消息,我很欣慰,便狠狠地跟舊友們碰杯,感謝他們?yōu)槲倚断铝艘恍┬睦戆ぁ字徊AП瑫r(shí)相觸,發(fā)出清脆的聲響。
但是,靜子呢,你們有沒(méi)有她的消息?我的話一出口,大家都沉默了,低頭看著自己的酒杯,杯沿一圈圈的啤酒泡沫正在緩緩地消逝。大勇搭著我的肩膀說(shuō),沒(méi)有消息就是好消息,靜子不會(huì)有事的,你不要擔(dān)心。
五
第二天,以及以后的每一天,來(lái)到“另一面”的顧客們,都在東一撮、西一撮地竊竊私語(yǔ),先是低聲講話,然后放肆地爆發(fā)出一陣快樂(lè)的笑聲。我無(wú)法肯定是不是嚴(yán)紫粉給她們帶來(lái)了這么多的歡樂(lè),但她們的對(duì)話還是零零星星地跑進(jìn)我的耳朵——
有其母,必有其女。看這一家人,還來(lái)這里化妝,打腫臉充胖子吧!
瞧她娘那個(gè)管事婆的模樣,干脆以后連女兒結(jié)婚、生孩子這檔子事也給包了吧!
可不是,我看她老娘得現(xiàn)場(chǎng)指導(dǎo)才行,可不把她女婿嚇個(gè)魂飛魄散?
類似的葷話逗得這群女人開(kāi)懷大笑。甚至連在等候卸妝時(shí),原本極少聊天的她們,也都在三三兩兩地用舌根嚼著嚴(yán)紫粉的故事。
其實(shí)今天晚上,妝容館里還發(fā)生了另外一個(gè)故事。在卸妝時(shí),那個(gè)曾經(jīng)向眾人夸耀男友當(dāng)眾求婚的女孩子,當(dāng)著我的面哭得很厲害,說(shuō)白了也就是當(dāng)著外面那些等候卸妝的顧客的面哭。原來(lái),原來(lái),她抽咽著說(shuō),他曾經(jīng)被兩個(gè)富婆包養(yǎng)著,怪不得跟我約會(huì)時(shí)經(jīng)常遲到,怪不得對(duì)我沒(méi)有“性趣”。本來(lái)我們馬上要訂婚了,我真傻,還好我朋友提醒了我,得去查一查對(duì)方的底細(xì),比如身份證號(hào)。沒(méi)想到還真中槍了,身份證居然是假的,我就知道會(huì)有狗血?jiǎng)∏榘l(fā)生了,只不過(guò)沒(méi)想到,這事情來(lái)得這么狗血……
店堂里安靜了片刻,估計(jì)大家都在屏息聽(tīng)卸妝間里的現(xiàn)場(chǎng)直播。但很快,她們又開(kāi)始聊起來(lái)了。畢竟狗血事件在生活中多不勝數(shù),她們已經(jīng)審美疲勞了,但是將別人的生活撕開(kāi)一個(gè)小口子,從這個(gè)口子里窺視里面的世界,是件多么富有意味的事情。她們樂(lè)此不疲,在窺視中獲得了心理上的愉悅。
在這樣一片舉眾皆歡的笑聲里,嚴(yán)紫粉好久沒(méi)過(guò)來(lái)了。大家都認(rèn)為是嚴(yán)紫粉母親的嚴(yán)苛管教起了作用,她不會(huì)再到“另一面”來(lái)化妝了。大家又恢復(fù)了各自的生活,新鮮事件在不斷爭(zhēng)奪她們的注意力,誰(shuí)也沒(méi)有閑工夫?qū)ν患虑閮A注太多時(shí)間和注意力。
一日下班后,我又將登記簿翻到嚴(yán)紫粉登記過(guò)的那一頁(yè)上,停留了許久。藍(lán)妙芝問(wèn),阿朗老師,要不要我打個(gè)電話給她?我合上本子說(shuō),下班吧。就在這個(gè)時(shí)候,我突然感覺(jué)到了一陣疲憊,當(dāng)初做心理治療師時(shí)的倦怠感很直白地殺了回來(lái)。我對(duì)藍(lán)妙芝說(shuō),我明天要出差杭州,參加一個(gè)化妝技術(shù)高級(jí)研修班,一周后回來(lái),你也休息一陣子,“另一面”就閉門(mén)謝客吧。藍(lán)妙芝沒(méi)有表示出任何的意外,只是將鎖上的大門(mén)重新打開(kāi),從倉(cāng)庫(kù)里拿出個(gè)“外出學(xué)習(xí),暫停營(yíng)業(yè)”的告示牌掛在門(mén)把上,才放心地離去。
我并沒(méi)有真的去參加什么化妝技術(shù)研修班,而是去了靜子住過(guò)的那個(gè)小山村。悄悄地去,悄悄地遙望那扇簡(jiǎn)陋的小門(mén),悄悄地向一名村民打聽(tīng)靜子的消息。山村很小,住在這里的人彼此間應(yīng)該都很熟稔,只要有一個(gè)外人進(jìn)入,都會(huì)引起他們的警覺(jué)。在村民給不出任何有用的答案時(shí),我悄悄地塞給他二百塊錢說(shuō),就當(dāng)我沒(méi)來(lái)過(guò)。
看來(lái)靜子是真的走了,誠(chéng)如她當(dāng)時(shí)發(fā)給我的短信中說(shuō)的:我要離開(kāi)這里了,愿此后有永遠(yuǎn)的寧?kù)o伴隨著我。靜子就這樣從這座小山村里消失了,來(lái)不及聽(tīng)我一句解釋。我仰望著靜子家門(mén)對(duì)面的小土丘,那天,我們就是在那里相遇,靜子臂彎里挽著一盆洗好的衣服。土丘上只有豐茂的野草、野花,一直延伸到我腳下。在這芬芳的四下里,我感念起了嚴(yán)紫粉。——不知在上帝開(kāi)啟高溫模式的盛夏,這個(gè)女孩是否還裹得像只沒(méi)有煮熟的粽子?
在“另一面”暫停營(yíng)業(yè)的這幾天里,我的手機(jī)幾乎要被顧客打爆,她們都殷殷地盼望我早日回來(lái)開(kāi)門(mén)營(yíng)業(yè)。我的行程已定無(wú)法更改,只得在微信上一一詢問(wèn)顧客,如果不是特別重要的宴會(huì),她們是否愿意由藍(lán)妙芝為她們化妝?藍(lán)妙芝在我身邊工作多年,耳濡目染,論技巧,她還是有兩下子的,只是苦心學(xué)來(lái)的技巧,終究讓她缺少了一種叫作“靈氣”的抽象事物。結(jié)果,有超過(guò)一半的顧客表示愿意,我分辨不清她們到底是認(rèn)可藍(lán)妙芝,還是認(rèn)可“另一面”這張招牌。不管怎樣,這個(gè)周四開(kāi)始,藍(lán)妙芝代替我,當(dāng)起了“另一面”暫時(shí)的掌門(mén)人,我吩咐她,化妝費(fèi)用打六折,只需收取三百元便可。
藍(lán)妙芝獨(dú)自撐了四天,我一回來(lái),發(fā)現(xiàn)銀行賬戶上的錢和預(yù)約登記的本子都滿滿當(dāng)當(dāng)。我沒(méi)有去計(jì)算藍(lán)妙芝到底接待了幾位顧客,我對(duì)她一向信任有加。我跟藍(lán)妙芝,其實(shí)很符合舊時(shí)對(duì)于夫妻的定義:男主外、女主內(nèi),夫唱婦隨。我們似乎從來(lái)沒(méi)有意見(jiàn)相左的時(shí)候,“心有靈犀”雖是熟語(yǔ),但用來(lái)形容我跟藍(lán)妙芝的關(guān)系卻非常妥帖。每天該做什么事情,她都安排得井井有條,我需要的東西,不用開(kāi)口,她都替我準(zhǔn)備好了,當(dāng)我用到的時(shí)候,這件物品就會(huì)恰好在我手邊。有時(shí)候,我不免認(rèn)為,這或許就是夫妻之道的最高境界。只是我跟藍(lán)妙芝從來(lái)沒(méi)有撞出過(guò)任何火花,我們之間像老板與雇員,像姐弟,像朋友,就是不像情侶。藍(lán)妙芝從來(lái)不提自己的家事,我亦從來(lái)不問(wèn),只要她認(rèn)為自己過(guò)得好,就好了。有時(shí)候,看著藍(lán)妙芝溫順的眼神,我遐想著,或許我有意無(wú)意地碰一下她的手,她也不會(huì)反對(duì)。但我不愿意也沒(méi)必要這樣做,我更愿意享受這種光風(fēng)霽月的清朗關(guān)系。
我和藍(lán)妙芝加班加點(diǎn),消化這一周來(lái)積累下來(lái)的預(yù)約客源。沒(méi)有看到嚴(yán)紫粉,當(dāng)然這也不是什么意外的事情。這一天,臨近下班時(shí),藍(lán)妙芝正在打掃店堂衛(wèi)生,我在清理化妝工具。藍(lán)妙芝突然低聲說(shuō),這不是嚴(yán)紫粉嗎?嚴(yán)紫粉正站在店外面的路燈下打電話,還是之前一成不變的粉色上衣、黑色褲子。不同的是,她的一頭黑色長(zhǎng)發(fā)不見(jiàn)了,戴著頂黑色鴨舌帽,帽檐壓得很低,遮去了大部分臉,一圈短發(fā)茬從鴨舌帽的邊緣露出來(lái)。
越來(lái)越怪了。藍(lán)妙芝說(shuō),阿朗老師,你說(shuō)她是不是該去看一下心理醫(yī)生?藍(lán)妙芝平時(shí)極少評(píng)價(jià)別人,她這次可能真是有些忍無(wú)可忍了。她解釋說(shuō),我不是多嘴多舌的人,我只是實(shí)在看不下去了,這個(gè)孩子明顯有心理問(wèn)題,你是這方面的專家,怎么都不提醒她一下呢?一個(gè)好好的孩子,糟蹋了可惜呀。
你說(shuō)我該怎么提醒呢?那天她母親來(lái)“踢館”,我該趁勢(shì)告訴她,你女兒有憂郁癥,有病得趕緊治,得去看醫(yī)生?那樣的話,她還不真的踢掉我這個(gè)妝容館?
藍(lán)妙芝無(wú)話可說(shuō)了。
我不想惹是生非,不料第二天,“另一面”剛開(kāi)門(mén),嚴(yán)紫粉母親就大駕光臨,把藍(lán)妙芝叫到門(mén)口談了很久。顧客擔(dān)心藍(lán)妙芝吃虧,都焦急地要為她出頭。我沒(méi)有停下手頭的活兒,阻止她們說(shuō),沒(méi)事,藍(lán)妙芝應(yīng)付得來(lái)。直到穿長(zhǎng)袖、戴帽子的嚴(yán)紫粉現(xiàn)身,狠狠地瞪了她母親一眼,她母親才打住了滔滔不絕的話頭。嚴(yán)紫粉怒氣沖沖地在前頭飛快地?cái)[著雙腿,她母親想加快速度追上她,卻終究追不上,母女倆一前一后地走遠(yuǎn)了。
藍(lán)妙芝回到店里,額頭滲滿汗珠,不住地?fù)u動(dòng)左手做扇子狀。妝容館又掀起一股久違的熱潮,嚴(yán)紫粉重新回歸大家的視線。
這都什么天氣了,這副打扮,簡(jiǎn)直是個(gè)精神病人。
該不是瘋?cè)嗽豪锾映鰜?lái)的?
藍(lán)經(jīng)理,她老娘都跟你說(shuō)了些什么?
眼下,藍(lán)妙芝是大家眼里的寶庫(kù),埋藏了巨大的、大家感興趣的寶藏。但是任憑大家怎么追問(wèn),藍(lán)妙芝都只是搖搖頭說(shuō),沒(méi)什么,就聊了幾句而已。大家敗下興來(lái),又各自圍繞嚴(yán)紫粉展開(kāi)了討論。
下班時(shí),藍(lán)妙芝從前臺(tái)拖出一只大塑料袋說(shuō),這是嚴(yán)紫粉母親給你的。
什么東西?
一些土雞蛋、玉米棒什么的。
送這些給我干嗎?
說(shuō)讓你可憐一下她這個(gè)當(dāng)媽的,以后嚴(yán)紫粉要是再來(lái)化妝,就直接拒絕掉。她說(shuō),嚴(yán)紫粉年紀(jì)小不懂事,受了壞人迷惑,迷上了化妝、走臺(tái)步,連上班都沒(méi)有心思了,再這樣下去,她家要出大事的。
受了壞人迷惑?我無(wú)語(yǔ),頓了一下又問(wèn),那你怎么能擅自收下她送來(lái)的東西呢?
是她扔下東西就走了。
我長(zhǎng)嘆一口氣說(shuō),你看著辦吧,有什么親戚可以送的,就拿去送掉。
你說(shuō)嚴(yán)紫粉是不是有憂郁癥?看她的樣子,每一條都符合憂郁癥病人的特征。但我查了資料,說(shuō)得憂郁癥的人對(duì)任何事情都很淡漠的,那嚴(yán)紫粉對(duì)化妝又如此感興趣。阿朗老師,你說(shuō)她到底有沒(méi)有憂郁癥呢?
我微笑著說(shuō),別杞人憂天,早點(diǎn)回去休息。
藍(lán)妙芝看看我,對(duì)我眼睜睜看著嚴(yán)紫粉往火坑跳卻不加以干涉的行為,表示完全無(wú)法理解。我不免又想起了靜子。當(dāng)時(shí),我一直以為靜子低著頭,那樣冷淡地回應(yīng)我們,辜負(fù)了我們千里迢迢去看她的心意。直到后來(lái)事情的走向才讓我明白,有時(shí)候我們自認(rèn)為的善意,對(duì)別人來(lái)說(shuō)卻是致命的傷害。我知道已經(jīng)發(fā)生的一切無(wú)法彌補(bǔ),我現(xiàn)在能做的,也不是在彌補(bǔ)誰(shuí),而是遵從自己內(nèi)心的意愿罷了。
六
不知道怎么地,嚴(yán)紫粉患有憂郁癥的消息像水一樣,漸漸在“另一面”鋪開(kāi)來(lái)。我知道不是藍(lán)妙芝傳出去的消息,在這方面,我相信她是個(gè)非常牢靠的人,只要她認(rèn)為不可說(shuō)的事情,一滴水也不會(huì)漏出去。或許是壞消息自己會(huì)不脛而走。
因?yàn)橛辛恕皣?yán)紫粉”這個(gè)人,“另一面”的顧客都成了心理醫(yī)生,大家都在拿嚴(yán)紫粉做案例分析——
聽(tīng)說(shuō)患憂郁癥的人怕冷,所以,你們看她穿那么多衣服,就知道她有問(wèn)題了。
她這種不單單是內(nèi)向那么簡(jiǎn)單,她每次都低著頭獨(dú)來(lái)獨(dú)往,看得出來(lái)的,是心理有問(wèn)題。
估計(jì)是在家里嬌生慣養(yǎng),到了社會(huì)上禁不起一點(diǎn)風(fēng)吹雨淋,碰到個(gè)事情就憂郁了。
得吃藥,得趕快治,否則會(huì)出大事情。
……
大家都以一種過(guò)來(lái)人的身份,熱鬧圍觀嚴(yán)紫粉的生活,雖然自己的生活可能也只是一地雞毛。大家猜測(cè)完畢,就一齊將目光轉(zhuǎn)向我,阿朗老師,你認(rèn)為呢?
我無(wú)言以對(duì),只顧忙著自己手頭的活兒。大家都成了心理醫(yī)生,我還能說(shuō)什么?
下班時(shí),我對(duì)藍(lán)妙芝說(shuō),每個(gè)人都有自己的內(nèi)心世界,如果她不愿意向別人開(kāi)放,我們?yōu)槭裁匆欢ㄒヌ骄磕兀?/p>
但是阿朗老師,你不能因?yàn)樽约翰蛔鲂睦磲t(yī)生了,就閉口不談心理問(wèn)題了呀?這個(gè)孩子,如果不加以干涉,肯定要出大事的。現(xiàn)在的社會(huì),那些跳樓、服安眠藥的事還少嗎?
我說(shuō),有時(shí)候可能恰恰就是因?yàn)楦深A(yù)太多了吧!讓她按照自己的意愿發(fā)展,不是挺好的嗎?
藍(lán)妙芝睜大了眼睛。
我沒(méi)有說(shuō)出口的事情是,其實(shí)我知道藍(lán)妙芝根本沒(méi)有結(jié)過(guò)婚,她住在一個(gè)環(huán)境臟亂的舊小區(qū)里,房子是父母留給她的。她收養(yǎng)了一群流浪貓,但只有兩個(gè)名字:小喵、小咪。小區(qū)里的小孩子奇怪地說(shuō),阿姨有十幾只貓,為什么只有兩個(gè)名字?那它們?cè)趺粗溃⒁痰降自诮姓l(shuí)?可是,每當(dāng)她叫小喵或小咪的時(shí)候,總有不同的貓跑過(guò)來(lái),吃她手里的貓糧。小喵、小咪就是她的一子一女。這時(shí)候,總有家長(zhǎng)拉住自家孩子的手,暗地里緊緊攥住,用眼神暗示孩子不要到這位阿姨身邊去。他們的意思很明白:這位阿姨心理有問(wèn)題,不要靠近。
我還知道,我出差那周,藍(lán)妙芝獨(dú)自頂了四天班,好幾位顧客的賬入了她的口袋。對(duì)于我來(lái)說(shuō),為一點(diǎn)錢而撕破臉的時(shí)代已經(jīng)過(guò)去了。所以,我很高興看到藍(lán)妙芝拿了我店里的錢,為她豢養(yǎng)的貓買玩具、買貓糧,然后很開(kāi)心地跟我說(shuō),我前天為我女兒買了一個(gè)撥浪鼓,她整天握在手里搖啊搖;我昨天給兒子買的巧克力棒,他可喜歡吃了。
我只是靜靜地看著這一切,不去點(diǎn)破,也不言明。大家都向往靜好的歲月。歲月靜好的背后,總是有人在負(fù)重前行,只是有時(shí)候我們不知道,到底是誰(shuí)在暗地里負(fù)重,又是誰(shuí)在默默地給予祝福。——就像靜子,她念大學(xué)時(shí)就是個(gè)非常嫻靜的女孩子,貌不出眾,技不壓人,但我卻一直在暗中關(guān)注她。畢業(yè)后,在一次大學(xué)同學(xué)聚會(huì)時(shí),我聽(tīng)說(shuō)靜子過(guò)得并不好,找不到工作,沒(méi)有結(jié)婚,像個(gè)農(nóng)婦一樣生活在山村里時(shí),陡然起了善念,覺(jué)得靜子這時(shí)候最需要的應(yīng)該是心理安慰,便帶了我的團(tuán)隊(duì),呼啦啦跑去看望她。正如靜子自己所說(shuō),平靜生活是她所能擁有的最華麗的外衣,是我?guī)е蝗烘倚Φ靡獾娜怂毫蚜怂淖饑?yán)。
藍(lán)妙芝見(jiàn)我陷入了沉思,沒(méi)有打擾我,只是輕輕地說(shuō)了一句,老板,我先走了。每當(dāng)聽(tīng)到“老板”這個(gè)詞時(shí),我就恍悟過(guò)來(lái),一天的工作結(jié)束了。
回到家,父母都坐在客廳里等我。偌大的客廳里,他們只開(kāi)了一盞頂燈,兩位老人惴惴地枯坐著,像兩團(tuán)干瘦的影子。平時(shí)的這個(gè)時(shí)間點(diǎn),一般都是母親在廚房里煮餛飩,父親在陽(yáng)臺(tái)上納涼。我訝異地問(wèn),怎么了?他們見(jiàn)我回來(lái),搓著手,互相望著,意思是叫對(duì)方先開(kāi)口。
終于,母親開(kāi)口說(shuō)話了,強(qiáng)子,我跟你爸想回鄉(xiāng)下老家去。
父親搭腔了,這里什么都好,就是,我們?cè)谶@里沒(méi)有啥事可做,又沒(méi)有老朋友,不自在。
母親說(shuō),你放心,我們把原來(lái)在你家種的這些菜啊、養(yǎng)的母雞啊都收整起來(lái)了,菜拔了吃了,母雞帶回老家去,等下了蛋攢起來(lái)給你吃。
我擺擺手說(shuō),行,我明天就開(kāi)車送你們回去,你們什么時(shí)候想過(guò)來(lái)玩了就打電話給我。
之前我一直都竭力反對(duì)父母回老家,他們大概沒(méi)料到我此次居然答應(yīng)得如此爽快,都疑惑地望著我。我說(shuō),我是真的同意你們回去了,老家的山好、水好、空氣好,老朋友也多,回去不是壞事。父母如卸下大包袱般挺直了身子,臉上干癟的皮膚像被春夜細(xì)雨潤(rùn)過(guò),欣欣然舒展開(kāi)來(lái)。母親說(shuō),你過(guò)得好,我們很放心,要是早點(diǎn)找個(gè)女朋友,就更好了。我點(diǎn)點(diǎn)頭說(shuō),會(huì)的,到時(shí)候帶回家來(lái)給你們看。
第二天,天剛蒙蒙亮,我便起了床,幫父母把行李裝到汽車后備廂里。兩位老人家一旦決定了要回去,便覺(jué)得片刻也不能等了,連夜將在城市里鋪開(kāi)的生活卷起、打包。父親把所有的行李都裝好之后,訕笑著問(wèn),他從老家?guī)н^(guò)來(lái)的那頂斗笠還在不??jī)赡昵埃野迅改笍睦霞医舆^(guò)來(lái)時(shí),父親就是戴著一頂斗笠,坐著我的越野車來(lái)的。后來(lái)有一次“另一面”局部裝修,我把斗笠拿到妝容館給工人用了,用過(guò)之后就被我塞在了倉(cāng)庫(kù)里。我早把這頂斗笠給忘了,沒(méi)想到父親居然還念想著它。在我店里,我去取,我對(duì)父親說(shuō)。
遠(yuǎn)遠(yuǎn)地,我竟然看到嚴(yán)紫粉站在我的店門(mén)外等候。她身穿一件短袖T恤,一條牛仔短褲,沒(méi)有戴帽子,正站立在熹微的晨光中,披著一身清涼的霞光,很有儀式感。她的短發(fā)一根根豎著,指向太陽(yáng)。我停下車,走過(guò)去跟她打招呼道,早!嚴(yán)紫粉的嘴角往兩邊綻開(kāi)去,露出一個(gè)淺淺的笑容,回答道,阿朗老師早!
她仰起頭,一縷陽(yáng)光照在她的眼窩處,又從旁邊發(fā)散開(kāi)去,令她的臉龐明暗得當(dāng),凸顯立體。我看了一眼她深邃的眼窩、挺拔的鼻梁,已然明白了什么。
阿朗老師,您現(xiàn)在有空為我化個(gè)妝嗎?我有急事。嚴(yán)紫粉的聲音還是那么細(xì),但是滲出絲絲縷縷的底氣來(lái)。
我點(diǎn)點(diǎn)頭。雖然她沒(méi)有預(yù)約,現(xiàn)在也不是“另一面”的營(yíng)業(yè)時(shí)間,更何況我還要趕時(shí)間送父母回老家。
四大皆空。嚴(yán)紫粉說(shuō),您幫我化妝成這個(gè)。
作為一名資深化妝師,我是第一次聽(tīng)說(shuō)“四大皆空妝”。但我思索了一下,便胸有成竹地行動(dòng)起來(lái)。棱角分明的臉,象征著這個(gè)尖銳刻板的世界,尤其是下巴,尖利地直指地心;五官?zèng)]有描輪廓,只用桃粉色腮紅在她臉上大片渲染,深邃的眼窩、高挺的鼻梁,便都隱在一層紗帳后面,宛如春天無(wú)邊的風(fēng)月,似有,似無(wú)。
嚴(yán)紫粉對(duì)著鏡子中的自己點(diǎn)點(diǎn)頭,起身向我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打開(kāi)背包準(zhǔn)備掏錢。我說(shuō),現(xiàn)在不是工作時(shí)間,算是友情贈(zèng)送,不收錢。嚴(yán)紫粉掏出五百元錢放在前臺(tái)上,拉開(kāi)玻璃門(mén),很快就融入了四處彌漫的光明里。
我送父母回了老家。一路上,父親戴著那頂斗笠,母親手里捧著母雞,他們臉上都掛著滿足且愜意的微笑。尤其是看到他們下車走進(jìn)灰塵遍布的老家,深深地、深深地吸著房里略帶霉味的空氣時(shí),我不覺(jué)眼眶濡濕,對(duì)父母說(shuō),等天涼了,我就叫工人來(lái)看看,把房子給翻修一下。
十點(diǎn)鐘,我準(zhǔn)時(shí)回到“另一面”。藍(lán)妙芝來(lái)上班時(shí),看到桌子上的一沓錢,問(wèn),誰(shuí)的?
我說(shuō):早上一位顧客有急事,來(lái)不及預(yù)約,我也沒(méi)有問(wèn)名字,你隨便記一個(gè)名字吧。
還有一本畫(huà)冊(cè),藍(lán)妙芝打開(kāi)畫(huà)冊(cè)翻了一下說(shuō),畫(huà)得真好。
是一本鉛筆素描畫(huà)。第一頁(yè)畫(huà)的是昭君出塞,配詩(shī):絕艷驚人出漢宮,紅顏命薄古今同。第二頁(yè)畫(huà)的是聶小倩,配詩(shī):君記我一瞬,我念君半生。第三頁(yè),畫(huà)的是一個(gè)發(fā)髻高聳、身穿拖地紗裙的女子,高額頭瘦兩腮尖下巴,一大片胭脂從上到下暈染開(kāi)來(lái),似一朵桃花盛開(kāi)在臉上,她的五官,就隱在這一片桃花底下,叫人看不清楚。這一頁(yè)沒(méi)有配詩(shī),好像是匆匆忙忙完成的。
這是不是那位顧客掉下的?藍(lán)妙芝問(wèn)。
也許吧,你先收起來(lái)。
“另一面”漸漸熱鬧起來(lái),顧客們陸續(xù)來(lái)了。她們跟往常一樣聚在一起,像大多數(shù)心懷良善的人一樣,交流著她們得來(lái)的消息。她們中的一個(gè),已經(jīng)打聽(tīng)到嚴(yán)紫粉的工作單位了,據(jù)說(shuō)還是個(gè)公務(wù)員呢,只是她完全無(wú)法勝任現(xiàn)在的崗位,一味地想辭職,甚至想離家出走。她母親動(dòng)員了家里所有的親戚,一雙雙手有力地按住了她想辭職的念頭。
果然,有憂郁癥。要不然的話,像她這種沒(méi)有多大能耐的人,怎么可能千辛萬(wàn)苦考上公務(wù)員了,還要辭職呢?這是她們得出的最符合猜測(cè)的結(jié)論。于是,大家都很得意地笑起來(lái)了,在心里為自己狠狠地干了一杯。笑過(guò)之后,她們又對(duì)生活表示出像樣的怨憤:這個(gè)社會(huì)有病,殺了人、燒了車,甚至連工作做不好,都以一句“心理有問(wèn)題”敷衍過(guò)去,這樣下去怎么得了?
對(duì)嚴(yán)紫粉的終極結(jié)論出來(lái)后,她們顯然對(duì)她失去了興趣,開(kāi)始翻看手機(jī),意欲從手機(jī)上尋找新的談話點(diǎn)。她們很快看到了一條新聞:在上午剛剛舉行的一場(chǎng)模特大賽中,一位新入門(mén)的模特化著“四大皆空妝”走T臺(tái),走紅網(wǎng)絡(luò),成網(wǎng)紅了。由于“四大皆空妝”的最大特點(diǎn)便是五官模糊難辨,因此,顧客們又紛紛開(kāi)始猜測(cè)這位模特到底是何許人物。有人說(shuō),是一位剛從模特培訓(xùn)學(xué)校畢業(yè)的學(xué)生。也有人說(shuō),是一位剛出道便遭封殺的演員,轉(zhuǎn)戰(zhàn)模特界了。
藍(lán)妙芝趁著午飯前的空當(dāng),問(wèn)我,那個(gè)網(wǎng)紅是嚴(yán)紫粉吧?
我也看到了這條新聞,也仔細(xì)看了圖片。網(wǎng)上的圖片雖然像素不是很高,T臺(tái)離得又遠(yuǎn),但一切都逃不過(guò)化妝師的眼睛,然而我假裝肯定地告訴藍(lán)妙芝,不是嚴(yán)紫粉。
那本畫(huà)冊(cè)是嚴(yán)紫粉丟下的吧,那么湊巧?
我覺(jué)得這模特更像我以前認(rèn)識(shí)的一個(gè)人。你叫外賣吧,中午要一個(gè)鯽魚(yú)豆腐湯。
鯽魚(yú)豆腐湯?你今天怎么吃這個(gè)?
是的。
藍(lán)妙芝不再說(shuō)話,開(kāi)始撥打田園餐廳的外賣電話,據(jù)說(shuō)那里的鯽魚(yú)豆腐湯做得非常地道。
藍(lán)妙芝認(rèn)識(shí)我的時(shí)候,我就一直不吃任何由鯽魚(yú)做成的菜肴。因?yàn)槟翘欤谌タ赐o子返程的路上,我們一幫人都又累又餓,便在路邊找了個(gè)魚(yú)莊,點(diǎn)了份鯽魚(yú)豆腐湯,吃點(diǎn)墊墊肚子。隊(duì)友們都吃得津津有味,我卻覺(jué)得那魚(yú)湯土腥味濃重,皺著眉頭也無(wú)法下咽。但今天,今天的魚(yú)湯或許會(huì)是另外一番味道吧?
“四大皆空妝”,這個(gè)新名詞成了扔進(jìn)顧客心湖里的一塊石子,一層層漣漪在“另一面”蕩起。我跟藍(lán)妙芝還在吃午飯,就不斷有顧客涌進(jìn)門(mén)。她們也不顧自己有沒(méi)有預(yù)約,紛紛要求說(shuō),給我們也化個(gè)“四大皆空妝”吧!這個(gè)妝好,輪廓鮮明,五官又柔和,什么雀斑、皺紋、下垂統(tǒng)統(tǒng)不是問(wèn)題。
我笑笑,放下筷子問(wèn),你們知道“四大皆空”到底是哪“四大”嗎?
阿朗老師,你今天故弄什么玄虛?
我吃魚(yú)喝湯,但笑不語(y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