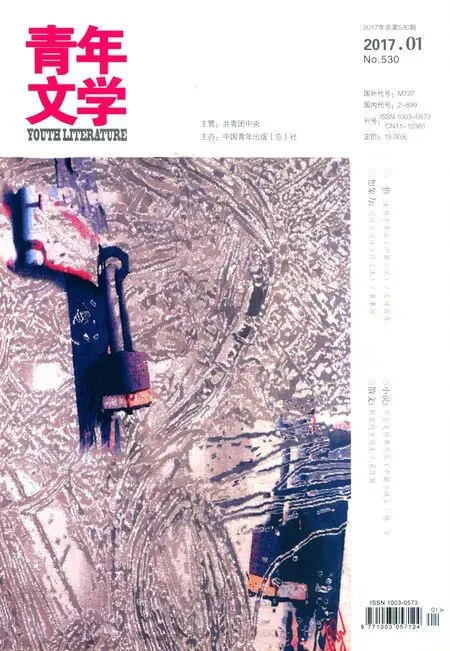淳安在天上
⊙ 文 / 王威廉
淳安在天上
⊙ 文 / 王威廉
王威廉: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作品散見于《收獲》《十月》《作家》《花城》等刊。獲首屆“紫金·人民文學之星”文學獎、《十月》文學獎、廣東省散文獎等。出版有長篇小說《獲救者》、小說集《內臉》《非法入住》《聽鹽生長的聲音》等。現任職于廣東省作家協會。
有些地方,也許你并不真的知道,但你總感到自己是早就知道的。比如千島湖,只要提起,很多人都仿佛知道這個地方,因為這個名字太美,瞬間就給人強烈的畫面想象。
我也是如此。我總覺得什么時候看過相關的地理書籍,知道千島湖是有名的自然景觀。
我第一次到千島湖的時候,那心底想象出的美好畫面,還比不上眼前所看到的:真的有上千座形態各異的綠島,在開闊而清澈的水面上站立,仿佛蘊藏著盛大活力的生命體。我被這種美景所震撼。總以為“千”是形容詞,沒想到是真實的量詞。那諸多的島嶼,除了幾座被開發的,許多小島是漁船也不登臨的,那兒維持了最自然的樣態,洋溢著自然界自足的歡樂。
我們坐船,登臨了幾座比較大的島嶼,上面亭臺樓閣樣樣俱全。沿著山路攀登,來到島的頂端,便可看到更多的綠島、更加開闊的風景。梅峰島是千島湖的最高峰,其實也算不得太高,但為了游客的方便,也架設了纜車,可以毫不費力地來到頂峰。在最高峰的觀景臺望去,發現千島湖的宣傳畫大多是在這里拍攝的。眼見為實,這風景終于沖破了照片的束縛,自由舒展在面前。上千座島嶼星羅棋布,船舶穿插其間,不知開往何處,簡直是一座水上的迷宮。
周圍人,包括我自己,都掏出手機,拍照留念。手機已經成為現代人的另一雙眼睛,我們用它來保存我們看到的世界表面。我們選取角度,我們調色,讓保存下來的這片風景更符合我們對于“美”的觀念。當然,我們也經常把自己攝入其中,證明自己曾經來過。否則,人真的很難自證這次的“到來”,記憶是那么不可靠,而到來的意義又是那么稍縱即逝。
眼睛是最健忘的,那么震撼的風景,眼睛也會很快習慣,繼而在接踵而來的歲月磨礪中,忘記那樣的美景。心靈的記憶是強健的,卻無法保持那片風景的純粹。心靈的記憶對冰冷的客觀之物是絕緣的,它一定要一種能刺進內心的精神感觸。
千島湖,比風景更動人的,是它背后的故事。它的故事,和其他的好故事一樣,都是在緩慢與耐心地了解下,才逐漸展開了它的敘述的。
我是到了千島湖之后才知道,這兒并非天然的湖泊,而是一座人工湖。也不是專門為旅游而建造的湖,而是為了下游杭州和上海的供電而修建的水庫。水庫,這個詞一出現,便本能地覺得掃興了。這是個太功能性的詞,太人工化的感覺,完全與眼前美如仙境的千島湖不搭界。但,這就是真實的,必須接受。在知道“真相”之后,再看千島湖,還是那座湖,但感受是不同了,變得更加復雜了。那些島,竟然是被淹沒的山的頂峰,難怪島嶼的形狀保持著一種奇特的張力,原來是山脈的走向。而水下,又是怎樣的一個世界?
我早先自以為是的“地理知識”瞬間破產了,道聽途說的事物太多了,有太多的事物像是千島湖底的古城一樣,在黑暗中沉睡。
那年初次來千島湖,其實對這些問題、這些故事根本來不及細想,美景太搶眼了,只要你投去目光,它就奪去你的心思。美總是令人沉溺。我帶著美好的風景印象,如塵世行旅的一次出神喘息,匆匆間就告別了千島湖。
如果不是機緣巧合,再來千島湖,那么千島湖在我心中就和別的旅游景點毫無兩樣,就像游客和景點的關系,彼此在一種約定俗成的層面上,達成默契。對方努力呈現出來的美的點,我們盡量接受并形成一種膚淺的認識,完全滿足對方的期待。這不就是我們今天的旅游嗎?當旅游不再是個人的歷險,而是一種工業化的產業行為,便出現了千篇一律的模式。
但重游,畢竟是不一樣了。
故地重游,在中國文學中,原本就是一個特別動人心魄的主題。人的短暫與物的長久,人的變化與物的變化,都能激起人心底那種最深沉的情感,從而刺中心靈的記憶。
重游千島湖,心靈的記憶被激活了。不同角度的欣賞,都是在激活曾經的記憶。一邊在印證,一邊在補充,那片風景不再屬于遠方,而是漸漸有了情感和記憶的景深。
我第一次來時,多為晴天,可以完全看清千島湖的細節,目眺極遠處,水天相接,如有一根藍色的細帶將千座綠島輕輕環繞。而這次來,多為陰天,水面霧氣縈繞,遠處的小島隱藏在水汽中,隨著風的吹拂,露出不同的曼妙,一切都在變動不居地變化著,你只需要靜靜地凝視,它仿佛是一座舞臺,有情有義地自為你傾情演出。
我突然意識到,湖不僅僅是水,還有水的相關形態,蒸騰的水汽、濃霧的氤氳,也是湖的一部分。
千島湖水質極佳,隨行朋友用手舀起一捧水,就直接喝下,據說甘洌無比。我雖無如此直接的舉動,但我在賓館不再喝瓶裝的純凈水,更喜燒開自來水,慢慢品嘗。我常年生活在廣州,那兒的自來水不敢恭維,燒開后總有一股說不清的味道,喝多了舌面還會發澀,因此養成了喝純凈水的習慣。喝著千島湖的水,才知道白開水也能這么好喝。我有一種略微悲哀的心緒,感到自己與自然隔絕得越來越厲害。
除卻再度欣賞美景,我心底的問題又冒了出來,而且比前次為甚。我望向湖水,心里沉甸甸的,那水下的古城,不再是神秘的,而有了一種類似鄉愁的懷想。
在梅峰島上,至今還刻著郭沫若題寫的詩句:“西子三千個,群山已失高。峰巒成島嶼,平地卷波濤。”群山失高,峰巒成島,帶著這樣生動的描述,再望千島湖,有一種苦澀的滋味,令人對眼前的美景甚至心生悲憫。有人文歷史的地方,天然地要喚醒你的情緒,讓你不再僅僅是你,而要面對歷史,成為歷史中的個人。個人與歷史中的個人,是相當不同的兩種人。
那些曾經生活在那里的人,現在都去哪里了?至少有三十萬人啊,他們過得好不好?家園變湖,大山變島,豈不是當代的滄海桑田嗎?一個人得有多強大的心靈,才能抗住這樣巨大的變遷?
千島湖所屬的浙江淳安縣,歷史極為悠久。春秋時是吳越之地,戰國時屬楚國,秦統一后,劃為歙縣轄地。三國時期,孫權重新規劃歙縣,是為淳安、遂安建縣之始。這里和江南其他地方一樣,文化昌明,南宋時,朱熹來這里講學,寫下了那首傳誦千古的詩:“半畝方塘一鑒開,天光云影共徘徊。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朱熹與淳安的緣分,還有著更緊密的延續:宋末元初時,朱熹第四代曾孫朱澹,為逃避元兵迫害,遷徙至此,建立了朱家村。朱澹不忘祖宗功德,每逢過年都用豬頭祭祖,供奉祖先朱熹,延續八百余年,直到今天,朱家村依然保持著這樣的風俗。
到了明代,這里出了名人商輅,他在鄉試、會試、殿試中皆為第一,稱為“三元及第”;他歷仕英宗、代宗、憲宗三朝,歷任兵部尚書、戶部尚書、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相當于宰相級別,故又稱“三元宰相”。明人稱“我朝賢佐,商公第一”。能培育出商公這樣的人物,也反映出當地文教質量之高。此外,明代的另一位象征性極強的著名官員,海瑞,他于仕途之初,在淳安做過四年多的縣令,當地人為他修建了海瑞祠。如今,這座祠堂靜靜地沉默于水底,今人在“五龍島”上又新建了一座海瑞祠。
這樣的歷史,放在任何縣城,都是不得了的精神財富。故當地人總是自豪地說:我們有一千八百年的輝煌史。
公元一九五八年,因建新安江水電站,水庫開始蓄水,原淳安縣治賀城、遂安縣治獅城,皆被水淹沒。當時水勢來得很猛,人們剛剛撤離,這兒就被淹沒了,因而水下古城基本上保存了當年的原樣。現在的淳安縣,領域實為原來淳安與遂安的合并,縣治位于新建的千島湖鎮上。因而,一九五八年,是淳安一千八百年歷史的一個巨大休止符,也是千島湖誕生的元年。
假如,淳安歷來就是不毛之地,現在變作絕美的千島湖,那要感慨這是一件偉大的藝術品了。但淳安的歷史如此豐富久遠,人們的生活原本和諧自洽,這種目的明確、代價極大的人工變化,如果不仔細思辨,將會缺失掉太多珍貴的東西。
鄉愁是人類最不可融化的情感,無根便意味著流亡。我自是一個無根者,但我深知我對根須的渴念。三十萬人的鄉愁,一千八百年的文化記憶,是一股強大的不可能被泯滅的力量。就在我此行的年初,在千島湖邊的淳安縣姜家鎮,按照獅城原貌,營建復原了那座水下的古城。千年古城獅城,得名于原遂安縣城北部的五獅山,從大唐武德四年起作為遂安縣治,迄今亦有一千四百年歷史了。那兒自唐至今的各種建筑與文物,一應俱全,承載著無數人的生活史封存在數十米深的水底。那些白色的徽派建筑,在水底會是什么顏色?黑褐色的飛檐上長滿了綠色的水草嗎?
世上有了兩座一模一樣的城,一座在水下,一座在地上。我在地上的獅城行走的時候,仿佛水下也有一個我在行走,我甚至像魚那樣靈活地游動,鉆進那些古舊的裂紋中,如同進入了時間的隧道。
世上還有三座同名同姓的村,都叫晨光村。搬遷之日,原晨光村一分為三,一部分村民后靠,成為現在的晨光村,另兩部分村民則分別遷至江西鄱陽與鵝湖兩地。到了江西的移民們,懷戀故土,也將當地的村落命名為晨光村。五十年后的一天,江西這兩個晨光村的村民,聚合在一起共有一百一十人,出發前往現在淳安的晨光村,進行了一場跨越半世紀的對話。兒時的伙伴,暮年重聚,昔日的鄰居,遙想往昔……傷口如花綻放,不知有多少淚水要灑落。
一位移民,這樣回憶當年的情景:
“離開的那天,岸上的人呼喚著,你們常回來看看!船上的人哭喊著,你們要記住我們!離開時,我們全家共六口人,國家當時的宣傳口號是:‘少拿舊家具,多帶新思想’,我們響應號召,當時只拿了幾只裝衣服的木箱、幾副碗筷,還有國家發的每人五元錢。”
讀來,令人揪心。今天也有大批不幸的移民,但真的都沒法和淳安的移民相比。那個時代,國家并不富裕,號召人們搬遷沒有討價還價的巨額補償,只有服從大局的思想工作。而讓后人感懷的是,那時的人可以接受國家的思想,哪怕這意味著巨大的犧牲。是耶非耶,時間推得越遠,評價變得愈加不重要,重要的,永遠是人的命運。命運,在不同的時代,有著不同的體現。
移民后,大家的日子都不順利,去到江西的,在本地人眼中如同“土匪”一般,因為突然來了那么多張嘴,一來就要分山、分田、分地,矛盾是必然的,持械毆斗更不稀奇。留在當地的那些人也不容易,因為良田被淹,靠后到了山地,不能栽種太多的農作物。人多地少,糧食也成問題。
靠著幾十年的努力,他們都逃離了饑饉。
這三個地方的人,硬是在三個地方開枝散葉了。他們如今相聚在一起,各自的記憶如同殘損的部分,都在尋找著一個整體。但摔碎的磁石在接近時,在具備更大的吸引力的同時,卻不能再恢復原石的原狀。他們彼此搜尋著過去的記憶,拼接出了一個無法再辨認的過去。我不禁想起,在復建的獅城中,有座小博物館,里面的墻壁上貼滿了過去的老照片,那些人、那些物、那些場景,都像是時間的標本,永遠在上演著一個屬于過去的活著的世界。
我有了比拍攝湖水美景時更激動的心情,一直拍攝著那些人、那些物、那些場景。我并不認識他們,我更不了解他們當年的生活,但我如此被他們打動,仿佛我的根就在他們當中。
對于我,這究竟是一種什么樣的情愫呢?我回答不上來,我用手機不斷回看著那些照片,情感在發酵,有了“心事浩渺連廣宇”的意味。
我只知道,群山失高,滄海桑田,個人渺小如蜉蝣。
而我也堅信,即便蜉蝣,和山水雨霧一樣,在這宇宙中有存在的權力。
我住在千島湖邊的酒店里,透過巨大的落地窗,就能看到湖水和綠島。我一直保持著窗簾拉開的狀態,以便隨時一抬眼,就能看見湖。
夜晚,熄燈后,漆黑中只有窗外傳來微光。我望向窗外,仿佛能清楚地看見黑暗的湖面,水的波紋在起伏動蕩,與大海毫無二致。
我想起清代詩人黃仲則路過這里寫的一首詩:
“一灘又一灘,一灘高十丈。三百六十灘,淳安在天上。”
淳安在天上。千島湖在天上。現在,我是在天上的淳安,望著天上的湖水,那一切的秀美與苦難、繁華與短暫、傷感與愉悅、絕望與期待、死亡與復活,都蒸發凝結成了星云那不規則的形狀,懸掛在天上。
當我明日離去,回頭再看時,便是要抬頭仰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