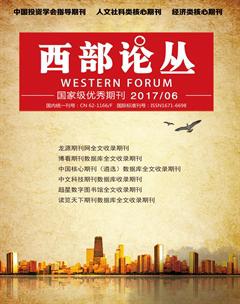淺析中學語文
王良垚
摘 要:鄉土文學,它的出現溯源于魯迅的《故鄉》 。上個世紀20年代,文壇上出現了一批比較接近農村的年輕作家,他們的創作較多受到魯迅影響,以農村生活為題材,以農民疾苦為主要內容,形成所謂“鄉土文學”。鄉土文學是在“為人生”文學主張的影響和發展下出現的。這一時期,鄉土文學的表現主題是社會現實、時事政治,具有現實主義悲劇性特點。30年代它通過陶醉于田園風光的沈從文筆下,“美化落后”“詩化麻木”,成為人們心靈的世外桃源,具有浪漫主義特征。在革命文學出現后,鄉土文學作家們的視角變得更“客觀”“中立”,此時的主題則在于表現社會變革后人民生活和精神的變化。在90年代以后,城市化的快速發展導致了鄉村的沒落,鄉土文學也處于邊緣地位,許多新一代作家傾向于都市文學,如90后作家群中涉足于鄉土文學的作者只有李傻傻一人。而這一時期的鄉土文學不再是以表現社會,人民生活變化等為主題,它的娛樂性和故事性增強,文學價值較為低下,缺乏現實主義和幽默感是它顯著的特點。
關鍵詞:鄉土文學;現實主義;悲劇性;中間性;魯迅
所謂“鄉土文學”,往往讓人聯想到生機盎然、野氣撲人的田園詩意,月下小景、水鄉夜色或空靈雪景常常成為鄉土文學恬靜怡人的意境。青瓦、黃墻、白塔、老人、小孩更是時常作為一種鄉土文學的典型背景,昭示著鄉土文學所可能具備的某種超然的美學特征。不過,鄉土文學中也亦時常出現粗獷的民俗,剽悍的民風,甚至是野蠻的陋俗,愚昧的鄉規和殘酷的階級壓迫,所以,鄉土文學應當是一種廣泛的鄉土生活的描繪,應當以樸素、蘊藉、濃郁的鄉土氣息和鮮明的地方色彩為基本美學特征,其內容涉及本土山川風情、民俗民情等。
魯迅是開創鄉土小說范型的先行者,他對東南沿海鄉鎮人的出色描寫,為現代小說的發展展示了新的路徑。在他的“改造國民性”思想的啟迪下,一些來自鄉村,寓居京滬等大都市的游子,目擊現代文明和宗法制農村的差異,帶著對故鄉和童年的回憶,用隱含著鄉愁的筆觸,將“鄉間的生死,泥土的氣息,移在紙上”,以其剛健、清新、質樸之氣使創作界面目一新,又由于挾帶著各地鄉情民俗的記實和描寫,顯示了鮮明的地方色彩,從整體上呈現出比較自覺而可貴的民俗化追求。從而形成了鄉土小說的崛起。
20世紀二三十年代,作為中國鄉土文學的第一分期,其代表作家有魯迅、許杰、王魯彥、臺靜農、廢名、裴文中、蹇先艾、許欽文等。其中,魯迅筆下的鄉土世界無疑最具代表性。在他的鄉土小說世界里,鄉土環境不是寄予著某種人生理想的世外桃源,而是扼殺民族生命力的所在。
他所成功塑造的主要人物有閏土(《故鄉》)、孔乙己(《孔乙己》)、祥林嫂(《祝福》)、阿Q(《阿Q正傳》)等。在未莊、土谷祠、魯鎮、烏篷船、咸亨酒店構成的鄉土環境中,魯迅以一個啟蒙者的眼光揭示著鄉土人物的麻木、愚昧和殘酷,對他們的悲劇性命運表示深切同情。例《阿Q正傳》中阿Q是一個被剝奪得一無所有的貧苦農民同時又是一個深受封建觀念侵蝕和毒害,帶有小生產者狹隘保守特點的落后、不覺悟的農民。小說第一章寫到:“阿Q沒有家,住在未莊的土谷祠里,也沒有固定的職業,只給人家做短工,割麥便割麥,舂米便舂米,撐船便撐船。工作略長久時,他也或住在臨時主人的家里,但一完就走了。”表明了阿Q的實際境遇:他沒有土地,沒有家,住在土谷祠里;沒有固定的職業,靠打短工,做幫工維持生活,是一個地道的赤貧的鄉村勞動者。
20世紀40-60年代,鄉土小說以普通農民為視角,政治斗爭故事和戰爭故事成為主宰,代表作家有趙樹理、孫犁、周立波、柳青、茹志娟等。其中最具代表性作家則是趙樹理。他的筆下成功塑造了三仙姑、二諸葛、小二黑、小芹(《小二黑結婚》),惹不起、鐵算盤(《鍛煉鍛煉》)等老一輩和新一輩的農民形象。他的鄉土小說題材不再是魯迅筆下毫無生氣的“未莊”世界,明顯的封建地主階級對農民階級的政治、經濟壓迫,而是民主意識與封建意識和鄉村惡勢力的沖突,以鄉土小說為輸出革命和繼續革命理念的所在,注重塑造鄉土世界中具有高度革命覺悟的農村“新人”形象。
20世紀70-80年代,鄉土題材小說以其“表現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別”獨樹一幟,真實地反映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農民的生活歷程,深刻地揭示了造成他們幸酸命運的政治、經濟、歷史及民族性格和民族心理等深層根源,形象地顯示了極“左”路線給人民造成的苦難。同時,小說中也大量細致逼真地描繪了新時期的社會變革所帶來的農民性格和心理方面的變化。這一時期代表作家有高曉聲、劉紹棠、路遙、汪曾祺等,以高曉聲最具代表性。他繼續了五四以來中國現代文學對于“國民性”問題的探討,成功地塑造了李順大(《李順大造屋》)、陳奐生(《陳奐生上城》)、李興大(《水東流》)等一系列典型形象。作者以深刻的“探求者”的眼光所塑造的這一系列人物形象被稱為“中國農民的靈魂”,他們有著中國農民善良、樸實、忠厚的傳統美德,也有著數千年的歷史傳統所積淀下來的民族的“劣根性”。
20世紀90年代以后,鄉土小說產生了巨大的嬗變。城市經濟的迅猛發展導致鄉村逐漸沒落,鄉村經驗的分裂。這一時期鄉土小說的巨大特點是缺乏現實主義和政治性。代表作家有李銳、遲子建、賈平凹、李傻傻等。其中以遲子建以大興安嶺一帶為背景的鄉土小說為特色,她用茫茫的雪原,長長的流淌不息的漠河,無邊的松林等大自然浩蕩的意象來聚焦于她所講述的彼時彼地的人物情緒與感情,絲絲縷縷地刻畫出人物的膽怯與傷感,無奈與應對,從而顯示了小人物的煩惱、甜蜜與善良。雖以某特定時期為背景,暗含了一定的政治性,但并不抨擊時事,表現社會性。
無論是哪一時期的鄉土小說,都沒有脫離人物的中間性,即塑造的人物形象是社會中層人物形象代表。例如:阿Q、陳奐生、二諸葛等他們并不是社會最底層人民,也不是統治階層,他們所代表的是各社會背景下的一類人。對于他們形象的塑造,作家們堅持“不溢美、不掩惡、不飾、不丑化”“美丑并舉”的原則,他們的思想意識是一種“中性意識”,作家通過這種“中性意識”來關注社會,表現他們的崇高與平庸。“中間”則是鄉土文學創作的“共性現象”,在其將近一個世紀的發展過程中,從最初的崛起、繁榮到當下所呈現的沒落化,它始終沒有脫離其“中間性”。
參考文獻:
[1] 高曉聲《高曉聲小說選》 江蘇文藝出版社, 2009年版
[2] 遲子建《鬼魅丹青》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