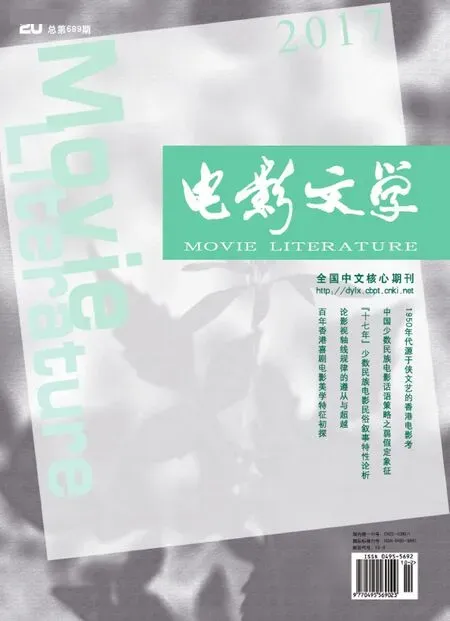中國少數民族電影話語策略之弱假定象征
朱茂青
(四川民族學院,四川 康定 626000)
電影影像的“言說”與其他藝術門類的“言說”一樣有“故事”(“言說”什么)和“話語”(怎樣言說)。其中,電影“故事”和其他媒介敘事內容不外乎表述人類對現實、生命感知的共同體驗,電影更多的是由敘事話語體現其獨特的藝術魅力。象征一直是藝術表達的重要方式,而電影更是熱衷于將象征作為常用的“措辭途徑”,國內少數民族電影從產生初期就自覺地熱衷于象征手法的使用,并在之后不斷進行探索,諸如《靜靜的嘛呢石》等作品已經尋求到合乎自身表述的象征方式,即弱假定象征。
國內外對中國少數民族電影的研究不計其數,涉及影視象征的也不少,但是,全是單一地評論某一部影視作品象征手法的使用,并沒關注到少數民族電影象征手法使用的流變過程,對于當前電影廣泛使用的象征也沒做優劣的辨析。在此,將通過以下論證對所提到之缺失做填補。
自古希臘起,文學、宗教學、哲學、心理學、符號學、語言學、人類學等諸多領域,包括電影也在自我立場上對“象征”進行分析解說,但至今仍無定論。在此,象征僅指“人文主義”性質的美學象征;另外論證基于象征諸多內涵界定中的兩個共同點:(1)象征是一種類比活動。(2)象征具有不確定性。[1]
1949年前,國內電影鮮有少數民族形象的呈現。1949年,新中國誕生,少數民族與邊疆的形象組合成為國家主體想象的開端。內地的電影制片廠、電影主創人員又都不是影片涉及的少數民族。因此,新中國成立十七年的少數民族電影更多的只是通過“少數民族”這一符號構建能展現國家活力與浪漫的理想空間。這批電影更注重的是“說什么”,即內容主要是強調民族國家,宣揚黨政方針,而“怎么說”也主要考慮如何明確地展示新生民族國家的政治形象。諸如《五朵金花》《阿詩瑪》《劉三姐》《冰山上的來客》等以民歌、風情、動人的愛情、傳奇的敘事給被紅色革命創作充斥的“十七年”藝術帶來新鮮、豐富的感受和體驗。但是,這些影片的主旨確實還是宣傳教育的政治目的,以發揮構建國族的重要作用。需要鮮明地突出主題,所以“象征”的使用,從影片形成的整體象征,到《阿詩瑪》中愛情的山茶花,《農奴》中象征封建枷鎖的鐵鏈,《五朵金花》中象征美好、幸福的金花等局部象征,都必須是社會上約定俗成的“公共符號象征”,即是創作者將社會上約定俗成的一些具有象征意義的事物直接搬入作品,觀者看到這些事物可以立刻明白其中的象征意義。“十七年”的少數民族電影刻意規避了“象征”手法應該具有的朦朧性。雖然有象征手法的使用,但是因缺乏象征暗示的多義性,而難以營造豐富的內涵和意蘊。
新時期,一類以《舞戀》《幸福之歌》為代表的少數民族影片反映改革開放后的現實敘說。“這一時期的電影與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電影沒有實質性區別。總之,追求差異與邊緣性完全是出于中心的自我利益的需要。”[2]另一類少數民族電影形成“去政治化”“去中心化”的文化表述轉型,邊地的神秘和特異給電影提供了較豐富的娛樂元素,因此,20世紀80年代,少數民族電影刻意而且大膽地追求娛樂性。這段時期成為少數民族娛樂片的創作高峰期。《美人之死》《恐怖的鬼森林》,包括當時革命歷史題材的《戈壁殘月》《黑樓鼓聲》等都添加多種娛樂元素:懸疑、私情、裸露、血腥等。影片大多利用少數民族獨特的地域空間,片面追求離奇怪誕的情節,內容上非常單一,形式更缺乏藝術上的追求,這一類少數民族影片幾乎沒有象征的運用。
值得重視的一類是新時期部分少數民族電影導演隨中國“第五代”電影共同開啟的“探索”之路:《紅高粱》《黃土地》中單純而超越歷史的符號,最大限度地實現象征的厚度,成為中國電影史上的經典。《黃土地》成功運用的象征也使得同時期的少數民族電影紛紛將其視為有效的表達模式。其中代表性的作品如田壯壯的《獵場札撒》《盜馬賊》。但是田壯壯本人表明態度,“不過借這塊地方來拍現在”,即是借少數民族影像做自我主體表達,再加上田壯壯等漢族導演在進行少數民族影片拍攝時難以避免“局外人”視角,所以對影片中大量展示的儀式、符號,并沒有深入精準地揭示其文化內核,難以通過符號形成自然、豐富的象征意蘊,而且民俗、物件不加整理地表現,再加上觀眾不熟悉藏地文化、傳統,更感覺影片含混。影片又刻意削弱故事的邏輯性,多是片斷的人物行為。所以普通觀眾覺得“深奧難解”,學界反映寥寥,田壯壯的兩部影片《獵場札撒》《盜馬賊》,拷貝在當時創下歷史新低。以至于田壯壯自己慨嘆他的電影是拍給下個世紀的人看的。[3]
21世紀,中國電影中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少數民族題材電影,特別是具有原生態文化氛圍電影的出現。民營資本拍攝,導演和演員、大部分生產團隊都是少數民族,“母語電影”成為少數民族電影的“文化主體性”實踐。然而,由于過分強調“主體意識”,一些少數民族電影在“自我”展示中,失卻了“話語”的所指。而在單一能指功能中成為民族的“影像化石”,比如《尼瑪家的女人們》,場景、人物、習俗連同思想、心理,都刻意選擇能反映傳統的題材內容。如果把其中所有的符號理解為象征,那么象征也是僅單一指向傳統文化,處處顯示“回歸”傳統文化,反現代化的傾向無所不在,喪失了象征該有的多義性;另外,這類追求紀實的影片反而沒有呈現出現代化進程中真實的民族地區。比如《馬背上的法庭》《碧羅雪山》,在其中仍然是對少數民族文化價值所做的單向度弘揚。《青春祭》《滾拉拉的槍》《這兒是香格里拉》,則以象征、隱喻的手法創建了一個全球化之外的文化空間,仍然證明長期以來對外族文化獵奇的自覺意識所呈現的藏區:要么是原初封閉、落后的邊地;要么是美好、純凈、超現實的桃花源。因此,在故事層面情節淡化、人物模糊、場景虛化;在話語層面又難以形成飽滿豐厚的“話語蘊藉”,而且,強化了他者對藏區長期的誤讀。
少數民族電影中頻繁使用的象征,如何才能發揮它所有的意指功能?在此以萬瑪才旦在2005年拍攝的《靜靜的嘛呢石》為例做相關探討。選擇《靜靜的嘛呢石》為例,原因有三:第一,它毫無爭議地屬于少數民族電影。關于“少數民族電影”,概念的界定及對其衡量的標準至今仍在做“名”“實”之辯。但是從創作者、演員、題材及使用的母語對白等方面,都可認證《靜靜的嘛呢石》是一部純正的“少數民族電影”,評論界認為“唯有由藏族導演萬瑪才旦執導的《靜靜的嘛呢石》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少數民族電影”[4]370。第二,《靜靜的嘛呢石》較成功地實施了少數民族電影慣常使用的影像話語策略——象征。其實,準確地說,該部電影應該是使用了“弱假定象征”。第三,實現了政治上的“叫好”和文化上的“叫絕”。[4]47《靜靜的嘛呢石》將電影的所指超越了銀幕上的具象化的能指。影片使用的是象征類型中的“弱假定象征”。強假定象征是將不能共存的因素放在一起,以其敘述中的突兀性、無邏輯性刺激逼迫觀眾思考其內涵意義。而弱假定象征是具有象征性的元素自然處于影片敘事中,不能接受象征的觀眾可對影片作順利解讀,能接受象征的觀眾可以從中體驗象征所帶來的暗示與多義。[5]
首先,《靜靜的嘛呢石》中具有象征性的元素全部通過故事做自然呈現。萬瑪才旦是藏族知名小說家,講故事是其拿手的本領。“我創作一個故事片,它肯定得有故事,劇本提前寫好,然后完全按編的故事拍。”[6]影片講述了主人公小喇嘛從寺廟回到位于村落的家里過年,然后又回到寺廟的三天經歷。故事以循環式的結構,將小喇嘛不斷克服各種阻礙實現他戲劇性的需求做完整敘述,故事顯得精嚴工巧。其中大有深意的場景、人、物:朝圣、祈愿大法會、喇嘛、刻石老人、放生羊等藏族文化元素,被以長鏡頭甚至定格、特寫之類的手法拍攝出來,并被置于敘事的“前景”,可以看出導演希望觀眾能對他們做一種由外而內的深刻“凝視”。但這些都是故事中必不可少的構成。沒有參與“象征”猜謎的觀眾完全可以毫不費力地理解故事。例如,“電視”這一物象貫穿影片始終,與片名、片頭、片中頻繁出現的象征著宗教、傳統的嘛呢石對應,它象征了世俗、現代。同時,“電視”又是具有宗教身份的小喇嘛情不自禁的世俗需要,這一具有象征性的元素完全通過故事做自然呈現,是構成故事的重要元素、線索,不能接受象征的觀眾可對影片做順利解讀。
另一方面,又以象征暗示影片的多義性,能接受象征的觀眾可以從中體驗象征所帶來的內涵的豐富性和表達的藝術性。
影片的片名、片頭、片中,嘛呢石頻繁出現,作為一個石頭原本沒有任何意義,但在藏區刻有經文或者佛像的嘛呢石就帶有豐富的含義:路標、鎮邪祈愿。導演以特寫、長鏡頭展現嘛呢石,企圖通過嘛呢石靜默的狀態以及默無聲息的變化,表現藏族在樸實的生活常態下的質樸品質及其執著、信仰,也隱喻藏區傳統與現代的沖突與融合。
影片圍繞小喇嘛丹培進行敘事,小喇嘛自身有著宗教和世俗雙重身份,另外,他又成長于傳統和現代交融、碰撞的環境之中,他是“一個多維的(圓形)人物”。小喇嘛所處的兩個場景——寺廟和村子,也分別代表傳統的宗教世界和現代化進程中的世俗世界。影片既顯示了宗教與世俗、傳統與現代的對立,同時又反映了幾者的相互融合。一方面是宗教與世俗、傳統與現代的交融,如寺廟里面也有娛樂、電視,有相互之間的禮尚往來、噓寒問暖,特別是小喇嘛和老喇嘛之間的感情,相互體恤,關愛慰藉,更像世俗的親情;而在村子里,村民的生活,從物質到精神多與宗教掛鉤,如小喇嘛因宗教身份受到村民尊敬,村民們放生、生小孩請喇嘛念經等,都反映了藏區宗教與世俗生活的密切關系;藏傳佛教是具有鮮明民族、地域特色思想文化內涵的信仰體系,對藏民族的社會行為與心理特征都有極其深刻的影響,影片反映出佛教對凡俗生活的影響程度。另一方面,在日常化、瑣碎化的生活中,又常常面臨傳統和現代的沖突。在規范、單調的寺廟生活中,小喇嘛想方設法地看電視;看電視時,不想看藏族的傳統藏戲,而說服師父看現代戲謔式的電視劇《西游記》;看《西游記》時老喇嘛提議看唐僧求取真經的幾集,體現出苦行求法的信仰認同,而小喇嘛卻一心想看孫悟空大鬧天宮和菩薩變成女人考驗師徒的內容,體現了一種娛樂化的消費認同。大年初二,小喇嘛和弟弟看厭了傳統藏戲《智美更登》,于是奔向錄像室,但親吻的鏡頭讓小喇嘛當即離開錄像室又返回去觀看《智美更登》。這種反復無常的選擇反映了小喇嘛在傳統文化中成長,內心卻渴望著現代文化,但在現代文化中發現糟粕、受阻時,又會自覺回歸傳統。然而,這種回歸同樣會遭遇挫折。傳統藏戲《智美更登》結束,演員們馬上大跳現代迪斯科。影片先用長鏡頭、固定鏡頭拍攝:小喇嘛戴著孫悟空面具,孤獨、靜默地看著這一切,之后,機位變化,他被拉到整個遠景畫面邊緣。這一畫面,即象征傳統文化、信仰在藏區的現代化進程中不斷面臨挑戰,又有面臨的日常化、瑣碎化的文化沖突中所產生的精神、信念困惑。影片最后以長鏡頭的方式展演小喇嘛在寺廟和家之間的穿梭,更藝術、凝練地象征了宗教和世俗、傳統與現代對立卻又相融的關系。影片結尾,小喇嘛不舍地把孫悟空面具裝進懷里跑向了祈愿法會,片尾有十幾分鐘沒有對白,僅僅展示小喇嘛從父親那頭“跑”到大法會,“跑”的過程其實隱喻的是他心靈的轉換必需的過程。這樣的結尾寓意現代、世俗生活結束后,依然要進入宗教生活的莊嚴與神圣之中,藏民族信仰、文化的隱憂仍然無法撼落其藏民族信仰、文化自信。
綜觀整部影片,其通過小喇嘛的故事隱喻了如下兩點:
一、真實的藏區
正如導演萬瑪才旦在“導演闡述”中表示:“我渴望以自己的方式講述發生在故鄉真實的故事,要真實地反映藏區的現實生活。”[4]45《靜靜的嘛呢石》沒有主題先行的預設,有意背離此前藏族題材電影的強烈(社會)沖突大敘事模式,以生活流的方式在清晰的故事情節中反映真實的藏區,沒有好萊塢的殖民主義意識下所形成的民俗、宗教、政治大拼盤,也不是對外族文化獵奇而成的烏托邦。環境選取中不同于以往民族電影中刻意羅列雪山、草原、寺廟、民居等地域符號性較強的景物,或是藏區唯美的自然風光,而是將具體環境鎖定于冬天光禿禿的普通村莊。小喇嘛、小活佛均為現實中的喇嘛、活佛,以藏族非職業演員出演,客觀如實地反映人物的情感、氣質。場景、細節全部追求真實。在拍攝時以自然光、長鏡頭、固定鏡頭拍攝,取景多為遠景、全景和中景,靜靜地“旁觀”。揭示出真實的轉型期的藏族社會,反映傳統和現代、宗教和世俗對立、融合過程中人的思想、情感、觀念、信仰的變化。
二、面對傳統文化現代轉型的反思
(一)對傳統文化的態度
影片自豪地表現藏族文化的歷史悠久、博大精深、神秘獨特;同時對本民族命運、民族文化做反省和思考,有著弘揚傳承藏族文化的高度責任心;也表達了對傳統文化在現代化進程的沖擊下逐漸消亡的擔憂和焦慮。在此,萬瑪才旦清醒地認識到,在當今時代的現代化浪潮中沒有任何民族、文化可以故步自封。如何將現代文明與傳統文化完美地結合在一起,這是作者和現代人共同思考的重要問題。
(二)對傳統文化現代轉型的態度
1.影片反映了作者能正視社會轉型中必然遭遇的問題。陸學藝、景天魁提出“社會轉型是傳統向現代,是封閉向開放的社會變遷和發展”[7]。在其中,必然遭遇傳統和現代的沖突、內部和外部的沖突、局部和整體的沖突。影片客觀地揭示了藏區發展過程中的本質特征。
2.影片透露出對社會、文化發展的樂觀態度。一方面有對現代文明的肯定。如村里通電燈、公路后,連寺廟里的僧人都感慨生活方便多了,收音機、電視開闊了村里人的眼界,現代消費品豐富了藏區的生活等;另一方面顯示出藏民族的信仰、文化自信,影片中被仰拍鏡頭所展示的傳統、宗教文化的象征物件,影片結束時莊嚴悠長的法號聲,隱喻了藏民族信仰、文化的隱憂仍然無法撼落的藏民族信仰、文化自信。殘缺的嘛呢石終究不失其藏族信仰的神圣性。
從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到《靜靜的嘛呢石》中所使用的象征手法:弱假定象征,這種表達方式既可避免如《盜馬賊》等類電影由于文化距離產生的誤解,使不能接受象征的觀眾仍可對影片的故事較順利解讀;又可以以象征形成豐富的內涵,避免如早期《五朵金花》等只能形成單一的意指,讓能接受象征的觀眾可以從象征所帶來的暗示與多義中得到更為豐富的審美體驗。所以,弱假定象征可以是少數民族電影的一種有效的話語策略。雖然少數民族電影在不斷嘗試中,已經找到恰適自我表達的話語方式,但是我們縱覽少數民族電影對象征手法的使用,不管是“十七年”還是新世紀的電影,都是急于凸顯少數民族的主體性的,那么如何超越民族本位形成對“人”的關注,如何以文化為節點觀照“人”,如何在自我主體呈現的同時達成藝術的普適性,仍是少數民族電影發展所需要解決的關鍵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