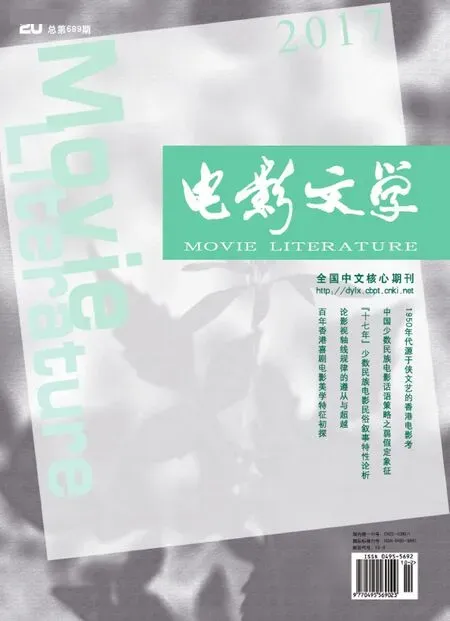論影視軸線規(guī)律的遵從與超越
馬權威
(南陽理工學院,河南 南陽 473004)
影視藝術是一種用二維的屏幕表現(xiàn)三維空間的藝術。在三維的現(xiàn)實空間中,任何一個事物都有其明確的坐標方位,不管是東西南北,還是上下、前后、左右,抑或是地理學意義上的坐標體系,都是三維空間方位或方向的表征方法。在影視創(chuàng)作實踐中,二維的屏幕方位和方向的表征方法變成了上下、左右、前后,并且上下、左右都是相對于四框來說的,于是,四邊成為重構(gòu)空間的參照,軸線成為人物關系和運動方向重新建構(gòu)的基礎。對大多數(shù)影視創(chuàng)作者來說,在遵從軸線規(guī)律的同時,也有故意違背越軸為達到某種藝術效果的。因此,要想解決超出軸線系統(tǒng)的基本范疇的問題,必須深刻理解軸線,只有理解軸線的本質(zhì),掌握軸線的理論系統(tǒng),才能正確處理軸線,才懂得何時需要遵從軸線規(guī)律,何時需要打破軸線規(guī)律。
一、軸線觀念的溯源與軸線的內(nèi)涵分析
對任何事物的研究首先要探尋其淵源,才能厘清其脈絡,進而掌握其本質(zhì),做到“辨章學術,考鏡源流”。軸線最原初的觀念并不是電影創(chuàng)作者的原創(chuàng),而是源自我們生活的經(jīng)驗。在日常的生活中,我們判斷甲、乙兩個正在面對面談話的人位于左邊或者右邊的時候常常依靠你所站的位置,當你站在一側(cè)判斷出甲居于畫面左側(cè),乙位于右側(cè),可是你站在兩個人的另一側(cè)時候,反而是甲居右而乙居左。總之,我們所說的生活中的軸線實際上也是我們視覺空間參照體系,而構(gòu)成軸線的主體,既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物,觀眾易于在軸線的一側(cè)完成視知覺的空間建構(gòu)。
在電影誕生的初期,《火車進站》《嬰兒的早餐》的影片攝影機沒有搬動,人們尚未發(fā)覺軸線的規(guī)律,“鏡頭的視角位于一個能夠以最佳角度和合適軸線來審視事物的觀察者之處”①。當盧米埃爾將活生生的自然生活搬上銀幕的時候,梅里愛也已經(jīng)開始借用戲劇手法將電影演出為一個個節(jié)目。可以說這一時期的電影視點一成不變,成為正前廳前排觀眾的視點,盡管1897年的《威尼斯運河》成為第一部擁有“移動鏡頭”的電影,但是絕大部分的電影仍舊是“正前廳前排觀眾的視點”。這一時期的影片依然處于單鏡頭時代。直到1903年,《火車大劫案》以一種非同尋常的方式按照“場景”結(jié)構(gòu)影片,影片才開始結(jié)束“單鏡頭時代”,開始以場景作為影片的基本構(gòu)成單位。雖然讓·米特里在其《電影符號學質(zhì)疑:語言與電影》一書中提出:“1901至1903年拍攝一些紀錄片的時候,埃德溫·波特在具有全景特征的自然背景中進行拍攝,甚至還拍攝了一個類似于正/反打的鏡頭。”但這時軸線的規(guī)律依舊沒有被發(fā)覺,僅僅是一次無意識的嘗試。“在1910年中期,保持銀幕方向一致性的觀念,成為好萊塢式剪輯的一個隱含規(guī)則。這種規(guī)則如此重要,以至于好萊塢把這種剪輯方法稱為180度系統(tǒng),也就是說攝影機應該放在動作的某一邊的半圓內(nèi)。”②在《一個國家的誕生》和《黨同伐異》中我們可以看到軸線規(guī)律的應用,而這種應用顯然沒有將軸線上升到系統(tǒng)的理論的高度,但這個時候已經(jīng)開始了軸線的使用。比如在《一個國家的誕生》中,為慶祝兄弟回歸一場戲,即81分15秒左右出現(xiàn)了在一個軸線的處理。
“1921年左右,這種風格方法(180度規(guī)則)成為好萊塢故事片的主流,使電影銜接得天衣無縫。”③綜上所述,軸線實際上是伴隨著電影的剪輯出現(xiàn)而誕生的,最早發(fā)現(xiàn)軸線,但真正提出并自覺運用軸線規(guī)律的一定是在經(jīng)典好萊塢時期,因為在經(jīng)典好萊塢時期,“既不能讓觀眾感到創(chuàng)作者的存在,也不能讓觀眾明顯地意識到自己的旁觀者的地位”④。可見,當時的創(chuàng)作者表達一個影視空間是通過各種剪輯手法將場景綜合展現(xiàn)出來的,同時盡量不讓觀眾覺察到這種手法的存在和觀眾自身的存在。
影視創(chuàng)作中“所謂的‘軸線規(guī)律’,指在用分切鏡頭拍攝同一場面的相同主體的時候,攝像機鏡頭的總方向須限制在同一側(cè)(如果軸線是直線,則各拍攝點應規(guī)定在這條線同一側(cè)的180度以內(nèi)),以保證被攝對象在畫面空間的正確位置和方向的統(tǒng)一”⑤。顯然這一定義源自我們對于現(xiàn)實空間的判斷和對于影像空間的再造性創(chuàng)造。當然,在影視中,所說的軸線又稱為關系線、運動線、180度規(guī)則,它是在影視拍攝中為保證影像的畫面空間統(tǒng)一感而形成的一條假想線、虛擬線。正是由于它是一條假想的線、虛擬的線,所以它存在于創(chuàng)作者的觀念中,表現(xiàn)在影視的畫面空間組合中以及觀眾的觀影體驗中。
二、軸線規(guī)律遵守的實踐“情境”
早期的電影為了保持空間的真實和視覺的連續(xù)性,采用戲劇式的手法,讓攝影機采用固定視點,以視點的固定和戲劇式的連貫維持視覺的連續(xù)流動與空間的統(tǒng)一這一“情境”,觀眾如欣賞戲劇一樣觀看電影。按照杜威的觀念,情境指的是“周圍的被經(jīng)驗的世界”的“背景性整體”,觀眾依然會按照“被經(jīng)驗的世界”和“背景性整體”去認知電影。“一切反省的探究都是從一個有問題的情境出發(fā)的,而這種情境不能用它自身來解決自己的問題,只有把這個情境本身所沒有的材料引入這個情境之后,這個發(fā)生問題的情境才能轉(zhuǎn)化為一個解決了問題的情境。”⑥不過,隨著電影作為藝術形式的屬性被開掘以來,導演們開始主動搬動攝影機,剪輯成為慣常的手法,視覺的連續(xù)流動與空間的統(tǒng)一的“情境”被打破。早期的電影工作者為了將這個“發(fā)生問題的情境”轉(zhuǎn)化為“一個解決了問題的情境”,首先在人物對話領域采用了正反打的方式處理視覺的連續(xù)流動與空間的統(tǒng)一,于是正反打被作為軸線規(guī)律的典型應用,并成為流暢性剪輯的慣用技法。隨后,好萊塢將軸線作為封閉敘事的基石,為了獲得流暢性的剪輯與空間的統(tǒng)一在前期的拍攝中,必須正確處理軸線,軸線開始從單純處理人物對話關系的規(guī)則邁向處理運動關系、空間指向、視角視線的理論系統(tǒng)。所以對于軸線的遵從就是為了保持銀幕方向一致性和空間連續(xù)性,因此,在影視創(chuàng)作中只要是為了保持這一原則往往要求遵守軸線。直到今天,這一規(guī)則仍然奏效,違背的話會冒很大風險,它被當作制作電影故事的較為順暢或流暢的創(chuàng)作方式。
軸線規(guī)律是在經(jīng)典好萊塢流暢敘事的土壤上的成長起來的一種創(chuàng)作手法。顏純鈞在其《中斷與連續(xù)——電影美學的基本范疇》一書中指出:“連戲”是經(jīng)典好萊塢時期在剪輯上的基本原則,不管鏡頭之間如何中斷,剪輯必須做到揭示出和呈現(xiàn)出敘事的連續(xù)性。⑦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軸線規(guī)律的主要功用不僅在于揭示出和呈現(xiàn)出敘事的連續(xù)性,還要保持空間的統(tǒng)一性以及觀眾觀看、視角視線的吻合性。其實,這都可歸結(jié)于為了維持視覺和敘事的連續(xù)性。因此,對于軸線規(guī)律的認識和使用都是出于這一目的,并且圍繞這一目的,在盡可能遵守的時候竭力遵守,對于不能遵守的采用合理越軸的辦法予以實現(xiàn),比如利用主體的運動、鏡頭的運動、特寫鏡頭、中性鏡頭等均可實行合理的越軸,這是軸線得以應用的實踐“情境”,從保持空間的真實出發(fā),逐步邁向視覺的連續(xù)性,進而達到空間連續(xù)與視覺連續(xù)的統(tǒng)一。在實踐的砥礪中,軸線作為一種相對獨立的藝術技法,現(xiàn)在已從最初的懵懂探索演化為成熟的技術方法,并且從藝術和技術的合流中趨向于珠聯(lián)璧合的圓潤。
三、遵守軸線規(guī)律的理論“語境”
“語境”是語言學的元理論范疇,而所有表達為語言的理論系統(tǒng),都必須考慮到理論系統(tǒng)表達的語境的客觀存在。軸線規(guī)律在眾多的理論表述中,大都從軸線的定義以及分類的角度來闡釋,很少能夠從軸線產(chǎn)生的背景、發(fā)展為理論系統(tǒng)的原因去探究以及使用軸線的原因和必要性角度去闡釋。僅僅從定義、分類、功能的作用方面去闡述軸線規(guī)律,顯然缺乏理論敘述的“語境”。軸線規(guī)律說到底就是為了維持觀眾的空間的真實性和視覺連續(xù)性,不讓觀眾頭腦中產(chǎn)生混亂感,從而分散觀眾對于影像故事的注意力,這是使用軸線的前提條件和目的。電影中的空間感是在二維的平面上塑造的一種空間真實感,觀眾為了獲得這種空間感,需要參照現(xiàn)實,以銀幕的四邊為參考重構(gòu)現(xiàn)實空間,這種空間現(xiàn)實感的生成依賴于觀眾的內(nèi)心世界和現(xiàn)實世界。當面對面交談的兩個人在上一個鏡頭中已經(jīng)確立了二者的位置關系,在下一個鏡頭中若有改變必須予以交代,否則觀眾便容易混淆是非。比如交戰(zhàn)的雙方在戰(zhàn)場上拼殺,必須充分利用軸線規(guī)律,準確地表達出雙方的位置關系和方向關系,否則就會讓觀眾迷失,甚至分不清交戰(zhàn)雙方,進而影響對劇作的理解。但是空間的真實性和視覺的連續(xù)性有時候并非所有影片和作者所追求的效果,比如有時候在一些MV中為了獲得節(jié)奏感而故意違背軸線,還有在電視直播類節(jié)目中一些突發(fā)的狀況根本無法估計軸線的遵從與違背,因為此時電視傳播的內(nèi)容要素要遠勝于形式考量。總之,對于軸線規(guī)律的遵守與違背來說,藝術創(chuàng)作本來就沒有鐵定的法則,規(guī)則說到底都是服務于藝術表達的,因此,創(chuàng)作者如果脫離維持觀眾的空間的真實性和視覺連續(xù)性這個目的和前提,進行的故意違背軸線就有了可能性與可行性。
四、軸線規(guī)律違背的可能性
1956年,法國新浪潮導演戈達爾拍攝了影片《筋疲力盡》,引起了電影界內(nèi)外的廣泛關注。戈達爾就不受軸線的制約,大量采用了跳切的手法,不管是在大街上從左至右行駛的公共汽車突然改變方向,還是在追逐的那場戲中卡車的突然消失,抑或是男女主人公在咖啡館里談話的那場戲中人物動作的不停“跳動”。在戈達爾的影片中,鏡頭不以時空和動作的連續(xù)性構(gòu)筑影片,而以跳切的形式組接鏡頭,突出必要的表現(xiàn)內(nèi)容,省略不必要的時空過程,以情節(jié)內(nèi)容的內(nèi)在邏輯為依據(jù),兼顧觀眾欣賞心理的能動性和連貫性。在這一理念的支撐下戈達爾甚至能夠把不同時空的場景直接剪輯在一起,絲毫不顧觀眾的觀影習慣以及軸線的制約。戈達爾熟悉好萊塢的造假手段,但是他遠離這些手段,富有獨創(chuàng)精神地開辟了跳切,違背軸線,采用布萊希特的間離表演效果而自成系統(tǒng)。這里戈達爾采用故意越軸線來達到空間的不連續(xù)性,從而遵從內(nèi)在邏輯、兼顧欣賞心理。
綜上所述,需要明確反映人物關系和環(huán)境關系以及人物和環(huán)境的關系時,軸線顯得特別重要;而在表現(xiàn)人物內(nèi)心、狀態(tài)化時,軸線顯得不重要,比如在影片《閃靈》中杰克·托蘭斯與格蘭蒂在洗手間對話的段落中,導演旨在側(cè)重人物的內(nèi)心世界描寫而做出的越軸就顯得不那么重要,甚至觀眾在關注劇情的時候就會忽略其已越軸,這就具備了為軸線規(guī)律的違背提供可能性與可行性。當然,有時候根本無須考量是否遵從,還是故意違背軸線,而要從創(chuàng)作和傳播的現(xiàn)實出發(fā),將軸線作為一種藝術手段、實現(xiàn)傳播效果的工具,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嫻熟地遵從,瀟灑地超越軸線。
五、結(jié) 語
總之,軸線并非金科玉律,不是任何導演、任何作品都要遵守的鐵定法則,也并非影視創(chuàng)作必須遵從的紅線或底線,不可逾越;與此同時,軸線亦非一無是處,它是建構(gòu)畫面空間、維系畫面方向的有力工具。當然,在有些創(chuàng)作中,只須關注傳播的內(nèi)容,無須考慮軸線。因此,對于軸線的理論必須從整體上考量,從影片拍攝的實際出發(fā),從最終的效果需要去選擇軸線的遵從與違背乃至超越。
注釋:
① [法]讓·米特里:《電影符號學質(zhì)疑:語言與電影》,方爾平譯,吉林出版集團有限公司,2012年版。
② [美]大衛(wèi)·波德維爾、克里斯汀·湯普森:《世界電影史》,范倍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
③ [美]道格拉斯·戈梅里、[荷]克拉克·帕福-奧維爾頓:《世界電影史》(第2版),中國電影出版社,2016年版。
④ 周傳基:《打破軸線,一個中國神話》,《電影藝術》,1996年第5期。
⑤ 謝紅焰主編,宋曉麗、王濤副主編:《電視畫面編輯=TV montage techniques》,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
⑥ 杜威:《確定性的尋求——關于知識行關系的研究》,傅統(tǒng)先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⑦ 顏純鈞:《中斷與連續(xù):電影美學的一對基本范疇》,中國電影出版社,201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