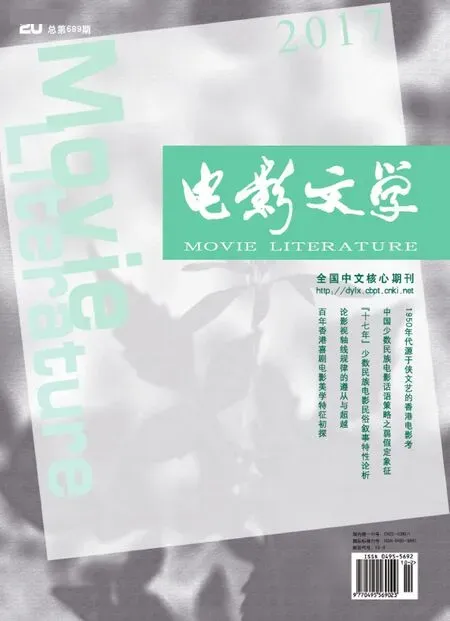美國諜戰電影的文化解析
于海燕
(內蒙古科技大學外國語學院,內蒙古 包頭 014010)
諜戰電影是世界電影史中不可忽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不僅以懸疑、驚險等審美風貌形成了較為穩定、成熟的藝術特點,并因此而備受大眾青睞,是商業電影中長盛不衰的亞類型片之一,同時,諜戰電影還關聯著特定的時代背景與地域語境,乃至具體的政治意識形態和文化。而在特殊的歷史、軍事、國際關系等原因的作用下,美國在國內外所參與的間諜活動可謂異常活躍,美國諜戰電影也由此層出不窮,盡管其發展過程中有過起伏,歐、日、韓等國家與地區也各有諜戰電影的崛起,但總體而論,美國諜戰電影依然在同類電影中扮演著領頭羊的角色。透過海量的諜戰電影,我們所感受到的不僅僅是美國(以及世界)間諜風云的興衰變遷,還有著對某種屬于美國的國民精神,以及從美國的角度出發,面向世界的時代文化宣傳的窺視。
一、商業娛樂文化
商業娛樂文化是大眾在進行文化消費過程中逐漸興起的一種文化形式,在美國諜戰電影中,商業娛樂文化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滑稽、反權威式的逗笑式娛樂;二是具有沖擊力的視聽體驗。
第一類中有如安吉拉·羅賓森的《少女特工隊》(2004)、保羅·費格的《女間諜》(2015)、蓋·里奇的《秘密特工》(2015)等。這一類電影只是借助了“諜戰”這一外衣,而將形形色色的人集合在一起,通過發生各種誤會來制造笑料,觀眾在欣賞這一類諜戰電影時,不需要在觀看的同時進行推測、想象或背景分析,而能得到一種酣暢淋漓的放松。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美英合作,由彼得·修伊特執導的《憨豆特工》(JohnnyEnglish,2003)。在這部處處調侃英國的電影中,英國皇室珠寶被盜,而沒多久,軍情六處的頂級特工全軍覆沒,軍情六處不得不派出一名絲毫不靠譜的菜鳥特工強尼·英格利來保衛有可能失竊的女皇皇冠。由“憨豆先生”飾演的強尼看似智勇全無,不像個職業特工的樣子,在調查過程中也是洋相百出,例如,自以為是地分析一番結果掉到巨坑里;開著房車在倫敦街頭和助手狂飆;攀爬敵人的城堡結果從廁所出來,等等。而對手,即盜竊王冠的法國人也有自己蹩腳的一面,他作案的動機也是滑稽的,即想當英國國王,從而以英倫三島發展他的監獄事業。兩個經常搞砸事情的人碰面后,喜劇感也就應運而生了。電影以這種“小人物歪打正著成功”的模式贏得了觀眾的喜愛。
第二類則幾乎體現在所有當代諜戰影片中,如《007之大破天幕殺機》(Skyfall,2012)的導演薩姆·門德斯直言受了《暗黑騎士》很多啟發,電影中為觀眾展現了霓虹燈下的現代大上海、貴族感極強的蘇格蘭莊園以及流光溢彩的澳門賭船等,都呈現得唯美而富有跨越感;除此之外,片中還有大量的槍戰、爆炸、飛車追逐以及主人公的水底逃生鏡頭,這些也能讓觀眾感到相當過癮。與之類似的還有如馬丁·坎貝爾的《007之大戰皇家賭場》(2006),同樣采用了中國景色的艾布拉姆斯的《碟中諜3》(2006)等。以馬修·沃恩的《王牌特工:特工學院》(Kingsman:TheSecretService,2014)為例。在電影中,反派瓦倫丁報復社會的方式是讓每個人的手機芯片影響人類的神志,從而讓人類彼此殺戮,而反派選中的所謂精英則在腦內植入了反狂躁芯片。主人公金士曼特工們則兵分兩路,女孩嘉澤勒乘坐宇航員的人造升空器上升到大氣層之上試圖破壞瓦倫丁的衛星,然后再冒死降落;男孩艾格西則孤身深入虎穴,最后引爆在場精英腦內的芯片。幾經波折,他們終于戰勝了瓦倫丁。電影中的教堂殺人、外太空景色、大腦爆炸的煙花齊放景象,都是電影提供給觀眾的“奇觀”。
必須指出的是,電影這門藝術本身就已經降低了接受者的準入門檻,而這種努力追求體現商業娛樂文化的諜戰電影更是代表了一種大眾傳播媒介的“去精英化”,它們將原本神秘的、高高在上的諜戰故事以一種有趣、輕松的方式展現在公共空間中。而敘事深度甚至敘事的合理性都不是必要的,這一類爆米花式的電影也無法對公共文化空間的政治質量有所提高。
二、暴力美學文化
如前所述,給觀眾制造令人驚嘆的視聽體驗,從而讓觀眾獲取直接的感官愉悅是諜戰電影實現商業價值的手段之一,這是一個經過長時間與大量作品反復驗證后得出的結果。盡管暴力不可能取代敘事技巧和內涵給電影制造的魅力,真實的諜報工作也并非處處是“斗智亦斗勇”,總是使諜報人員處于險象環生、需要動用暴力的環境中,但觀眾出于獲取快感的需要,賦予了暴力呈現合理性,甚至默認情報人員都必須掌握格斗、槍械等方面的技能,如道格·里曼的《諜影重重1》(TheBourneIdentity,2002)中,失憶的杰森·伯恩發現自己的特工身份時,自己超人的打斗能力就是依據之一。加之美國電影產業盡管也受政策束縛,但在分級制度下,并沒有特定的對“銀幕純潔性”的統一性要求,因此,早在消費時代全面來臨之前,暴力就已經成為美國諜戰電影的影像美學之一。
例如,在“暴力美學”這一美學風格先驅人物吳宇森執導的《碟中諜2》(Mission:ImpossibleII,2000)中,電影一開始就以一種帶有中式武俠意味的伊桑·亨特驚心動魄的攀巖場景來震撼觀眾,而在進入劇情后,電影中不僅出現大量亨特與對手的槍戰、摩托車追逐以及近身肉搏戲份,這些驚險、刺激的場景被吳宇森剪輯得既有節奏感,且突出了亨特任務的“不可能性”,又時刻顧及著觀眾的視覺疲勞。更重要的是,吳宇森善于在暴力中加入美,如倉庫打開時,劍拔弩張之際用慢鏡頭展現的飛出的鴿子,隨后就是亨特以槍掃射,敵人倒地的場景,以及在美中加入暴力,如男女主人公初遇時的弗拉明戈舞蹈,在吳宇森的重疊剪輯以及遮擋前景的設置下,觀眾能夠充分感受到這飄然若仙的舞蹈背后對抗的意味。與之類似的還有如動用了太空激光武器,冰上快艇作戰的李·塔瑪霍瑞的《007之擇日而亡》(2002),乃至《007之明日帝國》(1997)、《諜影重重2》(2004)等。
另外,電影技術的不斷發展,也從側面助長了暴力美學文化在諜戰電影中的流行。因為暴力美學的實質是形式美對暴力的鈍化,在技術的處理下,暴力行為的攻擊性、侵害性在視覺上被削弱,如子彈、流血等鏡頭能在處理之下顯得并不驚悚,從而對倫理道德也做出一定的妥協。
而需要注意的是,在當前的審美價值下,美國諜戰電影中的暴力存在一定的濫用現象。甚至對于一些已成為符號的系列電影來說,暴力場面已經成為電影的標準配置,電影的文戲與武戲的比例和順序設置都在工業流水線化生產中形成了模式。這實際上是有可能使觀眾因為對套路熟悉而失去暴力場面原本應起到的刺激感的。而部分電影更是頻繁在主人公身上展現夸張、不真實的暴力行為,使主人公成為“打不死”的角色。這樣是對暴力美學的傷害,對于這種在商業需要面前對藝術性的犧牲,電影人有必要給予一定的注意。
三、個人英雄主義文化
如果將諜戰電影中的暴力美學文化僅僅理解為制造感官刺激與非常態心理體驗的需要,那么依然不是對美國諜戰電影的全面認知。在電影中角色表現出具有野性的動作和具有美感的破壞力時,它代表的是一種身陷阻力、困難或絕境中,依然不肯服輸、尋求突破、奮勇向前的精神力量。觀眾也會因為對主人公有情感上的投射而在主人公這種對困境的突破中獲得快感。在人類的進化史上,正是這種精神為人類爭取到了更為廣闊、適宜的生存、發展空間,導致了人類文明的輝煌。因此,暴力被與英雄情結聯系在一起的。這就必須提及美國諜戰電影中的個人英雄主義文化。
可以說,在對個人主義以及個人英雄主義的崇尚上,美國是表現得最為明顯的國度之一。從包括好萊塢電影在內的多種文化輸出中,都不難看出美國文化習慣于將某項偉大的屬于多數人的事業,以及在完成這項事業中所要付出的巨大努力歸功于面目鮮明的個體,歌頌個體的性格品質,如英勇頑強、無私無畏、敢于犧牲等。而在諜戰電影(包括戰爭電影、科幻電影、西部電影等)中,作為故事片的電影本身就有著塑造令觀眾印象深刻的角色形象的任務,而對個人英雄主義的推崇更是促使美國電影人將個人英雄主義發揮到極致,塑造了一個又一個身懷絕技、在任何情況下都能化險為夷的孤膽英雄。尤其是在諜戰電影中,諜報工作的特殊性使主人公無法獲得戰爭片中氣勢恢宏的友軍支持,如走鋼絲般的,需要牢牢保密的工作往往將重任交于少數幾個人或一個人,這種后援的匱乏更凸顯了他們背負巨大壓力,但因為他們有膽有識、智慧英武,依然能夠獨來獨往完成任務的魅力。而主人公的單槍匹馬也很好地為觀眾制造了探究其究竟如何完成任務、會付出怎樣的代價的懸念。
一言以蔽之,對個人英雄主義文化的弘揚,是美國諜戰電影內外因兩個層面上的雙重需要。在馬丁·斯科塞斯的《無間道風云》(TheDeparted,2006)中,出身于底層,一心想成為一位堂堂正正的警察的比利被派去勢力猖獗的愛爾蘭黑幫中做臥底,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壓力,忍受著黑幫的暴戾,與自己熟悉的正義的警察生活剝離,以至于不得不去看心理醫生。在陷入層層矛盾時,比利也曾經在電話中對自己的上級吼道:“我要要回我的身份!”也曾對心愛的人表示過退縮的念頭:“我想換個城市住會更好,就不會這么痛苦了。”然而他還是克服了自己的恐懼與迷茫,在失去支持的情況下將自己的臥底工作堅持了下去。與此類似的電影還有如迪米特里講述二戰期間與納粹斗爭的《諜戰方程》(2005),克里斯托弗·漢普頓表現雙面間諜的《秘密間諜》(1996)等。
還有的影片則是以展現一個精干的特工小隊的方式來體現個人英雄主義。如整個《碟中諜》系列,在布拉德·伯德的《碟中諜4》(Mission:Impossible-GhostProtocol,2011)中,伊桑·亨特無疑是任務中最重要的人,但他的助手布蘭德、班吉和簡都給亨特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精妙配合,例如,在迪拜偷換鉆石的這一場戲中,四個人利用自己不同的才能和性別優勢合作得神完氣足,令人驚嘆。有了布蘭德這些綠葉,亨特這朵紅花才更為耀眼。
在經過了數十年的發展之后,一方面是內因上無可避免的審美疲勞,另一方面則是外因上“冷戰”的結束,諜戰電影也已經進入了瓶頸區。而在諜戰片本身的邏輯魅力之外,具有民族特色的,或是與其他類型或亞類型影片共通的文化特質的加入,能夠充分幫助諜戰片拓展劇情,提升內涵,創造更為豐滿的人物。在美國諜戰電影中,商業娛樂文化、暴力美學文化和個人英雄主義文化在迎合觀眾需要、獲得觀眾積極反饋方面,有著不可忽視的意義,而這三者之間是相互交叉、滲透的。在觀眾的“諜戰夢”和窺探欲、冒險欲還未得到充分滿足的當下,諜戰電影顯然還有繼續進行開掘和嘗試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