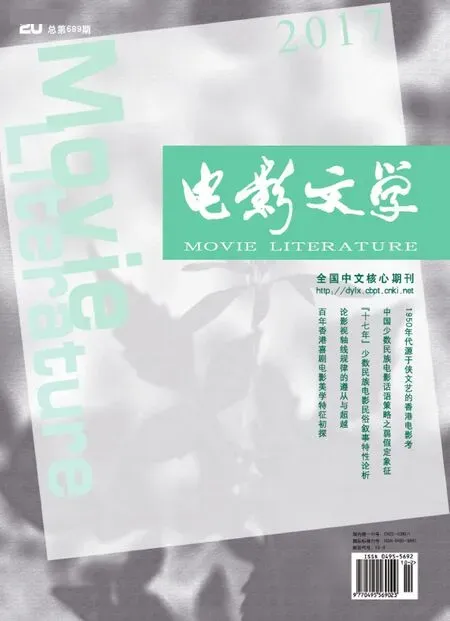國產(chǎn)古裝電影的視覺審美表現(xiàn)
王 巖
(河南工學(xué)院,河南 新鄉(xiāng) 453003)
由于我國具有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古典文化,因此在國產(chǎn)電影中,古裝電影成為電影創(chuàng)作者所熱衷于表現(xiàn)的一種電影類型。同時,古裝電影獨特的視覺情境、相對陌生化的審美表現(xiàn),以及對歷史或經(jīng)典的重寫、對特定時代傳統(tǒng)文化元素的再現(xiàn),都對觀眾具有很強的吸引力。很多既有口碑,又具有票房競爭力的古裝片,如《黃飛鴻》系列、《滿城盡帶黃金甲》《葉問》以及《捉妖記》等,都有其獨特的視覺審美元素。隨著電影技術(shù)的日新月異,古裝電影受到的拍攝條件限制也越來越少,其視覺審美表現(xiàn)的空間越來越多。本文從古裝電影的敘事空間、人物形象以及視覺的主題釋義作用三方面,來分析當(dāng)前國產(chǎn)古裝電影的視覺審美特色。
一、國產(chǎn)古裝電影的敘事空間
敘事空間是電影展開敘事的背景,為人物的活動提供場所。在很多影片中,敘事空間不僅是背景,而且作為重要的視覺表現(xiàn)對象,既有抒情功能,也有敘事作用。電影空間是非常復(fù)雜的,這種復(fù)雜性從多個層面決定著電影敘事的深度和廣度。不了解電影的這一特性,就難以對電影表達內(nèi)涵有深刻的洞察。對于古裝電影來說,敘事空間是最具審美表現(xiàn)力的元素之一。古裝電影與其他題材的影片相比,更加注重空間的境界感。它們?yōu)橛捌峁┖诵幕{(diào),不但能夠很好地提升審美力度,也使得整部影片具有審美統(tǒng)一性。比如,《滿城盡帶黃金甲》的華麗、《刺客聶隱娘》的詩意、《英雄》的悲愴、《葉問》的平實等,都與影片敘事空間的選擇、布局和節(jié)奏把握有著十分密切的關(guān)系。
首先,敘事背景能夠為觀眾提供很多與影片相關(guān)的信息,這使得觀眾能夠更好地融入影片具體的敘事空間當(dāng)中,更容易理解影片內(nèi)容和人物的生活現(xiàn)實。古裝電影的視覺審美作用之一,便是敘事背景的建構(gòu)。以《狄仁杰之通天帝國》為例,影片以唐代為背景,講述了狄仁杰對大臣自燃疑案的偵破過程。片中,高達66丈的“通天浮屠”完工在即,而洛陽城內(nèi)接連發(fā)生了被武則天提拔的親信無故自燃的事件。武后此時尚未登基,她起用了曾反對自己的狄仁杰來偵破此案。片中具有古典風(fēng)格的洛陽城,給觀眾留下了深刻印象。斗拱飛檐,雕梁畫棟,美妙的建筑散發(fā)出古典的氣息。而通天浮屠則展現(xiàn)出唐代佛教的興盛。影片中虛構(gòu)的鬼市則深藏在鬧市之下。這里如同幽深的洞窟,各種人物魚龍混雜。影片中展現(xiàn)的狄仁杰,不僅文可經(jīng)國,而且武功超群。因此,在敘事背景的搭建中,著重強調(diào)了洛陽城與其下的鬼市,洛陽對應(yīng)廟堂之高,而鬼市則對應(yīng)江湖之遠,狄仁杰在二者之間穿梭自如,展現(xiàn)出他超群的技藝。
其次,電影是時間與空間的藝術(shù)。時間是影片敘事的縱向線索,空間則是影片敘事的橫向展開。每一部影片都有其特定的空間風(fēng)格,也是影片視覺審美的重要內(nèi)容。以馮小剛的《夜宴》為例,影片改編自莎翁名劇《哈姆雷特》,因此影片充斥著一股陰翳的氣息。馮小剛將時代背景設(shè)定在我國五代十國時期,先帝駕崩,皇叔篡位并派人追殺在外巡游的太子,而太子后母婉后為了保全太子則委身厲帝。除了竹林中羽林衛(wèi)追殺太子的橋段,影片大部分為室內(nèi)場景,雖然皇宮大殿不可謂不恢宏,但影片用暗淡的光線使內(nèi)景備顯壓抑,這也詮釋了宮廷斗爭的殘酷。例如,太子無鸞在面見婉后時,他戴著面具,但從小與他青梅竹馬的婉后一眼就認出了太子。當(dāng)無鸞揭下面具跪倒,婉后則深情地擁住太子。宮殿內(nèi)昏黃的燈關(guān),使氣氛增加了幾分曖昧,但無鸞說了一句“母后”之后將婉后推開,生氣的婉后開始與無鸞舞劍。二人停手后,婉后與無鸞在寢殿內(nèi)交談,而厲帝則躲在屏風(fēng)后偷聽。陰暗的空間風(fēng)格,與宮廷斗爭的黑暗殘酷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構(gòu)成了影片敘事的主基調(diào)。
二、古裝電影的人物形象塑造
人物形象是電影視覺風(fēng)格的主要表現(xiàn)元素,是影片核心的審美對象,也是展現(xiàn)影片審美意境和價值立場的靈魂。古裝電影中的人物更是如此。觀眾通過人物的外部形象,可以了解很多信息,鮮明生動的人物形象,既能夠很好地烘托出人物的個性特征、心理世界,也能夠展現(xiàn)人物所處的特定歷史年代、特定地域文化以及生活狀態(tài)等。這些都便于觀眾對影片更深入地了解,更好地實現(xiàn)影片的審美價值。在古裝電影中,人物的視覺形象塑造更為重要。
首先,美觀得體的人物視覺形象塑造,可以從整體上提高影片的視覺審美價值。人物形象往往占據(jù)影片畫面的核心位置,其表情、行為與衣著,都是觀眾重點注目所在。因此,美觀得體的人物形象,首先具有視覺審美上的意義。以程小東執(zhí)導(dǎo)的《倩女幽魂》為例,影片講述了書生寧采臣與女鬼聶小倩相愛的故事。片中,寧采臣與聶小倩的形象,可以說給觀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片中,寧采臣是一個窮書生,他穿著灰布長衫,頭上戴著黑布帽子,腳上的鞋子還破了一個洞。寧采臣背著的破書簍,更是增添了幾分窮酸氣。與窮酸的外表相比,寧采臣有一顆執(zhí)著癡情的心,他對聶小倩的愛是令人動容的。反觀聶小倩,她在出場時頭上豎著高聳的美人髻,一襲白衣飄飄然如仙子一般。她在勾引一個過路的武生后,樹精姥姥將武生精氣盡數(shù)吸去,而聶小倩則在一邊垂淚。聶小倩在勾引過路人時表現(xiàn)出狐媚的一面,而在面對寧采臣時,則表露出清純的一面。聶小倩與寧采臣之間的搭配,使觀眾從外到內(nèi)生發(fā)出對二者的認同。
其次,雖然人物形象是觀眾的審美核心所在,但電影創(chuàng)作者卻不能一味地追求視覺效果上的賞心悅目,而脫離人物的生活實際。這個實際既包括具體的年代,也包括人物在現(xiàn)實生活中的身份特征,更重要的是與人物內(nèi)在的個性相呼應(yīng)、相一致。例如,國產(chǎn)的古裝劇,展現(xiàn)的是中國古代的歷史情況,而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等級觀念占據(jù)重要的位置,人物身份的不同在服飾上有不同的限制,而要在電影中表現(xiàn)這種等級觀念,人物服飾的設(shè)置就顯得尤其重要。例如,《英雄》中,無名一身黑衣來覲見秦王嬴政,此時秦王正野心勃勃要一統(tǒng)天下。在秦宮大殿上,只有無名和嬴政二人。嬴政一身戎裝,威嚴(yán)地坐于大殿之上。秦朝尚黑,二者雖同為黑衣,但氣勢卻明顯不同。無名為劍俠裝束,而嬴政則為軍人戎裝,但二者的心靈卻是相通的,當(dāng)十步之內(nèi),無名已經(jīng)掌握了主動權(quán),他卻主動放棄刺秦,這是他心系天下蒼生的表現(xiàn)。而秦王也領(lǐng)會了無名的想法,但無名作為刺客則必須身死。黑色,也代表了無名死亡的結(jié)局。
最后,古裝電影是展現(xiàn)傳統(tǒng)文化的一扇窗。很多傳統(tǒng)文化中的標(biāo)志性視覺符號,也為人物形象的塑造提供了豐富的素材。以《刺客聶隱娘》為例,影片改編自唐傳奇《聶隱娘》,由于原著文體的特點,加之篇幅短小,自不可能對于聶隱娘這一人物有全面精細的刻畫。《刺客聶隱娘》則利用電影這一媒介,為聶隱娘的形象進行了延展,展現(xiàn)出我國盛唐時期的女性風(fēng)貌。影片中,與那些高挽發(fā)髻、寬袍大袖的貴族婦女不同,聶隱娘除了在剛剛回家時以女裝示人意外,其他時候皆穿著緊身利落的服飾。如果說貴婦是傳統(tǒng)女性的代表,那么聶隱娘就是女中豪杰的典范。而小說中聶隱娘富于人情的特征,不僅并未在電影中消解,反而得到了加強。從這一點來說,電影是基于小說原有敘事空間所做出的延展,其轉(zhuǎn)化不僅在于藝術(shù)形式,更在于電影對于小說人物精神的深刻把握,因此在文本的深處取得了共鳴。在聶隱娘一襲黑衣的冷酷外表之下,是她極富人情的溫柔之心。
三、古裝電影視覺元素的主題釋義作用
電影作為一種認識世界的方式,觀眾在看的過程中不僅抱有視覺審美上的需求,也有情感和認知上的需要。電影以畫面的方式,同時滿足觀眾這兩方面的需要。電影創(chuàng)作者依據(jù)一定的藝術(shù)觀念和電影審美訴求來安排和結(jié)構(gòu)畫面,通過各種視覺元素,搭建起影片的敘事架構(gòu),并闡述其中之意。在古裝電影中,視覺元素在主題釋義方面,也有非常突出的審美職能。
首先,視覺元素存在的重要目的就是使主題表達更清晰。在視覺元素大行其道的今天,好萊塢等依靠視覺元素來吸引觀眾的手段,無疑引起了國內(nèi)電影人的效仿。但無論電影如何肆意地制造視覺空間影像,其表達真實的生命體驗、借助畫面表意仍然是電影敘事的宗旨。以《滿城盡帶黃金甲》為例,影片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形式大于內(nèi)容的問題。影片以展現(xiàn)古代宮廷斗爭的殘酷以及人性的復(fù)雜為宗旨,大王發(fā)現(xiàn)太子與其繼母王后亂倫,而王后在發(fā)現(xiàn)后,則唆使自己的兒子二王子元杰在重陽節(jié)謀反,逼迫大王讓出王位。而大王子元祥、小王子元成則同樣虎視眈眈,整個宮廷籠罩在一片陰霾中。重陽節(jié)上,宮廷廣場上鋪滿了菊花,金燦燦的盛大而耀眼。從大王、王后到王子,他們身上的金色與菊花相映成趣。影片整體給人的視覺震撼極其強烈,其故事亦脫胎于《雷雨》,但故事的完整性以及情節(jié)的縝密性仍存在較大的問題。這也是目前國產(chǎn)古裝電影中普遍存在的問題,華麗的古裝無法掩飾劇情的虛弱,在這方面,中國電影人還需要做出很大的努力。
其次,視覺元素具有評價意義。以陳凱歌的《趙氏孤兒》為例,影片改編自元雜劇《趙氏孤兒》,原著故事本就家喻戶曉,這對于改編者來說,是一個挑戰(zhàn)。陳凱歌在將這個故事以影像呈現(xiàn)時,非常注重視覺元素的隱喻功能。片中,國君晉靈公就是一個昏庸暗弱之輩,在大將趙朔取勝歸來的路上,他竟然從城樓之上用彈弓射中馬的眼睛,導(dǎo)致發(fā)生了混亂。而屠岸賈對趙家的冤枉,也有他的分辨不明之因。影片對晉靈公的塑造,凸顯了他的昏庸。他的身材矮胖渾圓,說起話來總是嬉皮笑臉,完全沒有作為一國之君的威嚴(yán)。晉靈公的形象,顯然是影片創(chuàng)作者所批判的,他最終死于屠岸賈之手,也是自然而然的了。在趙氏一門的滅門慘案中,灰暗成為影像的主基調(diào),這是影片主創(chuàng)對視覺隱喻有意識運用的結(jié)果。視覺形象所對應(yīng)的心理機制是具有普遍性的,如暗弱昏黃的畫面往往能夠給予觀眾一種壓抑、悲傷、曖昧之感。趙氏一家本為忠臣,但遭到小人屠岸賈的陷害,滿門上下皆死于非命,只剩下了孤兒趙武。視覺影像此處的評價則是對趙氏一族的憐憫和對孤兒命運未知的擔(dān)憂。此外,影片中視覺元素的重復(fù),實現(xiàn)了強調(diào)作用。例如,韓厥總是夜半來見程嬰,而程嬰也背著趙武與他相見,二人之間看似有茍且之事,實際上是韓厥不斷催促程嬰伺機殺掉屠岸賈。這一反復(fù)出現(xiàn)的鏡頭,實際上是強調(diào)時間的流逝以及二人15年來的處心積慮、持之以恒。影片以這種方式,完成了利用視覺元素來對片中內(nèi)容形成評價。
綜上所述,國產(chǎn)古裝電影作為中國發(fā)展最為成熟的電影類型,其視覺審美表現(xiàn)上有很多獨特之處。無論是敘事空間、人物形象,還是主題釋義方面,視覺元素都有其自身的語言優(yōu)勢。并且,由于古裝電影有著鮮明的民族和地域特色,是對傳統(tǒng)文化外在與內(nèi)在的傳承和延展。因此,在電影審美差異化方面,古裝電影有很多獨具的表現(xiàn)優(yōu)勢,也是國產(chǎn)電影市場競爭力的一個重要來源。中國電影人如何發(fā)展這一類型,使之大放異彩,獲得國內(nèi)外觀眾的認可,則是需要仔細探究的系統(tǒng)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