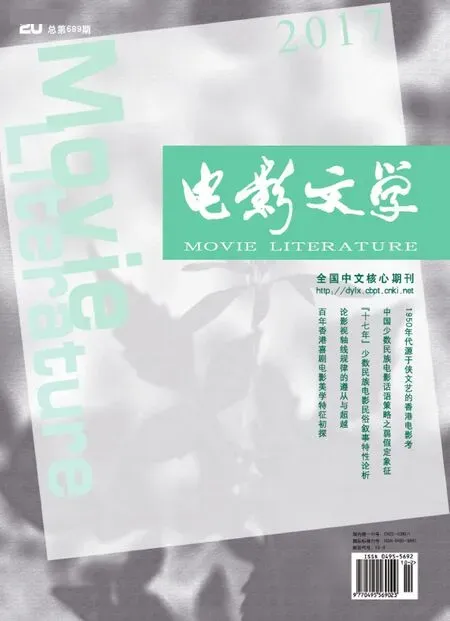淺析《驢得水》中的女性形象
曲明鑫
(海南熱帶海洋學院,海南 三亞 572022)
根據開心麻花同名話劇改編的《驢得水》講述了一個關于鄉村教育的故事,影片的情節完全來自虛構,但觀眾卻能從中看到歷史的真實痕跡,它喚醒了人們關于一段辛酸歷史的記憶。作為一部喜劇,《驢得水》不僅局限于調動觀眾的感官,還利用諷刺和荒誕的藝術手法令人產生更深的思考。
電影的時間設定在1942年,國民黨執政時期,四位有理想的教育者投身鄉村教育的建設中,充滿了雄心壯志。校長為教育事業付出了半生心血,裴魁山將改變農村的希望寄托在教育上,總會提出許多建設性的意見,周鐵男則愿意捐出自己的工資來為學生發獎學金,張一曼天真爛漫,親手為學生制作漂亮的校服。至于“呂得水”老師,實際上只是一頭驢,一直被說成是個人,目的是多要一份工資來維持學校的運轉。然而,國民教育司的特派員突然要來視察工作,萬般無奈之下他們只能找來銅匠來冒充“呂得水”老師,一場鬧劇由此展開。《驢得水》涉及鄉村教育難以為繼的困境和政府機構的貪污腐敗問題,同時揭示了人性的光明與黑暗,喜劇性的開端和悲劇性的結局令人唏噓不已,影片在審視歷史之時無疑也在針對現實,具有很強的批判和諷刺意識。
影片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角色是任素汐飾演的張一曼,她作為唯一一位女老師,代表了身體與意識已經覺醒的女性,沖破封建的枷鎖構建起女性主體形象,在與不同男性角色的互動中,她分別擔任了男性的反抗者與啟蒙者,是一個具有高度寓言特質的角色。然而一曼的悲劇結局則體現了更具壓迫性的權威對個體的摧殘。在《驢得水》中,銅匠媳婦和校長女兒孫佳作為女性的命運與一曼形成對照,成為那一時代女性群體的縮影。
一、女性主體的構建:從身體到意識
《驢得水》對張一曼的形象塑造是最為成功的,這個令人印象深刻的女性形象有著鮮明的個性和大膽的行事風格,在那個年代顯得特立獨行。電影版的《驢得水》仍然采用話劇版的原班人馬,任素汐已經在舞臺上演了五年張一曼這個角色,對人物性格有著非常深入的理解,在電影中依舊完成了出色的演繹。
雖然鄉下條件艱苦,但一曼依舊每天微笑面對生活,穿著漂亮的旗袍,平時喜歡唱歌跳舞。最重要的是,一曼把自由看得很重,正是因為不堪忍受世俗的目光,所以她來到了這片窮鄉僻壤追求自由自在的生活。一曼超前的性觀念在當時人眼中是傷風敗俗的,但她完全無視這種幾千年來延續下來的性道德對女性的壓迫,她只享受性為她帶來的身體愉悅,而并不將其作為一種愛情的保證或婚姻的籌碼,也不用封建社會的貞操觀念來約束自己。無論是與裴魁山還是和銅匠的結合,都僅僅是為了生理愉悅。她不僅直接地拒絕了裴魁山的表白,還主動去“睡服”銅匠,對她而言這種行為完全不與道德或責任產生任何關聯。一曼將掌控身體的權力完全把握在自己手中,這是對中國幾千年以來的男權主導下的社會意識的反抗,反對將女性作為男性的附屬品,拒絕承認男性對女性身體的所有權,她對身體權力掌控由此成為女性主體生成的一個關鍵環節。
影片中對于一曼的女性身體的刻畫令人印象深刻,她穿著自己制作的旗袍,將身體的曲線很好地凸顯出來,高開叉的設計又為她增添了一絲性感。一曼身材高挑,但也喜歡穿高跟鞋,顯得更為出眾。一曼還有一頭漂亮的頭發,燙過的頭發微微彎曲,流露出風情萬種。憑借自己的美色與誘惑力,一曼獲得了自己想要的東西,然而即便如此,她也要承受著世人對她的非議,忍受著屈辱的罵名。
對身體權力的追求與女性意識的覺醒緊密相連,一曼的內心是充滿自信的,當所有人對她的“放蕩”歷史心照不宣之時,她卻認為自己的檔案沒有任何污點,與世俗觀念的格格不入源于她超前的女性意識。她并不認為女性在任何層面上低于男性,她早于時代的女權意識反而被男性所壓制,他們無法接納不受控制的女性,尤其是自己的欲望得不到滿足之時。在影片中,男性用自己的權力去羞辱、毀滅一曼,一旦意識到自己對女性并不擁有支配權后就以毀滅的方式維護自己的尊嚴,這是傳統社會性別觀念的一種縮影,而這種狀況在現實之中或許依舊沒有得到徹底的解決。
二、對男性的反抗
影片的前半段圍繞著銅匠假扮老師騙過特派員一事平穩地展開,出人意料的是特派員此行的目的實際上是為美國慈善家羅斯先生考察農村基層教育家的資質,除了“呂得水”老師的檔案清清白白,剩下四位老師都有過“污點”。因此真正為鄉村教育做出貢獻的人一無所得,虛構的“呂得水”老師卻成了不折不扣的教育家,其中的諷刺一針見血。兩個月后,這件事情已經塵埃落定,鐵男為學校小操場裝飾了許多燈泡,通上電之后操場變得浪漫又夢幻,一曼和校長、鐵男和孫佳分別跳起了舞,這個令人印象深刻的場景十分動人。可是實際上這一幕卻成為影片中最后的柔情,歌聲與舞蹈過后,真正的鬧劇與悲劇開始上演了。
首先是裴魁山態度的轉變,因為得不到一曼而生出的怨氣和對金錢的向往,他已經沒了當初暢談理想的姿態,無法再和其他三個人共同為教育事業而奉獻自我,他的自私自利充分體現在對一曼和金錢的占有欲上,一曼對他的拒絕與反抗讓他徹底轉向了庸俗與市儈。對于一曼來說,自由才是真正的向往,而裴魁山卻想和她結婚,這對一曼來說是不可能的。裴魁山認為一曼不是放蕩,而是太單純了,他強行用一種可以被自己接受的邏輯去解釋一曼的行為,卻被一曼直接否定,她直言不諱地說道:“我就是放蕩,我喜歡,我高興,我愿意這樣。”歸根結底,裴魁山還是不懂一曼,他試圖用自己的方式去理解,卻無法掙脫固有觀念的束縛,他愿意相信所謂的“放蕩”不過是一曼用來保護自己的一種假象,一定還有更真實的自我隱藏在她的意識之中,這種“真實”更加符合裴魁山腦海中的理想女性形象。從一曼的角度來看事情則完全不同,她根本不認同自己的“隨便”會傷害到自己,她拼盡全力為自己尋找一種自在的生活,一旦和裴魁山結婚就意味著再次失去這種自由,因此她的拒絕不僅意味著對婚姻的抗拒,也是對男權及其背后的一整套社會觀念的反抗。
其次是銅匠的轉變,他原本是個木訥老實的手藝人,受到了一曼的性啟蒙之后他的情感與欲望都被開啟了,或許他認為在一曼這里他才獲得了真正的愛情,然而這只是他的一廂情愿,最終無法從一曼那里得到任何反饋。當銅匠聽到一曼說自己在她眼里就是個“牲口”之后,他認為自己完全是受到了欺騙,因此要對她進行報復,趁著特派員和羅斯先生到訪的機會,借用“呂得水”老師的身份對一曼進行要挾。原本善良木訥的銅匠為了扮演“呂得水”老師而受到學校里幾位老師的臨時教育,可實際上他們教育他的目的是為了利用他,這與教育的初衷背道而馳。錯誤的教育目的盡管讓銅匠有了讀書識字的機會,卻也將他人性中惡的一面激發了出來,徒有知識的銅匠只會錯誤地利用它們來達成自己的目的,從前被人欺負和利用的他這次也要抓住機會來進行報復。銅匠不僅借機讓眾人打她罵她,還要求把她的頭發剪掉。從此,張一曼精神失常,在影片結尾處開槍自殺。可以說,她對男性的反抗徹底失敗了,無論是從靈魂還是肉體層面看皆是如此。
一曼的放蕩只是一種表象,她對美好而真摯的愛情充滿了向往,但現實生活中并沒有出現值得她愛的男人:裴魁山自私自利趨炎附勢,屢屢在關鍵時刻“掉鏈子”;銅匠也是個欺軟怕硬、毫無擔當的人。實際上不僅是他們兩個,影片中其他男性角色也是如此:從前脾氣火暴的周鐵男在武器面前放下了一切尊嚴,連一曼要被強奸的時候都不敢站出來;校長的委曲求全看似出于無奈,實際上也不斷讓出底線,為達目的一再退縮;特派員利欲熏心,憑借權力為自己斂財。一曼在這樣的現實中根本得不到自己想要的愛情,但她對男性的拒絕與反抗也遭到了徹底的失敗,她承載著作為一個女性的悲劇命運。
三、女性的不同命運
一曼的悲劇結局令人感到唏噓不已,即便身處窮鄉僻壤,她也無法逃過世俗價值觀念的束縛,更敵不過權力和利益下的人心所向。最后一曼瘋了,但她卻是唯一一個還保有自我的人,其他人都在權力、金錢或暴力的裹挾之下妥協了,放棄了自己原來堅持的東西,難道相比之下他們可以算清醒的人嗎?影片的悲劇性在于底線的喪失,正如影片的兩位編劇周申、劉露所言,《驢得水》真正要談論的是底線喪失的后果,它刺痛的不僅是人們的歷史記憶,更是對現實的尖銳影射。
除了一曼,影片中還出現了兩位女性人物,分別是銅匠的妻子和校長女兒孫佳。銅匠的妻子被刻畫成了野蠻彪悍的形象,對丈夫的態度十分兇狠,儼然一個母夜叉。這一人物形象顯然是為了表達效果而進行了夸張表現,但她已經代表了當時的一類女性,其野蠻兇狠來自于教育的缺乏,唯一的本領或許就是對丈夫的管教。這種畸形的婚姻關系是不堪忍受的,銅匠早就受夠了她,一旦得到機會便拼命想要逃離,而妻子除了暴力地將丈夫帶回自己身邊就別無他法了。在影片的末尾,銅匠妻子怒闖婚禮現場,要把銅匠帶回家,即便她最終成功了,或許也只是繼續延續此前的畸形關系罷了。
校長的女兒孫佳是影片中唯一堅守底線的人,在她心中,對就是對,錯就是錯,她從一開始就不贊成用驢來假裝人騙空餉,因此她也認為最后造成的所有后果都應該由撒謊的人來承擔。她的所作所為在成年人眼里常常會顯得幼稚,比如在驢棚失火之后她不顧一切地用打來的水救火,但其他人都知道火已經無法撲滅,索性留著水喝。后來鐵男來求孫佳假扮銅匠的未婚妻,被她堅決拒絕,鐵男已經在槍口下意識到自己的強硬毫無用處,便完全妥協了,而孫佳則不愿如此,她的解決辦法是寫揭發信,通過教育部訴愿委員會來解決問題。孫佳依舊相信制度可以解決問題,她尚未意識到體制本身的腐朽,鐵男則指出這個方法未必會讓特派員受到處罰,但學校和老師一定會跟著遭殃。孫佳只相信做錯事就應該承擔后果,但她或許不知道,真正做錯事的未必會承擔后果,承擔后果的人也許是無辜的。孫佳最終無力改變現實,她臨走前依舊在對父親表達自己的困惑:“過去的如果就這么過去了,以后只會越來越糟。”不是這樣嗎?她有機會離開鄉村,這對于她個人而言是改變命運的轉折點,對于現實而言是否也是如此?那些被人們無視的過去埋下了深深的隱患,又如何帶來一個更好的未來呢?
一曼、銅匠妻子和孫佳代表了那個時代女性可能擁有的幾種命運,一曼追求身體權力和個人自由,不為社會所容,女性主體得不到伸展的空間,被男性權威完全摧毀。銅匠妻子依靠暴力維持婚姻,在傳統鄉村環境下野蠻生長,最終恐怕無力將銅匠留在自己的身邊。孫佳是唯一的希望,影片結尾顯示她去了延安,但她又會擁有怎樣的命運呢?她會成為革命者嗎?這一切留待觀眾想象,影片的意圖并不在于展望一個美好的未來,因為我們尚且不能面對過去的創傷,許多悲劇被遺忘在歷史的塵埃之中,除非我們真的有勇氣去面對這一切,否則永遠談不上真正的希望與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