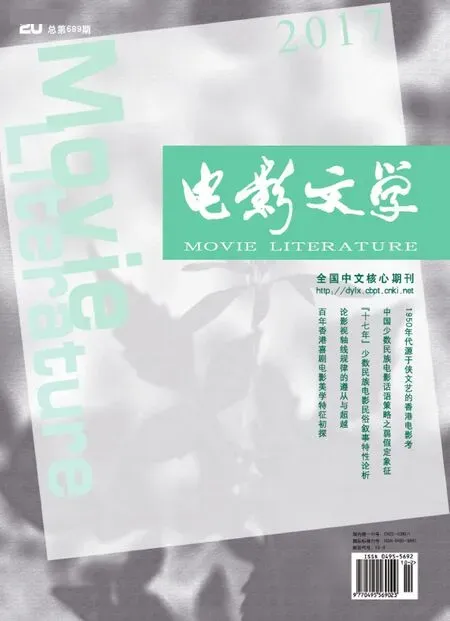《真愛》對《凝望上帝》的呼應與超越
趙東旭
(吉林化工學院,吉林 吉林 132022)
一、引 言
電影《真愛》和《凝望上帝》分別改編自美國黑人女性作家托妮·莫里森和佐拉·尼爾·赫斯頓的兩部同名小說,分別拍攝于1998年和2005年。《真愛》以廢奴運動期間為故事背景,上演了一場慘絕人寰的黑人母親的殺嬰事件;影片《凝望上帝》同樣是以黑人女性為主人公,通過描寫珍妮對平等愛情的追尋展現黑人婦女爭取平等自由的主題。兩部影片遙相呼應,運用不同的創作手法和拍攝手段歷時性地展現黑人女性以及黑人群體的生存狀態、心理特征和集體夙愿。
二、《真愛》與《凝望上帝》的一脈相承
電影《真愛》和《凝望上帝》均闡釋了女性主體建構、黑人民俗文化和黑人群體力量等主題元素,不難看出莫里森繼承并沿襲了赫斯頓的創作風格與主題,她們在創作中的繼承和發揚為更多的黑人女性作家創作建立了經典范式和寫作傳統。
(一)女性主體意識的建構
女性主體意識是指女性作為主體在客觀世界中的地位、作用和價值的自覺意識。[1]它是激發婦女追求獨立、自主,發揮主動性、創造性的內在動機。[2]這兩部影片共同圍繞一個重要的主題,那就是女性主體意識的建構。《真愛》中塞絲為獲取身份自由的出逃與《凝望上帝》中珍妮為爭取愛情的出逃,異曲同工地展現了黑人女性主體意識的覺醒,她們義無反顧地為實現獨立、平等的理想付諸行動,用她們的智慧勇敢地向壓抑她們的蓄奴制度和種族歧視反抗。
在電影《真愛》中,塞絲原本是美國南方畜牧業奴隸主加納先生的一名奴隸,當時奴隸制還沒有被廢除,塞絲沒有人身自由和人格尊嚴。一次,塞絲因留給孩子的奶水被奴隸主擅用稍顯不滿,便遭到主人的毒打,形成了她后背上的“苦櫻桃樹”,這非人般的待遇讓塞絲再也無法忍受白人的欺凌和虐待,毅然決然地帶著三個孩子冒死出逃。塞絲出逃的情節正是她萌生女性主體意識的印證,塞絲為擺脫白人的壓迫、束縛,追求自由、獨立出逃是黑人女性對蓄奴制強有力的反抗和抨擊。
珍妮在電影《凝望上帝》中經歷了三次婚姻,在屢次的婚姻變故中珍妮逐漸形成了女性主體意識,實現了對平等婚姻的追求。影片中有兩段珍妮掙脫傳統婚姻束縛而出逃的情節,這正是珍妮成長、蛻變成為獨立女性的必經之路。
(二)黑人音樂與記憶
赫斯頓和莫里森不僅是著名的美國黑人女性作家,同時對黑人傳統文化也頗有研究。赫斯頓做了大量的黑人民俗、民謠、故事的搜集,是杰出的民俗學家,莫里森被譽為“黑人民間文化的繼承者”。因而在她們的作品當中隨處可見黑人民俗文化的元素,影片《真愛》和《凝望上帝》中也多次出現黑人音樂,渲染了影片的深刻主題。
影片《真愛》中有一段情節:一名少女來到塞絲家中,頸上有一條長長的疤痕,年齡與塞絲殺害的女兒相當,而且有著一樣的名字“寵兒”,更讓塞絲確定這個女孩就是她死去的女兒,寵兒隨口哼唱的歌曲正是當年她唱給女兒的搖籃曲。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黑人沒有話語權,她們往往用音樂、吟唱的方式表達對生活的感受、對親人的情感。寵兒哼唱的這段搖籃曲勾起了塞絲對往事的回記,它包含對塞絲個人經歷的記憶與整個族人屈辱歷史的記憶。黑人音樂是黑人文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有緩解族人壓力、傳承傳統文化、洗禮凈化心靈的重要作用。影片中,塞絲的婆婆貝比,作為社區族人的精神領袖,向族人宣揚黑人傳統,她將族人聚集在一起,組織黑人共同歌唱、舞蹈,肯定黑人的社會價值,傳播黑人傳統文化,從而讓非洲傳統文化移植到美國,成為他們生存的精神動力。
電影《凝望上帝》中,也多次融入黑人音樂,有力地增強了作品的表現張力。其中,珍妮與甜心離開伊頓威爾鎮,來到大沼澤地生活的片段里,來自各個地區的族人們在一起載歌載舞,他們自由地彈奏、歌唱黑人的傳統音樂,似乎一時間穿越到了遙遠的非洲,尋找到了他們的生命之根。在這一情節中,音樂有著多重作用,首先它緩解了人們白天辛勤勞作的疲憊身體;其次,它象征著族人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最后,它是黑人群體對黑人文化的認同與宣揚。黑人音樂是黑人民族文化傳承的載體,它以輕松舒緩的形式將文化傳統與記憶代代相傳。
三、《真愛》對《凝望上帝》的超越
《真愛》與《凝望上帝》有著諸多的相通之處,它們譜寫共同的主題,傳承黑人傳統文化,重審黑人女性地位。然而,兩部影片仍存在許多迥異之處,體現了莫里森對赫斯頓的超越。
《凝望上帝》圍繞珍妮的三次婚姻展開,主要展現黑人女性獲得婚姻自由、男女平等的主題。而《真愛》情節復雜,主題多元化。依照塞絲逃離擺脫奴隸主的情節為主線,它的主題可定位為反對蓄奴制度;根據寵兒的消失、出現、再消失的故事,可以把母愛定為作品的主題;而根據塞絲個人的經歷亦可以將該作品的主題視為女性成長。《真愛》中的多重敘事手段將該影片的多元主題立體地呈現給觀眾,多方位地將黑人女性在蓄奴制時代的經歷展現出來。此外,該影片源自一段真實的黑人女性殺嬰事件,比起赫斯頓將故事背景設置在虛構的黑人小鎮伊頓威爾更具可信性、現實性。
在創作手法上,《真愛》更是超越了傳統的敘事手法,采用多人敘事、意識流、內心獨白等多種后現代主義創作元素,將故事深度模式削平,打破能指與所指之間的依存關系,運用魔幻現實主義手法創造出“寵兒”形象,它既非人,又非鬼;既是塞絲的女兒,又是塞絲的母親;既是母親的受害者,又是蓄奴制的受害者。而寵兒智力異常、語無倫次更使得意識流手法運用得十分靈活,她可以講述白人從非洲大量運輸黑人的罪惡歷史,也可以隨時流露對母愛的深切渴望,通過意識不清的寵兒的意識流描寫,作者最大限度地展現了黑人女性對平等生活的向往,揭示了蓄奴制下的種種罪行。莫里森超越了前人,通過采用后現代主義的多種手法將多維度、多主題的影視佳作呈現給觀眾。
四、結 語
赫斯頓被譽為黑人女性文學之母,為后世作家創立了經典的寫作框架和敘事策略,其代表作《凝望上帝》首次將黑人女性作為故事主人公,為黑人女性作品開了先河。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莫里森繼承并發揚了赫斯頓的創作風格,突破了歷史局限性,大膽運用后現代主義創作手法,在作品《真愛》中宣揚民主精神,并直面揭露了蓄奴制的罪行。赫斯頓與莫里森通過作品共同塑造積極的黑人女性形象,宣揚黑人傳統文化及價值觀,對少數族裔女性主體意識的建構、黑人傳統價值觀的重塑起到了積極的推進作用,同時,二者跨時代的繼承與發揚為美國黑人女性文學創作構建了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