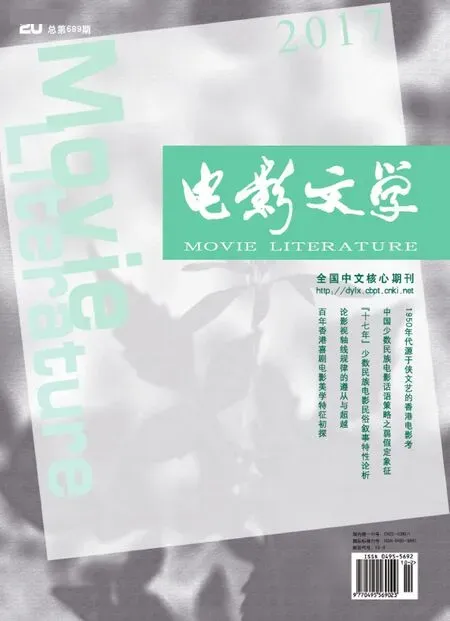淺析《地下》的政治隱喻
盛 珊
(長江大學工程技術學院,湖北 荊州 434020)
庫斯圖里卡是一個極具個人風格的導演,他的影片不僅與好萊塢的敘事風格迥異,也與歐洲藝術片在冷靜、克制中呈現哲學思考的傾向有所不同,而是擅長在荒誕、夸張與超現實的表達之中彰顯狂歡化敘事的魅力。但這種狂歡并沒有流于膚淺和無意義,而是在更深層次上飽含尖銳的現實政治隱喻。《地下》是庫斯圖里卡從美國回到貝爾格萊德之后的首部作品,或許是在異域的生活經歷激發了導演對于故鄉歷史的關注,影片極具諷刺性和感染力,在恣意的表達之中暗含對歷史的深刻反思。盡管現如今這個國度已經從地圖上消失,但觀眾依舊可以借助影像的力量體會那份苦難與悲痛。《地下》常被視作庫斯圖里卡的巔峰之作,這部影片雖因其政治傾向受到了很多批評與質疑,但依舊獲得了1995年的金棕櫚大獎,這或許能夠證明真正的藝術作品既有對現實的關懷,又能夠超越現實與政治的糾葛,憑借其藝術層面的純熟表達而彰顯價值。
一、對歷史的解構與重述
《地下》是一部史詩電影,影片基于南斯拉夫五十余年的近代歷史展開。充滿動亂與紛爭的南歐巴爾干半島從20世紀以來就未曾獲得過長久的安寧,南斯拉夫更是處于風暴的中心,不僅兩次世界大戰都被卷入,此后的內戰和鐵托的獨裁統治也為更深刻復雜的危機爆發埋下了伏筆。20世紀80年代鐵托逝世之后民族與種族沖突爆發,將南斯拉夫最終引向了分崩離析。庫斯圖里卡不僅親身經歷了鐵托統治時期,也品嘗過戰爭之殤。在90年代波黑戰爭中他的家人受到了戰火的紛擾,他的父親因薩拉熱窩的房子被摧毀而死于心臟病,家人也不得不開始避難,祖國的動蕩帶給他獨特的生命體驗,令他不斷對國家與政治的命題展開深入思考。對祖國的愛與對祖國前景的擔憂作為兩股矛盾的力量交織在一起,構成了庫斯圖里卡影片中的核心意涵。
《地下》的開端對應的歷史是1941年南斯拉夫被德國法西斯占領的時期,但影片從一開始就展現了對歷史的嘲諷與解構。在這里,影片的主人公馬高為慶祝黑仔加入共產黨而與之共同喝酒、騎馬,并請來了樂隊跟在馬車后面演奏,這種激情與狂歡完全掩蓋了戰爭的殘酷、革命的嚴肅。戰爭的影響是突如其來的,影片中的動物園是十分有象征意味的場所,它代表了人類對獸性的規訓,但炮火的轟炸卻釋放了一切被壓抑的不安力量,暗指戰爭本身就是對人類理性王國的摧毀,由此失序與混亂成為影片的主基調,原本殘酷的戰爭場面卻因為穿插著黑仔釋放性欲的情節和伊萬保護動物園黑猩猩宋妮的場景而令人感到荒誕不經。因此,影片從一開始對戰爭的書寫就是反向的,戰爭所帶來的苦難和恐怖被生命欲望和日常情境所代替,促使黑仔拿起槍奔赴戰場的原因或許不是他口中的家國情懷,而是炮火影響了吃飯所帶來的憤怒感。
不僅是戰爭,《地下》同時解構了革命歷史敘事的正義性,而是用情欲來支撐革命的動力。黑仔不顧即將生產的妻子而愛上了年輕美麗的娜塔莉,試圖從納粹軍官手中奪走她,卻被德軍抓獲。而馬高則不顧危險混入敵營解救了黑仔,在德國納粹的強力搜捕之下,馬高不得不帶著眾人躲入地窖之中,從此開始了“地下”生活,馬高也成了地下眾人和地面的唯一聯系。黑仔的妻子不幸難產而死,留下了兒子祖凡,至于娜塔莉則在馬高的甜言蜜語之下投入了他的懷抱。無論是“地下”這一空間場景還是“娜塔莉”這一人物設置都具有高度的象征性,它們是對歷史的模仿,也是對歷史的嘲諷。首先,“地下”是庇護民眾躲避納粹追擊的場所,它代表了革命力量在戰火紛飛的年代所賦予民眾的保護與希望;其次,“地下”具有封閉性和欺騙性,它營造了一個相對穩定的空間,卻也很容易成為被操控的對象,地下世界的人們一直被戰爭與仇恨所左右而高揚革命斗志,這種封閉性所帶來的盲目令人感到可笑又可憐。另外,娜塔莉被黑仔從納粹軍官那里搶來之后,又被馬高所勾引,她是一個愛慕虛榮而軟弱的女人,但她恰恰也是斗爭的核心原因,娜塔莉所象征的情欲力量甚至超越了革命的光輝而成為將個人卷入大歷史的關鍵所在。
影片將荒誕推向極致之處體現在馬高對眾人的欺騙上,四年之后侵略者已被趕走,南斯拉夫在鐵托的領導下建立了新的共和國,馬高和娜塔莉成了居功至偉的人物被群眾所擁戴。令人震驚的是馬高卻依舊維系著“地下”的運轉,讓人們相信戰爭還在持續,并讓他們不斷制造革命所需要的武器,殊不知這些武器被運到地上之后被馬高轉賣而大獲私利。《地下》對馬高這樣虛偽的政客的批判可謂入木三分,實際上庫斯圖里卡再次借助對歷史的改寫與扭曲完成了對歷史的審視與批判。戰爭的確是一個調動民眾情緒的絕佳契機,“地下”的組織滿足了戰時的需要,然而當戰爭結束之后,“地下”卻依舊能夠假以革命之名繼續存在,其悖謬之處就在于原本民眾所支持的力量反過來成為操控他們自由的力量。從劇情層面來講這自然可以被視為一個男人對他朋友、家人和戰友的欺騙,但觀眾無法不去聯想國家的權力機器對于民眾的愚弄。至此,《地下》用頗為戲劇化的方式講述了南斯拉夫的戰爭與政治,表面上的荒誕與內在的諷刺性構筑了十足的戲劇張力,帶有很深的歷史反思意識。在喧囂與狂歡的背后是無盡的孤獨與悲傷,《地下》那喜劇的外表與悲劇的內核不僅是笑中含淚的控訴,更是歷史反思意識的深刻呈現。
二、荒誕現實中的悲劇政治
盡管《地下》試圖講述歷史,但并沒有用理性的方式進行重新建構,而是用荒誕的方式來隱曲地展現政治意圖。馬高為了讓地下的人們相信戰爭依舊存在可謂煞費苦心,當黑仔想要回到地面投入革命的時候馬高卻告訴他是鐵托要求他暫時不要行動,并期望他能在戰爭的最后時刻發揮關鍵作用。馬高為黑仔帶來一塊懷表,說是鐵托同志送給他的禮物。手握懷表的黑仔仿佛立刻就感受到了領袖的光輝,開始唱起一首贊頌鐵托同志的歌。聲音傳到地上,地上的人聽到歌聲全都不自覺地開始跟著一起唱。地上地下的合唱可以看作是一種政治的隱喻,對領袖的偶像式崇拜消除了地上地下的區隔,所有人在精神上都處于“地下”的狀態,正如馬高對于地下世界的窺視與控制一樣,政治領袖用意識形態操控自己的人民,或許正如馬高所言:“我們每個人都在撒謊。”
如果將馬高看作地下的領袖,那么正是這個領袖營造了假象來維持地下的運轉,觀眾可以相當明確地看到這種操縱是如何進行的,實際上這與一個社會的建立、存續十分相似。但地上世界的構建過程在影片中的呈現則更為隱微,在地上,一部有關馬高和娜塔莉的影片正在拍攝之中,影片的目的自然是為了追述革命史并達到宣傳目的,但實際上與其說是追述,不如說是想象。因為無論是事件還是人物都極度失真,由此形成了夸張的喜劇效果。然而,庫斯圖里卡在設計這樣的情節之時顯然有更深的用意,他的電影本身也是對歷史和政治的再度呈現,不可避免地融入了導演的主觀判斷與藝術加工,影像至多只是一個維度,其目的是激發思考,而絕非試圖陳述事實。《地下》的確是對南斯拉夫歷史的呈現,但庫斯圖里卡不希望自己關于國家民族的思考被強行施加給觀眾,因此他在自己的電影中又講了一個拍電影的故事,這不僅是嘲諷與戲謔,更是清醒與反思。真實的歷史,《地下》呈現的歷史和作為《地下》情節的一部分被拍攝的電影之間形成了三重遞進的關系,重復著“歷史”與“被講述的歷史”之間的距離。如果現實是荒謬的,那么任何非黑即白、具有明確意圖和邏輯線索的歷史講述就都是失真的,庫斯圖里卡的電影用狂歡化的敘事來表達那個瘋狂的年代,亦是對掩蓋歷史與政治的復雜性和矛盾性的拒絕。
正是因為狂歡本身承載了許多深刻的歷史表達與政治反思,造成了狂歡內部的不穩定,在極端的情緒主宰之下隱藏著重重的危機。在《地下》中,婚禮場景是狂歡的代表,電影中一共有兩場婚禮,第一場是黑仔和娜塔莉的婚禮,第二場是黑仔的兒子約凡的婚禮,庫斯圖里卡的婚禮場景是喧囂與瘋狂的,無盡的酒、鮮花、音樂與舞蹈將人拋擲在情緒的海洋之中,但是第一次婚禮上納粹趕到逮捕了黑仔,第二次婚禮上黑猩猩宋妮進入坦克炸開了地下室并毀掉了馬高精心維護的世界。狂歡中隱藏的危機是推動敘事進行下去的關鍵力量,導演用這個簡單的對應關系完成了對現實政治的影射,無論是戰爭狀態還是集權之下的社會都被非理性的情緒所左右,支撐人們行動的力量往往十分簡單,因此它既是穩定的又是容易被摧毀的。從某種程度上說,人們的盲目與非理性正是政治家所需要的情緒與態度,但沒有任何一種控制是密不透風的墻,總會有某種力量沖破密不透風的“地下”。
三、理想的表達:一種烏托邦的可能
馬高對于“地下”的控制已經達到了極致,甚至連時間都被他左右了。事實上,人們已經在地下呆了20年,但是他派人定期調整時間,讓人們以為只過了15年。另外,馬高用攝像頭窺探地下的人們也仿若極權社會中的監視體系,令人感到不寒而栗。地下的人們生活在謊言之中而不自知,但他們的信念起碼是堅定的。而處于馬高身邊的娜塔莉則沒有這么幸運了,雖然她知道真相,卻不能透露半點,還要配合馬高演戲。實際上,娜塔莉作為女性的一個代表,從始至終都是被壓抑的個體,無論是納粹軍官、黑仔還是馬高都將她視作欲望的客體,沒有人問過她的想法。長期處于壓抑之中的娜塔莉是極度痛苦的,在第二次婚禮上她瘋狂地舞蹈并不是為了表達喜悅,而是希望借此來釋放壓抑,她想要把真相告訴黑仔卻被馬高的愛所束縛。最終,毀壞地下的力量來自于黑猩猩宋妮,進入坦克的宋妮用一個炮彈炸開了地下室。庫斯圖里卡用黑猩猩來象征被遺忘的人性,全部的謊言終于在意外之中被揭示。
地下世界被終結之后,幾個人物的命運有了完全不同的走向,馬高沉浸在革命的激情當中,到了地面上之后把電影的場景當成了真實的戰爭場景而展開殺戮,為了革命而瘋狂行進,可是第二天早上他卻因忙著射擊飛機而把不會游泳的兒子獨自留在水中導致他溺水身亡。伊萬為追趕宋妮陰差陽錯輾轉到了西德,娜塔莉與馬高則炸掉了整個地下室之后帶著錢跑了。長期的謊言與壓抑被瞬間釋放,每個個體都為此承擔了難言的后果,人們難以再用正常的眼光審視世界。
20年后,伊萬得知自己的哥哥騙了自己,他想沿著地下隧道回南斯拉夫,卻被告知已經沒有南斯拉夫了,等到他踏上故土之時,這片土地上依舊是不間斷的炮火聲,黑仔成了戰爭領袖,卻是以不再存在的法西斯為目標。馬高依舊在倒賣軍火,被伊萬怒而打死,之后自己上吊死去,娜塔莉死于射擊中,而馬高恍若聽到了水井中兒子的呼喚而跳入其中。真實的世界到這里已經全部終結,死亡的悲劇命運沒有放過任何一個人,但是庫斯圖里卡用一種超現實的手法描述了另一個死后的世界,所有人都在水中復活了,不計前嫌,并游上了岸開始了載歌載舞的幸福生活,他們腳下的土地逐漸分離成了一個小島漂向了水中。顯然,這個在歌舞聲中遠去的小島是個只有歡樂沒有痛苦的理想世界化身,是不會在現實中存在的烏托邦。庫斯圖里卡將全部的美好想象賦予這個烏托邦世界,或許這個小島所承載的即為理想政治的化身,盡管現實充滿戰爭、苦難與欺騙,但永遠有一個美好的世界停駐在人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