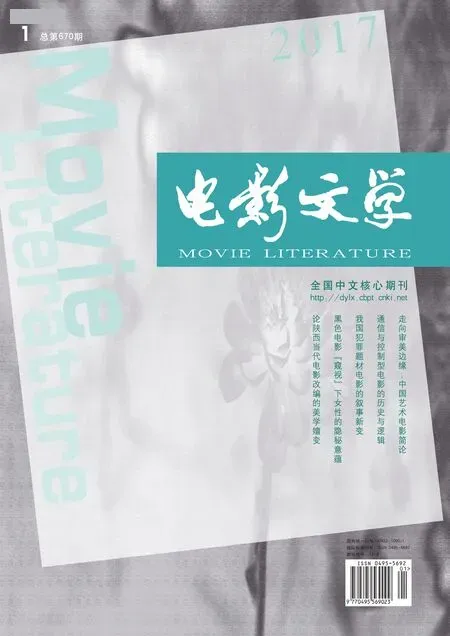二次元文化與中國電影審美的“呆毛性”對話
紀曉楠
(中國傳媒大學藝術研究院,北京 100024)
起源于日本動漫,原意為二維的、平面的藝術表述形式,后專指由漫畫、手游和動畫文化構筑起來的,有別于現實三維生活的虛擬世界——“二次元”,正以飛快的速度實現著從外來向本土、從亞文化向主流文化的發展與轉變。如果說每一套文化體系都會于潛移默化間形成自己獨特的語言系統,以此和其他文化現象進行對話,那么它亦不例外。以“呆毛”為例,原指一縷或多縷直立于頭頂的頭發,但在二次元語境下搖身一變成了充滿能量的代名詞,形態各異,會隨主人的心情變化而變化,如翹起或萎靡。二次元獨特用語的廣泛傳播為大眾文化增添了看似成熟的新鮮血液,那是一種引領年輕人的審美觀念,亦是一類具有“呆毛”特色的審美機制。雖然二次元文化如今已附著于成型的文化產業之上,成為新興的、充滿能量的商業模式,但其未來發展和與傳統電影藝術的融合對話仍處于易變狀態,故筆者引用“呆毛”之意稱其為“呆毛性”對話形態。基于以上態勢的表述與延伸,我們首先對二次元文化于國產電影產業中的優勢與新變進行一番審視與梳理。
一、呆毛翹起:縮小審美裂縫+增強角色價值
語言文本和視聽語言的“虛擬化革新”表征著“二次元文化”不但悄然進入了大眾生活,也在無形中改變著國產電影的影像風格和審美趨向。如果我們回望 “復調對話”不難發現,巴赫金認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中,主人公具備相對獨立的思維意識和權利,會和作者結成審美同盟,共同作用于觀眾,從而使三者進行無形中的對話溝通,達到穩固審美距離、縮小審美裂縫、增強角色價值的功效。基于以上觀點,筆者認為其同樣適用于二次元文化對中國電影的審美影響,那是由二次元元素改編并搭建起來的,全無地域性限制的奇幻電影,是充滿奇思妙想、另類獨特的奇觀影像,更是一部部瘋狂的、無章節的青春物語,盡管它們不以波折的劇情取勝,但其中的絲絲笑料卻不乏無厘頭的黑幽色彩。
(一)打造草根英雄,重塑崇高情節
從《十萬個冷笑話》中的少年郎、時空雞,到《魁拔》中的六代蠻吉,創作者無不向觀眾刻畫著一個個反哺于民間生活或來自于普通角色的“小人物”,無論怎樣變更,李靖、哪吒、孫悟空和《秦時明月》中的項少羽、荊天明都可以讓我們有據可循、有史可查,雖然他們都早已是在觀眾心中留下深刻印象的著名角色,但二次元的魅力恰恰在于力圖消解這些看似崇高的“英雄”,將角色的點滴與“屌絲文化”緊密結合,用草根打造草根中的草根。此外,在這種以重口味惡搞為主導的“草根動畫”中,草根英雄往往備受關注和追捧,類似宅男拯救世界、腐女重導人生、一只雞可以輕易操控時空輪回等細節屢見不鮮,雖然他們飛揚跋扈或憨傻無聊;他們放任不羈、蔑視規則,但他們單純、單一,不忘初心、永葆夢想。每一幀動畫、情節和人物都在為廣大網友帶來歡聲笑語的同時,大大地增強了每一位“草根英雄”的角色價值,以此縮短觀眾的審美距離,滿足大眾消費的觀影快感。
(二)淡化娛樂至死,惡搞凸顯使命
作者全力降低“狂歡式”娛樂的低俗性,為人物賦予特立獨行的思考、行為與使命,不但以“80后、90后”熟知的動畫形象和諸如“空手接白刃”的無厘頭技能惡搞,且持續激發著大眾對于熟悉角色“陌生化聯想”的新型審美意識。此外,每一位角色皆獨立于作者之外,直接和觀眾進行審美意義上的對話,這種“越界”的溝通讓觀眾成為潛在的使命合伙人,和角色一起完成拯救世界、解救蒼生的光榮任務,從而最大限度上關注到不同受眾需要的審美體驗。縱觀國內已有的二次元影片,無一例外地對經典人物、經典歷史、經典場景都做出了惡搞式的流變,但似乎每一步走得又并不出格,反而可以讓觀眾從中體會到對于責任、感恩、正義和夢想的認知。面對當今這么一群二次元文化語境下的動畫角色,他們身體的“狂歡”行為足可以給予現實中的我們短暫的精神慰藉,以求尋找到個體之上的普世價值。但世界萬物的運行皆靠“度”的把握,二次元影片在利用這一惡搞特性使“呆毛”高揚的同時,也暴露了它不容忽視的不足。以《十萬個冷笑話》為例,影片在對經典形象進行戲謔性再造的同時,反叛與調侃無不透露于敘事文本中,正和今天青年一代的懷舊情結互相契合,在無形中凸顯出媒體整合時代下大眾審美偏好的解構與顛覆。
(三)打破銀幕空間,引領主觀文化
1994年,鄭淵潔的《魔方大廈》被制作成10集電視動畫片于全國范圍內播出。縱觀全片,其中同樣具備二次元相關元素:假想出來的二維平面和充滿怪誕的虛擬空間,一些驚悚和懸疑的細節也都透露著對于時空重構的味道,但這畢竟是20年前的作品,繪圖、制作和人物行為都無法與當今的二次元動漫相比。2011年《魁拔》凈收入2510萬元;2014年投資1000萬元的《十萬個冷笑話》火速將1.2億票房收入囊中;2015年《大圣歸來》更是打破國產動漫票房紀錄,直達9.56億之巔峰。諸如此類的國產動畫在二次元文化的沖擊融合下順勢而上,以精品生產模式大踏步進入到國內外觀眾的視野,加之“互聯網+”思維與相關產業規定的扶持,中國本土動漫電影更是以二次元元素為視覺承載,引領著包括語言(《請叫我女王大人》)、服飾(Cosplay)、飲食(美食+)、生活(吐槽能量)等在內的多方面文化的潮流與風尚。此外,二次元的波及范圍不僅局限于電影審美的感官之上,還直接以多種傳播和呈現形式愈加被大眾所接受,如“彈幕”的流行。這是一個“吐槽”占據絕對主力,且潛力巨大的互文性系統,網絡為電影的觀看提供了便捷,而彈幕也為大眾基于這部影片的交流提供了群體性發泄的新渠道。在二次元文化的引領下,新興彈幕革新了影視傳播模式,改變了傳播關系,同時也對視頻文本本身進行二度加工,由此帶給觀眾全新的觀影體驗和互動快感。①
二、呆毛萎靡:過分商業消費+瓦解人物原型
與傳統影視相比,二次元文化給觀眾帶來的全新對話方式筆者稱其為“翹起的呆毛”,只因它與國產影視動漫的有機融合,且勢頭正旺、斗志昂揚。2014年與二次元相關的動漫、游戲和影音項目的融資規模高達1.73億元,2015年已然翻倍,僅騰訊投入的動畫基金和漫畫基金就分別高達6000萬和3000萬,市場制作空間與需求量甚是驚人。雖然二次元動漫與影視產業于近幾年間成為中國國產影音行業的重要支柱之一,但在此現象熾熱化上升的同時我們不禁放慢腳步,深度發掘二次元文化對電影審美產生的弊病與威脅。上文提到“呆毛”的存在與主體的心境、狀態有關,時而高揚或萎靡,那么筆者在討論二次元文化為國產電影帶來的創新性與互動性后更應有效地對其品質與水準進行檢索,防微杜漸,以避免二次元文化泡沫的急劇增長、爆破。
(一)消解人物原型,破壞創作生態
二次元影視可以在有限時間內匯集諸多80后、90后熟知的動畫角色,白雪公主、吮指雞、匹諾曹、葫蘆娃、牛魔王、哪吒父子、孫悟空、項羽、劉邦甚至牛頓等皆在旗下,這些人物一方面保持著本身的特性,一方面又被賦予了嶄新的歷史、技能和關聯。②雖然如此,但也產生了新的“認同”問題,哪吒被配上了滿身肌肉;葫蘆娃與蛇妖結婚生子;不同童話中的白雪公主和匹諾曹產生戀情。這些形象在對原型進行顛覆,滿足新一代觀影人群審美感受的同時,也在無形中喪失了熱衷動畫本體的80、90代群。以“十冷”電影版為例的二次元“雜糅潮流”和“快餐文化”追求個性、標新立異固然沒錯,但諸如此類的“成人動畫”在互聯網資本浪潮中會逐漸丟失國產動漫的人物原創性,愈加規訓于對已有動畫元素的一味拼湊,無法推陳出新,最終導致呆毛的日漸萎靡,長此以往必給中國動漫產業和相關影視文化帶來重創性生態危機。《十萬個冷笑話》制片人不董在接受采訪時談道:“漫畫領域最難做的正是創作生態環節。起初畫得好的作者我們會支持,現在一般的作者也會享有很多的激勵措施,但效果離期望值還差得很遠,因為還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幾種或者更多成功模式,寒舞相當于一個先驅者,他成功了,便會提供更具參考價值的發展模式,生態環境還需相當長的時間去建立。”
(二)二次元元素威脅觀眾審美
諸如“彈幕”等新興對話形式的出現增強了觀眾的交流與互動,但其隱患也是顯而易見的。由于缺乏正確的指引與規范,無法由監管部門統一其字號、顏色或字體,因此“彈幕”效果嚴重占據了銀幕的可視范圍,分散了觀眾的視覺焦點,破壞了影片的敘事節奏和畫面完整性,從而消解了影片對于大眾的審美效果和美學價值。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影視傳播研究中心主任尹鴻教授認為:“事實上,大部分影視作品都需要觀眾用萬分深入的態度進行觀賞,忘掉自我的存在,全身心地融入其中,這才是電影的魅力所在,也是藝術觀賞的必要規律。”③此外,先被發布的彈幕對其后觀看影片的觀眾起到了群體性的消極傳播效用,使觀眾在不自覺間被已有的評論和情緒所牽引,從而形成嚴重的心理依賴,喪失自己對于影片細節獨立思考的能力,實質上威脅到了大眾對于影視藝術的自主鑒賞和審美水平。因此,這種“彈幕對話”的出現會勾起觀眾的獵奇心理,但長此以往必將導致呆毛不再高昂,反而萎靡不振。
(三)商業資本動搖藝術地位
從《尸兄》到網絡大電影上映,從《十萬個冷笑話》到兩站創立收購,再從《大圣歸來》到巨額投入并攏,二次元在極快的時間內完成了廣泛娛樂化的產業整合,所有年輕化、忠誠度高的“宅男”“腐女”也在巨大的商業資本滲透下形成了標志性的“二次元”文化社區。隨即諸多互聯網巨頭投身于動漫產業,將其視為國民經濟的支柱性增長模塊,由此 “二次元文化”將作為新興經濟增長點不斷迎來廣泛的發展契機。但值得注意的問題也隨之而來,商業洪流是否會如同猛獸般吞噬對于藝術品質和影片質量的探討與把控,甚至有學者提出二次元文化不會與電影產業有機融合,而是使其愈加二次元化,即“消費性”“低俗性”和“碎片性”。我國動漫產業在持續發展中已經形成了自己獨有的價值鏈條,但整體附加值較低,主要表現為題材創意的缺乏、原創角色的陳舊和敘事文本的浮躁。如果不從以上幾個方面提高國產二次元影視的制作水準,即使投入再多的商業資本也是枉然,反而會隨著產業化泡沫的不斷積累最終崩潰,與觀眾、市場脫節,起到揠苗助長的反作用力。此外,媒體融合和資本積累會直接導致國產二次元影視的另一個弊病:跟風嚴重,以此發展下去會逐漸拉低影片創作質量,觀眾的審美水平也隨之停滯,對國產動漫影視的不良影響呼之欲出。
三、呆毛持續:優化產業結構+提高創作水平
二次元影響下的中國影視產業正飛速躋身主流審美市場,然而面對隨之而來的諸多不足,產業人員、相關機構和作為審美主體的觀眾該如何行動,才能將這種新興格局送回正確的發展方向,始終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關于“完善保護政策”“企業自主引資”等建議筆者暫且不提,單就藝術生產的三個環節——作者、作品和觀眾來說,應盡早提升從業者的創新意識,走精英、精品化路線尤為重要。早先中國已經有諸如《魔方大廈》《霹靂貝貝》等充斥著二次元文化的特色動畫、電影,因此要適當控制“拿來主義”,擺脫發達國家動漫產業對本民族的束縛與控制,逐漸積累并發揮多面思維能力,創造屬于我們自己的,帶有強烈民族氣質的符號化角色和中國特色的敘事文本,并通過如今優良的技術水平將其表達出來。但要注意:創新不等于一味地惡搞,而是應于產業化浪潮中找到合理重塑的途徑,以“復調對話”為先導提高角色的自主意識與對話價值,同時在保證審美連貫性和畫面整潔的基礎上增加與觀眾的互動,努力提升產業價值的市場競爭力,縮短審美裂縫。此外,普通觀眾也應盡量以合理的方式參與到中國電影與二次元文化的對話當中,通過保持對“二次元” 的借鑒與學習,為國產電影的優化、再生培養強烈的歸屬與認同。
四、結 語
在二次元界的“幻想世界”中,觀賞者可以與角色進行良好的獨立對話,且利用這種二維對話方式大大縮短審美間隙,由此,它甚至被一些學者定義為以互聯網為依托的虛擬屬性與青春特質共謀的動態世界觀。兩年之內在中國網絡上流行的二次元“萌語”超過63個類別,共計1100個左右,猶如“呆毛黨”的不斷擴大正向當今消費文化證明著二次元的波及之廣、效用之大,筆者借其特性引申為新興文化與當今中國電影的融合態勢并不為過。二次元文化在角色塑造和場景設計上不斷追求試聽上的極致呈現,凸顯奇幻美感,烘托人物價值,使其愈加充滿靈性與生命,雖然夸張、魔幻的世界空間刻意造成了與現實時空相異的審美距離,但若能良性循環、穩健前行,定可在濃郁的聯想與狂歡式的對話中為觀眾奉上特殊的草根美感,令人瘋于此、樂于此、美于此。
注釋:
① 周舟:《傳播學視野下網絡青年亞文化 ——“彈幕文化”解讀》,西南大學,2015年。
② 馬丹:《從〈十萬個冷笑話〉電影版看國產動畫電影內容的創新之處》,《新聞研究》,2015年第2期。
③ 馬凱文:《彈幕:視頻互動的新形式》,南京師范大學,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