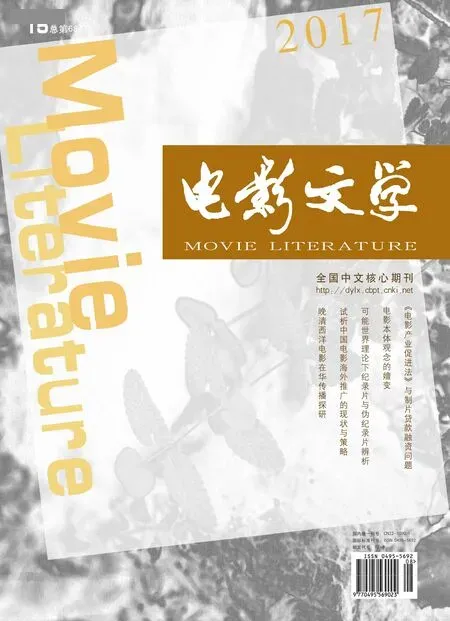中國當代懷舊電影研究
李姍姍
(洛陽師范學院,河南 洛陽 471002)
一、引 言
“結歡隨過隙,懷舊益沾巾。”早在中國封建社會時期,“懷舊”就被視為一種對故鄉、故人、故事的緬懷之情,在詩詞歌賦中常被詠嘆,甚至可以說“懷舊”在中國古典文學發展的各個階段都頻繁出現。雖然“懷舊”之情在中國古已有之,但這個詞語作為正式的用語卻是在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的西方,當時的“懷舊”主要被用在遠行征戰的士兵對家鄉的思念之苦上。在時間車輪不斷轉動的過程中,戰爭的硝煙已經遠去,但“懷舊”一詞卻得以保留并在日常生活當中及文藝創作領域被經常運用。[1]在日常生活中,“懷舊”體現在生活方式、衣著風格、娛樂休閑等諸多方面,如民國風的著裝、80后主題的餐廳等都是當今社會復古風潮中的代表,人們借此表達對故去年代或過往幸福的緬懷。從更深層次的角度來說,“懷舊”代表著一種返璞歸真的渴望,一種喜舊畏新的心境,也代表著對后工業時代快節奏生活、功利化追求的批判。
日常生活中的“懷舊”濫觴不僅為文藝創作中的“懷舊”提供了必要的題材,也使文藝創作中的“懷舊”擁有了更廣闊的市場,滿足了受眾“懷舊”的審美需求。在經歷了“文革”十年的文化浩劫后,中國的知識分子及文藝創作者開啟了“尋根”模式,尋根思想貫穿在文藝創作的各個方面之中,文藝創作者們通過對昔日故鄉的求索、對童年往事的追憶試圖建立起當今與過往的聯系,以修補“文革”十年的文化斷層。“文革”后的十余年間,驟變的不僅是中國文藝,還有整個中國社會。改革開放使中國人民在接納了大洋彼岸的新鮮思想的同時,也承受著社會轉型所帶來的陣痛,這進一步催生了文藝創作領域中的“懷舊”之緒。隨著改革開放進程的不斷推進和全球化發展的不斷蔓延,集合影、音、像為一體的電影成為“懷舊”審美的最便捷途徑,[2]以懷舊文學為基礎蓬勃發展,在中國大地上落地生根、花繁果碩。本文將以闡釋“懷舊”為開端,立足《陽光燦爛的日子》《大紅燈籠高高掛》《孔雀》《紫蝴蝶》等中國當代影壇上的懷舊力作,從“懷舊之源”“懷舊之敘”“懷舊之蘊”三個層面探析中國當代電影中的懷舊情結。
二、中國當代電影懷舊之源
20世紀初,一部名為《定軍山》的影片敲開了中國電影的大門,在隨后很長的一段時間內,流行于中國影壇的影片均以戲曲片為主,其間也有《閻瑞生》等故事性較強的影片。20世紀20年代,中國內地興起了許多小型電影公司,為了迎合大眾的審美口味,這一階段《火燒紅蓮寺》等宗教題材的影片十分多見。30年代以來,中國影壇興起了左翼之風,《狂流》《春蠶》《漁光曲存》等左翼影片成為主宰中國內地影壇的類型化作品,左翼之風在40年代的戰爭時期逐步轉變為抗日影片和解放戰爭題材的影片,這一階段中國電影的發展直接得益于中國共產黨對政治工作的領導,《保衛我們的土地》《松花江上》《木蘭從軍》《一江春水向東流》等帶有紀錄性質的故事片稱霸影壇。在新中國成立后,中國電影獲得了更廣闊的發展空間,《白毛女》《新兒女英雄傳》《鋼鐵戰士》等優秀的影片涌現而出,尤其是在毛澤東同志提出“雙百”文藝和科學發展方針后,中國影壇更是呈現出了快速發展的景象。但受政治運動的影響,這一階段的影片題材的表現方式并不豐富,尤其是在“文革”十年間,中國電影在題材和風格發展方面幾乎停滯。
正如上文所述,“文革”十年后的中國電影融入了“尋根”潮流中,開始呈現出具有特定時代特色的“懷舊”傾向,中國內地的第三代、第四代導演群以“反思”和“傷痕”為關鍵詞創作了許多懷舊電影,如反思中體現批判精神的《牧馬人》《天云山傳奇》;追尋中華文化之根的《紅高粱》《黃土地》等。[3]在以“反思”為主導的懷舊影片之后,中國影壇在20世紀90年代迎來了更為純粹的“懷舊”之風,一些褪去了尖銳的批判而披上朦朧情感的懷舊影片大量涌現,《陽光燦爛的日子》《大紅燈籠高高掛》《我的父親母親》就是其中的優秀之作。在新世紀后,“懷舊”之風雖不再鼎盛,卻依然以傲然獨立的姿態飄蕩在中國影壇之上,《孔雀》《紫蝴蝶》等影片也再次喚起了人們對于過往年代的集體記憶。如果說“反思”與“尋根”是中國當代懷舊電影發展的內部驅動力,那么電影全球化的發展進程就為中國當代懷舊電影的發展提供了外部影響力。正所謂,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在中國電影進軍國際影壇之初,中國導演便敏銳地發覺,想要在競爭激烈的世界影壇上立足,中國元素是中國影片走出國門、走向世界的“利劍”,而通過“懷舊”實現的獨特文化呈現及樹立的中華民族品格則成為一條很好的發展之路,這也是在商業大片林立的市場化競爭中,懷舊影片在中國當代影壇中不斷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中國當代電影懷舊之敘
在中國當代影壇之上,懷舊電影的敘事題材主要指向“文革”題材影片和民國題材影片,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出品的懷舊影片中,更多的是對“文革”的控訴和對民國時期中國社會的批判。而到了20世紀90年代,激烈的批判和血淚般的控訴在時間的洗禮中逐漸被柔化,更為純粹的懷舊情結得以呈現。
在20世紀90年代的“文革”題材的影片中,敘事更多的是在講述個體的成長,他們不是“文革”的縮影,只是恰巧生活在了那樣一個特殊而值得懷念的年代。上映于1995年的影片《陽光燦爛的日子》可謂是其中的優秀代表作,這部影片由導演姜文執導,改編自王朔創作的名為《動物兇猛》的小說,由夏雨、耿樂、寧靜、陶虹等演員擔任主演。《陽光燦爛的日子》講述了在那個停課、罷工、搞運動的時代里,一群大院里的孩子的成長歷程。由夏雨飾演的馬小軍經常以撬鎖為樂,撬鎖的目的是進到別人家中玩耍,而并非偷盜財物,這也成為馬小軍“混社會”的資本;由寧靜飾演的米蘭美麗性感,是馬小軍的愛慕對象,但米蘭卻對頑皮幼稚的馬小軍不屑一顧,鐘情于由耿樂飾演的“硬漢”劉憶苦。在嬉笑怒罵中,這群大院里的孩子長大了,已坐擁豪宅豪車的他們卻依然會時常追憶那段青蔥歲月。可以說,《陽光燦爛的日子》以一種滑稽戲謔的方式呈現出了一代人關于“文革”的記憶,而身處其中的他們卻并沒有背上傷痕、懷著怨恨,而是在對獨特年代的青春回憶中做著“懷舊”的夢。上映于2005年的影片《孔雀》與《陽光燦爛的日子》一樣在國際上獲得了很高的評價和關注度,這部由顧長衛執導、張靜初等人擔任主演的影片依然以“文革”大環境下的個體成長為敘事焦點,講述了小鎮一家中哥哥、姐姐、弟弟的成長故事。由張靜初飾演的姐姐一直懷抱著飛行的夢想在禁錮的年代和閉塞的小鎮掙扎,面對她的只有一次次的失敗和悵惘的無奈。在這部影片中,“文革”的傷痛被無限淡化,略顯哀傷的基調呈現出的是姐姐等人在特定時代中的青春記憶。
在20世紀90年代的中國影壇上,年代劇異軍突起,簡單來說,年代劇就是呈現清朝末期到20世紀三四十年代故事的影片。在年代劇中我們能夠看到革命題材、民國題材以及抵抗侵略題材的影片,以特定時代為基礎的年代劇因多元化題材的呈現而顯得豐富多彩。上映于1992年的影片《大紅燈籠高高掛》改變自蘇童所著的小說《妻妾成群》,由張藝謀執導、鞏俐等人出演,講述了一個民國女性的悲劇故事,在北美地區創造了中國影片的票房紀錄。影片中,鞏俐飾演的女主人公頌蓮因父親的亡故而被迫嫁入“豪門”成為四姨太,從女學生到爭寵者,從失寵者到瘋女人的生命歷程表征著頌蓮這位新女性在時代潮流中的沒落。可以說,這部影片并不是頌蓮一個人的悲劇故事,它講述的是民國時期女學生以及女性群體的命運悲劇。在年代劇中,“老上海”的故事無疑是重要的組成部分,上映于2003年的影片《紫蝴蝶》便講述了發生在老上海時期的諜戰故事,這部影片由婁燁執導,章子怡、劉燁、李冰冰等知名演員出演,講述了一個民間反戰組織“紫蝴蝶”的故事,這部影片曾入圍戛納國際電影節的最高獎項金棕櫚獎。《紫蝴蝶》中由劉燁飾演的小職員司徒被誤以為是暗殺組織“紫蝴蝶”派來謀殺日本人山本的殺手,從而卷入了一段混亂而危險的關系中。一方面,日方認為司徒是掌控暗殺組織機密情報的殺手,對其嚴刑拷打;另一方面,暗殺組織認為司徒是背叛組織的叛徒,對其窮追不舍。同時,暗殺計劃的失敗使司徒的女友被誤殺,為女友報仇的決心驅使著司徒不斷探求事情的真相,走向了越來越混亂的迷宮之中。在這部影片中,導演以男主人公的身心活動為線索,勾連起了戰爭年代多方勢力的爭斗,從而呈現出時代洪流對個體命運的深刻且不可預測的影響,對遙遠年代的亂世思索與感懷呼之欲出。
四、中國當代電影懷舊之蘊
中國當代懷舊電影之所以興盛數十載,其原因在于所蘊藏的懷舊之思與懷舊之美,這不僅使中國當代的懷舊影片彰顯著獨特的民族品格,還在某種程度上迎合了大眾審美的懷舊需求。懷舊情結在社會轉型時期尤為凸顯,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社會轉型使民眾的生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原有的宏大敘事已然落伍,精英敘事也在文藝大眾化發展的過程中逐漸被淡化,符合大眾審美的影片大行其道,而這些具有懷舊情結的影片在很大程度上撫慰著民眾在社會轉型期的陣痛,同時在懷舊過程中帶來了深沉的思索。中國社會的轉型使民眾的生活水平快速提升,生活節奏驟然加快,原有的生活模式被逐漸打破,人與人之間的冷漠侵襲著社會生活中的每個個體,面對生活的變革和精神的危機,社會生活中的個體開始在迷惘中反思,去追憶逝去的幸福。這種反思不僅僅能夠慰藉掙扎的靈魂,還在某種程度上為中國社會的快速發展按下了慢進鍵,讓疲于趕路的人們停下來思考生命的意義和生存的價值,同時也為整個社會提供了一面反觀歷史的鏡子以明得失。
縱觀中國當代影壇之上的懷舊影片,無論是“文革”影片,還是年代劇,這些影片均具有相類似的審美風格,即感傷與唯美,這似乎已經成為中國當代影壇言說懷舊的一種固定風格。[4]感傷唯美的風格體現在慢敘事之上,在較為柔緩的敘事節奏中,懷舊之情擁有了生長的空間。此外更為重要的是,這些懷舊影片對影片色調的把控均具有相似的方式,對于過往的回憶,影片大多采用溫暖色調;而對于現實的敘述,影片則更多地使用了黑白灰等色彩,使現實與記憶形成了“本末倒置”的對比,從而凸顯出在敘述過往時的濃墨重彩,懷舊之緒進一步得到凸顯,將觀影者的思緒和情感自然而然地帶回到過去。
有評論者曾言,社會的快速發展和急劇變革隔斷了游子的歸鄉之路。從這一角度來說,“懷舊”不僅僅是對過往人事的懷念和追思,還是一次精神的救贖和心靈的回歸;“懷舊”是一場尋根之旅,也是一次反思之行,帶給快節奏生活中的人們以“驀然回首”的撫慰,帶給快速發展中的社會以“以史為鏡”的思索。但令人擔憂的是,“懷舊”之濫觴使市場化運營模式下的中國當代電影爭相披上“懷舊”的外衣,從而產出許多空有“懷舊”其表而無“懷舊”之實的影片,真正展開懷舊之敘、呈現懷舊之蘊無疑是中國當代懷舊電影的發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