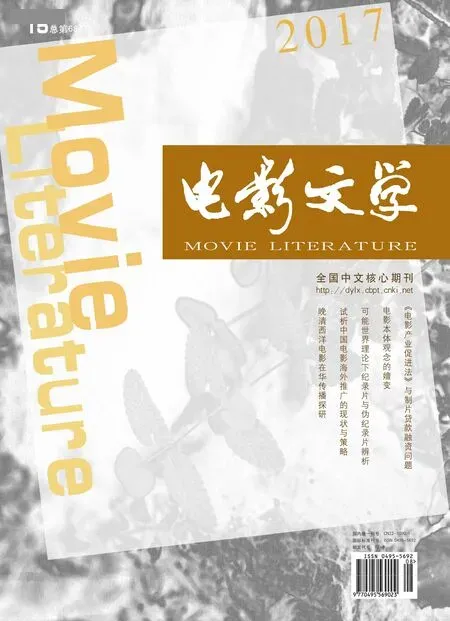新世紀以來美國電影中的中國符號
張慶艷
(聊城大學,山東 聊城 252059)
一、引 言
所謂“符號”,就是在社會生活中被大多數人認可或熟知的指稱一定對象的標志物。符號通常可分為語言符號和非語言符號兩大類。符號不僅具有直觀可感的外在形式,還必然呈現某種意義,在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層面均有豐富的運用,[1]而文藝創作領域自然也不例外。簡單來說,本文所論及的中國符號是指具有中國風格的符號,其內涵豐富、外延廣泛,無論是物質層面的景觀、服飾、食物、工藝品等,還是精神領域的品牌、文化、民俗等,都是中國符號的具體內容。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中國符號不僅呈現著中國的社會風貌,而且傳遞著中國的古典文化和現代文化。
在美國電影產生發展的數百年間,許多異域元素或異域文化在美國的好萊塢影片中有著不同程度的體現。究其原因,美國是一個典型的移民國家,本土的歷史文化并不豐富,作為一個各族人民的“大熔爐”,美國具有強大的兼容并蓄精神,這就使美國民眾從審美心理上更樂于接受具有異域風情的事物。[2]但令人遺憾的是,美國與中國相對較遠的地理位置及19世紀以來的東西方勢力對比使美國電影并沒有在其產生發展之初便接納或采用中國符號,直到20世紀70年代,中國人開始以配角的身份出現在好萊塢電影中。也正是從這時候開始,中國形象和中國故事進入了美國民眾的視野。新世紀以來,在中國形象和中國故事越來越多地出現在美國影壇的同時,許多中國符號也活躍在美國影片里。眾所周知,美國好萊塢電影的發展處于世界領先水平,融入不同國家和地區的電影市場是美國好萊塢電影當今發展的重要策略之一。而將中國元素納入美國電影中就能夠更好地獲得中國乃至東方文化圈的觀影者的認同,這無疑是豐富美國電影內涵及提升其商業價值的良策。本文將從較為微觀的角度入手,重點以影片《花木蘭2》《龍騎士》《面紗》《異能》《2012》《功夫熊貓》為例,從中國圖騰、中國景觀、中國物飾三個方面解讀新世紀以來美國電影中的中國符號。
二、新世紀以來美國電影中的中國圖騰
圖騰產生于人類發展階段的早期,即原始時代,當時低下的生產力使人類在面對自然及自然界中的動植物時均充滿了敬畏之情,也出現了許多以不同動物或植物為保護神或祖先的情形,這就是我們現在所言的圖騰。不同部族擁有著不同的圖騰,而中華民族的集體圖騰則非“龍”莫屬。龍是盛行于中國以及東亞地區的傳說中的神獸,龍擁有著似牛的頭、似鹿的角、似蝦的眼、似魚的鱗、似人的須等“九似”的形象,這個虛擬的神獸在中國代表著祥瑞和守護,在漫長年代的傳承中已經成為中華精神的重要承載。新世紀以來,美國電影中出現了許多龍的形象,從表面上看,這是美國對中華文化的進一步接受,但細觀之下,美國電影中的龍卻缺少了其真實的內蘊。
系列影片《花木蘭》的第一部上映于20世紀末期,其第二部上映于21世紀初。在這一系列的影片中,中國歷史中的巾幗英雄花木蘭成為故事的主人公,而中國圖騰——龍也在其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從某種程度上推動著劇情的發展。雖然其中木須龍的形象十分符合好萊塢動畫形象的畫風,但不可否認的是這一系列中的龍形象消解了作為中國圖騰的龍的嚴肅性,成為一個令人發笑、活躍氣氛的“小丑”形象。在影片《花木蘭2》中,已成為名震全國的女將軍的花木蘭不僅大膽地追求自己的愛情,還幫助三位公主打破階級的限制找到了摯愛。但在這一過程中,木須龍卻因為自己的利益破壞了木蘭的計劃,使木蘭身陷危境。木蘭的臨危也使木須龍幡然悔悟,最終木蘭和三位公主都獲得了幸福。細觀《花木蘭2》中的木蘭形象,不難發現這個長著東方外貌、有著中國身份的女性實際上卻擁有著美國女性的特質,其反抗權威和勇敢追尋的品質更是具有鮮明的“美國夢”特質。相比之下,固守傳統、自私狹隘的木須龍形象則黯然失色。同時,從影片故事結局來看,木蘭教化了木須龍,代表著東方文化對西方文化的順服,流露出了西方文化優等論的情感傾向。
上映于2007年的影片《龍騎士》講述了“龍騎士”集團內的戰斗。在富饒、和諧、美麗的阿拉蓋西亞王國中有許多龍騎士,一位名為蓋爾巴特瑞克斯的少年龍騎士因年少氣盛使自己的同伴和飛龍喪命,而蓋爾巴特瑞克斯也因無法再成為龍騎士而陷入了瘋狂。瘋狂之中的蓋爾巴特瑞克斯召集了另外12位龍騎士組成了反抗組織并將阿拉蓋西亞王國推向了戰亂和殘酷。就在民不聊生之際,一個名為艾瑞岡的小男孩無意間找到了一顆散發著藍光的龍卵,而艾瑞岡也從此擔負著成為正義龍騎士并拯救家園的重任。在影片《龍騎士》中,龍形象具備了嚴肅的特性,不再成為滑稽擔當,卻成為一種缺失性情的“工具”,因其坐騎的身份而具有鮮明的附屬性,與蓋爾巴特瑞克斯共同戰斗的龍代表著邪惡,而艾瑞岡身邊的幼龍則代表著正義和希望。除了上述兩部影片以外,還有許多新世紀以來的美國電影中出現了龍這一中國圖騰形象,比如《藍精靈》中與恐怖相伴而生的青龍雕像、黑暗勢力格格巫手中的龍杖;《霍比特人》中霸占矮人族保障的邪惡之龍等。總的來說,美國電影對于中國圖騰龍的呈現并不客觀,或是帶有戲謔之感,或是具有敵對之意,抑或是體現出蔑視之情。但也需要看到的是,在新世紀以來的美國電影中,龍形象逐漸增多,這也體現出中國符號,甚至是中國文化在美國影壇上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關注。
三、新世紀以來美國電影中的中國景觀
在以龍為代表的中國圖騰之外,新世紀以來的美國電影中還出現了許多中國景觀,其中展現著懷舊情調的老上海,代表著現代開放的香港、凸顯純美神圣的西藏以及異域中的唐人街都成為美國電影中引人注目的中國景觀。
影片《面紗》上映于2006年,由導演約翰·卡蘭執導,娜奧米·沃茨、黃秋生等人擔任主演。這部影片改編自著名作家毛姆的作品《華麗的面紗》,講述了英國人沃特和吉蒂在異鄉(即中國)的經歷及二人之間的情感故事,而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老上海則成為影片《面紗》的重要取景地。影片中,愛慕虛榮的女主人公陰差陽錯地嫁給了平凡的醫生并隨之移居到了中國上海,在歌舞升平的老上海與英國外交官發生了婚外戀情。得知真相的丈夫決定用自己的方式懲罰妻子,帶著妻子來到了疾病橫行的地區,遠離繁華、面對死亡的日子反而使二人重新審視這段婚姻。在影片《面紗》中,男女主人公在異鄉逐漸走進彼此的故事自然是主線,在此之外老上海的獨特風情也成為這部影片的吸睛之處。平民區江南風情的民居、租界里的有軌電車、舞廳中的老唱片和身著華麗旗袍的女郎等,都呈現出一種老上海獨特的風貌,在一定程度上也滿足了西方觀影者的獵奇心理。香港的殖民歷史和現代開放的發展狀態使其成為最早出現在美國影片中的中國城市之一,當今的香港早已擺脫了殖民的陰影,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同時其獨特的地理位置也使香港具有開放和兼容的姿態,新世紀以來,“東方之珠”香港更成為美國影片中的座上客。享譽全球的科幻巨制《環太平洋》便將故事的主要發生地設置在中國香港;另外一部科幻影片《異能》更是將香港作為主要取景地。影片《異能》上映于2009年,對白語言為英語和粵語,這在美國大片中并不多見,影片講述了一個異能殺人組織的故事,其中男主人尼克長期生活在香港,而香港的街景與民居也在這部影片中被大量呈現。西藏對于西方人而言,無疑是一個自然純凈且充滿夢幻奇跡之地,這一特性在多部美國影片中都有體現。上映于2009年的《2012》可謂是美國災難片歷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影片中瑪雅人關于世界末日的預言應驗,人們為了延續生命建設了諾亞方舟,而諾亞方舟的修建場所就位于中國西藏。影片中喜馬拉雅山脈及西藏的人文建筑都有呈現,同時這些中國西藏的景觀也從某種程度上強化了整部影片的神化色彩。在災難片《2012》之外,上映于2008年的《木乃伊3》、上映于2013年的《特種部隊》等影片也都在中國西藏取景。比如《特種部隊》中一個名為白幽靈的重要角色就曾經在西藏經歷了神奇的療傷治愈過程。事實上,美國影片對于中國西藏景觀的關注以及神化闡釋源自歷經數代的集體記憶,在西方民眾的傳統觀念中,東方一直具有濃厚的神秘色彩,而西藏則成為這種神秘感的最好體現。
相比于中國國境之內的上海、香港和西藏而言,中國國境之外的“中國城”和“唐人街”則是較為特殊的中國景觀。顧名思義,“中國城”和“唐人街”是華人聚居之地,是在外國領土內一個相對封閉和獨立的區域,其產生根源在于異鄉華人的自我保護。也正因如此,“中國城”和“唐人街”的“與世隔絕”使其出現并保存了大量的中國景觀。在影片《藍精靈》中,唐人街上的幽暗小屋、存有咒語書的神秘書店等都透露出神秘莫測的氣息,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暗示著罪惡的發生。
四、美國電影中的中國物飾
在中國圖騰和中國景觀之外,新世紀以來美國電影中的中國符號還主要體現在服裝、食物等中國物飾之上。系列影片《功夫熊貓》是一部具有濃郁中國風的動畫喜劇影片,在這一系列的影片中,故事的發生背景為中國古代,而一只立志成為功夫高手的熊貓就是整個系列影片的主角。這一系列影片自2008年上映以來,已拍攝了多部續集,在美國本土、中國及世界多個國家和地區均取得了不俗的票房成績。在系列影片《功夫熊貓》中,熊貓阿寶等主要角色的服裝設置十分講究,阿寶身著的長袍馬褂都是中國清朝時期的典型裝扮,同時,綁腿、馬蹄袖又符合阿寶功夫者的身份,這些細節處理成為功夫熊貓形象塑造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無獨有偶,在由中國功夫明星成龍擔任主演的系列影片《尖峰時刻》中,不僅香港成為主要取景地之一,而且成龍的搭檔卡特還以一身唐裝出現,雖然這些中國服飾在影片中大多為驚鴻一瞥,卻以十分直觀而鮮明的方式呈現出了中國風情。
眾所周知,中國的飲食文化博大精深,受到傳統儒家倫理、中醫養生、審美風尚等影響,中國飲食不僅講究色香味俱全,而且與修養境界相關聯,這也使中國飲食逐漸上升到了文化的層面,從而不斷發展,在世界范圍內獨樹一幟。新世紀以來,美國電影中出現了不少中國特色的食物,在令觀眾大飽眼福的同時,也從側面傳遞了中國獨特的飲食文化。在系列影片《功夫熊貓》中,主人公阿寶對食物擁有著超乎尋常的興趣,甚至可以說是伴隨著食物逐漸走上了習武之路。在這一過程中,中國傳統美食及現下流行的食物都在影片中得到呈現,如麻婆豆腐、火鍋等,甚至盛裝食物的器皿也具有濃郁的中國特色。[3]
總的來說,新世紀以來美國電影中的中國符號逐漸增多、日益豐富,體現了中國符號在世界影壇影響力的提升。但細讀這些中國符號也不難發現其中的問題,美國電影對中國符號的解讀并不客觀深入,這不僅使中國圖騰、中國景觀及中國物飾均難逃絕對的“配角”地位,[4]還在一定程度上出現了被丑化或誤讀的現象,由此觀之,美國電影對中國符號的運用喜憂參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