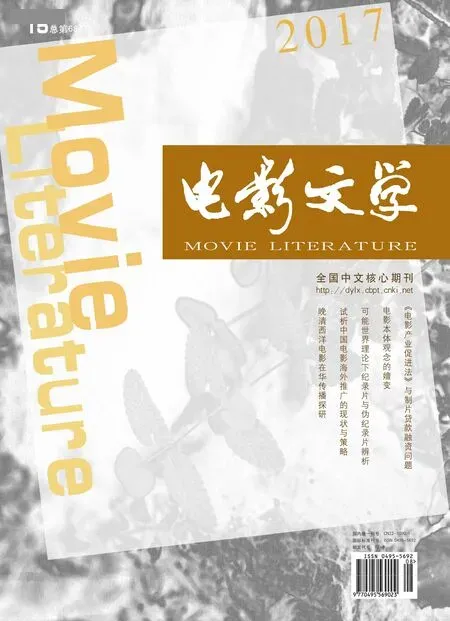美國戰爭電影的視覺隱喻
楊 凱
(河北工程大學文法學院,河北 邯鄲 056038)
戰爭是一項與災難、死亡和恐懼緊密掛鉤的集體式暴行,通常情況下,戰爭意味著丑陋、屠殺,令人排斥,而電影的生產和消費則是以審美和娛樂為目的的藝術活動。由于與戰爭有關的內容和場景能夠在視聽感官以及情緒情感上給予人們強烈的震撼,電影通常會將戰爭作為審美化的對象。在電影的處理下,戰爭的傷害、血腥等與觀眾保持了一定距離,成為觀眾審美快感的來源。目前,美國戰爭電影在拍攝制作模式與票房上都處于領先地位。其不僅擁有獨特的意識形態,在形式上,隨著一代代導演的不斷探索,美國戰爭電影也形成了獨特的審美形式。在世界已經高度“圖像化”的今天,這些審美形式理應得到電影人的注意。其中各類視覺隱喻便是值得關注的外在形式之一。“在我們慣用的所有隱喻中,視覺隱喻肯定是其中最普遍的一個。它滲透在我們的語言和思想之中——特別是關于思想的語言中。盡管我們的科學和哲學導師們一再告誡不要混淆直覺對象的觀念、形象和理念,但是我們似乎可以很有把握地預知,用于洞察的視覺隱喻將始終是有效的和占主導的。”
一、道具隱喻
由于道具的靈活性,它是電影中最容易設置隱喻的單元。但導演對其的選取以及對道具與敘事關系的處理,也考驗著導演的圖像化能力。尤其是在以真實戰爭為背景的電影中,道具在富含深意的同時,怎樣在整體環境中既不突兀,又能吸引觀眾的注意,成為導演們要考慮的關鍵問題。
這方面較為著名的有史蒂芬·斯皮爾伯格的《辛德勒的名單》(Schindler’sList,1993)中的金戒指等。在電影中,辛德勒得到了一個禮物,即科拉科集中營幸存的猶太人用自己的金牙給辛德勒鑄成的金戒指。在戒指上刻著猶太法典的一句希伯來語經文:“救一個人,就是救了整個世界。”辛德勒在得到這枚戒指后因為心情激動而不小心使戒指掉在了地上,他趕緊低下身來找戒指。觀眾可以從辛德勒的反應中看出他對這個禮物的重視。道具本身及辛德勒的一系列動作承載了豐富的內容,它提醒觀眾的是辛德勒得到的無形的、精神上的回饋,即成為一個新的、為他人所感恩的人。辛德勒在電影開場時是以一個“拜金”的形象為觀眾所認識的,他抱著在戰爭中賺一筆錢的目的提出招募猶太工人。然而在電影結束時,辛德勒已經是真心地希望能從納粹手中挽救猶太人,他甚至后悔自己沒有能賣車、賣金徽章以籌集更多的錢,多救十幾個猶太人。因此,一枚小小的戒指從辛德勒手中跌落意味著一種凡人的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猶太人幸存者的稱頌和感恩與辛德勒無法釋懷的內疚在由金牙鑄成的戒指上得到了具象化。
與之類似的還有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執導的《現代啟示錄》(ApocalypseNow,1979)中的無線電話。電影改編自康拉德的小說《黑暗的心靈》,只不過出于對越戰的反思,電影將原著中的非洲改為亞洲,但戰爭地遠離文明這一點卻是共同的。美軍上尉威拉德和科茨上校實際上是美軍的一體兩面,他們都曾經在美軍中服役,并且立下汗馬功勞,另一方面又都目睹了長期的戰爭給美軍帶來的精神扭曲。所不同的是,科茨上校選擇了脫離軍隊,在柬埔寨建立一個自己的原始王國。在這個王國中,他被當地人當成神一樣崇拜,科茨上校以這種最徹底的方式告別美軍身份,而威拉德則奉命來抓捕他。在影片的最后,威拉德殺死了科茨,威拉德選擇了關掉無線電話對講接收器,斷絕了這條與上級聯系的唯一途徑,轉舵駕著汽艇離開了湄南河深處的叢林,畫面一片黑暗。威拉德關閉無線電話的行為,代表他也走上了一條類似科茨的路,即遠離美軍所代表的“文明”,跟隨自己的心靈尋找真正的自由。
又如,在奧利弗·斯通“越南三部曲”之一的《野戰排》(Platoon,1986)中,男主人公克里斯·泰勒實際上是斯通本人的自況。相對于以女人視角展開的《天與地》,《野戰排》則是以美國男性的口吻講述的故事,甚至可以視為斯通的虛擬傳記作品。在電影中出現的一些道具既是真實存在的,又是具有隱喻意味的。例如,泰勒曾經一手背背包、一手拿鋼盔經過一個木頭柱子,柱子上面釘滿了白底黑字的路牌,下面則堆放著一些美軍的物資。這樣的柱子在當時的美軍軍營中是隨處可見的。其關鍵之處就在于路牌上寫的地點——河內:710公里,香港:685公里,洛杉磯:8757公里,此外還有堪薩斯、西貢、得克薩斯等。每個路牌的尖角都指向所標注城市的方向。很顯然,以美軍在越戰時期的科技程度,這樣的路牌實際上并不是承擔指示作用的,它們的存在是長期陷于越戰泥潭中的美軍士兵厭惡戰爭,思念萬里之外美國家鄉的體現。在電影中,泰勒、伊利亞斯、巴恩斯等人不斷遭受著戰爭的戕害,也使人質疑這場戰爭的正義性,而路牌上美國與亞洲城市下的數字對比也委婉地表示了導演對美軍入侵屬性的判斷。由于斯通對真實感和殘酷性的苦心追求,斯皮爾伯格在評價《野戰排》時曾經給出了極高的評價,斯皮爾伯格認為:“(《野戰排》)它已超出了電影的范疇,它使人覺得自己到過越南,并且今生今世永遠不想再去了。”“覺得到過越南”正是電影在視覺上給予觀眾的身臨其境感,而“永遠不想再去”則應該歸功于導演對戰爭殘忍一面的淋漓展示。與之類似的還有如邁克爾·西米諾執導的《獵鹿人》(TheDeerHunter,1978)中的“俄羅斯輪盤賭”等。
二、場景和畫面隱喻
場景既是一種表示陳列、位置的空間構造,也有著傳遞審美理念和文化思考的責任,電影中每一個精心設計的場景,都是一個精神空間。在美國戰爭電影中,場景也同樣滲透了隱喻。
深受中國傳統美學影響的李安也是一位善于運用視覺隱喻的杰出導演。李安本人并不熱衷于戰爭題材,他更關注的是人處于一種尷尬、進退維谷局面時反映出來的人性。在李安的《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BillyLynn’sLongHalftimeWalk,2016)中,他特意安排了一個鏡頭,當林恩等士兵在橄欖球場的舞臺旁邊候場時,有一道巨大的鐵網攔在他們面前,而鐵網的那一面便是他們的偶像“真命天女”組合。這道鐵網是可見的,然而還有一道無形的、更為堅固的網也橫亙在士兵與娛樂明星中間,那便是無處不在的消費主義。事實上,以“真命天女”為代表的、光鮮的娛樂圈人士與觀眾并無意去了解士兵們在殘忍的戰場上究竟經歷過什么(李安之前已經做了足夠的鋪墊,如人們問士兵的問題往往是某種武器怎樣,槍打在人體上是什么聲音等),而站在鐵網這一頭的士兵們被置于一個另類的環境中,他們也會懷疑自己付出出生入死的代價來保護鐵網那頭麻木的、會對他們大打出手的人群究竟是否值得。這一場景再一次照應了電影的主題之一,即在消費時代下理想主義者們所遇到的窘境,在一個“偉大”已經變得尷尬的時代,人們是否還能夠保持自己的信仰與承諾。與之類似的還有斯通另一部“越南三部曲”《天與地》(Heaven&Earth,1993)中隱喻越南所代表的蒙昧、落后的大片大片的稻田等。
除此之外,一些畫面的特殊處理也體現著美國戰爭電影的視覺隱喻。如疊化處理,在斯坦利·庫布里克的《全金屬外殼》(FullMetalJacket,1987)中,派爾尸體的鏡頭還沒有消失,“小丑”在越南跟當地妓女調情的畫面已經淡入。兩個畫面的交疊令人備感諷刺,因為小丑在上一個鏡頭中還在惋惜、哀悼著派爾的死。這里顯示著在戰爭面前,小丑等人的麻木。又如色彩隱喻,在《辛德勒的名單》中,斯皮爾伯格幾乎全部采用黑白畫面,而只用紅色表現了一個猶太小女孩,這醒目的紅色震撼著辛德勒和觀眾的眼球,它暗示了整個猶太民族一線希望的消逝,在此不贅。
三、人物形象隱喻
人物是戰爭電影中的重要表現對象。人是戰爭的發起者和承受者,尤其是對軍人而言,戰爭所給予他們的不僅是肉體上的傷害,還有精神上的沖突。在戰爭中,人的自然屬性、暴力和求生的本能以及有限性均會被放大。觀眾在賞析戰爭電影時,人物也是占據其主要注意力的對象。因此,人物(包括主要人物與次要人物)本身也會被導演賦予隱喻作用,只有當觀眾充分解讀了這些隱喻,才能理解導演所構建的心理空間與人物關系。
主要人物以《現代啟示錄》為例:在《現代啟示錄》中,威拉德的臉時而滿是泥水,時而被雨水沖刷干凈,這一臟一凈兩個形象隱喻的是威拉德掙扎中的靈魂狀態。如他殺死科茨時,他的臉是被泥漿覆蓋的;而他心中的人性復蘇時,天降大雨,他的臉又恢復了本來面貌,這意味著他完成了一次自外而內的洗禮。
次要人物則以李安《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為例。在電影中,林恩等人在即將上場時,卻收到導演的通知:“現在最重要的是,先解決你們的服裝問題。”這對于戰士們來說無疑是意外的,他們都整齊地穿著筆挺帥氣的軍禮服。戰士們表示他們就這一套軍禮服,而導演卻要他們換下軍禮服,改穿在戰地的作訓服。理由是“現場穿軍禮服的人太多了”,導演為了突出B班就只好讓他們換裝。于是觀眾可以看到,在中場表演的時候,B班身穿作訓服站在舞臺上,他們身后的方隊全部穿著軍禮服。李安為了再一次突出軍禮服形象的隱喻,在電影的結尾,林恩與姐姐在停車場告別的時候,還安排了兩個身穿軍禮服的表演者在不遠處經過。這里“演員+軍禮服”的形象暗示的依然是這個社會讓林恩們感到格格不入的氛圍。對于林恩等人來說,軍禮服是他們在重要場合,如授勛等時刻才會穿上的服裝。如果說作訓服代表了男兒的奮斗和作戰訓練時的艱苦,那么軍禮服對他們來說就意味著榮耀與莊嚴。然而這一次換裝波折卻明確地告訴他們,這對于別人來說僅僅是一套演出服裝。而由此擴展開來,也不難理解林恩等人實際上也是可以被隨意擺放、調整的演出“道具”(而并不是思想和感情得到尊重的人)這一概念了。
戰爭電影作為經久不衰的類型片之一,與其他類型片在形式上的區別是明顯的:既有大量直觀表現千軍萬馬、你死我活的戰爭圖像,又有微妙的、靜態的,具有暗示性的視覺符號共同參與到電影的視覺運作機制中來。戰爭電影要想取得一定的深度,其視覺運作機制就必須肩負著讓抽象而晦澀的內容變為形象可感的畫面,而視覺隱喻正在其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本身的軍事實力以及在世界軍事活動中的參與程度,美國戰爭電影在世界電影市場中擁有強勢的地位,已經成為一種能夠主導、影響觀眾的媒介。在這一媒介長期的控制下,人們對于視覺隱喻的理解判斷逐漸趨向標準化、穩定化和強制化。美國戰爭電影通常會在多個對象上滲透視覺隱喻,小至場景或道具,再到人物形象乃至整幅畫面,它們或是對應某一具體的本體,或是暗示某種較為抽象的觀念。導演們以視覺隱喻來溝通著一個和平的現世生活和一個炮火紛飛、矢石交攻的彼岸世界,讓觀眾在感性體驗中與自己達成理性思考上的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