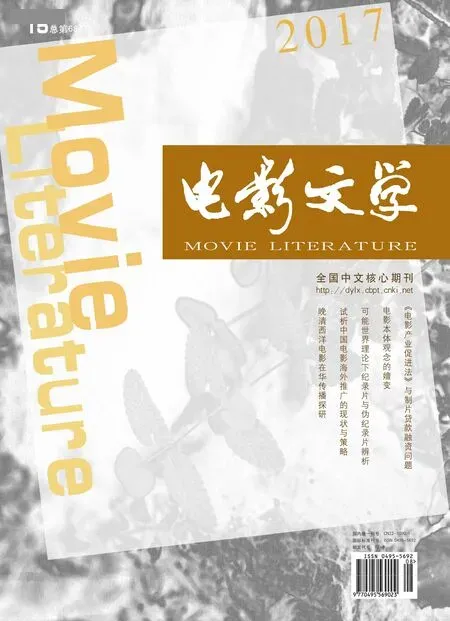晚清西洋電影在華傳播探研
王子藤
(中南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4)
近年來,學術界在電影史的開端研究中做出許多成果,學者普遍將1905年中國人自制電影《定軍山》作為中國電影史的發端。晚清西洋電影傳播由于影片資料的缺乏,被當作中國電影史發軔前的準備階段而未受足夠的重視。本文擬從清末時人的日記手稿、報刊等資料入手,探究晚清西洋電影傳播發展中帶來的問題與應對。
一、電影傳入與國人反應
電影初入時,國人因其以電力運作,表演形式又類似于中國漢武以來的傳統戲劇,故稱之為“電光影戲”。晚清第一部電影于何時何地傳入,又由哪家公司或個人公開放映,學術界暫無定論。但最早出現的文獻可見于1896年8月11日,上海徐園內“又一村”公開放映的西洋戲影,此后陸續有電影放映。[1]1897年5月,美國商人雍松攜帶影片來到上海,首先在上海著名的查理飯店首映,只準外國人前往觀看。[2]隨后供國人觀賞,有幸最先接觸到西洋玩意兒的莫過于上層中國人。1897年6月4日晚孫寶瑄前往味莼園觀“電光戲影”,在日記中寫道:“能作水騰煙起,使人忘其為幻影。”[3]11日和13日連載于《新聞報》頭版上的《味莼園觀影戲記》(上、下)一文中又記載道:“驅車入園,園之四隅,車馬停歇已無隙地……報時鐘剛九擊,男女雜坐于廳事之間,客座約百數十人,撲朔迷離不可辨認。”[4]由孫寶瑄與新聞報的記述可以看出電影初到中國時受到上層人士的熱烈追捧。“天地之間,千變萬化如蜃樓海市,與過影何以異?……乍影乍現,人生真夢幻泡影耳,皆可作如是觀。”[5]中下層人士對電影的熱愛亦可見一斑。“燈火驟滅,山川銀河印于白布間”的奇景使得眼界初開的國人流連忘返。
電影帶來的商機是顯而易見的,但是電影的放映并沒有特定的場所,晚清民眾的娛樂場所多集中于茶館、戲園等,隨著西洋鏡、賣野人頭、影戲(幻燈片)等新型娛樂設備的傳入,逐漸出現了多功能、兼容傳統消遣方式與新式洋器玩樂為一體的公園、游戲園,各園主為獲利紛紛開始通過登報的形式為上映的電影做宣傳,這也是中國電影史首次宣傳嘗試。茲列舉天華茶園、同慶茶園所做廣告比較。“美國新到一百年來未有神奇之影戲,此戲純用機器運動,靈活如生且戲目繁多,使觀者如入山陰道上,有應接不暇之勢,第一出系……自本月二十七晚起,準演五天,定價頭等座位五角、二等座位四角、三等座位二角、四等座位一角。”[6]“啟者西人某君,由美國帶來機器電光影戲,其精致化出泰西各國故事,比真尤活,栩栩如生,靈妙無極,今西人回國在即,特借小園由初九、十、十一連演三夜,其價從廉,頭等收洋四角正、二等二角正,務望諸君早降光臨玩賞是荷。”[7]不難看出這天華與同慶兩家茶園只能限時放映影片,只有張園、徐園經常性放映電影,其他茶園只得允許放映幾日。電影的受眾逐漸由上層人士向中下層人士開放,票價也相應地減少。當電影初到上海,由查理飯店首映時,外國人需支付的金額為入場票1美元,座位票1.5美元。[2]而在電影向下推廣時,頭等坐票已降至五角,數月過后又降價為四角,電影的票價由受眾人群不同導致降價的同時還摻雜了時間因素,即同一部電影會因上映時間的前后產生價格的差異。中國自古以來傳統戲劇很難因為上映時間的長短而產生觀看費用的不同,考慮到演戲的人工成本與戲曲文化的跨時代經久不衰因素,電影的制作成本相對較低且播放頻率高。這也折射出近代國人的娛樂方式步入了近代較快的節奏。
二、電影初傳帶來的問題
電影傳入中國后,并不是暢通無阻地可以在各地上演的,而是劃定了具體的放映地點。自1896年電影流入上海后,先后在北京、天津、廣州等地放映,隨著20世紀初電影技術的快速發展,電影的數量與播放地點也在急劇增加,在巨大利潤的驅動下,電影只準在通商口岸上映的限制開始被打破。在有清之年,電影始終沒有形成特定的行業,表現為私人謀利的手段,這就使得晚清西洋電影在傳播過程中,給中國帶來了利權、治安和習俗風化等一系列隱患。
(一)利權問題
電影帶來的最突出問題便是利權問題。依據通商條例規定,外商只準在通商口岸進行貿易活動,在內地不得開設行棧,但中國人為牟利而私自攜帶電影放映機深入內地的行為卻屢見不鮮。1904年8月,揚州人黃家柟稱自己來自上海英租界老晉隆洋行英美影戲公司,現在新勝街租房來放映各國電光戲影,請縣令出具告示對其商業放映給予保護,卻沒有合法執照。縣令以“洋人到內地游歷、通商均應按照約章辦理,至于來內地放映電光影戲,則沒有明確的條文參照。況且揚州城內不比通商口岸和租界,夜間放映容易引起糾紛”[8]拒絕了黃某的請求。又有熟通日語的教習高馥園、廩生陳某打著日本商人森島的名號,由陳擔任經理,擬在江寧縣滸墅鎮龍王廟租房上映電光影戲。江寧縣當晚差人將其查禁,15日接岡部總辦函稱,森島次郎并未授權他人放映,純系高、陳二人持其名片私自前來放映,可見華人經常借洋人聲勢,為己牟利,若不嚴加懲辦,則不足以儆效尤。[9]除了假托洋人關系鋌而走險到內地撈金的中國商人外,洋人強行在內地公演并造成沖突的事件則嚴重損害了中國主權。1906年2月4日申報刊載一則新聞,華人馮東巖、張如松伙同日本人清水直性、巖崎良一在九江成內發放通貼,租借房屋場地,準備初三這一天在四碼頭開演電光影戲,警察總巡繁司馬、嚴孟以日本領事沒有發送照會,也未經道憲允許為由禁止其公開放映,派巡長江炳榮、郭蘭亭前往查禁。但引發肢體沖突,巡長被日人毆擊,總巡聞訊前來鎮壓,但對方仍氣焰囂張,旁觀者憤憤不平,合力將日人及馮、張治服,繁司馬將被傷巡長送往徳化縣醫治。同時稟請道憲按照律法進行懲辦,最終日人認錯,愿即日出境,而勾結日本人的流氓吳子卿則笞責七百板。[10]晚清政府為利權問題而限制電影在內地的傳播,一方面出于保護利權的考慮,另一方面卻也阻礙了電影在中國內地的深入發展。
(二)治安問題
中國內地民眾由于對外來之物的好奇,蜂擁前至觀賞勢必引發治安問題。1906年10月上海四馬路青蓮閣茶館樓梯邊有電光影戲放映,旁觀者甚多。在此期間該茶館剛開張上市,茶客紛紛前來品茶,將電影戲臺設在此處,若遇有不測,逃離通道阻塞,后果不堪設想。捕頭惠爾生君令包探竇如海前往勘查后,傳諭“停止電影放映或將其搬往他處,不得阻礙要道”[11]。撇開人為制造的治安問題外,天氣因素也不得不被認真對待。1909年7月,有電光戲影在浙江郡垣張家衖內寄園開映,欲一觀而開眼界者蜂擁而至,但近段時間水災頻繁,聚眾觀影容易引發事故。英太守聞訊,特飭秀水縣“本府訪聞城內張家衖寄園夜間開演電戲,已經多夕,觀者雜沓,男女喧闐,難免不滋生事端。現當霪雨兼旬……況電之為物,研究稍有未精,則觸發肇災,在在堪虞。究竟寄園所演電戲曾否稟準該縣開演有案?如未經稟準,系私自開演者,應即嚴札禁止,不準復演,以免危險而保治安”[12]。
(三)社會風化問題
風化問題是電影傳入中國后遇到的一大挑戰,1910年底有一宗美國決斗電影流入上海,并準備在上海各租界上演,但此電影曾因容易誘發青年私斗的隱患而遭美政府查禁。清民政部派人暗地調查,“如果有二人決斗及各等壞人心術之電影,查有實據后,即禁其至內地開演,以維風化。若我民政部者,亦可謂防患未然矣”[13]。中國孔孟之道提倡人性之善,須加以善導,外國流入的電影如果涉及與晚清社會倫理道德發生沖突的部分即會被禁止放映。20世紀初期的黑白電影,只見其影不見其音,為達到聲茂并存的效果,人們往往在幕后配音,報紙曾刊出演唱淫詞為電影配音的丑聞。“木作頭朱森記近在大達輪步馬頭搭蓋席棚,開演電光影戲,并招集無賴施蘭亭、林小坤等唱演淫詞,昨被工程局董訪悉,立即飭探嚴行查禁”[14]。
三、電影規章制度的建立與時人對電影發展的肯定
歷時十余年的傳播,電影的發展愈發普遍化與日常化,雖存在眾多問題,但發展趨勢已不可阻擋。意識到電影放映時的混亂無章,清政府于1911年6月頒布了《取締影戲場條例》,其內容包括:開設電光影戲場所須報領執照;男女必須分座;不得有淫褻影片;停場時刻至遲以夜間12點鐘為限;巡警得隨時查察。條例頒布后,在上海首先施行,這是中國第一個有關電影放映的管理法規,可以說是中國電影檢查制度的雛形。盡管男女分座、電影放映至遲到12點等規定顯出落后保守,不得有淫穢電影的界定又無具體的甄別規定,但在晚清具體社會背景下,如何維護治安穩定與整頓風化問題上無疑值得肯定。
電影滲透民間生活的一大體現即在大眾報刊上的頻繁宣傳,涉及電影的評論也日益增多。這時的電影雖然還是作為娛樂方式供人消遣時光,但已有報刊評論人從電影中獲得思想啟蒙,將電影描述為“一件精神上的美術”,并贊賞電影制作者為“世界上無聲的大教育家”[15]。他們跳出娛樂范疇,開始用專業的眼光來看待電影無疑肯定了電影是門藝術。電影內容也日益豐富,這也就推廣了電影的使用范圍。學校、青年會、教堂莫不用之,也有各大商家,取各種貨樣制成影片各處開演以獲其利。有關疾病傳播、抽煙酗酒的危害、社會不公等情狀,都可以一一攝像后做成影片,使觀看者一目了然。這說明電影或多或少有指導社會的教育色彩。電影的用途被加以發掘,各行各業人士對電影有著不同的期待,教育界的有識之士倡導將電影引入學校,借助電影生動形象的畫面,可彌補書本教學中晦澀難懂的地理等自然學科的不足,或者將諸道德倫理應用進教學,使學生易受其刺激。商業買辦也看到了電影的巨大商業潛力,效仿歐美各國,在電影放映結束閉幕休息之時插播商業廣告。社會工作者及歷史學家也將目光轉向電影,由于電影能夠生動形象地再現歷史,在保存史料上具有口述傳承、筆記保存等方法無可比擬的優勢,如最近英皇加冕儀式與聯軍攻陷南京等,用影片保存時間長久且真實性較高,可供后人參考。
四、結 語
晚清電影發展雖有諸多阻礙,但總體來說,電影順應了歷史潮流,為國人帶來新的愉悅體驗的同時,也推動了商業、報紙業、教育業等行業的發展,其發展潛力巨大。回顧晚清20年,電影文化在中國生長和發展的過程雖然相對簡單、零散,卻為我們勾勒出一幅欣欣向榮之態,為20世紀二三十年代電影業的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