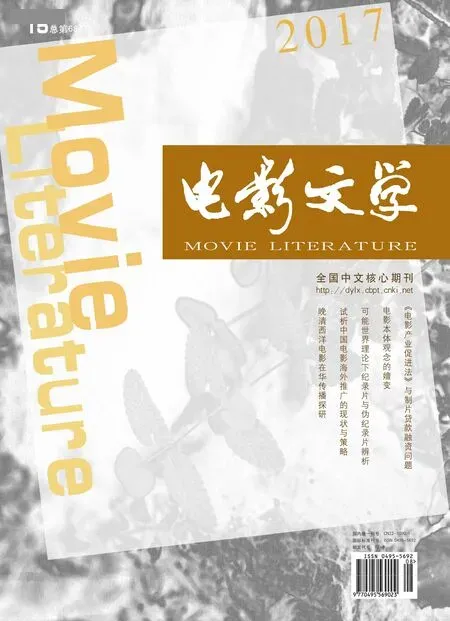《哥斯拉》中的日本族群式話語
尚學艷
(新鄉學院,河南 新鄉 453000)
由本多豬四郎拍攝于20世紀中葉的《哥斯拉》(Gojira,1954)被認為是一部曠世經典。電影不僅僅在上映之際引起了日本國內外的轟動,也奠定了后來的一系列“哥斯拉”電影的基礎。時至今日,哥斯拉這個大怪獸已經不僅是一個人們恐懼心理的刺激物,而是已經成為一個具有多重文化內涵的能指。盡管其后的哥斯拉又經過了美國導演的多次演繹,如1998的羅蘭·艾默里奇版,2014的加里斯·愛德華斯版等,但不可否認哥斯拉的形象已經被打上了鮮明的日本烙印。從最早的這一版《哥斯拉》中,人們可以窺見日本社會的一角,乃至日本的某種族群式話語。
一、電影與族群式話語表達
電影反映了人們的日常生活實踐,又在這種反映中成為一種權力話語,代表了某種媒介視角與民眾的意識形態。
馬爾庫塞曾經指出,藝術就是一種反抗,人類只有在藝術中才能將現實原則與快樂原則統一,而這又體現在“不僅在個體的層次上,而且在歷史的層次上,藝術都是最顯而易見的‘被壓抑物的回歸’”。這話也可以理解為,這種“被壓抑物的回歸”也是在群體的層次上出現的。在《哥斯拉》中,這種被壓抑物一般被解讀為日本人的核恐懼,盡管在電影中,哥斯拉從何處來,最終又到何處去并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但是當時對電影的權威解讀(包括電影里的古生物教授的分析)都認為,哥斯拉的出現正是因為人們在太平洋上不斷地進行核試驗,這使得原本沉睡于海中的,屬于侏羅紀時代的古老巨獸被喚醒,并且在喚醒的過程中,哥斯拉也遭遇了核污染,從而發生了變異。從表面來看,哥斯拉蹂躪日本人的生命,觸發日本人對核爆的痛苦記憶,這本身看似是與“快樂原則”無關的,然而實際上,“快樂”源于表達的自由。
根據馬爾庫塞在《審美之維》中的理論,電影來源于現實,但是又可以超越現實,人類的潛能正是在包括電影在內的藝術中得到解放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美國對日本實行了長期的單獨占領與全方位的管制,盡管由于美國后來因共產主義的威脅,加上日本特殊的戰略位置,而將日本作為其在遠東的盟友,然而美日之間的關系并不是完全平等的。作為戰敗的一方,日本人無法明確地在藝術創作之中表達對美國統治以及美國投下兩顆原子彈的不滿,對于美國的愛恨交織就成為日本社會一種普遍的“被壓抑物”,而《哥斯拉》的出現則意味著這種被壓抑物以另一種隱晦的方式實現了回歸,電影為人們隱藏于內心深處的族群式話語提供了一個宣泄的渠道。盡管《哥斯拉》盡可能地以科幻、恐怖類型片的方式模糊其中對現實社會的影射,但電影在美國上映時依然被迫剪去了諸多情節。如當人們在四散奔逃之際,有人哀嘆道:“好不容易在長崎撿了條命,可是……”又如居民被強制疏散時,其方式完全是戰時式的。從這些被刪去的橋段不難發現,哥斯拉與戰爭、長崎核爆的概念是緊密的,在電影中普通日本民眾并沒有因為二戰的結束而獲得平和安定的生活,美國終結了日本的戰爭之旅,但是核爆的后遺癥又使他們陷入了類似戰爭的境地之中。這樣帶有明顯抱怨意味的鏡頭不得不在面對美國觀眾時刪去,可見當時這一族群式話語的禁忌程度。
二、《哥斯拉》與族群式恐懼話語
《哥斯拉》表現的境況是超現實的,但是其中蘊含的族群式話語卻是符合日本當代現實的。
(一)孤島恐懼
日本是一個四面環海的島國,這是其民眾某種集體無意識恐懼的來源,正是在這種恐懼的支配之下,日本在19世紀與20世紀中葉不斷進行對外擴張,渴望將大陸劃進自己的統治范圍。誘使日本國民這種恐懼感的一方面是日本本土內資源并不豐富,而更重要的一方面則是島內陸上以及沿海海底的大量處于活躍狀態的火山常常導致日本地震頻發,這也使得日本人無論男女老幼都有著深重的災難意識。在電影中,調查人員去到受災村莊時,當地的老村民講述了吞吃魚蝦的怪物“哥斯拉”的傳說,并讓村民在篝火旁表演了有關哥斯拉的傳統歌舞,這就表明當地人對海中怪物的恐懼是根深蒂固的,以至于已經圍繞哥斯拉形成了一套話語。而除了民眾靠海吃海以外,努力發展海上力量則成為日本高層在數十年中堅持的國策之一,強大的海軍成為日本人全民安全感的來源之一,而自中日甲午戰爭直至與美國的太平洋戰爭,舊日本海軍也確實顯示出較高素質,為日本人不斷獲取實際的戰爭利益與虛幻的民族自豪感。而在二戰之后,舊日本海軍被徹底摧毀,日本僅能保留一點微弱的海上自衛力量。在《哥斯拉》中,哥斯拉的入侵也是由海上先開始的。先是貨輪“榮光丸”號神奇地失蹤,隨后“備后丸”也不見蹤影,而派出去進行救援的船也與陸地失去了聯系。貨舶航線被迫終止,之后漁船也漸漸無法在海上捕到魚,日本陷入孤立中。電報、海難救援、對火山噴發的懷疑等都是孤島恐懼的體現。
(二)核爆恐懼與殖民恐懼
哥斯拉這一意象代表了日本舉國的核爆恐懼,這一點基本上是公認的。哥斯拉在電影中被明確交代是因為核爆引來的,專家在它身邊的沙子中提取到了大量的鍶,甚至核爆還重新復活了已經滅絕兩百萬年的三葉蟲,而哥斯拉嘴中噴射的具有殺傷力的物質也有核輻射。一時間民眾再一次感覺到,核輻射的陰影原來始終籠罩在人們的頭上。
盡管主流觀點認為,美國在日本廣島、長崎投放的原子彈促使日本盡早投降,加速了二戰結束的進程,也使日本人民能早日從戰爭的旋渦中解脫出來。但是原子彈在客觀上的破壞性卻是不容置疑的,而相對于發起戰爭的軍國主義者而言,承受這一點的更多的是更為無辜的日本民眾。而在《哥斯拉》中,民眾這一群體也無數次被強調。如在一開始漁船失事時,搜救部門外圍聚著大量心急如焚的民眾;而當政府部門召開聽證會,研究要不要對群眾保密時,又是代表民眾的女記者強烈要求公開哥斯拉真相,甚至為此不惜罵人;信息公開后核污染怪獸很快成為公車上人們的談資;當專家們去進行田野調查時,群眾也是緊緊跟隨著專家,隨時準備與專家交流意見。在美國翻拍的《哥斯拉》中,民眾是一個面貌模糊的群體。一是美國電影更為強調個人英雄主義的審美原則,在災難之中慌亂地、無目的地逃竄的民眾只是主人公的背景,映襯著主人公過人的才智或道德。另一點則是由于哥斯拉在日本語境中與核爆掛鉤,民眾作為核爆的主要受害者,也就成為推動情節的重要角色。
在電影的最后,三根教授指出,哥斯拉并不會只有這一只,只要人類還在繼續進行核試驗,新的哥斯拉還會產生,并且下次哥斯拉出現的時候很可能就不是在日本,而是在其他地方。換言之,日本并不是核試驗、核戰爭的唯一受害者,為核爆買單的應該是全體人類。這也是日本的族群式話語之一。作為世界上唯一一個在戰爭中遭受了核彈襲擊的國家,日本人認為自己是最有資格來警示人們不要濫用核武器的。尤其三根本人是一個科學家,由這一角色來表達這一話語是恰如其分的。三根清楚地看到,科學研究原本應該是用來保障人類生存的安全,提升人類發展的質量的,然而一旦科研走過了界限,如日益泛濫的核試驗、美蘇陣營之間的軍備競賽等,科學研究就有可能站在人類生存的對立面。
而與核爆恐懼緊密相連的便是殖民恐懼。在日本遭受了兩顆原子彈的侵襲后,投放原子彈的美國接管了日本社會的一切,開始大刀闊斧地對日本進行改造,這種強制性的改造也構成了日本人對被殖民產生了擔憂。對日本民眾有著壓倒性優勢的哥斯拉在這種語境下成為強悍的、耀武揚威的美國大兵的化身。因此,在《哥斯拉》中,無論是夜間哥斯拉在狂風暴雨中對村莊的摧毀,抑或是白天出現在山頭上,以及在歌舞升平的游輪旁邊的海面突然冒起,電影中出現了永遠驚慌失措的群像。這里表達的是日本社會對美國(西方)統治下的一種群體性的恐懼。
(三)南海“玉碎”恐懼
哥斯拉除象征美軍以外,一般還被認為是在南海“玉碎”的日本士兵。這一觀點四方田犬彥在他的《日本電影與戰后的神話》中解釋得較為清晰:在日本的傳統神話中,南海本來就是作為一個能引發人恐懼感和向往之情的異域空間存在的。而在日本現代化之后,就開始了對南海的征服,企圖一直攻打至澳大利亞。面對美軍在太平洋的強大力量,大批日本士兵戰死于遠離本土的塞班、帕勞等地,以至于當時的民俗學家反對出征南海,因為這會使士兵的靈魂無法順利歸家。而電影中,哥斯拉正是由東京灣登陸,破壞了新橋、銀座等地后進入了隅田川,在穿越皇宮之后又消失在了東京灣中。這也被認為是死于異地他鄉的士兵們的靈魂對拋棄他們的天皇的一種抱怨,而裕仁天皇恰恰便是專業研究海洋生物的。這些為天皇而“玉碎”的士兵與哥斯拉一樣,既有破壞力,又是戰爭的受害者。而在《哥斯拉》拍攝的年代,日本已經走上了民主化、繁榮化的復蘇道路,戰爭、死者等都是人們不愿意回首的恐懼事物,一旦哥斯拉被與南海死亡士兵聯系起來,哥斯拉帶給人們的壓抑感便更加強烈。
三、《哥斯拉》對族群式話語的超越
《哥斯拉》的意義并不僅僅在于其借由哥斯拉這一怪獸為載體,對當時日本人的心態進行了巧妙的表達,還在于它能夠對族群式話語有所超越,即激發人們對恐懼的回憶,訴說人們痛苦的記憶后,又沒有止步于呻吟和憂傷,而是積極地化解這種恐懼,激勵人們戰勝痛苦,并反思戰爭的危害。《哥斯拉》最后能夠得到國際社會的共同認可,與它所站的這一高度是密不可分的。
在《哥斯拉》中,日本并沒有得到外界的有效援助,日本人以一種“自救”的方式完成了救贖。蘆澤博士發明了威力強大的“水中氧破壞劑”,這一研究成果只要投入一小片進入東京灣,就能使整個東京灣變為墓地。而蘆澤本人對二戰心有余悸,正是戰爭帶來的身心創傷使他與三根之女惠美子鴛盟難諧,他清醒地意識到水中氧破壞劑雖然能夠殺死哥斯拉,但是也能夠成為繼哥斯拉之后的另一人類災難,一旦水中氧破壞劑落入別有用心的戰爭狂人之手,世界便有可能毀于一旦。蘆澤與三根形成了一組對立。三根作為古生物學家,并不愿意人類殺死哥斯拉。而蘆澤則決定從人類的福祉出發消滅哥斯拉。最終蘆澤在深海投放了水中氧破壞劑,并主動割斷上岸的繩子,用自己的死使水中氧破壞劑徹底地消失在這個世界上。此時,哥斯拉作為喻體,其象征的本體出現的變化。水中氧破壞劑成為核武的代表,而曾經到處殺戮、破壞、侵略的哥斯拉則象征了舊日本。三根對于哥斯拉的憐惜,代表了當時部分日本人(尤其是老一輩日本人)對曾經輝煌一時的舊日本帝國的懷念以及對戰敗的不甘,而這種思想絕不是個別的,它也是一種隱性的族群話語,而蘆澤則能夠超越這種話語,表達徹底摧毀舊日本的決心。拋開這一設定的時代性和地域性,這種“人類為戰勝破壞力強的A而發明了破壞力更強、更難以控制的B”的敘事套路由于具有戲劇性,后來也為美國電影廣為運用。
在日本恐怖電影《哥斯拉》中,怪獸哥斯拉是一個承擔多重譬喻的喻體,它由表及里地引發著日本人的恐懼感,并為與這種恐懼感有關的日本族群式話語代言,表達著日本人對社群利益的思考。電影這種在制造矛盾沖突上的深刻性,使得《哥斯拉》成為一部經典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