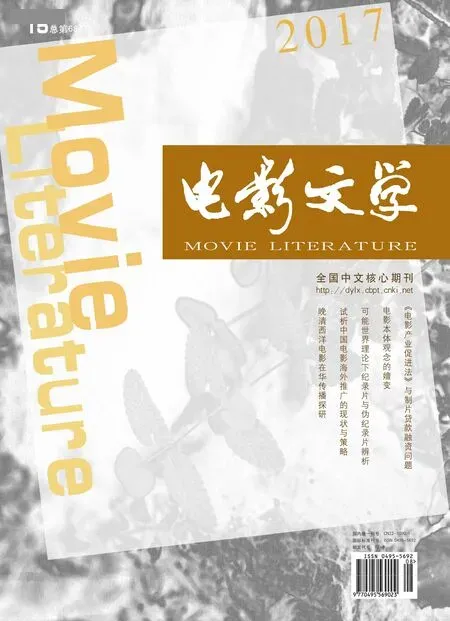《戴珍珠耳環的少女》維米爾的筆色情愫
牟音昊
(大連大學美術學院,遼寧 大連 116622)
在第76屆奧斯卡獎的評選過程中,英國導演彼得·韋伯(Peter Webber)創作的影片《戴珍珠耳環的少女》榮獲3項提名(最佳攝影、最佳服裝設計、最佳美術指導)。在《戴珍珠耳環的少女》這幅畫作名垂藝術史300年之后,韋伯又將這幅靜止的畫作以古典主義美學的再現方式進行了由視覺藝術語言向視聽藝術語言的二次轉換,再次確立了其在電影史上的不朽豐碑。在西方繪畫史中,荷蘭畫家維米爾所創作的《戴珍珠耳環的少女》被譽為“北方的蒙娜麗莎”。彼得·韋伯以《戴珍珠耳環的少女》這幅作品為引線,重新將維米爾這位17世紀荷蘭“隱士畫家”的情感生活與“北方蒙娜麗莎”的纏綿身世展示給當代的藝術觀眾。
一、彼得·韋伯的《戴珍珠耳環的少女》
韋伯的影片《戴珍珠耳環的少女》,其劇本源自美國女作家崔西·雪佛蘭所創作的長篇小說《戴珍珠耳環的少女》。影片主人公葛麗葉是畫家的女兒,父親的意外失明使得家境日漸艱難。年少的葛麗葉不得不擔起養家的重任,于是她來到畫家維米爾家里做幫傭。維米爾婚后仍和岳母同住,表面上看這是個穩定而富有的家庭,家中的陳設、排場以及生活習慣都顯得高貴典雅。但在這富貴奢華的外表下卻是不和諧的家庭氛圍。懷孕的妻子虛榮而淺薄,完全不能理解自己丈夫的繪畫藝術,甚至不愿踏進他的畫室。主持家務的岳母吝嗇而又刻薄,在這樣一個由女人掌管一切的家庭里,維米爾的生活更像是一個陌生的房客,整日郁郁寡歡。可是這個家庭全部的經濟來源都是由他的繪畫作品換來的,為維系一家人體面的生活,維米爾只能服從一個貪婪而又自大的贊助人的擺布,創作一些迎合他人興趣愛好的畫作。
葛麗葉的幫傭生活并不順利,每日辛勤地勞作換來的卻是不公的對待,還經常遭到斥責,連家中的幾個孩子都會隨意欺負她。為了生活,葛麗葉默默地忍受著這一切。或許是得到父親的遺傳,她被維米爾的繪畫藝術深深地吸引。在安靜的畫室里,葛麗葉專注于維米爾的每一幅畫作。為了不引起女主人的猜疑,她寧可在凌晨起床,為維米爾調制繪畫顏料。隨著兩個人接觸時間的增多,維米爾發現了葛麗葉的藝術天賦,她能夠讀懂自己畫中所表達的含義,不像妻子那樣對繪畫一竅不通。從此葛麗葉走進了維米爾的藝術世界,兩個人的情感世界也發生了微妙的變化。由于以往有過出軌的經歷,妻子神經質般的疑神疑鬼,使得維米爾和葛麗葉之間的感情只能是謹慎而壓抑,不越雷池一步。
與此同時,贊助人也發現了美貌的葛麗葉,并對她圖謀不軌。為了達到目的,他資助維米爾為葛麗葉創作一幅肖像畫,這一次,維米爾可以名正言順地為葛麗葉畫像了。而葛麗葉深知自己永遠不能真正擁有這個讓她心動的男人,于是,她戴上了美麗的珍珠耳環。在維米爾的畫布前回眸凝視,就這樣成就了一幅傳世名畫——《戴珍珠耳環的少女》。
沒過多久,維米爾的妻子覺察到了二人之間的感情變化,她在畫室里歇斯底里地大哭大鬧。由于社會地位的懸殊,葛麗葉只能選擇默默地離開。她懷著無限的遺憾回到家中,最終嫁給了屠戶的兒子。
二、“小畫派”畫家被“放大”的陰郁人生
在17世紀的荷蘭,流行著一個著名的美術畫派,名為“小畫派”。小畫派名稱的由來,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理解:一為畫家的作品尺寸較小;二是所表現的內容不再是高大上的宗教和宮廷題材。1609年“尼德蘭事件”的成功,迎來了歐洲歷史上第一個,也是最富強、最先進的“荷蘭共和國”的誕生。新興資產階級誕生和宗教、宮廷勢力的瓦解,反映在藝術創作中,畫家的視線從教堂、宮廷的墻壁轉向中產階級的客廳。同大尺寸的宗教宮廷繪畫相比,內容貼近市民生活,且尺寸較小、能懸掛于家中的消費藝術品成為創作的主體。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17世紀的荷蘭,一個與市民生活息息相關的繪畫流派應運而生,即“荷蘭小畫派”。在小畫派畫家中,維米爾是極具代表性的一位出色的畫家。
坦率地說,雖然《戴珍珠耳環的少女》出自畫家維米爾之手,但是在當代人的藝術感覺中,畫作的名字同畫家的名字相比,要更加顯得聲譽隆重。維米爾出現在17世紀的荷蘭畫壇,43歲的人生時光只構成了荷蘭美術的一束火花,但是,維米爾作品不朽的影響力卻是藝術家生前所無法想象的。20世紀90年代,以描寫舊時女性自我解放、重塑自身命運為主題的美國女作家崔西·雪佛蘭被維米爾的作品所打動。她從“第二性”的視角駐足在《戴珍珠耳環的少女》這幅作品面前時,長期關注女性題材而積累的心靈感應,使她不自覺地透過少女那憂郁、清澈的雙眸感受到了作品背后那段沉寂的暗涌情愫。女作家所要了解的也是幾百年來,喜愛這幅作品的受眾群體迫切想要知道的“藝術之謎”。為此,雪佛蘭帶著無限的好奇心力求在有生之年遍覽維米爾僅存于世的35幅真跡。
1999年,長篇小說《戴珍珠耳環的少女》首版發行。雪佛蘭的這部作品一經問世,同這幅繪畫作品的成功一樣,立刻催生了一個龐大的“少女讀者群”(十幾年間被翻譯成38種語言,全球銷量超過500萬冊)。盡管人與事都有虛構元素,但是絲毫不影響讀者們的熱情。同東方的小說創作不同,西方的小說家多數不賦予作品政治使命,“因而,他(她)們無需在歷史故紙堆中探尋、考證,力求還原真實的歷史。而是注重‘神似’,憑借自己對歷史的理解和對理想等追求,游刃有余地駕馭史料,傳達出自己對未來美好生活的憧憬與暢想”[1]。雪佛蘭創作的《戴珍珠耳環的少女》,正如衛報所評價的那樣:“爭論畫中女子的身份已不重要,小說虛構這一出似有若無的情愫,才更讓人唏噓嘆息。”在讀者群中,又有一位名人被打動,他就是英國著名導演彼得·韋伯。在韋伯的精心執導下,2003年,電影《戴珍珠耳環的少女》問世,讓世人從繪畫、文學、電影三個層面認識維米爾及《戴珍珠耳環的少女》。維米爾不幸的、陰郁的感情生活與這幅畫作聯系在一起。起初,人們還在思索文學和電影中所描述的情節哪一部分是虛構的,哪一部分是真實的。但是隨著思想漸漸融入創作情境之中,人們已不想知道真實和虛構是什么關系,對這段感情的唏噓嘆息已成為一種“遺憾姻緣”的代名詞深藏于當代人的情感意識中。可以說,維米爾的陰郁人生是被當代人從自身的視角放大的,這種放大是基于作家對于繪畫的解讀、基于歷史的文學“虛構”以及影像制作的“再次重構”,這種放大的“層層重構”同原本的《戴珍珠耳環的少女》的誕生已顯得“走樣和變形”。但從另一個角度說,又是經過藝術家的努力,將一幅古典畫作背后的美麗故事以“不傳統地應用傳統”的方式納入當代人的精神生活中去,這也是當代藝術家對當代社會生活的一個貢獻。
三、“隱身畫家”的感情糾結與古典主義風格的當代視覺藝術再現
彼得·韋伯執導的電影《戴珍珠耳環的少女》獲得成功,從藝術創作的自律性來看,從內容到形式上都具有其出色的創作手法。首先,從內容上看,這幅同名畫作在美術史上的顯赫地位以及雪佛蘭在文學創作上的先期成就為這部電影提供了有利的先決條件。比起莎士比亞筆下的文學作品,維米爾的感情經歷并不算愛情史上的經典案例。但是當與《戴珍珠耳環的少女》這幅畫作聯系到一起時,便顯得格外引人注目。在整部影片的藝術處理方面,有以下幾個方面反映出彼得·韋伯的獨到之處。
首先,在畫面的整體色調處理上,古典主義繪畫的“光影技法”使用得恰到好處。整部影片韋伯借用了古典繪畫的黑白光影效果,取得了與17世紀西方繪畫相同的視覺感知力。所不同的是,一個是靜止的繪畫效果;一個是移動的影像效果。在強調繪畫本體語言的“表現主義”的印象派繪畫產生之前,為了追求對自然的再現效果,焦點透視被大量采用。同時,利用光影視效突出主體形象也是畫家為營造畫面效果而廣泛采用的處理手法。這部影片從頭至尾,畫面多呈現深暗的環境色,襯托出光亮處的主體人物,一方面使主體人物形象單純凸顯;另一方面也與影片的憂傷格調相互一致。在影片中,屠夫的兒子與葛麗葉交談時,曾對她說:“你還欠我一個微笑。”如果用這句話來形容整個影片效果,則可以說,影片似乎“欠觀眾一個微笑”。唯一讓人從沉悶中解脫出來的一個片段,即屠夫的兒子與葛麗葉在野外奔跑、嬉笑時的畫面讓人們從維米爾壓抑的婚姻生活之外,看到了年輕人天真爛漫、沒有世俗約束的美好生活。可以說,影片按照《戴珍珠耳環的少女》這幅繪畫作品所設定的視覺環境做了影片視效的處理,讓觀者真切地感受到17世紀荷蘭的社會文化環境以及誕生這部偉大作品的藝術語境。
其次,在影片的藝術語言構思方面,采用了“隱喻”的表現手法。在影片的開始部分,鏡頭下,一把廚刀切割著不同形狀、不同顏色的蔬菜。葛麗葉在廚房里切菜的場景告訴我們:這個家庭拮據的生活已瀕臨底線;此外也預示著后面的情節像不同色彩的置換一樣跌宕起伏。在情節處理上,維米爾和葛麗葉之間是一種由藝術上的共識而引發出的心靈愛慕,無須太多的語言溝通,影片更多的是用“隱喻”的方式讓受眾去體會二人的情感。而維米爾與妻子及岳母之間雖然對白較多,反倒讓人感覺到在這個勢利的家庭中,維米爾的藝術世界與妻子、岳母的現實世界之間沒有任何交會之處。維米爾讓葛麗葉站在窗前,他看到的是光從窗外折射到少女面龐的優美畫面;他讓葛麗葉細數藍天中的色彩是尋找藝術上的知音和心靈伙伴。維米爾作為一個藝術家,有超乎世俗之上的心靈世界;而妻子和岳母在與經紀人的言語交流中,用盡阿諛奉承的詞句,她們對奢飾品的偏愛,讓人看到的是現實社會貪戀世俗享受的另一面。這種反差注定了維米爾和妻子、岳母之間雖身處一室,但彼此心靈都是孤獨的。這種隔閡最終將維米爾的感情世界推向了那個善良、單純卻有著相同藝術感知力的女傭。影片中的“隱喻”手法較少表現直觀的愛,但已經讓人們看到了什么是愛情,什么是裂紋。觀眾的心靈參與已經完全領會了導演的意圖,這也是影片耐人尋味的獨到之處。
四、對影片中“真實”與“虛構”的當代美學闡釋
《戴珍珠耳環的少女》獲得奧斯卡獎的3項提名,在藝術創作方面的成功從現代解釋學的角度出發,是“文本—自身”雙方理解之上的藝術真理觀的體現。在現代解釋學看來,“藝術也是一種傳播真理的認識”逐漸被人們所接收。為此,伽達默爾認為:“游戲必將在主體的理解活動中實現其意義,觀者游戲帶來了‘整體性’。”在藝術作品傳遞給觀者的過程中,觀者對作品的“意義期待”也決定了接受的變動性和多元性。不同的觀者欣賞藝術作品,“解釋的多樣性不是主觀的多樣性,而是藝術作品可以有這樣那樣解釋的可能性。藝術作品盡管在其表現中有眾多的改變和變形,但它仍是它自身”[2]。
《戴珍珠耳環的少女》這部影片所描寫的是真實的、已成定論的歷史人物,當代藝術創作在還原歷史的同時也必然摻雜當代人的情感訴求。如克羅齊所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真實”地去虛構“真實的歷史”是以歷史為創作題材的藝術創作的重要手法。觀眾的審美既是法官,也是參與者。“觀者真理的獲得,必然要在歷史的變遷里被賦予時間維度。觀者積極參與其認同體而全面地介入審美特性,而不是穩定重復的靜態接受”[3]當代解釋學為《戴珍珠耳環的少女》的成功提供了美學理論方面的重要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