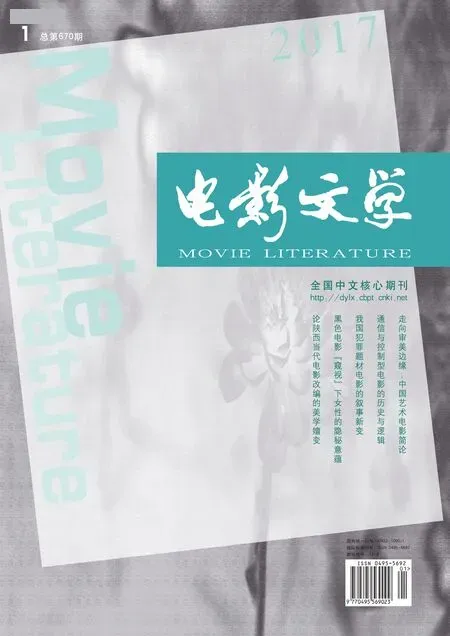我國犯罪題材電影的敘事新變
胡 輝
(華南農業大學藝術學院,廣東 廣州 510642)
犯罪題材電影抑或稱警匪片一直以來都是電影中較為穩定的類型,這種穩定不是指敘事模式上的一成不變,而是指此類電影由于所涉及的題材領域及其對“罪與罰”的直接表現,從而具有較為鮮明和固定的類型元素,并在接受領域形成了較為固定的觀影訴求。例如,對執法者和犯罪者二元對立式人物認同和解讀心理,對突破常規狀態的犯罪過程的窺視欲望,對類似“貓捉老鼠”的執法過程的游戲性期待等。同時,犯罪題材電影因其主要以人類社會兩種極端對立的“罪與罰”“破壞和懲戒”“失范和規范”等行為狀態/意識形態為表現內容,因而先天具有商業(視覺觀賞層面)和藝術(主題、風格層面)更多結合的可能性,也因此,在這一類型下,既誕生了商業化較高的警匪片,如《疤臉大盜》《小凱撒》《盜火線》等,也有昆汀·塔倫蒂諾的《低俗小說》《落水狗》、科恩兄弟的《冰血暴》《血迷宮》等藝術氣質較為濃厚的警匪片。
近十年來,內地雖然也出現過幾部比較優秀的警匪片,例如《神探亨特張》《西風烈》《硬漢》等,但由于這些電影在“風格化”和“類型化”之間的切割過于生硬,既缺乏商業類型電影的精氣,又在藝術氣質層面乏善可陳,因而落得了“藝術”不親、“市場”不愛的尷尬境地。2014年的《白日焰火》、2015年的《烈日灼心》則以其鮮明的敘事風格和對商業與藝術的巧妙縫合,取得了從商業到藝術的不俗表現并引發關注,成為近年來中國電影無法忽視的存在。
一、因循警匪片“貓捉老鼠”的游戲規則,注重故事情節的懸念鋪陳
警匪片作為類型電影的觀賞核心不外乎以下兩點:其一,警匪之間的外部對抗,如警匪追逐、槍戰和搏斗以及由此帶來的暴力內容(制暴和抗暴);其二,警匪之間的智謀對抗,主要表現為警察追索蛛絲馬跡、抽絲剝繭尋找犯罪證據,而同時犯罪者也在想方設法擺脫調查。好看的警匪片必然要在上述內外兩層之間做出關聯和牽扯,這樣才能夠完成此類電影在“視覺”和“心智”上對受眾的復合刺激。而值得一提的是,后一層面,也即“心理和心智”的較量,才是警匪片真正的魅力所在。所以,優秀的警匪片必然是“聰明的貓和聰明的老鼠”之間的游戲,否則這種玩法一定不精彩,也難以和動作片做出區分。而“心理和心智的較量”則在情節設計和接受心理上同時觸及了“懸念”之一至關重要的敘事法寶。
《烈日灼心》總體上采用了開放式懸念來設計故事走向。影片開頭就通過說書人之口提到了七年前的一樁滅門慘案,觀眾已經通過黑白畫面知曉了辛小豐、楊自道和陳比覺三人就是兇手。這種將最大懸念揭底的處理并沒有減弱懸念的作用力,因為一個最大的懸念解開后,隨之而來的則是另外一些未解之謎,如七年前殺人的兇手為什么現在依然相互聯系而且還生活在一個城市?三個年輕人為什么當年犯下那樣的案件?等等。事實上,《烈日灼心》中,鄧超飾演的協警辛小豐和段奕宏飾演的警長伊春谷之間看似不經意但實際上都步步驚心的心智較量成為全片最具看點的段落。
而《白日焰火》則采取了封閉式懸念作為開頭,影片僅僅使用一個鏡頭就完成了碎尸案的交代:一輛滿載煤塊的卡車在隧道中行駛,隨著鏡頭慢慢后移,煤堆中一只殘手赫然映入觀眾視野,戛然而止的情節已然將“懸念”以令人震驚的方式第一時間灌注給了觀眾。之后圍繞著“追兇”這一主線,影片中的各式人等都在觀眾眼前呈現出一種神秘感,如洗衣女工吳志貞的反常,洗衣店老板的鬼鬼祟祟,梁志軍的生死之謎,甚至包括兩段跟主線沒有瓜葛的分支線也誤導著觀眾的猜測,如“街邊面館里上演的面條中吃出眼球”和街道辦的走廊里出現一匹馬。而影片中穿插的兩處冰刀的特寫(第一次出現的冰刀特寫與影片開頭殘肢的出現,都是毫無征兆地突兀出現,令人驚訝)以及這部電影對于夜幕下的冬季哈爾濱帶有神秘感的光影營造,更加深著受眾心理上的懸念感。
可以說,講好一個吸引人的故事是兩部電影不約而同的追求,結合警匪片對于懸念情節的內在要求,兩部電影還都通過情節突轉的方式給觀眾帶來意外的“震驚”“驚詫”的心理感受,以此強化故事本身的戲劇張力。如兩部電影中都出現了警察在抓捕疑犯時突然發生的疑犯槍擊警察導致其犧牲的情節,瞬間超越了內地觀眾對于國產警匪片的觀影經驗,從而獲得震驚的體驗。再如《烈日灼心》結尾部分,七年前真正的殺人犯的落網所帶來的顛覆全片的劇情突轉雖然邏輯的嚴密度尚有不足,但此設計依然讓觀眾感受到了不一樣的警匪故事。上述突轉式的情節處理,讓觀眾仿佛坐上了過山車,時刻繃緊著神經,在前路未知的懸疑中感受到日常生活中感受不到的驚奇體驗。
二、在類型與反類型之間強化人格心理的深度呈現
就警匪片的類型而言,因其涉及犯罪這種直接對抗社會秩序的極端行為,因而必然會牽涉到非常態人物——罪犯的刻畫和描寫。對一般警匪片而言,定型化的人物是其類型識別的基礎,因此,在眾多經典的警匪片當中,罪犯和警察的形象更具視覺化和可識別性,換言之,人物外在的容貌、氣質、裝扮以及行為舉止等都會在很短的時間內就讓觀眾清楚地識別到人物身份、性格和歸屬。而在這兩部電影中,警察和犯罪者的塑造都強化了對人物內在人格和心理層面的呈現,使之在類型化人物的基礎上更趨向于文藝作品所追求的人性挖掘,甚至將這種心理層面的掙扎糾結與外在的斗智斗勇較為緊密地融合在一起,使得人物塑造和情節處理共同匯聚在“追兇”所營造的“懸念”氛圍下,促進了人物和情節的精彩呈現。
如《白日焰火》中刑警張自力從一出場就表現出一個不一樣的警察形象:對前妻的挽留演變為一種無賴式的騷擾, 前妻轉身時那一句“有病”似乎已經將張自力的形象降格到了近乎猥瑣了。而他在一次抓捕行動中的大意致使兩位戰友犧牲之后,則完全墜入了酒鬼痞子之流,雪夜喝醉酒倒臥在路邊、跟工廠女工公然打情罵俏,這些已經完全背離了國產警匪片受眾所認知的警察形象當然,影片對此有合理的解釋,就是戰友犧牲后張自力已經不再是警察了,但即便如此,這樣的人物依然具有反英雄的特征。與張自力反英雄形象相對應的則是吳志貞,她飽受欺辱、軟弱被動,她的美麗帶給她的不是利益而是苦難。在這部電影中,張與吳呈現更多的是基于內心層面的復雜糾結,其中牽涉罪與罰的拷問、靈與肉的糾纏、背叛與救贖的混沌等,與“追兇”的主線相映襯,這構成了該片的第二層敘事話語。如影片中兩人在午夜的冰場溜野冰、在洗衣店內送創可貼、在清晨的早點鋪吃早點,以及影片最后張自力在樓頂釋放的煙花,都細膩而鋪張地呈現出人物復雜的內在。也正是通過這樣的人物,受眾看到了罪與罰背后真實人性層面的東西,張自力和吳志貞似乎都在進行某種層面的救贖,從而使得本片由一個通俗意味的犯罪題材故事,被處理成具有藝術氣質的值得玩味的探索片。
再如《烈日灼心》中的辛小豐,由于命案在身,他一直生活在一種糾結、無奈、慌亂、神經質狀態中,靠憤怒掩飾自己的恐懼和自卑。他不斷試圖用善舉為過去贖罪,卻始終難以撫平內心存在的負罪感,于是只能每日都提心吊膽地活在煉獄中。電影中諸多細節將他內心的糾結和復雜袒露給受眾:常常用手壓滅煙頭,抓壞人時勇往直前不顧生死,眼睛永遠不敢直視警長,想辭職又放棄,希望那一天來臨但又希望真相永遠被掩蓋,等等。在他身上,受眾感受到的是負罪感的沉重和反復在希望和恐懼中的煎熬。而警長伊谷舂所遭受的拷問同樣煎熬,某種意義上而言,他需要代替法律去權衡自己的手下——已然在贖罪的“壞人”,能否將罪惡一筆勾銷。也因此,兩人的每次單獨相處,幾乎都有一種緊張壓抑感存在。雙方之間或言語、或行為、或由此透露出的心理層面的試探、猜測、疑慮等就構成了這部電影最為吸引人的東西。應該說,這部電影中所塑造的三個犯罪者都不再是常規警匪類型片中的壞人,而是帶有灰色性質的“干過壞事的好人”,這是在國產電影中長期諱言的,正如有論者所言,曹保平果斷挑破這層窗戶紙,才令影片真正具備了 “灼心”的力度。
三、以風格化的影像效果構建起真實且帶有意象性的“城市空間”
好看的電影一定不止于故事層面,電影的敘事本身就包括將包裹這個故事的時空和氛圍一同呈現。可以說,《白日焰火》《烈日灼心》這兩部電影都在影像層面體現出某些一致的痕跡,那就是試圖在類型化的商業訴求和作者化的藝術表達之間尋求一種個人風格的抒寫。因此,無論是《白日焰火》還是《烈日灼心》中都通過影像構建起真實且帶有意象性的“城市空間”,從而在烘托出一個好看故事的同時,彰顯出國產警匪片中少有的風格化的視覺效果。
《白日焰火》《烈日灼心》都是講述太陽下的罪與罰的故事,一個發生在北方,一個發生在南方,且明顯帶有地域化的特征,并將這種地域化以一種意象性的東西深深融進故事和人物之中。例如,《白日焰火》中明確無誤地指明故事發生地為中國的哈爾濱,這在國產電影中并不多見。當然,哈爾濱在國人尤其是非哈爾濱人的印象中幾乎就是寒冷的象征。這樣的意象十分適合《白日焰火》所要求的故事環境,沒有一線城市的繁華喧鬧和光怪陸離,卻有嚴寒覆蓋下的冰火交織的風情和欲望。影片通過松花江、鐵路橋以及大量水泥盒子式的蘇式老居民樓、雪夜昏黃的馬路以及兩邊的倉買、火鍋和烤串兒等有效地透露出這座城市的氣息,既充滿冰冷的神秘感,同時也帶有壓抑不住的欲望。導演將大部分的重頭戲置于夜幕下,昏暗的街頭,慘白的雪地、破敗的建筑、迷離的路燈……陰冷的氣息充斥著整個鏡頭,讓人陷入一種難以自拔的陰郁情緒中,頗具希區柯克式的懸疑氣氛。而為了應對或是強化這種城市意象,創作者通過極為簡單的紅藍綠的燈光并置處理,如理發店內紅綠對立的色光,榮榮干洗店正面的外景,不僅有霓虹燈和店內色調的對比,遠處還有紅光和藍光,以及干洗店老板的流動房車中懸掛的小彩燈等,達到了一種神秘野性而又迷離的環境效果。
而與蕭索寒冷的哈爾濱不同,《烈日灼心》中的城市雖然沒有指明為廈門,但是鏡頭中的街道、海濱和潮濕的樹林,都能夠讓觀眾明白電影中顯然是一座潮濕的“南方城市”。影片中凹凸不平的石板路鋪成的小道、隱藏在林中的別墅以及經常下雨的天氣等,都讓這部電影充滿了潮濕和陰霾。在這部電影中,看不到燈紅酒綠和霓虹閃爍,只能看到逼仄和壓抑,警長窄小的辦公室、擁擠的警隊宿舍還是陡峭的樓梯間和擁擠的菜市場,再加上多數場景呈現出的暗淡的光線,更讓這種環境有了難以逃脫的壓抑感。電影中最能代表這種環境光線的百葉窗的大量出現,不但跟廈門這座海濱城市的氣質很契合,而且由它帶來的明暗和隔斷讓空間更加局促,從而加強了警察和協警之間的戲劇關系。而與空間環境展現相呼應的則是手持攝影所帶來的晃動感以及大量變焦鏡頭呈現的人物面部特寫,都在加強著一種壓抑焦慮和不安的情緒,直逼人物內在。
值得一提的是,兩部電影中都出現了煙花綻放的情節,《白日焰火》在結尾處,而在《烈日灼心》中是大年三十楊自道載著伊谷夏在高架橋上飆車慶祝新年,這是一種難得的巧合,卻有著某些不約而同的東西,既商業又文藝,有溫暖亦有冰冷,恰如這兩部電影在國產警匪片中類聚而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