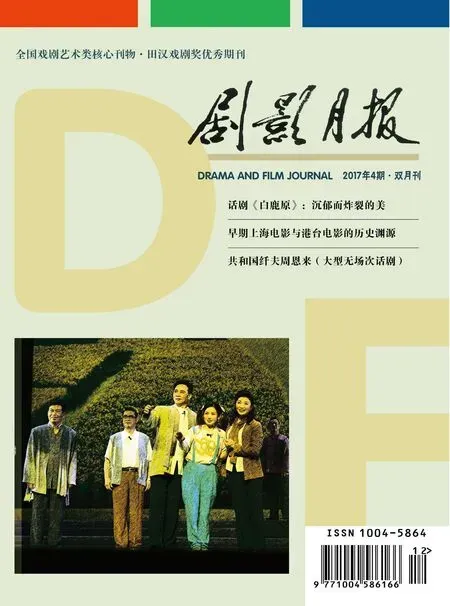金陵琴派與儒家禮樂文化
■姚曉琴 刁悅然
金陵琴派與儒家禮樂文化
■姚曉琴 刁悅然
古琴,最早在人們眼中是一件圣器,距今已有三千年的歷史,屬“八音”中的“絲”,自古就有“八音之中惟絲最密,而琴為首”(《新論.琴道》)之語。“八音”最早的記載見于《周禮.春官.大師》。而后司馬遷的《史記.五帝本紀》中提到:“詩言意,歌長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和諧,毋相奪倫,人神以和”,這時的古琴是祭祀時伴奏用的。由此可推測,古琴最初是因祭祀而被廣泛使用,從而慢慢發展興盛起來。西周時期,周公為維護王朝統治,制禮作樂,“禮樂制度”也成為了周朝帝王統治疆土子民的根本。春秋時期,禮崩樂壞,“士”階層的快速崛起,使“禮”字在世道傳承中,由祭祀的本意逐漸轉變為儒家學者的禮儀規范、處事風尚。“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論語.八佾》),儒家認為,樂可轉化為仁,進而轉化為道,及禮樂之道。
金陵,現在的南京。作為六朝古都,十朝都會,中國四大古都之一,南京在古時的地位可見一斑,從古至今文人騷客在金陵帝都都留下了足跡。追溯金陵琴學,自東吳始,可見端倪。據宋朝郭茂靜所著《樂府詩集》所載,蔡邕曾經到金陵游覽盛景,根據青溪的不同,寫出《蔡氏五弄》(《游春》《淥水》《幽居》《坐愁》《秋思》)。曾在金陵會友的“竹林七賢”之首阮籍也拜其為師跟其學琴,阮籍“夜中不能寐,坐起彈鳴琴”(《詠懷八十二首》阮籍),可見其癡琴至深。現今南京市北崗21號四十三中學內仍有其衣冠冢供后人敬仰,而阮籍早年也推崇儒家思想,志在用世。南朝皇帝也酷喜音樂,如梁武帝蕭衍著《琴要》,從上層帶動金陵琴學。由此可見,金陵作為東吳與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政治經濟娛樂的主要活動中心,對金陵琴學的發展起到了巨大推動作用。唐朝詩人李白曾七次游歷金陵,《示金陵子》中就有因琴與金陵子結為紅顏知己的描述,從而一時傳為佳話:“金陵城東誰家子,竊聽琴聲碧窗里。落葉一片天上來,隨人直渡江西水。楚歌吳語嬌不成,似能無能最有情。謝公正要東山妓,攜手林泉處處行。”唐朝詩人陸龜蒙的《送琴客之建康》:“蕙風杉露共泠泠,三峽寒泉漱玉清。君到南朝訪遺事,柳家雙鎖舊知名。”北宋王安石罷相后隱居金陵半山園,仿《胡笳十八拍》曲相贈詩人郭祥正,交為摯友。從中,我們可以看到金陵琴學的繁盛。
明朝初期,朱元璋定都南京,開創一番盛世,南京成為政治文化中心,金陵之地吸引眾多才子名士聚集,其中不乏許多琴人。朝廷招攬名家為皇家樂官,專為皇家譜曲奏樂,于是開始逐漸在此地養成風格。永樂年間,朱棣遷都北京,政治文化中心逐漸北移,但南京因已有一定時間積累沉淀,且帝都地位仍在,仍有許多琴人在此生活。代表琴家有楊掄等。楊掄,江寧人,《真傳正宗琴譜》(《太古遺音》《伯牙心法》)是他經久不衰之作,其人“為人敏而慎,謙遜少欲”(《伯牙心法.序》),奏琴具有“參差有節,抑揚有序”得“古韻之遺”(《琴旨》)的風格,在當時著名琴家黃龍山、楊表正等人的共同影響和江南水鄉的特有環境滋潤下,南京地區的琴派已然形成,在明朝中后期產生不小的影響,當時的“江派”,“江”就是“江左”,主要指現在南京,為金陵琴派的前身。
金陵古琴流派是江蘇四大古琴流派中的重要派別之一。金陵古琴底蘊深遠,由來已久,但“金陵派”一詞卻是后來才有。清代乾隆時期文人王坦的《琴旨》就有早期對金陵琴派演奏特點的描述:“金陵派之參序有節,抑揚有紀,可謂得古韻之遺。”從這句話中可以看出金陵琴派符合儒門“致中”“致和”之意。其后清代道光時期文人陳幼慈在他《琴論》中提到:“動稱宗常熟派、金陵派、松江派、中州派。或以閩派、浙派為俗,以常熟派為雅,以中州派為正。”由此可見,金陵琴派發展繁榮,在全國琴派中已占得一席之地。
古琴,聲音空淡悠遠,如詩人淺吟低唱,有超脫世人的淺雅之風。而古琴的聲音特色,西漢的桓譚所著的《新論.琴道》一文中總結:“大聲不振華而流漫,細聲不湮滅而不聞”,這點正好迎合儒家學派中所說的中庸之道的理念。故而又有“八音廣博,琴德最優”(《新論.琴道》)之說法。《禮記.中庸》有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中和,是中庸之道的主要內涵,也是儒家主要思想之一。
金陵琴派生于明朝皇家又發展于明朝皇家,集眾家之所長,演奏風格大氣端正,儒雅肅穆,莊嚴平和,盡顯皇族風范,節奏平穩,抑揚皆有章法規律可循。以《五知齋琴譜》中明確記載的金陵派代表曲目《秋塞吟》(《搔首問天》《水仙操》)為例,《秋塞吟》表現了一種別涼感慨,憂抑悲憤之意。“時莫悲于秋,地莫極于寒。高秋遠塞,飛鳥不下,走獸忘群,傷心慘目,孰有過于此哉?此蓋以傷昭君出塞之苦也”(蕭鸞《太音補遺》)。縱觀全曲,不相同的音名之間皆未超5度,多以2、3度平穩進行。曲調雖以下行居多,縱然表現荒涼戚傷之感,但并沒有大起大落波濤洶涌,總體平和,節奏穩健。
再以另一個金陵琴派代表作《漢宮秋月》為例,《真傳正宗琴譜》中明確記載此曲是描述漢代深宮女子秋夜難眠,輾轉反側,信步于庭院,見秋月凄涼,不禁凄惻傷感難抑。整曲曲風纏綿,音韻古樸雅正,意蘊憂愁深遠,雖戚戚泠泠,然未至慘慘切切,雖有幽怨卻又節制不憤怒。
另有一曲金陵派代表曲目《佩蘭》為證,此曲取屈原之《離騷》“紉秋蘭以為佩”之意,用蘭花的高潔喻自己忠貞愛國之情懷。全曲音韻醇和,前半段“曲調細而不迫,徐而抑揚”(《太還閣琴譜》),淡雅而深沉,清新而雄厚,從容淡定,有君子之不染塵世之傲。后半段多用滑音又夾雜重音,表現大義凜然、榮辱不驚的氣節。末尾音節悠揚、縹緲,又回歸了遠遁江湖,泛舟湖上的隱者風格。聽罷全曲著實令人欲罷不能,久聞蘭香。
這就是金陵琴派的特色,正符合了儒家之推崇“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的雅樂的理念。現在看來,儒家的禮樂思想是一種對人們的高度理性下秩序的規范,也是統治者高度人性化的人文關懷。金陵古琴之道,正好符合了儒家禮樂之道、帝王治世思想,是以備受推崇。
其實,金陵琴派不論從演奏理念,還是音樂特色,都與儒家之道、治世之道相符合并非偶然。地域文化因素也是原因之一。金陵琴派屬吳文化范疇,地處江南,有良好的經濟基礎和學術文化氛圍。金陵,是一座有著豐富歷史背景和文化底蘊的城市,虎踞龍盤,有著與生俱來的王者之氣。多方文化的結合是這座城市所特有的包含通融的氣度,從而醞釀出金陵琴派的獨特風格,使之能在“聲”與“韻”,“吊古”與“創新”,“雅”與“俗”,“剛”與“柔”等矛盾中尋找到平衡點,這也正好對應了儒家的入世哲學之說,起修生養性,樂性倫清的作用。
禮樂思想不單單是人性,更是對政治的促進,而金陵琴家們正是用琴音來達到“致中和”這個儒家和諧思想追求的理想境界。這要求人與社會,人與自然都能達到融洽和諧的關系,正如金陵琴音,平和中庸,既清高俊逸,又堅穩平實,謙遜內斂,以“中和”的態度保持和諧。金陵琴音乃真正的“德”音,提倡誠信仁愛,寬容謙和。溯古至今,在這金陵王城之中,先賢大儒們以琴論調,思民間疾苦,論治世之禮,以一顆琴心,審萬民之事。不以高而傲,不因低而悲,不憑喜而狂,不借悲而傷,只有像此這般王氣之音才能與儒門之禮、帝王之說相契合。正如儒家在處理人際或世間萬物關系方面,力圖追求事物變化的多樣性,滲透著儒家文化以和為上,以和為貴的禮樂思想。
(作者單位:南京師范大學音樂學院。本文系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江蘇古琴流派研究》系列論文之一)
[1]彭定求等《全唐詩》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431頁。
[2]王蓉《唐詩中的古琴藝術研究》2010年。
[3]明.楊掄《伯牙心法.序》琴曲集成第七冊,中華書局,1981年版。
[4]清.王坦《琴旨》,四部全書經部樂類,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5]清.王坦《琴旨》,四部全書經部樂類,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引用陳麗娜《古琴“中州琴派”略考》,《音樂創作》2012年第五期。
[6]譚桓《新論.琴道》,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7]譚桓《新論.琴道》,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8]王菲古琴_新浪博客《我的微語錄周記》2011.5.2—201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