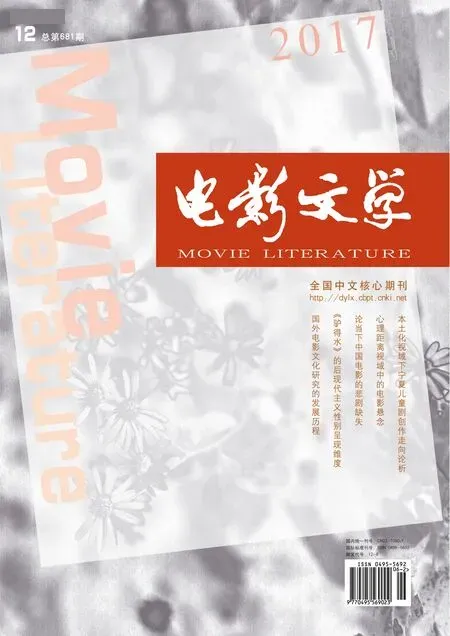國外電影文化研究的發(fā)展歷程
王丙珍
(牡丹江師范學(xué)院文學(xué)院,黑龍江 牡丹江 157011;黑龍江大學(xué)文學(xué)院,黑龍江 哈爾濱 150080)
作為一種藝術(shù)性、技術(shù)性與工業(yè)性現(xiàn)象的電影與全球化緊密關(guān)聯(lián),電影跨越了國家、民族、階級、性別與語言的邊界,達到了人類對話、思想及文化的高度,一方面,以美國好萊塢為軸心的電影文化占據(jù)著話語權(quán);另一方面,所有國家都希望通過電影承載與傳播本民族文化,建構(gòu)能夠被人類普遍認同的核心文化價值觀。可見,電影作為一種大眾媒介,應(yīng)當(dāng)成為傳播與弘揚人類多元文化的途徑。
一、電影即文化:全球化時代的文化霸權(quán)與視覺狂歡
電影將文化、藝術(shù)、政治與歷史納入其體系范疇之內(nèi)。電影是一種屬于大眾的文化藝術(shù),因此,電影是最具有全球性的一種文化形式,成為文化系統(tǒng)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列寧有句名言:‘在所有的藝術(shù)中,電影對于我們是最重要的’。”[1]文化概念的內(nèi)涵與外延具有不確定性,就電影而言,“文化是由表達和交流、表現(xiàn)、影像、聲音和故事構(gòu)成的。它既是地區(qū)性,又是全球性的,它不斷地因個人和組織的需要而流行和變化”[2]。羅伯特·考克爾的這個電影文化定義表明電影是國家、世界與宇宙相互聯(lián)系的關(guān)系總和,電影與政治、法律、宗教、文學(xué)、藝術(shù)一樣,是文化有機體的組織。
電影作為文化呈現(xiàn)出無處不在的文化霸權(quán),如美國電影《逃離德黑蘭》對伊朗文化及其宗教文化的解讀,美國電影《美國往事》對中國人開鴉片煙店及中國人形象的表現(xiàn)等。此外,作為視覺狂歡的電影又呈現(xiàn)出文化的地域性、民族性、大眾性與多元性,進而以跨文化認同的態(tài)度達成文化間的平等對話,尋求各種電影因素的融合,注重電影內(nèi)容和形式的開放性,最終引向人性和文化的共性層面。因此,電影既不要美化,也不要丑化民族文化,而是要“文”化之。
當(dāng)下,電影文化關(guān)聯(lián)著對話、認同、想象、情感與記憶。電影文化的研究內(nèi)容包括主體、客體和本體。電影文化研究按其歷史發(fā)展分為古典主義、現(xiàn)代主義、后現(xiàn)代主義、后殖民主義與全球化。“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全球化與社會經(jīng)濟維度的聯(lián)系越來越密切,導(dǎo)致電影研究學(xué)者開始批判性地考慮好萊塢在海外市場的文化霸權(quán)和經(jīng)濟宰制,因此世界電影就可以被看作是所謂‘全球性好萊塢’這一新帝國的復(fù)雜結(jié)構(gòu)的一部分了。”[3]這實質(zhì)上只強調(diào)西方文化的共通性,卻忽略東方文化的異質(zhì)存在。因此,第三世界國家本土文化策略即為地區(qū)性審美文化建構(gòu)與文化想象的民族主義。“因為媒體不僅是一個統(tǒng)一的網(wǎng)絡(luò)實體,也是一個把世界拴在一起的非常有效的方式。”[4]因此,每一個國家或民族的電影導(dǎo)演都應(yīng)有文化自覺與文化責(zé)任,對電影的民族化與全球化有所擔(dān)當(dāng)。起碼,在文化殖民即后殖民語境中,發(fā)展中國家的導(dǎo)演不要主動地迎合發(fā)達國家或民族對發(fā)展中國家或民族的異樣審美趣味,尤其是不要為了揚名或評獎而主動站在被殖民的立場。
二、國外電影文化研究述評
國外電影創(chuàng)作、實踐與評論幾乎是同時開始的。電影文化研究除以電影作品為對象外,還與社會思潮和人文學(xué)術(shù)思想相關(guān)聯(lián)。電影是19世紀(jì)末最偉大的科學(xué)與藝術(shù)成就,是世界文化史上最重要的文化現(xiàn)象,電影事業(yè)發(fā)展的過程也是電影藝術(shù)身份、功能和特點逐漸被認識和明確的過程。
(一)20世紀(jì)初至30年代,以意、匈為中心的早期本體論時期
早期的本體論批評集中于電影的視聽語言。1911年,意大利詩人和電影先驅(qū)喬托·卡努杜的《第七藝術(shù)宣言》宣稱電影是“光與影的交響樂”。法國埃米爾·克萊斯的《電影機的歷史》(1912)是世界上第一部電影史。美國中西部詩人瓦契爾·林賽的《活動畫面的藝術(shù)》(1915)將“活動的雕塑”作為電影的基本特征。相關(guān)的著作還有德國心理學(xué)家雨果·明斯特伯格的《電影:一次心理學(xué)研究》(1916)、匈牙利貝拉·巴拉茲的《可見的人類:論電影文化》(1924)、《電影的精神》(1930)及《電影文化》(1945)。事實上,巴拉茲在《電影文化》中提出的“電影文化”并沒有引起關(guān)注與接受,因為其俄譯本為《電影藝術(shù)》、英譯本為《電影理論》、中譯本與意大利譯本為《電影美學(xué)》。
(二)20世紀(jì)40至60年代,以德、法為中心的轉(zhuǎn)型期與成熟期
20世紀(jì)40年代,隨著電影藝術(shù)的發(fā)展,電影理論研究進入轉(zhuǎn)型期。40年代中后期,電影作為社會文化現(xiàn)象、藝術(shù)現(xiàn)象以及大眾傳播媒介加以研究的電影學(xué)誕生。法國的G·柯亨-西特辨析了法語的電影詞匯。1944年,德國“紀(jì)錄”派代表人物齊格弗里德·克拉考爾的《從卡利加里到希特勒——德國電影心理史》與巴贊的理論構(gòu)成二戰(zhàn)后“寫實主義”的核心知識體系,其《電影的本性——物質(zhì)現(xiàn)實的復(fù)原》(1960)闡述了“電影化”概念。克拉考爾將電影理論從電影美學(xué)推向電影哲學(xué),表明電影文化已經(jīng)擺脫了現(xiàn)實的功利要求,走向絕對的學(xué)術(shù)性和思辨性。另外,1945年,法國莫里斯·梅洛-龐蒂的《電影與新型心理學(xué)》是電影心理學(xué)的重要論述。
20世紀(jì)五六十年代是現(xiàn)代電影文化的成熟期,電影批評不再附屬于創(chuàng)作與電影工業(yè),形成了獨立的哲學(xué)思想與文化領(lǐng)域。法國的電影文化研究成績斐然,主要包括亨利·阿杰爾的《電影美學(xué)概論》(1957)、安德烈·巴贊的《電影是什么?》(1961)、讓·米特里的《電影心理學(xué)與美學(xué)》(1963—1965)、弗朗索瓦·特呂弗的《希區(qū)柯克與特呂弗對話錄》(1967)、米特里的《問題中的符號學(xué)》(1987)等。值得關(guān)注的是克里斯蒂安·麥茨的《電影語言——電影符號學(xué)導(dǎo)論》(1968)、《想象的能指:精神分析與電影》(1977)與《無人稱表述》(1991)。此外,60年代末,英國《新左派評論》采取以政治為導(dǎo)向的法國結(jié)構(gòu)主義立場,奠定了好萊塢類型電影與結(jié)構(gòu)作者論的中心地位,影響了70年代中期英美電影理論的走向。
(三)20世紀(jì)70至90年代,以法、美為中心的文化政治研究發(fā)展階段
電影文化研究反映了人文科學(xué)對電影藝術(shù)的影響。1973年,世界上第一個電影史學(xué)家喬治·薩杜爾的《電影通史》構(gòu)建了宏大的電影歷史觀。蘇聯(lián)謝·金茲堡的《電影理論概述》(1974)研究了觀眾心理。法國羅伯特·布萊松的《關(guān)于電影機的筆記》(1975)反思了電影技術(shù)及其哲學(xué)與美學(xué)的含義。
20世紀(jì)80年代,以文化、社會、政治作為批評的切入點,電影成為20世紀(jì)語言學(xué)轉(zhuǎn)向之后進入文化思潮的路徑。在法國,有影響的論著包括吉爾·德勒茲的《電影》(1983—1985)、米歇爾·科林的《語言、電影、話語》(1985)、米歇爾·瓊的《電影的聲音》(1985)、讓·鮑德里亞的《假象與假象化》(1985)、帕斯卡爾·鮑尼澤爾的《電影與繪畫》(1986)、喬治·迪-于貝爾曼的《在影像前》(1990)、雅克·奧蒙的《影像》(1990)等。
女性主義電影文化理論借助社會學(xué)、心理學(xué)、文化研究深刻地闡釋了電影中的性別問題。美國的勞拉·穆爾維在《銀幕》雜志中發(fā)表的《視覺快感和敘事性電影》(1975)、《視覺快感和敘事性電影的反思》(1981)是重要文獻。進入80年代后,女性主義電影理論在美國逐步走向成熟,集中于對性別差異的比較研究,包括安·卡普蘭的《女性主義與電影》(1983)、斯圖爾特·M·卡明斯基等的《美國電視類型》(1985)、康斯坦斯·彭利的《女性主義與電影理論》(1988)等。再者, 英國桑德蘭大學(xué)教授蘇·索恩哈姆的《女性主義者電影理論:讀本》(1999)將電影作為女權(quán)主義文化、表現(xiàn)形式及其身份的斗爭之地。
(四)21世紀(jì)以來,以英、美為中心的多元文化批評階段
此時,法國的理論優(yōu)勢被英、美取代,從女性主義電影理論到受西方馬克思主義與精神分析理論影響的意識形態(tài)批評,從受新歷史主義與后現(xiàn)代主義影響的電影敘事學(xué)理論到文化研究,電影文化研究進入多媒體、新技術(shù)的“后電影時代”。
英國哲學(xué)家史蒂芬·馬爾霍爾的《論電影:在行動中思考》(2002)、菲利普·辛普森、安德魯·厄特森與卡倫·謝潑德森的《電影理論:媒體與文化研究的批評概念》(2003—2004)、珍妮·邁克白的《女性主義電影研究:書寫電影中的女性》(2004)、羅納德·伯根的《目擊者:電影》(2006)、斯泰西·帕克斯的《獨立電影分配的知情者導(dǎo)論》(2007)、帕梅拉·格雷斯的《宗教電影:基督教教義與圣徒文學(xué)》(2009)、《電影書》(2011)等建構(gòu)了電影在文化層面的政治、文化、性別、經(jīng)濟與宗教功能。
美國的許多宗教學(xué)家、哲學(xué)家、音樂家、作家轉(zhuǎn)向電影文化研究,如達納學(xué)院宗教系教授約翰·萊登的《電影作為宗教:神話、道德與儀式》(2003); 哲學(xué)家托馬斯·馬藤貝格與安格拉·柯倫的《電影哲學(xué):文本與讀本導(dǎo)論》(2005)、 保羅·戈姆利的《新暴力電影:當(dāng)代好萊塢電影中的種族與影響》(2005)、 丹尼爾·富蘭克林的《政治與電影:美國電影的政治文化》(2006)、 哈里·本肖夫與肖恩·格里芬的《美國電影:電影里表現(xiàn)的種族、階級、性別與性》(2009)、 里查德·富默頓與戴安·杰斯科的《通過電影介紹哲學(xué):關(guān)鍵文本、討論和電影選萃》(2009)。此外,維森學(xué)院音樂教授尼爾·威廉姆·勒內(nèi)的《恐怖電影中的音樂:聆聽恐懼》(2010)與自由作家馬麗·斯奈德的《分析文學(xué)到電影的改編:一個小說家的探索和指南》(2011)分別闡述了電影作為音樂與文學(xué)的媒介作用。
三、存在的不足及發(fā)展趨勢
縱觀國外電影文化研究史,其存在三方面問題:第一,電影學(xué)的學(xué)科研究范疇不是特別清晰,不利于學(xué)科獨立發(fā)展,反而成為其他學(xué)科的附庸,“‘電影學(xué)’是從各學(xué)科角度對電影文化和電影藝術(shù)進行的跨學(xué)科研究”[5]。第二,國外電影文化研究受宗教、哲學(xué)、歷史、文學(xué)與教育影響,追求學(xué)科理論的方法性、系統(tǒng)性、科學(xué)性、普遍性與形式性,類型與商業(yè)電影文化研究成果豐厚。第三,英國與美國占據(jù)著文化霸權(quán)地位,強調(diào)美國好萊塢標(biāo)準(zhǔn)敘事。“一旦本真性不再適用于藝術(shù)生產(chǎn),藝術(shù)的整個功能就被翻轉(zhuǎn)過來。它不再建立在儀式的基礎(chǔ)上,而是建立在另一種實踐的基礎(chǔ)上,這種實踐便是政治。”[6]
國外電影文化研究的發(fā)展趨勢為:首先,關(guān)注后殖民批評、生態(tài)美學(xué)、女性主義批評、地緣政治學(xué)等多元文化研究領(lǐng)域;其次,全球化時代,電影文化研究將向生態(tài)文化、全球化美學(xué)與藝術(shù)、民族文化與地域文化方向延伸;再次,將電影理論提升到宗教與哲學(xué)的高度,關(guān)注個人的存在與情感問題,力圖成為新一輪的“文化拯救者”;最后,國外學(xué)者不僅關(guān)注國家的政治權(quán)力,而且關(guān)注傳媒的政治話語與霸權(quán),將電影作為文化殖民的最佳工具。因此,國外電影文化研究史凸顯了本土性與民族性問題,電影如何樹立民族品性并跟上文化全球化思潮,這是一個值得思考與亟待解決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