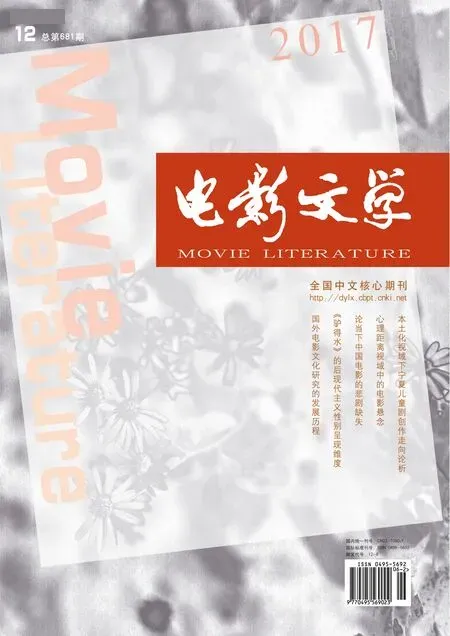論中國影壇的“戲”“影”關系
付 佳 (鄭州升達經貿管理學院,河南 鄭州 450000)
一、中國電影的影戲傳統
中國電影在產生之初經常被稱為“影戲”,顧名思義,“影戲”這一名字直接反映了中國電影的產生與中國傳統戲劇具有深刻的關聯。“影戲”這一名詞可以分開進行釋義,所謂“影”主要是指電影中故事的表現形式;而“戲”就是指電影中的故事本身。[1]在中國電影產生發展的早期階段,許多文藝評論者都將電影與戲劇進行類比,甚至有人認為電影與戲劇具有相同的表現形式及價值,是戲劇分化出的另外一種藝術形式。可以說,中國影壇的“影戲”傳統不僅體現在中國電影產生之初,還對中國電影的發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在中國電影產生發展之初,電影創作的取材還十分具有局限性,所以中國的傳統戲劇便成為早期中國電影創作的重要給養,無論是在敘事題材,還是在結構布局、人物造型等方面,都具有濃重的戲劇色彩。鄭正秋、張石川等人在電影創作中便注重運用戲劇沖突,如20世紀早期的影片《難夫難妻》《孤兒救祖記》等便將戲劇沖突恰當地運用到了影片曲折的故事情節之中,并通過影片中的故事情節和人物塑造傳遞了對于社會現象的諷刺之情及對于民眾的教化之意。正因如此,包括鄭正秋、張石川在內的許多中國早期電影人的電影創作被評論者認為在中國影壇確立了“影戲”的基調。[2]在中國電影開始獨立發展之后的數十年間,戲曲片及自傳統戲劇中挖掘創作元素的影片不勝枚舉,其中不僅有將傳統戲劇直接搬上銀幕的電影,還有講述戲劇故事或由戲劇藝人直接參演的影片。20世紀40年代,中國第二代導演中的代表人物費穆執導拍攝了影片《生死恨》,這部影片由戲劇大家梅蘭芳主演,講述梅蘭芳與京劇之間的不解之緣。這部影片無論是在題材選擇,還是在色彩運用及布景設置等方面,都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京劇藝術的特色。在《生死恨》之后,以個體為視角講述戲劇故事的影片也逐漸增多,如《霸王別姬》《舞臺姐妹》《人·鬼·情》等。在講述戲劇名角的記錄性質的電影之外,中國影壇還逐漸出現了一些反映戲劇發展命運的影片。隨著時代的發展,藝術形式逐漸豐富,傳統的戲劇藝術不斷受到挑戰,在《心香》《找樂》等影片中,我們能夠看到這種對于戲劇發展及戲劇藝術家命運變化的故事。此外,中國影壇還涌現出許多由經典傳統戲劇改編而成的影片,如《梁山伯與祝英臺》《紅樓夢》《天仙配》《齊王求將》等。
提到中國影壇上的“戲”“影”關系不可繞過的還有特定歷史時期涌現出的樣板戲。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大部分類型影片的發展處于停滯狀態,僅有樣板戲不斷發展,《智取威虎山》《紅燈記》《紅色娘子軍》《沙家浜》等八部著名樣板戲雖然在一定程度上過分夸大了藝術的政治教化意義,卻在中國電影發展歷程中凸顯了戲劇的重要價值。[3]在“文革”之后,中國迎來了改革開放的浪潮,許多西方現代化的電影創作觀念及技巧被中國電影人所接納,在中國傳統文藝與西方現代文藝創作思想的交鋒中,關于“戲”“影”的討論再次興起。許多中國電影人為了凸顯電影創制的獨立性,刻意劃清了電影與傳統戲劇的界限。但謝晉等電影人卻在傷痕電影的創作中探索出了一條將中國傳統戲劇與當代電影相互融合的現代化發展道路,創制了包括《芙蓉鎮》《牧馬人》《天云山傳奇》等在內的具有“影戲”特質的影片。與此同時,中國臺灣的武俠片導演也巧妙地從武俠題材出發,創作了許多具有戲劇風格的武俠影片,如《俠女》《龍門客棧》《忠烈圖》等。本文將以探討中國電影影戲傳統為基礎,從傳統戲劇的敘事題材、曲折突轉的敘事情節及含蓄內斂的民族底蘊三個層面探討中國影壇“戲”與“影”的關系。
二、傳統戲劇的敘事題材
正如上文所述,在中國電影產生發展之初,其敘事題材很多源自傳統戲劇,可以說經歷了漫長的發展時期,中國戲劇講述著不計其數的動人故事。中國首部敘事電影《莊子試妻》便改編自粵劇經典《莊周蝴蝶夢》 ,此后的中國內地及中國香港出現了許多傳統戲劇題材的影片,其中孟姜女哭長城、唐伯虎點秋香、李逵負荊請罪、昭君出塞、木蘭替父從軍等傳統戲劇中的經典故事都被搬上大銀幕。隨著中國電影的不斷發展,影壇上開始出現古裝劇,這些古裝劇大部分以武俠故事為視點,采用了傳統戲劇中武俠傳奇等題材進行創作。此時的武俠片已不再單純地對傳統戲劇進行改編,而是融入了許多戲劇元素的獨立創制,其中較具代表性的有《大醉俠》《倩女幽魂》《青蛇》等,這些影片將傳統戲劇中的相同題材進行了不同方向和不同層面的拓展并呈現在銀幕之上。
在從傳統戲劇敘事題材中汲養的過程中,一些講述戲劇人物的戲劇人生的影片給當代中國觀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也是對傳統戲劇敘事題材的一種現代化應用。影片《霸王別姬》由導演陳凱歌執導,張國榮、張豐毅擔任主演,上映于20世紀90年代,這部影片不僅被認為是中國戲劇類題材影片中的扛鼎之作,甚至流傳至今依然被視為中國電影之經典。在創制《霸王別姬》之前,陳凱歌曾明確表示自己對戲劇題材影片的反感,認為戲劇類電影常常存在哲理大于故事、情境大于人物的弊端。但事實上,在《霸王別姬》中,陳凱歌便巧妙地將人生哲理蘊含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之中,通過講述京劇名伶程蝶衣與段小樓之間在半個多世紀間的命運糾葛,將二人的藝術追尋和生活情感融合呈現,書寫了一段關于失落理想、愛恨背叛的生存悲歌。影片中導演陳凱歌通過塑造程蝶衣這位為藝術瘋魔、為情感瘋魔的“雌雄同體”的名伶形象,從戲劇題材出發,借用舞臺上的浪漫主義情調,在浪漫與現實的強烈對比中,將生命的局限與人性的善惡美丑體現得淋漓盡致。
在另外一部戲劇題材的影片《人·鬼·情》中,導演黃蜀芹采用“上帝視角”的方式全面呈現了一位河北梆子女演員秋蕓舞臺上下的人生經歷。秋蕓自幼生活在鄉村話劇團中,原本頗有天賦的秋蕓卻因為家庭的變故告別了舞臺發展之路。但長大后的秋蕓卻用自己對于藝術的執著打動了父親和老師,開始正式學戲。在學習過程中,秋蕓卻與年長自己許多并已為人夫的老師產生了感情。在情感的挫折和流言蜚語中,秋蕓艱難地成長,并最終成為一位河北梆子名角。在《人·鬼·情》中,戲劇題材不僅體現在女主人公的職業與理想之中,還體現在劇情之中,在影片中曾多次出現由秋蕓出演的《鐘馗嫁妹》的橋段,通過戲內戲外反差對比這種別樣的方式將女主人公秋蕓復雜的性格特征和孤苦的內心世界呈現在觀眾面前。
三、曲折突轉的故事情節
在中國影壇經常被提及的“戲劇沖突”強調影片要具有曲折回環、突變轉折的故事情節,在一定程度上滿足觀眾審美期待的同時,通過突轉來超越觀眾的審美期待。這種突轉常常伴隨著一定的矛盾,人物之間的矛盾、個體與社會和時代的矛盾都成為推動影片故事情節發展的關鍵點,通過這些矛盾展現出個體在大環境中的命運起伏、悲歡離合。就電影創作而言,曲折的情節能夠引人入勝,突轉的故事能夠令人嘆為觀止,縱觀當代中國影壇,有許多傳承戲劇曲折突轉這一特性的優秀影片。
影片《武狀元蘇乞兒》上映于20世紀90年代,由導演陳嘉上執導,周星馳、張敏等著名影星擔任主演,講述了出生于官宦之家的蘇燦為了獲得如霜姑娘的芳心,勵志通過考取武狀元來獲得“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地位。但在參加武狀元考試時,蘇燦遭人陷害并淪為乞丐,成為乞丐的蘇燦在父親的鼓勵下振作起來,最終成為丐幫幫主并拯救皇帝于危難之中,成為“奉旨乞食”的第一人,與如霜姑娘共赴行乞人間的自由與快樂。在這部影片中,我們能夠看到三個明顯的情節突轉,在影片伊始,蘇燦被塑造成為一個典型的紈绔子弟形象,雖然身手不凡,卻無意于功名,與父親過著揮金如土的生活。然而在一次浪跡妓院的過程中,蘇燦迎來了人生中的第一個轉折,愛上如霜姑娘的他決定考取武狀元,同時故事的情節也隨之發生突轉。影片的第二次情節突轉也是最動人心弦的部分,在武狀元考試中表現出眾的蘇燦遭人陷害,不僅與武狀元失之交臂,還得罪權貴被罰永生行乞。從富霸一方的公子哥到近在咫尺的武狀元,再到人人唾棄的乞丐,影片主人公的命運可謂是急轉直下。影片的第三次情節突轉自然是蘇燦從淪落街頭、灰心喪氣到統領四分五裂的丐幫并對抗邪惡勢力的部分。三次突轉使《武狀元蘇乞兒》的故事情節曲折、節奏緊湊,在批判官本位社會糟粕的同時,體現出一種適者生存、強者恒強的人生哲理。
影片《風聲》被認為是中國內地的首部諜戰大片,由陳國富、高群書執導,周迅、李冰冰、張涵予等人擔任主演。影片將故事背景置于汪偽政權時期,在一系列汪偽政府高官被暗殺后,日軍決定開始內部清查,包括顧曉夢、吳志國、李寧玉在內的五名汪偽政府核心官員被收押調查。在經歷了曲折回環的劇情發展后,代號“老鬼”的共產黨員用自己的生命傳出情報;代號“老槍”的共產黨員憑借堅定的意志力活著走出了汪偽魔窟。在《風聲》中,導演分別呈現了被關押的日偽官員的審訊過程和監控過程,每一次審訊都為影片的故事帶來了突轉,直到影片最后呈現幸存的共產黨員“老槍”的回憶和講述,觀眾才將影片中共產黨員深入虎穴、刺探情報的整個過程完整勾連。可以說,影片《風聲》通過曲折突轉的故事情節將諜戰片的精髓演繹了出來。
四、含蓄內斂的民族底蘊
無論是中國傳統戲劇,還是中國電影,都強調情感的投入與呈現,只有在劇中真情實感地投入,才能夠引發劇外觀眾的內心共鳴。在情感表達這一方面,中國傳統戲劇雖然重視情感,卻在一定程度上節制表達,這種情感表達的態勢來源于中國傳統民族文化中“發乎情止乎禮”的倫理道德及含蓄內斂的處世風格。[4]
影片《小城之春》由導演費穆執導,韋偉、石羽等人擔任主演,于1948年出品,影片圍繞戴家在抗戰后的生活展開,戴禮言與妻子周玉紋婚后長期兩地分居;妹妹戴秀還在讀初中,由忠厚的家仆照料,在戰后硝煙尚未全然散去的氤氳中,戴家人的生活平靜而寡淡。這種幾近死水的生活被一個故人的到來打破,這位名為章志忱的故人既是哥哥戴禮言的年少好友,也是嫂子周玉紋的初戀男友,他的到訪不僅改變了戴家日常的生活,還在戴家人中激起了情感的波瀾。面對章志忱,周玉紋陷入了初戀的回憶中無法自拔;戴禮言在洞察妻子與年少故交的情感后大受刺激,心臟病復發;而年幼的戴秀更是對章志忱產生了朦朧的愛意。在四個人之間的情感糾葛之中,章志忱、周玉紋、戴秀都選擇了“發乎情而止乎禮”,周玉紋和章志忱面對病中的戴禮言深感愧疚,將情愛深埋于心;而戴秀則選擇了放手,將愛交給時間,與即將離開戴家的章志忱相約在第二年春天。整部影片中主人公的情感流露雖然有悖風俗,卻十分含蓄內斂,并最終以道德至上作為故事的結局,無疑代表了對中國傳統戲劇中主導的禮義廉恥的遵從,而情感要受到道德的制約也是中國尚禮民族文化的重要表現。
相比于中國電影產生之初,當代中國影壇上的影片具有更加豐富的類型,典型意義上的戲曲片也逐漸退出歷史舞臺,但這并不能夠抹殺中國傳統戲劇對中國電影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即使是在現代化發展的中國電影藝術領域,探討“戲”與“影”的關系依然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