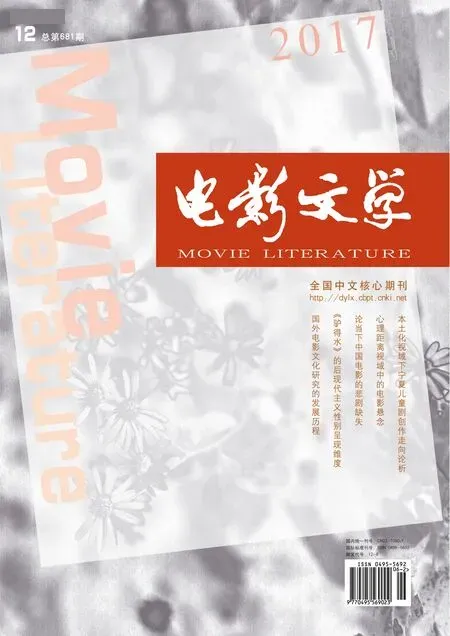美國商業影片的視覺文化語境
李 翠 (武昌首義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0)
一部電影是否成功首先體現在畫面上,電影以視覺語言作用于觀眾的感官和精神世界,電影的發展離不開畫面的不斷提升。1927年,三原色膠片減色法被用于電影拍攝,凡爾納在做《海底兩萬里》的視覺構思時就嘗試將其表現于火山爆發、氣球墜落等畫面元素。20世紀30年代,播放技術得到提升,梅里埃的《月球旅行記》為體現科幻主題的鏡頭,將其運用到表現爆彈入眼等畫面,凸顯了視覺上的魔幻色彩。隨著現代電影技術的發展以及觀影環境的日益改善,觀眾對影片的視覺審美價值更加重視,要求也不斷提高。商業電影作為一種最大限度上追求投資回報的市場化產品,無疑更加關注影片的視覺審美效果。視覺文化時代改變了人們認知世界的方式,也深深改變著人們的生活方式。對于身處視覺時代的,被圖像世界所包圍著的商業電影創作者和觀者來說,前者的創作取向與后者的視覺選擇,無一不受到當代視覺文化語境的影響。美國商業電影是研究視覺文化的一個合適范本。
一、美國商業電影的快感消費
視覺文化最突出的特質在于視覺快感的張揚。電影與其他視覺藝術相比,在視覺快感的營造方面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而美國商業電影對觀者視覺快感需求的迎合,對快感審美價值的強調尤為明顯。在視覺藝術完全走入慣常生活的今天,觀影作為一種消費行為,必然對一部影片所能實現的視覺快感有著獨特的期待。
首先,在電影技術不斷發展的今天,電影的畫面表現能力得到了飛躍式的發展。基于視覺快感消費目的走入影院的觀眾也越來越多。美國商業電影創作者無不將大量的投資用于電影畫面的制作上。視覺為中心取代敘事為中心的創作策略,創作過程中專業的團隊與高科技兩相結合,營銷過程中對電影預告片視覺沖擊力的追求等,使電影的視覺價值被刻意突出和放大。如,路易斯·萊特里爾執導的《諸神之戰》(ClashoftheTitans,2010)翻拍自1981年版《諸神之戰》,而影片在故事情節上也多沿用原情節。所以,電影要吸引觀眾,一個重要因素就是要在視覺上贏得主動權。新版《諸神之戰》拍攝的條件已絕非當年可比,計算機動畫技術的成熟以及3D技術的運用,使畫面有了質的提升。影片中的美杜莎是真正意義上的蛇發女妖,她的頭上布滿了吐信的蛇,令觀眾看了汗毛倒豎、頭皮發麻。而沙漠中珀爾修斯與巨蝎戰斗的場景,則恢宏而壯麗,令觀眾熱血沸騰。雖然影片的情節乏善可陳,但其仍以7000萬美元的制作成本,收回了接近5億美元的票房,可見,觀眾還是對視覺沖擊十分買賬的。安德烈·巴贊曾經主張的,將人對于電影的干預降到最低的“冷眼旁觀”式拍攝方式已經不適用于當前的電影市場。缺乏令人振奮的視覺元素的電影,是難以調動觀眾的觀影積極性的。
其次,這種視覺快感消費并不是完全停留在淺層次的視覺方面。電影所帶來的視覺快感,也美飾了現實生活。觀眾通過視覺快感實現情感上的宣泄和精神上的慰藉。因為,一方面,畫面是表現形式最為直觀的一種語言。畫面作為一種認識世界的感性方式,最容易為觀眾所理解,最容易激發觀眾的情緒。另一方面,現代社會的快節奏生活、生存的壓力以及人與人之間越發疏離的心理距離,是導致個體精神苦悶與壓抑的重要誘因。電影作為人們日常生活的一種陪襯,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種種精神焦慮。以彼得·杰克遜的《指環王》(TheLordoftheRings)系列為例,影片既有壯闊宏大的場景,又有史詩般的恢宏氣勢,尤其是激烈的戰爭場面給觀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電影的取景選自新西蘭的帕蘭諾平原,電影的整體環境給人一種遼闊的感覺,激烈的戰爭場面給人一種身臨其境的真實感,具有強烈的藝術表現力。而影片著力打造的魔都,陰森而詭秘,城墻上半獸人一族的守衛林立,這里充斥著青灰色,令人不寒而栗。觀眾在觀看影片的過程中,會為弗羅多一行人擔憂,同時也會期待人類、精靈、矮人等與魔都軍團的大戰。如此一來,現實生活中的煩惱就會被暫時放下,觀眾跟隨劇中人一起體味憂傷、快樂、恐懼、憤怒等情緒,從而得到了身心的放松,舒緩了精神的焦慮。
二、美國商業電影的視覺化演繹
布迪厄曾言及,“美國文化的審美世界里,深度沒有一席之地,只有娛樂和觀賞”。文化氛圍在大眾文化籠罩四野的今日尤其凸顯,視覺文化已經引領人們進入“讀圖時代”。今日的大眾沉溺于影視閱讀為主的文化體驗之中,電影成為大眾消費品。電影作為視覺文化時代的重要表征和推動性力量,其本身也是受視覺文化環境影響最深的一種文化形式和藝術形式。如何調整自身來適應時代的發展和觀眾日新月異的口味,美國商業電影給出了自己的答案。
首先,奇觀是吸引觀眾的法寶。以李安執導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LifeofPi,2012)為例,揚·馬特爾的《少年派》曾一度被認為是最難搬上銀幕的小說,但是李安憑借其天才般的想象,借助科技的表現形式將這部小說中的精華全部再現給了觀眾,贏得了世界的贊譽。怎樣能將小說中的情景真實、形象地呈現在觀眾的面前,這是李安思考的問題。李安在承接這個項目后就立即決定使用3D形式進行拍攝,并覺得這樣獨特的方式一定能使電影獲得成功。事實證明,李安的直覺是正確的。李安使技術與藝術的界限變得模糊,3D技術,讓我們零距離地觸摸到了主人公派想象中的那個充滿瑰麗浪漫的童話天堂。如,電影中最令人震撼的就是男孩兒派在海上漂泊的過程中突遇暴風雨:平時靜謐的大海此時像一頭發了瘋的野獸,震耳欲聾的雷鳴聲,肆虐的狂風……這一切不僅震撼著少年派,使他發出“太美了”的呼喊,更使觀眾的心靈在這次暴風雨中仿佛也得到了凈化。最后派的一聲呼喊,似乎是所有人的吶喊:“我向你臣服,上帝,你還想要什么。”一種撕裂般的痛感直擊觀眾的心房,流動的畫面、無限的審美意蘊都在激烈的情感表達中得到彰顯。此外,派碰到的成群的飛魚、透明的發光水母、巨大的發光抹香鯨等,都是在營造視覺上的奇觀。影片最終能夠拿下奧斯卡最佳視覺效果獎,充分說明了影片中視效的華麗。
其次,非奇觀題材的美國商業電影,也會采用視覺上的刺激(諸如陌生化等手段)來吸引觀眾,這方面的典型是恐怖電影。運用大量赤裸、暴力、血腥的鏡頭來震懾觀眾,常常是西方電影人擅長的手法,其以此來達到使觀眾懼怕的目的。影片中時常出現帶血的頭顱、被肢解四肢的鏡頭,這些都是與現實生活具有很大差距的。恐怖影片的審美特點在于給予觀眾焦慮、恐懼、擔心甚至是惡心的情緒體驗,滿足處于旁觀者地位的觀眾對于丑惡的好奇心理和邪惡趣味。而在營造恐怖感時,最核心的部分便是人物形象的塑造。以《突變怪嬰》為例,影片中以類似于惡魔的嬰兒不斷嗜血殺戮為故事內核。嬰兒在現實生活中無疑是人們眼中的天使,但在影片中卻是不折不扣的怪物,這對于觀眾來說是非常震撼的。恐怖電影之所以能夠激發人不適的生理反應,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它暴露出了人性中陰暗的一面,這種陰暗面對應著大多數觀眾日常情況下被理性所壓抑的本我。在《電鋸驚魂》(Saw)系列電影中,反復出現的角色被設入圈套后無法逃脫,最后以各種花樣的方式折磨致死、血流如注,都能給觀眾視覺上的強烈刺激。此外,美國恐怖電影還更加注重畫面的整體感,如果畫面想表達恐怖,那么畫面上一定每個元素都是令人恐懼的。
三、視覺背后的人文要素
美國商業電影并非僅僅在視覺上給觀眾強烈的刺激,其視覺背后還包含眾多人文要素。電影本身是一種文化產品,它體現著國家與民族的核心軟實力,包含、植入著具體的價值觀念,能夠深刻而廣泛地影響人們的思維方式、思想觀念。好萊塢商業電影是美國社會價值觀的直觀體現。
首先,英雄主義可以說是美國商業電影的招牌。一方面,對英雄的崇拜是各民族自古有之的,商業電影自然會利用觀眾的這一心理訴求。以《加勒比海盜》(PiratesoftheCaribbean)為例,《加勒比海盜》三部曲是導演戈爾·維賓斯基的代表作,每一部影片都有一個不同的故事主題,貫穿起來就構成了一部壯麗的海盜冒險史詩,其中充滿了詭異而又浪漫的情節、荒誕滑稽的冒險主人公,呈現出一以貫之的奇幻風格。影片通過一次次的海上冒險營造出一個神秘而又奇幻的電影世界。在這個神秘的海盜世界中,既有現實中浪漫唯美的愛情故事、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的鉤心斗角,同時也彰顯了美國社會個人英雄主義的主流價值觀,這股熾熱的海盜熱潮從北美洲到亞洲,在世界范圍內引起強烈的反響。黑珍珠號的船長杰克·斯派洛就是一個典型的個人英雄主義人物。雖然他有著痞子一般的外表和性格,但每到危難時刻,杰克總是能夠挺身而出。與巴博薩船長激斗解救伊麗莎白,與戴維·瓊斯大戰搶奪聚魂棺,而他也總能化險為夷,最終完成對他人的拯救和自我救贖。而另一方面,英雄主義背后的正邪價值判斷則是具有普世意義的,是超越美國文化存在的,心存正義感或善良意愿的電影主人公無論是否能得到官方的認可(甚至在好萊塢電影中,主人公往往被政府孤立或打壓,扮演反面形象的政府同樣是好萊塢用以強化個人英雄主義文化的元素),他都可以為觀眾所同情、支持。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何在大多數好萊塢影片之中都可以看見個人英雄主義文化的影子了。
其次,在美國商業電影中,還處處可見“美國夢”的影子。“美國夢”中所崇尚的個人奮斗是美國社會的主流價值觀,而普通人通過奮斗實現“美國夢”則反映了大眾普遍渴望實現成功的愿望。美國商業電影抓住了觀眾的這一渴求,以主人公實現“美國夢”的過程來吸引觀眾。典型的例子是《阿甘正傳》(ForrestGump,1993),阿甘作為一個先天性智障者,連普通人都談不上,但他通過自己的努力成了橄欖球巨星、告發了水門事件的竊聽者、參與中美乒乓外交,甚至還擁有自己的漁業公司。阿甘的傳奇經歷是典型的“美國夢”范本,觀眾也可以在阿甘的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此外,美國商業電影也通過展現主人公“美國夢”的破碎來提醒觀眾,奮斗不一定都能帶來成功。以伊納里多的《鳥人》(Birdman,2014)為例,主人公里根·湯姆森已經年過半百,年輕時曾經因為扮演好萊塢超級英雄系列大片《飛鳥俠》中的主人公而家喻戶曉。然而隨著年紀增大他已經無法再在飛鳥俠這個角色上延續輝煌而不得不轉戰百老匯,準備用舞臺劇《當我們談論愛情的時候,我們在談論什么》來向挑剔的觀眾證實自己也有表現純藝術的實力,以重新贏得尊重。但里根的奮斗卻是失敗的。在影片的最后,導演給里根安排了一個開放性的結局,對于他是否跳樓自殺,影片并沒有給予明確的答案。
綜上,電影既是一種藝術形式,也是一種大眾文化,兩者既相互矛盾,又相互推進,兩者都是構成現代視覺文化的重要元素。通過對美國商業電影的視覺文化語境進行研究,有助于國產電影吸收借鑒其有益經驗,從而為自身的發展鋪平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