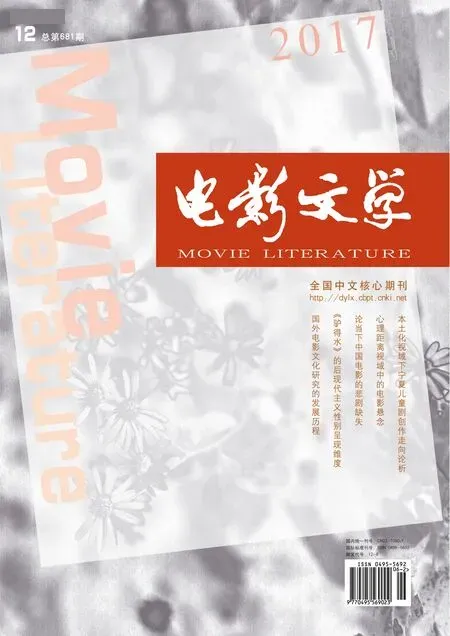美國獨(dú)立電影的審美空間
王會凡 (河南牧業(yè)經(jīng)濟(jì)學(xué)院,河南 鄭州 450045)
美國電影往往與好萊塢電影畫等號。事實上,電影大國美國直到20世紀(jì)60年代后,才形成較為完善的好萊塢經(jīng)典類型片范式。而早在20世紀(jì)50年代中期,就出現(xiàn)了被視作主動脫離大制片廠制度的電影,為當(dāng)時的美國電影注入了新的活力,由德爾波特·曼(Delbert Mann)執(zhí)導(dǎo)的《馬蒂》(Marty,1955)就可以視作低成本獨(dú)立電影的里程碑。這一類電影由于制作者負(fù)責(zé)為影片的制作籌措資金而非依賴迪士尼、福克斯、環(huán)球、派拉蒙等好萊塢巨頭的支持,并在電影攝制完成之后自己組織影片的銷售和發(fā)行,故而被稱為獨(dú)立電影。早年部分獨(dú)立電影的“叫好又叫座”,促使好萊塢電影公司也插手獨(dú)立電影的創(chuàng)作以獲取利潤,甚至將獨(dú)立制片公司買下,或直接建立所謂獨(dú)立制片公司,暗中為自己拍攝的“獨(dú)立電影”注入資金。數(shù)十年來,美國獨(dú)立電影與主流陣營相對抗,打破了各大巨頭對美國電影市場的壟斷。獨(dú)立電影人們既獨(dú)來獨(dú)往于自己作品的創(chuàng)作,又在貢獻(xiàn)出一部部電影的同時形成了能夠在批評、宣傳、發(fā)行上有所襄助的“獨(dú)立”陣營,是美國電影不可忽視的一支力量。
獨(dú)立電影的獨(dú)立之處,并不僅僅在于其拍攝之前的融資方式,以及在拍攝過程中導(dǎo)演對全片的個人控制權(quán),還在于其有迥異于制片廠制度下出來的“流水線”電影產(chǎn)品的審美空間。對獨(dú)立電影的審美空間進(jìn)行分析,無疑能為國產(chǎn)電影在全球化時代下的“非公式化”,拓展國產(chǎn)電影的生存環(huán)境尋找到一條可以借鑒的道路。
一、美國獨(dú)立電影的審美內(nèi)容
如前所述,何為投資方早已不是衡量一部電影是否為獨(dú)立電影的圭臬。正如美國獨(dú)立電影節(jié)主辦方所聲明的:“今天,影片的投資方式在提名時已不再是要加以考慮的因素,今后起作用的只是資金的合理安排、題材的挑戰(zhàn)性與獨(dú)特性和視點(diǎn)的新穎。”由此可見,除卻資本以外,審美內(nèi)容(題材與視點(diǎn))才是決定一部電影是否能被稱為獨(dú)立電影的關(guān)鍵。
獨(dú)立電影的內(nèi)容是與好萊塢經(jīng)典類型片有重合之處又截然不同的。好萊塢類型片如音樂歌舞片、科幻片、戰(zhàn)爭片、西部片等,其分類正是立足于絕大多數(shù)觀眾的審美趣味,其目的在于獲取高額的票房回報。有針對性地安排電影的內(nèi)容與表達(dá)方式,迎合大眾的娛樂需求與道德判斷,如對人道主義的高揚(yáng),對“美國精神”的肯定等,只有如此才能夠最有效地規(guī)避電影投資者的風(fēng)險。而獨(dú)立電影則恰恰是要質(zhì)疑經(jīng)典類型片中表露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這種質(zhì)疑最直觀的體現(xiàn)便是獨(dú)立電影的內(nèi)容。在獨(dú)立電影中,非主流的性取向、暴力行為等游離于主流意識形態(tài)之外的生活方式往往是導(dǎo)演的關(guān)注點(diǎn)。
隨著時間的流逝,最初經(jīng)濟(jì)掣肘造成的不得已而為之的特色,反而成為部分獨(dú)立電影維護(hù)自身獨(dú)立性的藝術(shù)需要。如在伍迪·艾倫(Woody Allen)拍攝《賽末點(diǎn)》(MatchPoint,2005)時,早已成名的他顯然已經(jīng)不必為資金問題和票房而殫精竭慮,可以隨心所欲地在電影中表露自己的想法,但《賽末點(diǎn)》依然是圍繞著性展開的,而一系列敘事內(nèi)容的高潮正是兇殺案。主人公窮小子威爾頓為了混入上流社會不擇手段。他在來自中產(chǎn)階級的克洛伊與和自己一樣出身平平的諾拉之間徘徊,在與前者保持婚姻關(guān)系時又讓后者做了自己的情婦。而當(dāng)諾拉懷孕后,威爾頓為了保住自己現(xiàn)在富足的生活,殺死諾拉與諾拉的房東,可謂是毫無人性。且與崇尚“正義最終得到伸張”的好萊塢懸疑、犯罪電影不同,《賽末點(diǎn)》中的威爾頓卻逃脫了法律的制裁,殺人是他人生的“賽末點(diǎn)”,而卑鄙的他最后顯然是這場比賽的贏家。正如《滾石》對《賽末點(diǎn)》的評價,《賽末點(diǎn)》關(guān)注的是人類最容易犯的錯誤,即性的誘惑。此時,與其說性和兇殺內(nèi)容是伍迪·艾倫為吸引眼球而設(shè)置的,倒不如說這兩種內(nèi)容已經(jīng)成為獨(dú)立電影的一個固化了的審美內(nèi)容。與之類似的還有大衛(wèi)·林奇(David Lynch)的《我心狂野》(WildatHeart,1990)等。
這種看似另類的審美內(nèi)容卻并不意味著獨(dú)立電影注定缺乏受眾。相對于正面、幸福的內(nèi)容,人們更愿意投入精力,也更容易記住消極信息。里維斯和納斯指出:無論是在媒體抑或現(xiàn)實中,消極信息往往更直接指向人類生存受到的威脅,因此總是更能給予人持久而深刻的影響。由此可知,第一,對消極信息大加刻畫的獨(dú)立電影完全有可能得到觀眾的青睞、市場的回應(yīng)。這正是獨(dú)立電影與經(jīng)典類型片之間不能單純以票房進(jìn)行區(qū)分的原因之一。第二,美國獨(dú)立電影在這方面的嘗試,也是符合電影這一門藝術(shù)的傳媒性質(zhì)的,它實質(zhì)上發(fā)揚(yáng)了電影的媒介效能,甚至還能與好萊塢經(jīng)典類型片一起(如類型片中大量的劇情、懸疑、犯罪電影,皆與獨(dú)立電影有共通之處),增強(qiáng)美國電影在全世界范圍內(nèi)的戰(zhàn)略影響力。
二、美國獨(dú)立電影的審美形式
與審美內(nèi)容相對應(yīng)的必然是審美形式。一般來說,獨(dú)立電影是個性化的,在形式上自然也因?qū)а輦€性的不同而不同(如賈姆什熱衷于使用的長鏡頭、橫移,塔倫蒂諾喜歡的MV式鏡頭等就并不是獨(dú)立電影在審美形式上的共性),但是它們依然可以被總結(jié)出一些近似之處。
(一)視聽語言
獨(dú)立電影在鏡語風(fēng)格上最大的相似之處就是大多具有暴力場面與血腥鏡頭。如大衛(wèi)·林奇的《穆赫蘭道》(MulhollandDr.,2001)。在《穆赫蘭道》中,真正的兇殺實際上只發(fā)生了一次,但是整部電影四分之三的篇幅都是在描述貝蒂(戴安娜)的夢境。貝蒂因為雇殺手去殺死自己愛而不得的麗塔(卡米拉),因此在巨大的恐懼與愧疚之中陷入了噩夢。在噩夢里,麗塔遭遇車禍;在與貝蒂相遇之后,咖啡廳的墻后出現(xiàn)了一個魔鬼,夢境中的殺手在殺死長發(fā)男子之后又因為打中女秘書而不得不殺了女秘書,結(jié)果又因為被清潔工發(fā)現(xiàn)只能殺清潔工滅口;貝蒂與麗塔來到戴安娜家里時,竟然發(fā)現(xiàn)床上有一具腐爛的女尸,等等。之所以說這些并非“內(nèi)容”而是“形式”,是由于,與《賽末點(diǎn)》不同,上述令人產(chǎn)生不適的鏡語是高頻、碎片式、轟炸式出現(xiàn)的,如違背現(xiàn)實經(jīng)驗的魔鬼從銀幕中央驟然出現(xiàn),貝蒂送別的老人突然在車中變得面目猙獰等,其目的就僅僅是對觀眾造成驚嚇而已。這猶如原本通暢的語句被復(fù)制后打亂順序粘貼,此時文字就成為形式而非有意義的內(nèi)容。暴力場面反復(fù)在貝蒂的夢境中出現(xiàn),這是因為她潛意識中是后悔自己對心愛的麗塔痛下殺手的,厄運(yùn)無處不在,纏繞著現(xiàn)實與夢境之中的她,也令觀眾感到驚恐。與之類似的還有昆汀·塔倫蒂諾(Quentin Tarantino)的《落水狗》(ReservoirDogs,1992)等。
這并不意味著經(jīng)典類型片中沒有這類引人注目的場面,二者的區(qū)別在于以其為形式的目的性,獨(dú)立電影對這些視覺場面的展示是并不包含政治隱喻或道德教化目的的,經(jīng)典類型片的場面具有可供觀眾“閱讀”的意義,而獨(dú)立電影則消解了這種“閱讀”背后應(yīng)有的意義深度,將“閱讀”轉(zhuǎn)為“觀看”。
(二)敘述邏輯
從“閱讀”到“觀看”也就意味著在獨(dú)立電影中,導(dǎo)演對劇情的因果邏輯有可能是不做闡釋的,甚至電影中人物行為的價值判斷也是被導(dǎo)演懸置的。在美國獨(dú)立電影中,現(xiàn)實往往被以一種碎片化的方式展示出來,觀眾無法以觀看類型片的習(xí)慣來追隨獨(dú)立電影導(dǎo)演的敘述邏輯,而只能勉力跟隨電影的節(jié)奏。例如,在塔倫蒂諾執(zhí)導(dǎo)的《低俗小說》(PulpFiction,1994)中,影片的敘事線被有意進(jìn)行了切分,以至于初看此片的觀眾往往會陷入困惑中。在《低俗小說》中,一共存在四個較為獨(dú)立的故事:(1)小南瓜與小兔子在早餐店的打劫遭到了黑社會成員的破壞;(2)黑社會成員文森特和朱爾斯奉大哥馬沙·華萊士之命去催債;(3)文森特與馬沙的美艷妻子發(fā)生了關(guān)系,這讓他陷入苦惱;(4)拳擊手布奇回家找自己祖?zhèn)鞯慕鸨恚馔饩攘笋R沙。這四個故事的真實順序?qū)嶋H上應(yīng)該是2—1—3—4,在表面的混亂背后,實際上人物的命運(yùn)是有邏輯聯(lián)系的,并且敘事在首尾銜接上形成一種呼應(yīng),即一開始是小南瓜和小兔子在商量去哪里打劫,而電影的結(jié)尾是他們的打劫被阻止。然而又與邏輯不符的是,在布奇金表的故事中,文森特已經(jīng)喪命了,但是在后來他又起死回生。而在小南瓜與小兔子起念打劫到打劫未遂的這一段時間中,朱爾斯的人生觀已經(jīng)被徹底改變了。一言以蔽之,塔倫蒂諾在割裂中建立聯(lián)系,在合理中又制造不合理,這讓早已習(xí)慣類型片平鋪直敘表達(dá)方式的觀眾耳目一新。在戛納風(fēng)光無限的《低俗小說》讓這種敘述邏輯與塔倫蒂諾聲名大噪,但實際上早在塔倫蒂諾之前,有“美國獨(dú)立電影宗師”之稱的吉姆·賈姆什(James Jarmusch)在其《神秘列車》(MysteryTrain,1989)與《地球之夜》(NightonEarth,1991)中就已經(jīng)做出嘗試。
三、美國獨(dú)立電影的審美本質(zhì)
審美本質(zhì)指的是審美活動背后的意識形態(tài)。1986年,美國獨(dú)立電影迎來了一個其專屬的、可以與奧斯卡分庭抗禮的獎項,即由獨(dú)立影片規(guī)劃委員會籌辦的“獨(dú)立精神獎”。獨(dú)立精神成為獨(dú)立電影最為重要的本質(zhì)。獨(dú)立電影的形成是多種合力造就的,在審美之外,作用于電影的力來自經(jīng)濟(jì)、技術(shù)、媒介等多方面。而在審美之內(nèi),決定一部獨(dú)立電影之所以是獨(dú)立電影的只有電影人的獨(dú)立精神。盡管在拍攝時所有電影人都無法進(jìn)入無拘無束的理想狀態(tài),但電影人依然要盡可能地在電影中以保證純粹的原創(chuàng)性和自覺處于主流之外的姿態(tài),將個人風(fēng)格發(fā)揮到極致,表現(xiàn)出天馬行空、無所滯礙的審美精神。美國獨(dú)立電影人基本上都以“局外人”自居,不奉行好萊塢式的商業(yè)與藝術(shù)準(zhǔn)則,以“局外人”這一身份來為自我以及與自我處于類似狀態(tài)者進(jìn)行表達(dá),如執(zhí)導(dǎo)《珍愛》(Precious,2009)的李·丹尼爾斯(Lee Daniels)等。
同時還要廓清的是這一審美本質(zhì)與“美國精神”之間的關(guān)系。1994年奧斯卡最佳影片在兩部經(jīng)典類型片《肖申克的救贖》(TheShawshankRedemption,1994)、《阿甘正傳》(ForrestGump,1994)和獨(dú)立電影《低俗小說》中角逐產(chǎn)生,最后宣揚(yáng)正能量的《阿甘正傳》勝出,這令為《低俗小說》鳴不平的電影批評者表示,《阿甘正傳》屬于美國,而《低俗小說》屬于世界。似乎獨(dú)立精神是與美國精神對立的,而獨(dú)立精神實際上正是一種“美國精神”的體現(xiàn)。獨(dú)立精神的出現(xiàn)在相對較為寬松的美國社會環(huán)境,電影人的各類審美心理結(jié)構(gòu),以及在此心理結(jié)構(gòu)上生發(fā)出來的審美創(chuàng)造、鑒賞行為等基本上都能夠得到包容。
無論是美國電影處于“古典好萊塢”時期(70年代之前)抑或是“新好萊塢”時期(70年代之后),總是有敢于破除平庸、挑戰(zhàn)模式化與商業(yè)化的電影出現(xiàn),與處于主流的好萊塢類型電影分庭抗禮,這便是美國獨(dú)立電影。而在不斷的嘗試中,美國獨(dú)立電影在獨(dú)立精神這一審美本質(zhì)的指導(dǎo)下,形成了自己的審美內(nèi)容與審美形式。可以預(yù)見的是,隨著電影發(fā)行渠道、電影市場的變動,美國獨(dú)立電影的審美空間也將處于流動的狀態(tài)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