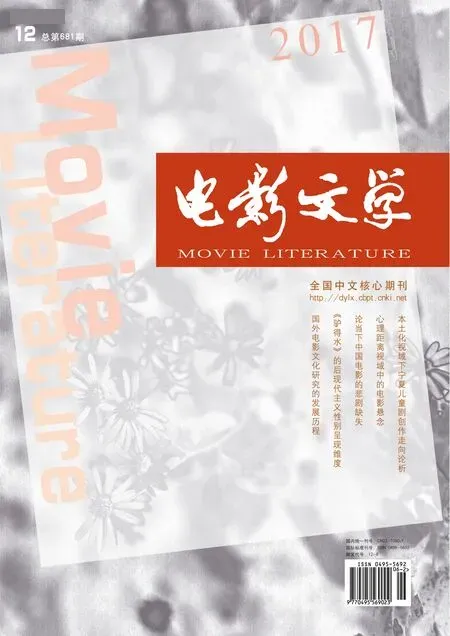《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接受的三層次
陳憶澄 (東南大學藝術學院,江蘇 南京 211189)
李安導演的電影《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首次采用120幀/4K/3D的規格進行拍攝,沖擊了觀眾對于電影藝術的接受習慣。高幀率的技術直接帶來了敘事方法和鏡頭語言的變化,導致觀眾在知覺、理解、體驗三個層次的接受活動與以往有所不同。
一、知覺層
電影接受往往是從知覺活動開始的。雨果·閔斯特伯格認為,“我們是通過自身的心理機制創造出縱深和連續性的”[1]。
(一)寫實的“密度”
《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由于采用了高幀攝影機,最終在大銀幕上的呈現將逼真度、還原度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甚至連人物的毛孔和衣服的質地都能一覽無余。這種寫實的高“密度”打破了傳統電影的慣例。電影畫面的縱深感被加強了,導致前景、中景、背景的關系重置,這需要觀眾花費更多的主觀調整來適應這種變化。電影開場時,林恩在酒店外等候接送車輛的時候,在不同方向的街道都構成了縱深空間。觀眾的視線被拉長,哪怕是相距主要人物數米遠的路人和街景,也都可能在觀眾的知覺活動中成為中心區域的表象。
傳統電影寫實的“密度”是不均勻的。蒙太奇有時也能對寫實的“密度”進行調節。正如克拉考爾指出的,“交替出現的鏡頭必須能使觀眾跟著活動起來,從而真正體驗到街上的示威游行或任何其他企圖以其特大的規模來給予觀眾深刻印象的東西”[2]。通過畫面的組接,導演能夠引導觀眾加深對于知覺物象的實際印象。
(二)尋找“焦點”
影片使用索尼最新型的F65攝影機,用120幀每秒的超高幀率進行4K下的3D電影拍攝,是在現有科技條件下對電影藝術的技術創新。觀眾在高幀率的場景還原中迷失了知覺起點,無法找尋到“焦點”。
在后臺,林恩與菲姍展開了一場私密的對話,在大量的近景和移動鏡頭前,雖然觀眾被高度清晰的細節所困擾,比如明明注意到了人物衣角的一絲褶皺是那么清晰可辨,但仍能夠準確地捕捉到畫面傳達的幾乎全部的關鍵信息。
“焦點”的模糊性也不會消解導演對觀眾接受活動的引導力和控制力。“即便最為現實的影像,也不是再現或復制,而是一種詮釋。”[3]影片中對現實的還原再真實,也是經過加工和選擇的,知覺的對象都不會是現實本身,而是電影語言。比如,執行戰事任務的刻畫,并沒有像傳統戰爭片的模式化處理一樣,而是打造一種平常的、毫不矯揉造作的真實。
(三)消逝的界限
隨著3D技術的發展,景深鏡頭雖仍大量使用,但由于在知覺層面,觀眾對于平面空間的物象關系認知有了很大不同。這種趨勢在《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中表現得更為顯著,由于高清和高幀拉近了觀眾與影片的距離,影片中人物近景和特寫鏡頭的比例極高。例如,在林恩回家后,與姐姐在屋內的交談,淺焦鏡頭不斷推拉,對焦在兩個人物臉部不斷切換,給觀眾的印象就像是直面兩人的談話。鏡頭和表意鏈接的慣性在這里失效了,鏡頭語言的界限變得模糊。
消逝的界限導致了慣例的失效,也直接促使觀眾的接受經驗在部分情境中失效。在B班于伊拉克執行任務的那一場關鍵戲中,觀眾的“期待視野”落在與敵方的激烈戰斗中,但導演幾乎沒有對敵方的情況有太多的交代。高幀率帶來了移動鏡頭的極高穩定性,以往畫面抖動引發的觀眾感知效果也不起任何作用。界限消逝帶來的接受活動的變化,并不是消極的,因為它在制約傳統觀影習慣和經驗的同時,又建立了一種新的接受規則:雖然身臨其境,但也要保持距離,節制情感,釋放理性。
二、理解層
理解是電影接受的第二個層次。影片通過一個19歲男孩兒的眼光來看待這個世界,把個人自由意志置于現實的生存環境中。
(一)平行的倒敘
林恩在伊拉克戰場與其他七名突擊隊成員共同完成了3分43秒的激戰,這一切被攝像頭記錄下來,他們成為美國的國家英雄,這是前因。影片的主線,則是他們歸國后應邀前往感恩節橄欖球公開賽的中場表演這一天的生活。平行敘事的兩個事件之間是先后相繼的,實質是一種倒敘。倒敘的過程被精巧地安排在主線中,情節的起伏是跟隨主線來展開的。
平行敘事、插敘、倒敘等敘事策略,在電影藝術中頗為常見,都是線性敘事的一種。“線性事理結構并不意味著完全遵循順時的時間向度,在不動搖線性順時基本走向的前提下,短暫而適當的倒敘和插敘不但是可以被經典敘事接受的,而且也極大地豐富了經典敘事的表現性內涵,倒敘和插敘的確也經常受到導演們的青睞。”[4]
李安導演將倒敘平行化,將前因和后果并置在主線中交替發展,這種處理一方面維護了中場表演當天的“三一律”原則,造成林恩個人真人秀的錯覺;另一方面又制造了一種在真人秀里穿插紀錄短片的效果。
(二)兩種視野
影片采用了兩種視野的鏡頭語言:一是以冷靜的旁觀者凝視林恩在伊拉克的訓練、作戰過程以及受邀參加橄欖球賽中場表演的一天的境遇;二是以林恩這個主要人物的視線來觀察這兩個時空段落里周遭的世界。
“觀眾的視線被人物的連續性活動所吸引。在每一個鏡頭中同一個人物都必須看著同一個方向,以便觀眾理解。這被稱為視線匹配,是連貫性剪輯方法的重要因素。”[5]中場表演開始后,林恩和戰友們在臺上最高處的幕布后,隨著幕布被拉下,他們緩緩走下臺階,鏡頭從對準林恩一個人行進到舞臺中部轉移到從背后對準“真命天女”組合的表演,這種精準的對接造成了林恩主觀視野的結果。
影片中另一種表達主觀視野的方法是呈現林恩的想象。例如,在媒體見面會上,林恩內心對問題的回答是通過想象戰友說出他本人的想法而呈現的。
(三)社會的鏡像
面對不解、疑慮和糾結,林恩最終還是做出了艱難的決定,和戰友們一起回到戰場。這固然可以理解為林恩個人的成長,但更重要的意涵在于揭示個人如何在社會中生存的主題:個人的自由、價值,個人的存在方式是沒有辦法脫離社會評價和社會認知所建立的鏡像的。群體內的個人無力改變這種社會鏡像,他們本身就參與了公眾塑造鏡像的過程。公眾的誤解和誤判也沒有惡意,常常是盲目的,他們無法克服誤讀。
李安導演的這種反思,體現出“戀父情結”的癥候。“在李安的所有電影背后都隱藏著一個揮之不去的情結:與父親之間既依戀又沖突的,糾纏難解的心理情結——‘戀父情結’。而正是對這一情結的認識和探索成為貫穿李安所有電影的原動力和核心情感。”[6]這并非全然是一種蠡測,李安導演接受采訪時曾多次談及父親對他個人的影響,他的成長伴隨著父親的權威,總是在尋找自我,面對父親的期望,顯得有些愧疚。①正是在這樣的心理癥候之下,影片將個人的不安、歉意和逡巡發揮到了極致。
三、體驗層
觀影體驗指向觀眾的視覺、聽覺等多種感官,是一種整體的感受,是對電影情境的感知。
(一)身臨其境
根據 “豆瓣電影”等門戶網站的評價系統顯示,大多數觀眾并不認為在《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這部影片中,高幀率會帶來負面感覺。②“高幀率技術還存在一個技術與內容契合度的問題,高幀率技術并非適用于所有的電影創作。”[7]李安導演將高幀率看成是觀眾進入電影情境,獲得更為真切體驗的有效途徑,與故事內核、敘事策略都是一致的。
由于信息量劇增,場景的空間感也更為立體,觀眾不得不時刻調整自己的注意力,隨時調動更多的想象。該片中施洛姆與林恩有一段在露天的談話,施洛姆用宗教觀念向林恩詮釋了戰爭和生死,在整個談話空間中,樹、街道、墻體上的圖樣,都是極度清晰的物象,觀眾必須通過思考和注意力的切換,才能體會人物語言和環境之間的聯系,從而跟上觀影的節奏。因此,身臨其境的體驗,讓觀眾就像是去了伊拉克一樣,就坐在林恩和施洛姆的旁邊,這是對這個電影情境整體感知的感知,是感知的升華。
(二)安全感
如果我們借用法國藝術理論家狄德羅談論戲劇時提出的“第四面墻”的理論來看待電影藝術,那么在很多情況下,導演會根據需要適時打破或建立“第四面墻”,以維持觀眾與影片的安全距離。觀眾和導演在關于“第四面墻”的問題上維持著一種張力和平衡,有些觀眾需要適當與影片保持距離,以獲得舒適、安然的觀影體驗,也有些觀眾則希望這種距離可以近乎為零,融入影片對他們來說或許才是最佳的觀影體驗。
影片《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就在設立和取消“第四面墻”之間游刃有余。對于部分觀眾而言,高清晰度和大量的細節造成了安全距離的消失,即便不是人物的主觀視野,鏡頭保持冷眼旁觀,高度的逼真性依然讓不少觀眾完全進入了電影的情境中。如此一來,對電影主題的思考有可能讓位于人物情感的體恤和浸染。
伊拉克戰場上危險的任務,幾乎采用了紀錄片一般的鏡頭,但高幀率的清晰度畢竟帶來了真實感,不少觀眾的情緒隨著人物心情的變化而產生波動。爭論場面在片中也有若干處,無論是林恩跟姐姐的爭論還是士兵們與體育場工作人員的爭吵,都帶有一定的情緒侵略性,高幀技術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這種效果。
(三)綿長的記憶
影片延長了觀眾的記憶,無論是對形式的感知還是對情感的介入,都要更為持續。
綿長的觀影記憶,主要是由于高逼真度促使觀眾在接受過程中,能夠如親身體驗電影中發生的事件一般,不再純粹作為認知的對象,而是成為實踐的對象。“人類始終對自己親歷的一切都抱有極大的好奇心,而想方設法滿足這種好奇心和親歷欲望,即是觀眾觀影的深層心理動機。”[8]高幀率帶來的巨量信息、細節,必然導致記憶的強化,從短時向長時過渡。觀眾更像是見證了一次中場表演和戰地訓練。不少觀眾認為,觀影就像是參與了整個過程。一般的電影通常在散場后很快會被遺忘,而這部影片卻反復在腦海中回蕩,記憶非常綿長。③
觀影記憶是一種情景記憶,有時也伴有情緒記憶。鏡頭的縱深感、精細的物象、穩定的鏡頭運動等構成了全新的電影時空情景,關于它的記憶,很容易在往后的時間被提取和激活。影片尾聲溫暖人心的情節,則提供了感動、凈化的情緒記憶,同樣讓人久久難以忘懷。
影片《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作為高幀率技術電影的全新嘗試,引導著觀眾在接受活動中養成新的習慣和方法。與其說這種改變是對觀影的干擾,毋寧說這是試圖建立起新的接受方式,是適應、調整和選擇的過程。
注釋:
① 參見《李安的“安”與“不安”》陳魯豫采訪李安視頻,網頁鏈接:https://v.qq.com/x/cover/9aaopv19wz8grpx.html?ptag=iqiyi。
② 根據“豆瓣電影”的數據整理,網址鏈接:https://movie.douban.com/subject/25983044/。
③ 根據IMDb短評整理,網址鏈接:http://www.imdb.com/title/tt25130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