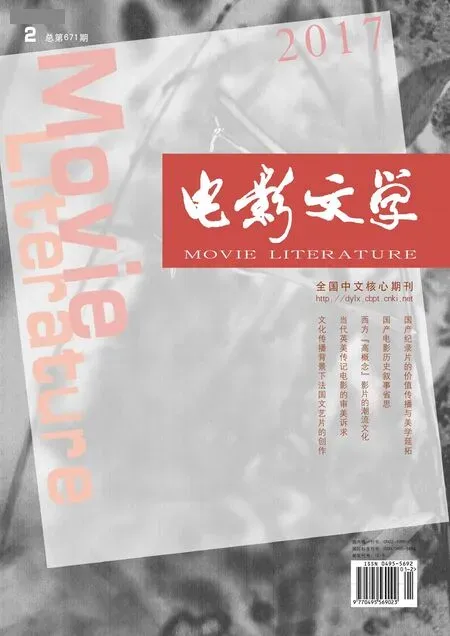《爆裂鼓手》的反勵志敘事模式
李鶴藝
(四川幼兒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四川 江油 621709)
《爆裂鼓手》(Whiplash)是2014年上映的一部美國音樂劇情片,曾獲得多項奧斯卡提名,并榮獲2015年奧斯卡最佳男配角及最佳音效獎。影片凌厲緊湊的剪輯、張弛有度的音樂控制、精準傳神的表演以及獨特的視角風格迎得了良好的口碑。尤其是主人公安德魯和導師弗萊徹頗富爭議的師徒關系讓人耳目一新,兩人之間亦師亦敵的對手戲融入暴風驟雨般的節奏和急轉猛烈的矛盾沖突中,讓整部影片看起來又像一部動作懸疑片或教育倫理片。
《爆裂鼓手》塑造了一對關系異常的師徒。一個是成長在單親家庭的19歲少年安德魯,初出茅廬的他一心想成為頂級爵士樂鼓手,并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一個是美國頂級音樂學院的爵士樂隊指揮弗萊徹,這位魔鬼導師對學員有著變態的水準要求,他暴躁無常的性格、變態的謾罵侮辱以及仇虐般的訓練手段挑戰著每個學員的極限。安德魯在強壓下承受著信心被撕裂的苦痛,又憑著骨子里的倔強勉力支撐著。長時間的耳濡目染和非人性化訓練讓原本溫順的少年逐漸變得偏激暴躁,他與家人、女友之間的關系開始淡漠,原本對音樂的一腔熱情也日益扭曲成師徒之間近乎瘋魔的對決。最后,在弗萊徹難得一見的溫情鼓舞下,安德魯終于登上了紐約音樂廳的舞臺,可是此時安德魯才驚恐地發現,原來弗萊徹自始至終都是那個自私又陰狠的陰謀家。臨時更改的樂譜讓安德魯的音樂事業瀕臨絕境,憤怒絕望的他孤注一擲,沖上臺完成了一段激情迸發的極致表演,登峰造極的技藝展示讓弗萊徹露出笑容,影片戛然而止。
這部影片究竟算不算得上是一部勵志電影?從劇情走向和安德魯的技藝發展上來看,玉不琢不成器,一個資質平平的后備學徒能夠成長為一流的爵士樂鼓手,這是標準的勵志電影橋段。然而它絕不是類似《死亡詩社》《心靈捕手》或《霍蘭德先生的樂章》這樣推崇師慈徒孝戲碼的“心靈雞湯”。影片到底是在展示一種暗黑式的教育理念,還是在批判音樂人從道德到心靈的迷失?在筆者看來,影片中處處透露著反勵志的情感主張,無論是人物性格設置,還是故事情節發展,抑或是畫風基調的處理、情感情緒的表達,都是在進行全面的“反勵志”述說。
一、勵志與反勵志
勵志主題是一種非常經典的劇本創作主題,其傳記式的故事結構和曲折復雜的情節為凸顯主人公的拼搏精神而服務,頌揚了為達目的不畏艱險的精神。正因為現實生活中有著種種不如意,所以觀眾尤其喜歡這類影片,這種影片常常給他們帶來自我激勵或逃避現實的情感撫慰。然而,一些觀眾也會唾棄這類白日幻想似的“心靈雞湯”,他們會對影片中的主角光環以及一味鼓勁、盲目樂觀的精神說教嗤之以鼻。
《爆裂鼓手》正是脫離了勵志片中主角萬能的陳詞濫調,通過傳達與主流意識截然相反的成功觀,達到反勵志的目的。盡管也是“嚴師出高徒”的橋段,但兩人的師徒關系一次又一次偏離勵志片的路數,兩人之間沒有惺惺相惜或者扶持互助,有的只是打壓摧殘與倔強的反抗,甚至到了最后一刻,兩人還在斗爭與算計。正是這種不按常理出牌的劇情讓影片充滿了層次感,原本在外行人眼中相對枯燥的鼓點也變得激昂亢奮起來,整部影片劍拔弩張的氣氛很好地表現了兩人之間的激烈對抗,也為觀眾帶來一種近乎自我毀滅的快感。
作為一部奧斯卡熱門影片,《爆裂鼓手》一方面非常符合美國的主流價值觀,它所表達的對個人主義的推崇、與對立面的抗爭以及對自我發展的需求,都迎合了大多數中產階級的審美趣味。另一方面,它對普世的鼓勵式教育方式進行顛覆,展現了對人物個性的扼殺以及對心靈的摧殘,這些無疑都帶有暗黑主義的色彩。就連影片編劇兼導演達米恩·查澤雷在接受采訪時也談道,《爆裂鼓手》的結尾其實是一種悲劇,盡管安德魯最后一場鼓打得讓人血脈僨張,但他的靈魂已經殘缺不全,他再也回不到最初的單純溫良,他對音樂再也沒有以往的赤子之心,他的職業生涯將像弗萊徹一樣,充滿了狠厲與算計。
二、人物設置與敘事基調
(一)魔鬼老師弗萊徹
要把影片中的弗萊徹稱為“良師”,相信大部分觀眾是不買賬的。如果說他那偏執極端的“天才如果放棄了就不是天才”的理念,和“寧可折磨死99%的學生也不放過一個天才”的暴力教育學只是教育理念的誤區,那么影片中段,明知學員被冤枉依然將其辭退的做法,和最后一段中,換樂譜蓄意陷害安德魯的行為,就絕對稱不上“讓人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苦心教導”了。哪怕當安德魯在這座世界頂級的爵士樂舞臺上最終完成了巔峰表演,二人目光相接時,弗萊徹露出難得一見的欣慰笑容,觀眾或許也只會滿心警惕,不怕以最大的惡意來揣度提問——這一幕算計到底有多少是公報私仇,又有多少是對學子偏執的逼迫?畢竟,如果安德魯沒有反戈一擊,他就會像弗萊徹曾驅逐或扼殺的無數學員一樣,在業界消失。
演員J.K.西蒙斯的確將弗萊徹演繹得既邪惡又立體。他的“毒舌”讓人隨時燃起反擊的怒火,而他強大迫人的氣場、暴君般恐怖的氣質又瞬間讓人又恨又怕地僵立當場。這種將瘋狂的控制和對名利的執著當成對學生的鼓勵,放任學生之間惡性競爭,為樹立威信不惜冤枉好人的做法讓他不僅算不得嚴師,他更像是陰暗的入魔者或偏執的藝術殉道者。
(二)精神爆裂的學子安德魯
鼓手安德魯本身也并非傳統的良善天才少年。出身單親家庭的他既沒有家學淵源,也沒有獨到的藝術天賦,他從父親那里獲取關愛,卻缺乏精神上的溝通與共鳴。他對成為頂尖鼓手有著堅定執著的追求,所以對弗萊徹的強壓訓練又怕又恨又報以希望。他的忍讓堅持以及最終表現在性格和手段上的變化恐怕源于內心深處對弗萊徹的一絲認可與贊同,從這個意義上講,弗萊徹又像是安德魯精神上的父親與導師,兩人之間的博弈與傾扎簡直稱得上是“相愛相殺”般的互虐了。
在弗萊徹極端的點化之下,安德魯像入魔一樣,每次練鼓時都能血沫橫飛,為了成為核心鼓手不惜在車禍后滿身鮮血地爬上舞臺,為了保持練鼓時的專注不惜以“愛情是藝術的阻礙”為由放棄了美好的戀情以及僅存的對美好生活的渴望。從謙遜平和的后備鼓手到肆意辱罵對手、精于掩飾和算計的種子選手,從閑暇時陪父親看電影并照顧父親零食偏好的乖巧兒子到偏激爆裂的叛逆分子,從單純地享受音樂到再也不會為音樂露出一絲笑容,安德魯越是勤奮刻苦,就越是與外界產生深厚的隔閡。盡管最終逼出了自己最大的潛能,卻實在稱不得讓人欣喜的成就,這一點從父親觀看兒子獨奏時臉上驚恐的表情就可見一斑。
(三)相互傾扎、相互博弈的師徒關系
影片沒有正面做出對弗萊徹式教育觀的評價,可是在支持普世教育觀的人眼中,這對師徒之間的關系無疑是扭曲的,弗萊徹所培養的這批“天才”也成為典型的悲劇式人物。安德魯因為絕地反擊也許從此名聲大噪,但那位因抑郁癥自殺的學生卻永遠失去了施展才華的機會。在瘋狂的強壓及扭曲的價值觀引導下,也許能逼出一兩個涅槃重生的天才,同時也有可能會無情地葬送一些沒有抗住壓力但天賦異稟的少年的夢想和才華。成為弗萊徹的學生之后,安德魯被激發的成功欲像黑洞一樣,吸走了他身上所有的美好,只剩下一個親情淡漠、拋棄愛人、算計隊友、瘋狂自虐的偏執狂。
換個角度看,也許弗萊徹和安德魯之間并不是單純的“師生”關系,影片開始時,安德魯無論是技藝的準確與熟練程度,還是為夢想拼搏的成功欲,都低于弗萊徹要求的水平。而受到弗萊徹點化后,兩人對藝術追求的心理高度已趨接近,他們就像一對鋒芒畢露的對手,類聚在一起,爆發出極致的藝術野心和寧愿粉身碎骨的偏執勁。影片結尾有如神來之筆,沒有像老套橋段一樣來一段春風化雨般的互助互愛,而是選擇更激烈的互虐,在疾風般的鼓點中產生藝術升華。
(四)疾風驟雨又暗黑壓抑的敘事基調
主角成功地獲得了通往頂級藝術殿堂的門票,但這無論如何算不得讓人暢快的結果。無論是影片陰沉的情節,還是昏暗壓抑的畫面色調,都與師生二人為藝術棄絕快樂的選擇相呼應,成為一部暗黑色調的反勵志片。
音樂是一種能撫慰心靈、帶給人快樂和感動的極致享受,然而影片雖然圍繞著爵士樂開展,但整部電影并沒有表達出爵士樂的美好,其中關于享受音樂的描寫也是屈指可數的:弗萊徹因為安德魯的指證被學校開除后,在酒吧里悠然深情地演奏鋼琴是他唯一一次表達對音樂本身的享受。安德魯在魔鬼訓練中始終壓抑的神情與幼時打鼓露出的燦爛笑容形成極大的反差。兩人只有在影片結尾處安德魯癲狂的爆發后,才露出滿足的微笑,而此時他們只是為勝利而笑,為終于滿足自身無限膨脹的功利心而笑,這一點與享受音樂無關。除了這有限的笑容,影片只剩下唾沫橫飛的謾罵侮辱和血濺鼓架的自虐報復,再沒有一丁點兒的溫情與快樂。
影片采用快速而錯綜的剪輯,加上對人物表情、鮮血、汗水、樂譜、樂器等詭譎的近景特寫,帶給觀眾強烈的視覺沖擊。在密集的鼓點中,以酷炫華麗的鏡頭感展現鼓手們的精湛技藝,呈現出一場無以倫比的視聽盛宴。然而這一切全部籠罩在“不瘋魔不成活”的極致瘋狂中——“溫吞就會造就庸人”“如果放棄了就不是天才”“沒有什么比隨便的贊美更害人的了”——所以,要成功就要忍受言語謾罵,要達到頂峰就要經歷剝皮拆骨的訓練,要成為團隊核心就要精于掩飾算計。正如影片英文名Whiplash所傳達的意思一樣,鞭笞,鞭撻,鞭伐,這就是影片傳遞的成功學。人物飽脹的情緒就淹沒在完美而精密的情節控制中,留待最后一刻爆發,這個話題讓人沉重。
三、結 語
《爆裂鼓手》之所以大獲好評,一定程度上源于它為勵志片提供了一個值得探索的新方向。這個琢玉成器、入魔飛升的故事不僅精彩在它一次次背離了人們對傳統勵志片的依賴與想象,還在于它所傳達的并不迎合主流的藝術主張。片中人物所遇到的皆是現實生活中隱藏在暗處的真實,不管它是否符合主流價值觀,它依然反映了社會上某個角落里的某種現實。藝術的極致追求與靈魂的干凈整潔是否能兼得?德藝雙馨是不是每個掙扎在路上的普通人能企及的高度?當安德魯在車禍中撞得渾身是血,還從車里爬出來堅持著趕去表演時;當他明知自己做不到,還在舞臺上不甘心地掙扎時,這種窮途末路的自尊、這種靈魂深處的卑微與掙扎表現得淋漓盡致,而這,其實是每個人在某一刻可能會體會的痛苦。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本片也有讓人在現實中激靈醒來的勵志效果。
當然,影片中人物的道德程度是值得批判的,基于這一點,導演有一個十分巧妙的設置:片中很多現場演出的橋段都刻意模糊了觀眾的存在,無論臺上表現如何,鏡頭里很少出現觀眾的掌聲。除了影片要刻意避免輸出價值觀這一目的外,還在于對于沉浸在自我狂熱追求中的弗萊徹和安德魯來說,他們的藝術追求本來就不打算迎合主流。他們這種孤注一擲的執著更加強化了反勵志的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