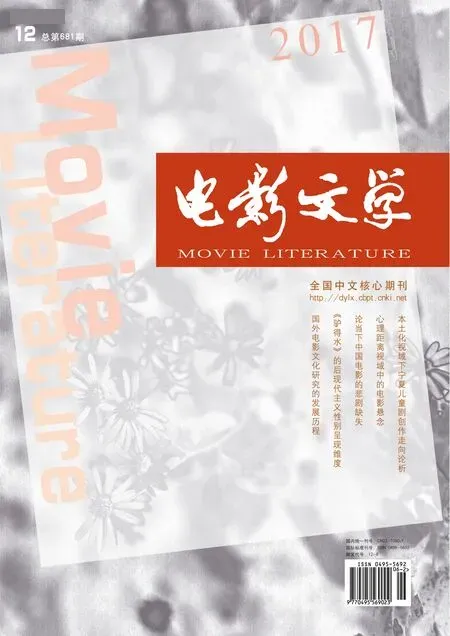論電影《驢得水》的歷史批判意識
崔永鋒 (大慶師范學院,黑龍江 大慶 163712)
《驢得水》是一部被知識界以及整個社會廣泛談論的電影文本,談論的范圍既包括影片內在的故事內容、主題意蘊、敘事方式,也包括外在的鏡頭設計、場景布置以及演員表演等。應當說這些面向文本本身的討論是十分具有建設性與啟發性的。但另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是,影片開始出現的字幕——“1942年 中國”,以及此后畫面中懸掛在樹樁上的民國國旗、“三民小學校”的牌匾、大總統掛像等,這些符號的作用一方面是出于敘述的需要,另一方面則不斷為電影建構歷史的真實感。一般情況下,文本中歷史真實感的作用是讓其獲得歷史反思與批判功能。從這個角度看,《驢得水》反思歷史的內容與意義究竟為何,便成了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
一、人物身份的轉換與隱喻
在影片中,銅匠的身份兩次轉換為“呂得水”老師,從表面來看,轉換后角色的思想、觀念、性格、精神狀態以及談吐舉止等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而更重要的則是這兩次轉化為其精神造成了難以治愈的創傷。
銅匠的第一次身份轉換是被動的。學校為了避免“領空餉”行為被教育部的特派員發現,校長和其他三名老師用盡手段讓他冒充“呂得水”老師。由于特派員的無知,這位假老師才能以毫無演技可言的表演和破綻百出的行為舉止蒙混過關,并且獲得“教育家”的稱號。特派員走后銅匠理所應當地結束了他第一次“教師生涯”,回歸到從前的生活。但作為“呂得水”老師的經驗對他自己的生活來講無疑是災難性的,就像他妻子所言:“就從你們這兒回去,回家活兒也不干了,天天整幾本破書擱那兒翻啊翻啊,叨咕叨咕,不知道說的哪國話。”這說明他在自己的生活中處于一種迷失狀態,雖然在現實中他的身份由老師轉為銅匠,但在其內心這一轉換尚未完成。
銅匠離開學校和張一曼道別時有一句舌誤:“我是老師,你是銅匠”,按照弗洛伊德的觀點,“舌誤本身都有意義。這就是說舌誤的結果本身可被看作是一種有目的的心理過程,是一種有內容和有意義的表示”[1]。在這一理論的基礎上,我們可以理解在銅匠的潛意識里,他希望自己的教師身份能夠得以延續,已經生成了的欲望在現實中卻無法得到滿足,這就是第一次身份轉換給銅匠帶來的創傷。
事實上,創傷的制造者既是三民小學的教職員工,也包括教育部特派員。前者出于貪念謊報了一名教師,并聲稱是為了養一頭驢解決用水難的問題。這個理由本身就值得推敲,養一頭驢的費用與一名老師的工資相比有多大差距,這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呂得水老師”工資的開銷中除了“飼料費、驢棚維修費、驢掌更換費”這類必需的費用,又出現了裴魁山的假牙費、張一曼的服裝布料費、周鐵男的健身器材費以及孫校長的眼鏡修理費等。上述四名教育者利用“呂得水老師”的工資為自己牟利,很難說不是一種變相的貪腐行為。特派員的不學無術與自以為是是鬧劇能夠持續進行并暫時收場的主要原因,如果他能以足夠的智慧揭穿這個騙局,銅匠就不會在表演中入戲太深最終難以自拔。
銅匠身份的第二次轉換是被張一曼侮辱后主動回到學校,以“呂得水老師”的身份向張一曼尋仇,而此時的人物性格發生了巨大變化,憨厚樸實被陰郁、殘酷和貪婪所替代。在得到特派員的支持后,他指使其他教師向張一曼實施多種暴力,最終導致后者精神失常。面對這段劇情,觀眾往往會因為同情張一曼而指責銅匠的行為過于荒唐與殘暴。而事實上,即便是作為施暴者的銅匠,其受害者的身份依舊沒有改變。銅匠的這種行為和變化在精神分析理論中能夠得到解釋:“欲望追求滿足會有三種結果:沖動無法進入意識和表象層,被‘壓抑’;表象層行為與精神活動指向一致,欲望獲得‘滿足’;表象層行為與精神目的不一致,‘反轉’成相反的欲望,比如得不到就毀掉。”[2]銅匠深愛張一曼,他一直將張一曼的頭發帶在身上便是證據。而他的愛不但得不到對方回應,對方還當眾侮辱他,說他是“牲口”,這就讓他對張一曼的愛欲反轉成了毀滅的欲望。張的頭發被剪掉后,他說他“滿意了”,這似乎意味著毀滅的欲望獲得了滿足。但事實絕非如此,當周鐵男再一次提起“牲口”二字時,銅匠便失去理智地質問周鐵男:“你罵誰呢?”顯然,毀掉張一曼的頭發并沒有讓銅匠的欲望得到滿足,而是超越與張一曼之間的關系轉化為對群體中所有人的仇恨,指使別人殺掉孫佳心愛的黑驢便是例證。事實上,銅匠的第二次身份轉換已經改變了他的本質。
應當說,影片中的三民小學不僅只有四名老師,其實還有一個潛在的學生——銅匠。第一次身份轉換時,銅匠將像普通的學生一樣,行為不斷被上述四人所規范,并從他們身上獲取知識,比如盡管有限卻貨真價實的英語短語。孫校長與銅匠的關系幾乎就是教育者與受教育者的關系,而整個教育活動的結果是不言而喻的。至此我們難免有此一問,如果銅匠隱喻的是學生,那么滿口謊言的孫校長、不負責任的張一曼、自私冷酷的裴魁山和霸道蠻橫的周鐵男這四名老師是否能夠擔當起教書育人的重任?
二、荒誕化的權力運作
對于權力的結構及其運作機制的另一種展現方式,是討論這部電影時不可回避的問題。在影片中,沒有一個確定的“權力者”,權力隨著人物關系的變化不斷生成,并且不斷被權力關系中的強力者所濫用與解構。
在大部分劇情中,代表國家機器的教育部特派員是圍繞其展開的權力關系中的強力者,并在各種關系中居于宰制地位。正是在這種形勢下,他一個人的力量便引發了一系列具有“黑色幽默”性質的情節,而當時社會所存在的種種問題也在這些情節中得以顯現。不懂英語的特派員謊稱自己有英國留學經歷,張一曼等人正是利用這個謊言,讓銅匠使用少數民族語言假冒英語授課,受騙后的特派員認定“只有呂得水老師有這個資格,有這個能力,來扛起這桿振興中國農村教育事業的大旗”。當事情的真相被周鐵男揭穿后,特派員毫無悔意,并聲稱:“老子說他是呂得水老師,他就是呂得水老師!教育部說他是教育家,他就是教育家!”在這個過程中,特派員并未對自己的錯誤承擔后果,而是以指鹿為馬的威勢扭轉了局面。這樣的權力運作得以完成,其保障因素包含了特派員的官員身份與握在他手里的槍。后者有效地揭露了當時社會體制的畸形化特征之一,即教育系統的官員擁有使用槍支并且以暴力與恐嚇的方式管理系統內部教師的權力。前者則有力地批判了“官本位”思想在當時教育界的地位,而這對教育本身而言才是最致命的。
在權力關系中植入暴力元素的結果是權力本身被解構,取而代之的是具有封建性質的專權與專制,這是影片對權力話語的另一種表現。被一顆擦身而過的子彈嚇破膽的周鐵男思想與性格所發生的巨大變化,就是最好的例證。按照福柯的理論,現代社會的權力話語特征之一是哪里有權力,哪里就有反抗,反抗是構成權力結構中的最本質的內容,“是權力關系中的另一極,是權力關系不可消除的對立面”[3]。也就是說,現代社會權力的運行必然后受到限制、沖擊、逃逸甚至斷裂,這實際上與西方資產階級走上政治舞臺后所提倡的民主與人文精神有關。然而在電影中,以三民主義為執政基本綱領的國民政府官員憑借暴力將權力關系轉化為君臣關系,這無疑是一種巨大的諷刺。
影片里權力關系中的主體是不斷變化的,這一點在銅匠身上表現得最為明顯,當他高聲朗讀“nice to meet you”,穿著裴魁山的貂絨進入觀眾的視線時,便不再是權力關系結構中的弱勢方,而成為整個群體具有壓迫性的中心。一組值得思考的鏡頭是銅匠進入房間后沒有坐特派員給他拿的椅子,而是直接坐到特派員的位子上,并毫不客氣地喝著特派員的茶。在中國傳統官場文化中,位子絕對是不可以隨便坐的,銅匠的“坐法”已經犯忌,而在未經特派員允許的情況下喝茶,這無疑是又一種冒犯。但特派員對銅匠這一系列舉動并沒有表示不滿,反而在此后的劇情中成為銅匠迫害張一曼的支持者。在這部分劇情中,銅匠的強勢地位源于美國人的“每個月十萬塊錢”,他合作與否關系到教育部或者說包括特派員在內的有關官員以后的收入,就是基于這一邏輯,特派員才不自覺地將自己置于弱勢境地。一句話,金錢讓一度驕橫跋扈的特派員變得卑微,這也反映出當時國民黨官員的金錢至上的價值觀。
三、女性意識的閹割
在男女平等的觀念下提升女性角色性別意識的自覺,已經成為國內外電影創作的一種潮流。比如《我不是潘金蓮》(馮小剛)、 《我的野蠻女友》(郭在容)、 《史密斯夫婦》(道格·里曼)等影片,都在不同維度上強調女主角的女性意識,其強調的結果就是締造出一個個生動鮮活又獨具個性色彩的女主人公形象。在一些影片中,這種女性意識甚至得到彰顯,例如《我不是潘金蓮》中的女主人公李雪蓮,其對自我意識的堅守、與不公正待遇的抗爭以及與男權社會權力群體的較量,都展現出從覺醒到抗爭的女性意識,這種趨于遞增趨勢的女性意識書寫和謳歌堪稱典范。女性意識在國內外電影創作中的凸顯趨勢,也符合當下社會中女性意識不斷增強的現實狀況,同時也反映出社會民眾在此問題上的期許,故而此類題材的描寫通常受到業界好評。影片《驢得水》中的女性意識,也得到了學界一定的關注,有學者指出,《驢得水》中的張一曼是個“忠實于自己身體與欲望的女性角色,她不僅在敘事上承載了影片最大的喜劇與悲情成分,而她自我意識的崛起與對自己身體的自覺掌握,又從一個側面預言了這個角色本身所存在的至大價值”[4]。然而在下文中,我們要討論的是另一個張一曼,一個被一步步“閹割”了女性意識的張一曼。
對于張一曼的“閹割”是由眾多男性角色經過一個較為漫長的過程完成的,其結果導致張一曼精神失常,這也意味著她不可避免地喪失了原有的女性意識。銅匠以呂得水老師的身份回到學校,開始實施對張一曼的報復,正是在這個過程中,“閹割”開始了。銅匠指使三名老師辱罵張一曼,裴魁山喪失理智一般從生活作風層面攻擊張一曼,語言極為惡毒。接下來,特派員讓周鐵男打張一曼“一巴掌”,將暴力行為升級,周鐵男沒有真打,為了避免場面失控,張一曼主動地一次又一次抽打自己。“閹割”活動最后的儀式是具有“去勢”象征的剪發,孫校長將張一曼曾經被銅匠稱贊“卷卷的,好看”的長發剪得七零八落,鏡子里的張一曼顯出精神失常的表情。影片的這段情節有效地展現出男權社會主體保證自身“霸權化”的運作機制。面對秩序的破壞者,居于社會主體地位的男性群體能夠迅速調動、組織,并采取有效措施對破壞者進行懲戒。在上述情節中,作為基層工作指導者的特派員沒有化解矛盾,而是不斷推波助瀾,將悲劇推向高潮;本是情敵的銅匠與裴魁山站到了一起,后者對張一曼的辱罵讓前者聽得心滿意足;以敦厚長者面目示人的孫校長,在聽到特派員的提議“那我們所有的人就罵她,罵到你滿意為止”后,表示“很公平,我同意”。顯而易見,他有意地忽視了這種懲罰行為從“量”到“度”的不公平性。從尊嚴到肉體,影片中男性角色們以極端到令人驚悚的方式對張一曼不斷實施“精準打擊”并最終獲得全面勝利。影片以上內容說明的是,以反封建為施政綱領之一的國民黨政權,并未將男女平等的理念貫徹到底,封建式的男尊女卑思想依舊深深根植于社會意識形態之中。
作為一部喜劇片,《驢得水》的創作者并未放棄對歷史的反思,反思的著眼點也具有以史為鑒意義上的現實價值。教師的素養、權力的運作方式以及女性的社會地位,這些話題在今天無疑是值得社會認真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