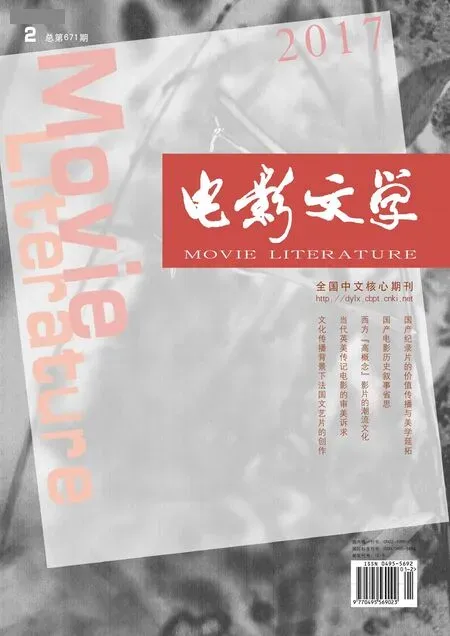李安電影的多模態隱喻
謝 靜
(三峽大學外國語學院,湖北 宜昌 443002)
隱喻并不僅僅是人們交流上語言層次的概念,它還與人類的認知思維有關。多模態隱喻原本是一個語言學概念,它關乎人們的識解機制,對采用多種符號進行審美創造的電影有著重要的意義。多模態隱喻的成立是一個互動的過程,它無法脫離人們的解讀而存在。華裔導演李安的電影向來以內涵豐富、耐人尋味著稱,在給予觀眾一個精彩故事之外,李安還總是隱晦地將自己的某種強烈的情感或對某件事物、某一時代現象的評價價值融入敘事之中。已經有批評者注意到李安電影中存在大量隱喻,但還無人從多模態隱喻的角度對李安電影進行深度解讀。李安的電影往往是一個復雜的符號表征空間,對李安電影的多模態隱喻建構過程,以及多模態隱喻對李安電影中情感效果和審美評價的影像,有必要給予一定的關注。
一、多模態隱喻與電影藝術
在討論李安電影的多模態隱喻之前,有必要對多模態隱喻的概念進行梳理。隱喻代表了一種人類對世界的基本認知方式,對隱喻的研究可謂由來已久。到了20世紀30年代之后,隱喻學開始進入語義學研究的領域,隨后多模態隱喻(multimodal metaphor)理論出現。如果說在修辭學與早期語義學中的隱喻,實際上還停留在語言層面這一單一的交流范式的隱喻的話,那么多模態隱喻理論則對隱喻的交流模態有所擴展。
多模態隱喻認為,既然隱喻體現的是人類在接觸外部世界時的一種基本思維,那么它必然不會僅僅存在于語言之中,因為人類對外界的認識,人類之間的交流方式是多樣化的,除語言之外,還有圖像、聲音和身體姿勢等。也就是說,多模態隱喻理論與傳統隱喻理論在對人類業已形成的概念隱喻體系的認同上并沒有區別,二者的區別僅僅是在于對隱喻表現方式的研究范圍上。多模態隱喻中的隱喻同樣指的是一種認知機制。多模態隱喻同樣認為,在隱喻中,人們面對始源域(source domain)與目標域(target domain),也就是英國文學評論家、語言學家I.A.理查茲所提出的本體與喻體,這一對概念也近似結構主義語言學家索緒爾的“能指”與“所指”。而連接起始源域與目標域的便是跨域映射,這種映射的建立過程就是人們對隱喻的理解過程。而多模態隱喻中,所謂模態指的便是符號系統。荷蘭認知語言學家、多模態隱喻研究的領軍人物查爾斯·福塞維爾指出,人類認識不同的符號系統使用的往往是不同的感知方式,如在認識圖像符號、書寫符號、手勢符號時使用的是視覺,而在認識聲音符號、音樂符號、語言符號時需要動用聽覺器官,除此之外,嗅覺與觸覺也同樣可以幫助人領悟隱喻。
相對于隱喻研究來說,電影藝術的誕生則要晚得多。但電影這門后起藝術卻極大地改變了人們的表達方式。電影中存在圖像、圖形、構圖和聲音,甚至可以出現文字(根據克里斯蒂安·麥茨的理論,上述元素均可視作符號),這極大地削弱了文字符號曾經在意義表達上面的壟斷地位——早先人們使用純粹的文字創作來運用隱喻,而電影則能同時調動起人們的視覺與聽覺,甚至更多關乎人們心智的感官,而其中視覺感知更是具有一種感性特權。盡管并不能斷言電影一定比文學傳遞出來的信息量更大,但就隱喻而言,電影的表征方式相對文學更豐富,且受時間限制更多,給接受者的印象也需要更為直觀和深刻卻是不容置疑的。因此,多模態隱喻被引入電影批評領域也就不足為奇了。
誠然,是電影先有其表達方式,隨后多模態隱喻才被用以觀照電影藝術,但電影藝術在發展過程中,一部分熱衷于哲理思辨和思維編碼的導演們也會主動采用多模態隱喻的手法,將電影的拍攝和放映變為一場多媒介符號彼此交織的交際過程。李安這一信奉“外儒內道”,深愛隱晦、含蓄和玄妙表達方式的導演,便是其中一例。
二、李安電影的多模態隱喻運用
在李安的電影中,多模態隱喻的運用一般都是以視覺模態、語言模態以及聽覺模態三種模態結合的方式出現的。李安力圖在最短的時間之內,根據不同模態的特點,讓它們以各自擅長的方式來為主題的推出服務,最終完成整部電影形象的打造。這三種模態各有分工,同時也是彼此協作的關系。
(一)視覺模態
毫無疑問,電影最突出的特征便是生動而豐富的畫面。相較于語言模態與聽覺模態,視覺模態無疑顯得更為直觀,也更有助于提升電影的審美價值。在李安的電影中,視覺模態也是運用得最為普遍的。例如,在《推手》(PushingHands,1991)中,電影罕見地以一段毫無對白的影像開場。在這七分鐘之內,身穿藍色中式練功服的老朱有板有眼地在兒子家的客廳中練太極拳,時不時還會發出肢體碰撞的拍擊聲,甚至為了獲得更大的練習空間,精神矍鑠的老朱還自己搬動家里的家具。而在書房中,老朱的美國兒媳婦瑪莎則面對電腦鍵盤遇到了寫作的瓶頸,于是她無奈地或是去開冰箱吃蛋糕,或是抱臂盯著電腦屏幕一言不發。很顯然,公公的存在對她造成了干擾。李安有意運用了一個在室外拍攝的鏡頭,觀眾可以明顯地從左右兩個窗口中看到身處兩個房間的這兩個年齡、性別、文化背景均不同的人。從這一視覺空間的分割中,老朱與瑪莎身處同一屋檐卻有著一觸即發的矛盾的隔閡感。隨后二人的正面沖突同樣是通過視覺來呈現的,老朱的早餐是米飯和中式的菜,而正在節食的瑪莎的早餐卻是果汁、餅干與水果沙拉。瑪莎因為老朱將錫紙放進了微波爐而對他說著他聽不懂的英文。這種在飲食上的區別便是兩種文化的區別在視覺模態上的隱喻。甚至為了強調這一點,李安還設計了老朱一個人在客廳看錄像帶時錄像帶中是表現晚清中國人吃飯的電影,一來再次用飲食來表現老朱的思鄉之情,二來電影人物吃飯而不說話,又意味著老朱依然很寂寞,而瑪莎依然受著干擾。
(二)語言模態
語言的特殊之處便在于其有釋義功能,另外,語言模態相對于視聽覺模態來說也有著后者無法比擬的準確性。這其中最為典型的便是《少年派的奇幻漂流》(LifeofPi,2012),李安在這部電影中不僅給觀眾獻上了一場3D視覺盛宴,更是由于電影主要是由兩個由人敘述的故事組成,因此其中帶有豐富的、雙重的(即導演本人運用的以及電影中派在敘事時運用的)語言模態隱喻。以派的名字為例,派原名“派西尼·莫利托·帕特”,因派西尼的讀音類似于英語中的“小便”而自己改名為“派”,即數學常數π。這個名字就有著多重隱喻。首先,它的使用直接反映了派家庭中父母的不和,而父母的不和直接意味著理性與宗教的沖突(派的母親是虔誠的印度教徒,父親則因為曾被西醫救活而篤信現代科學,認為宗教是騙人的),派本人出生在這樣一個家庭中,他的思維、生活方式與信仰構成都是多元的。其次,派本人對名字的改動是有著自欺欺人意味的,這也隱喻了他未來敘事的不可靠性,因此,在面對兩個前來采訪他的日本記者時,派才會給出兩個截然不同的故事,并告訴記者“你愿意怎么寫就怎么寫”,顯然派希望不可靠敘事被延續下去。而從派改名這一帶有“自我美化”的行為來看,很有可能他將殘酷的事實用語言包裝起來了。
(三)聽覺模態
聽覺模態包括聲音、音樂,它能夠在短時間內營造某種氛圍,觸發觀眾記憶,培養觀眾的情緒,能夠較為高效地提高電影的觀賞性。另外,聽覺模態是必須與視覺模態一起來傳達導演的意圖的。如在《臥虎藏龍》(CrouchingTiger,HiddenDragon,2000)中,在表現李慕白與玉嬌龍追逐于竹林之中時,作曲家譚盾在配樂中雜糅了中國戲曲,視聽方面都以“程式化”的方式來顯示他們打斗的一靜一動,一穩重一輕靈,并且這種打斗是屬于中國的,兩人的追打隱喻的是兩人在性格、世界觀上的巨大差異。與之類似的還有如玉嬌龍與羅小虎相愛之時,配樂中出現了維吾爾族的樂器熱瓦甫,熱瓦甫與當地沉寂的沙漠都隱喻著兩人闊朗、凜冽、追求自由的天性。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在此不再贅述。
三、李安電影中多模態隱喻的意義生成
只有最終的意義得到生成,多模態隱喻的工作機制才稱得上是有效的。李安電影存在一個巨大的意義網絡,這吸引著觀眾不斷推斷每一個隱喻背后的真正含義。李安電影多模態隱喻的意義生成主要有兩個特點:
首先是時間上的錯位性。如前所述,隱喻中存在始源域與目標域,但是二者一般是不會同時出現的,在大多數情況下,始源域在電影敘事中具有先行的姿態,而目標域的出現則往往是遲滯甚至是隱身的。這樣一來,吸引觀眾,促使觀眾進行思考的懸念就得以生成。例如,在《喜宴》(TheWeddingBanquet,1993)中,喜宴貫穿始終,然而觀眾并非在觀影時就能明白喜宴影射的對象。觀眾可以看到,對于年輕一代的偉同等人來說,所謂的喜宴是一場需要從簡的假婚禮,而對高爸爸、高媽媽來說,喜宴是飲食上升到“中國式婚禮”的象征。李安特意安排了高爸爸是一個曾經為許多人主持過婚禮的人,因此他必然會比他人更看重自己兒子的喜宴。無論是中國觀眾還是西方觀眾,都要在這場“喜宴”塵埃落定之后,才能悟出喜宴的真正含義,即中國人極為看重的,與人情往來緊密相關的形式。除此之外,喜宴還有著更高一層的隱喻。單純指形式的話,這一形式即使換成是清明掃墓、中秋團聚等也是可以的,只是喜宴在中國人的觀念中還代表了“傳宗接代”的婚姻大事。這種形式既是讓人苦不堪言的,但又是中國人不愿意失去的,因為它還關系著某種性壓抑下的狂歡。人們在嘈雜熱鬧中表現出西方人難以理解的,中國人平日含蓄儒雅背后的瘋狂。這種微妙的指向是包括“只緣身在此山中”的中國觀眾都難以馬上明白的。
其次是目標域的不確定性。根據后結構主義的觀點,任何隱喻的意義都是具有開放性和不確定性的,因為隱喻的創造性使用是依賴于具體的語境的。這一理論在電影藝術中便體現為,觀眾對電影中呈現的事物與他者之間存在何種相似關系,具有何種共同特征的察覺和認知是與觀眾所處的具體語境有關的。導演的創作過程是模態輸入,實現隱喻生成的過程,這個過程中存在導演主觀上認可的映射指向與意義合成目標,但最終的意義生成是由接受者(即觀眾)來完成的,觀眾所需要做的工作便是相似性聯想。換言之,并非所有的觀眾都能夠把握李安電影中隱喻的意義,更難以把握李安設置多模態隱喻的運作方式。李安部分電影給予了電影批評者和觀眾“解謎”的快感,不少觀眾表示在離開電影院時依然是帶著疑問與思考的。這種將觀影過程變為解謎活動的行為也增加了電影的可看性和對未觀影者的吸引力,使電影能在長時間內作為討論熱點與研究對象。正如在《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中,派對記者說的話其實也是李安本人對觀眾說的,即觀眾愿意怎樣理解這部電影就怎樣理解,比如究竟電影中的老虎是否隱喻著人內心中獸性的一面,在西方文化中通常被認為是卑鄙無恥的鬣狗是不是隱喻著善于處理食材、和派一家曾有過沖突的廚師,等等,李安都沒有給出標準答案。
一言以蔽之,多模態隱喻的運用豐富了李安電影的內涵,增加了李安電影的藝術魅力,也使得李安在東西方文化的碰撞之中找到了一個平衡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