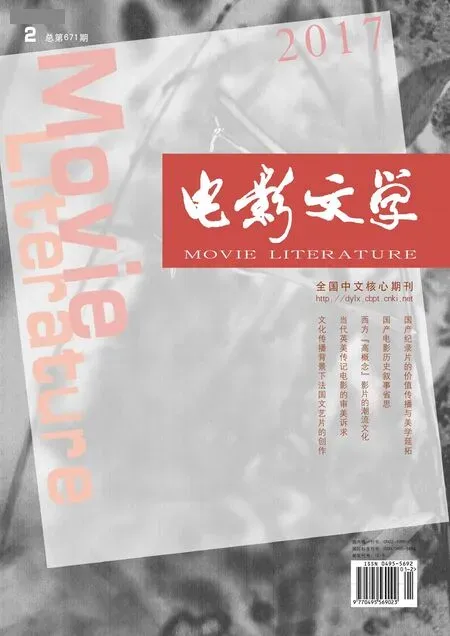《路邊野餐》的意識流與意象派風格
陽 雯
(重慶廣播電視大學,重慶 400052)
2015年,年輕導演畢贛憑借《路邊野餐》分別獲得第52屆臺灣電影金馬獎最佳新導演獎、洛迦諾國際電影節最佳新導演銀豹獎。2016年,此片繼續在各個國際電影節上屢屢獲獎。
《路邊野餐》講述了在貴州凱里,曾經入獄9年的陳升,出獄后孤苦一人,母親與前妻都已死去。陳升在診所當醫生,情感寄托是同父異母兄弟老歪的兒子小衛衛,老歪不務正業、成天賭牌,衛衛被送到鎮遠,陳升為了母親的遺囑,也為了尋找到一點對世界的聯系與愛,走上了尋找衛衛的旅程。離開之前,同樣做鄉村醫生的老醫生(女)托付了一些舊物讓陳升交給自己在鎮遠的舊情人(林愛人)。陳升在去鎮遠的路上來到蕩麥這個地方,遇到了與自己死去的妻子張夕相似的女人(過去),遇到了同樣叫衛衛的摩的司機(未來),最后用望遠鏡看到小衛衛在花和尚(曾經陳升混社會時追隨的老大)的照顧下開心自在地生活就離開了。電影是一個上路與尋找的過程,尋找的不過是男主人公的內心,他入獄9年后出來物是人非,9年的時間仿佛一個斷層,如何諒解過去?如何與未來握手?電影將過去、未來的隱喻人物放到蕩麥的時空里,具有幻象的色彩。與過去告別、與未來握手,是陳升內心悄然發生的變化,在外在戲劇化情節淡化的節奏下,人物內心的變化成為電影的主題——時間與和解。
《路邊野餐》的敘述方式具有意識流電影的特點:自由聯想、片段閃回、夢境、夢幻、時空錯亂。所謂“意識流”來源于20世紀的文學術語,受美國心理學家威廉·詹姆斯、法國哲學家伯格森和奧地利精神分析學家弗洛伊德等的理論影響,指人的心理真實狀態直接在文學上的呈現,打破傳統的外在敘事模式,將關注的視角由外部世界轉向意識領域,發掘人們心理上的重要瞬間。[1]人的真實心理狀態由無邏輯、非理性的潛意識等構成,經常時空跳躍,又像一條永不間斷的河流。意識流的觀點由文學走向了電影,被公認的意識流電影代表作有《野草莓》《廣島之戀》《去年在馬里昂巴德》等。[2]雖然《路邊野餐》的主線依然是人物的外在經歷,但人物的心理內線占的比重也非常多,特別是多次無關聯的畫面閃回,相同夢境的多次重現,蕩麥這個時間錯亂的迷幻時空與迷幻人物,使這部電影具有意識流電影的風格。
還有人認為《路邊野餐》沿襲了俄羅斯導演安德烈·塔爾科夫斯基的“詩意電影”,因為這部以詩歌穿插情節、大量詩歌意象堆砌、缺乏高潮線性戲劇化發展的電影,更多的是一種哲理的思考與情感的傳達,偏向于心理電影的風格。[3]當然,正如畢贛自己所說,他拍的只是自己想要的電影而已。雖然兩者都有重視人物心理狀態的非線性敘述風格,但在表現手法與意象上畢贛有自己的偏好與特點。
《路邊野餐》具有“意識流手法”與“意象派詩歌”兩個明顯的特點。為了細化電影片段的風格,以電影中出現的八首詩為界限分析如下:
一、第一首詩的空間——現實與意識流閃回
電影的開頭,陳升病了,咳嗽老不好,同樣在診所工作的同事老醫生(女)回憶說他上一次生病還是結婚的時候,這種講述提醒了老陳對前妻張夕的懷念。陳升去找小衛衛,門鎖換了,他還是撬開門鎖,帶衛衛出去吃粉、玩游樂園的車。在這一段敘述中,衛衛家里掛了一個類似于舞廳的金屬球燈,陳升關門的一剎那,閃回記憶了與前妻張夕相識時舞廳的金屬球燈,然而這幾秒鐘的閃回并沒有情節,只是一個模糊的紅衣女人的影子以及球滾過來的聲音,沒有起到交代情節的作用,只是陳升意識流的短暫出場,觀眾也意識不到這是陳升的前妻,片段非常個人化。衛衛的父親老歪和陳升是同父異母的兄弟,他非常不喜歡陳升,話中帶刺地拒絕了陳升想把衛衛帶去和他同住的想法。陳升晚上睡覺時在夢里聽到水聲與蘆笙混合的聲音,醒來在陽臺上站了一會兒(陽臺又出現一個金屬球燈),接著電影開始念出第一首詩。
開頭不到10分鐘,就穿插進大量意象,如野人、酒鬼、買香蕉、拾荒老人、夢中的水聲與蘆笙的聲音……這些意象是為了情感表達的豐富,電影鏡頭敘述上整體具有意象派詩歌的特點,以上意象是為了提示一種相關的情緒與感情。[4]而觀眾是否感受到了神秘、恐懼、迷惑、懷舊、夢幻等情緒,需要觀眾自己對畫面意象進行審美體悟,并且觀眾的體會是多元與開放式的。念第一首詩時出現的床頭花瓶、去掉護罩的風扇頭畫面以及窗邊取下的風扇葉、《路邊野餐》詩集的畫面,也是增加觀眾審美感受的群體意象。
二、第二首詩的空間——現實與魔幻
陳升去上班,給小孩打針、安撫小孩。與老醫生交談,老醫生說起往日的戀情,陳升在聽她講述年輕時舊情人(林愛人)用手電給她暖手的情節時,頭腦閃回了前妻張夕坐在那里時的一雙手,觀影的觀眾當時并不知道這是誰的手,這個畫面依然是非常個人化的,沒有交代情節的作用。聽著老醫生的談話,陳升的思緒就這樣跳躍出去,電影展現出人物意識流的變化,也是意識流風格電影體現出的時空無限性。[5]特別是當衛衛表示想和花和尚去鎮遠時,一個魔幻般的鏡頭出現:綠皮火車在衛衛家墻壁上駛過,在哐當哐當的火車聲中,場景慢慢消失。這個鏡頭是誰的意識投射是不可指的,更多的是導演大膽呈現出的意識流拼接空間。
在這一段,有意味的意象包括:舊輸液瓶、挖掘機操作、老歪摩托車右視鏡下的紅帶、衛衛畫的鐘芯的影子順時針轉動、夢里的藍色布鞋、野人的消息、風扇、老歪抓魚苗喂烏龜,這些意象對電影情緒起著烘托的作用,可以暗示出陳舊與埋葬、精細、時間、懷念等,然而這些體悟都是非常個人化式的審美,電影留給了觀眾大量開放式的審美空白去自由感受。
三、第三首詩的空間——現實與非線性插敘
陳升與老醫生在天臺上一起吃飯、飯后談話,陳升說到自己的夢以及往日混社會跟隨花和尚的事。就在收拾停當時,突然沒有預兆地插敘閃回到過去他與張夕在舞廳玩球,別人讓他唱歌的回憶。
陳升質問老歪小衛衛的去向時,也是沒有預兆地插敘閃回到過去陳升為了老大花和尚兒子的事去與一個女子對質。兩次非線性敘述插敘,打破了穩定的電影“現實”時空,由于插敘時上下邏輯缺乏關聯性,所以非常突兀,使電影具有時空雜糅之感,增加了觀眾初次觀影時的難度。
四、第四首詩的空間——現實與回憶
陳升與老歪打架被勸下。陳升找老歪談話,問衛衛被賣到哪里去了,提及房子分配和衛衛歸屬的事情,老歪最后說花和尚把衛衛帶到鎮遠玩去了。陳升躺在沙發上,老醫生給他拔火罐,說到她的舊情人林愛人病了想見她。陳升表示要去鎮遠,老醫生想讓他帶點東西給林愛人。陳升的旅程中,火車車廂內只有陳升一人(這個畫面具有魔幻的色彩),火車搖晃著,陳升漸漸進入回憶空間……
這一段出現與主線相關不大的意象是“魚”。陳升到魚店里自己站上稱稱重,老板說影響他做生意了,魚在空籃子里擺動。“魚”這個意象與前面老歪用小魚喂烏龜產生相關的聯想。“魚”是與主線情節相關不大,卻又多次出現的意象(后面“魚”被凍在冰箱里老醫生等陳升回去吃),對于情節發展并沒有推進作用,更多的是表現一種審美的開放式意象空間。
五、第五首詩的空間——回憶倒敘與進入時空交錯的蕩麥
回憶中陳升提著木箱子出獄,在河邊坐著,一個朋友來接他,這個情節雖然是回憶,卻非常完整。陳升開車,車上廣播新聞回應了老醫生兒子死時看到野人。陳升講述了自己在監獄中的遭遇,以及聽朋友說起母親、前妻已死。這一段的表現手法是鏡頭在汽車前擋風玻璃的位置,人物不出鏡,畫面呈現了車窗前崎嶇的山路與團團迷霧以及人物對話的聲音,表現形式具有夢的心理色彩。
回憶結束,陳升下了火車,跟著幾個苗人進了隧道,來到蕩麥。陳升坐上摩的司機衛衛的車去找會吹蘆笙的苗人……
六、第六首詩的空間——時空交錯的蕩麥
人們告訴陳升苗人師傅出去了,陳升想回鎮遠,他坐上演出隊的汽車,路中遇到被人整的摩的司機衛衛去幫助他。成年衛衛站在一個水桶里,頭上還戴一個水桶,背著手在數數(對應了小衛衛和陳升坐游樂園車時在數數)。陳升幫衛衛開了摩托車的鎖(對應了陳升幫小衛衛開門鎖),陳升請衛衛吃粉(對應了陳升帶小衛衛吃粉)。
陳升遇到理發店的女子,大概因為長相與前妻張夕太相似,陳升馬上跟隨而去,在理發店里和女子講起自己與妻子的故事,女子似乎也因為故事而情感有所觸及。在看演出隊演出時,陳升為女子唱起《小茉莉》,女子感動。陳升把磁帶《告別》給女子。就在衛衛送別陳升的時候,陳升獨自在河邊,畫面突然閃回了張夕靜靜坐在那里的全身,這次觀眾才看清楚了陳升記憶中的妻子。
電影技法上議論最多的即是蕩麥這一段的“長鏡頭”跟拍表現手法,搖晃不停的綿延感,對應了蕩麥這一幻象空間。導演自己解釋這一段的美學是“它變成持續的時間,持續的空間,但里面的文本意義又不是一個持續的時間。它們交互在一起時就產生了超現實”[6]。鏡頭就像蕩麥空間里的在場者,并且可以自由來往,還可以不與電影人物同步走自己的路(衛衛的摩托前行,鏡頭抄近路,鏡頭和摩托錯過后再次交接),這就像人類夢境中的自我感受——夢中的自我作為第三者不參與劇情而自由來去的在場感。
蕩麥這個空間是魔幻的,這里是過去(死去的張夕)與未來(長大后的衛衛)共同存在的空間,陳升在電影中說:“這就像夢一樣。”在現實電影空間里插入這個空間,是導演一個大膽的創想,他讓陳升的心理狀態在這個空間里完成告別的準備。
七、第七首詩的空間——和衛衛的告別
花和尚帶陳升去找衛衛,陳升用望遠鏡看到孩子自在的生活。
八、第八首詩的空間——替老醫生跟她的舊情人告別
找到知情人得知老醫生的舊情人(林愛人)已死。陳升在火車里,兩列火車對面交會重逢,陳升在火車上睡著了,而前面的情節陳升出發去鎮遠的路上也在火車上睡著了,電影蒙太奇的藝術,會讓觀眾迷惑:所以,蕩麥以及一切已經完成的告別都是一場夢嗎?陳升只是在去鎮遠的火車上做了一個夢?這個問題是沒有答案的,也是無需答案的,因為電影主題即是呈現一個人的心理狀態完成的告別,現實狀態只是陪襯。
導演畢贛的美學態度是非常獨立的,他只在貴州拍自己想要拍的東西,一個不考慮迎合觀眾的導演,更多地拍出了自我想要的審美空間。他喜歡侯孝賢的電影,欣賞《南國再見,南國》中的畫面,在這部電影中有相似的風格,正如他自己所說:“我夢想拍摩托車和火車的POV鏡頭,這次都拍到了,特別高興。因為自己喜歡,所以就拍了。”[6]正因為不過多地“顧忌”觀眾的接受,所以文藝片的個性化才展現出來。
影片中多次出現的意象還包括鐘表,它出現在墻上或者車上,象征過去不可追,時間不可回。另外,野人、夢境中的繡花藍布鞋、背手的姿勢、買香蕉、經常打不著火的摩托車、摩托車上的紅帶子等,這些意象多次出現,就像詩歌中有意味的形式,但所指是開放多元的,留給觀眾審美的空白與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