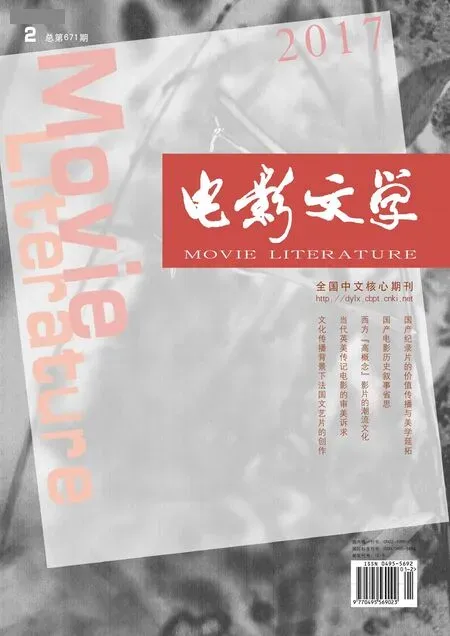《致青春》:被市場所消費的“青春”
王連峰
(山東青年政治學院,山東 濟南 250014)
《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簡稱《致青春》)是著名演員趙薇擔任導演的處女作。據相關統計,這部電影在上影當日即突破4500萬元票房,超越《泰囧》(首日票房3500萬元),刷新了2D電影史華語片首日票房紀錄,也超越了《鋼鐵俠3》等美國大片。七日內《致青春》再收3.3億票房,在內地上映一個月后,累計票房更是超過7億,趙薇也因此成為當時華語電影票房成績最高的女導演。電影的觀看熱潮甚至波及投資方在資本市場的表現,據新華網財經頻道調查,受《致青春》不斷升溫影響,電影投資方光線傳媒股價不斷攀升,自2013年4月12日公司除權除息之后,其股價上演了強勢填權行情,14個交易日股價已累計上漲60%。
仔細看來,這部電影的命名有些欠妥,雖然從不同的角度看,對“青春”的定義不盡相同,但該影片主要是講述青年的大學生活。在多姿多彩的大學生活中,導演也只是重點選取了愛情和友情這一熱點內容。大學生活是人青春時期的一個重要階段,大學時代的愛情和友情也彌足珍貴,但這些不是青春的全部,只是青春的看點,電影其實主要是在“致我們逝去的大學愛情”。
經過多年的培育,中國內地電影市場日益成熟,商業電影價值模式也基本成型。電影“藝術性與商業性共生”的二元價值模式也為大家所接受。“電影首先是一種商品”,既然是商品,就要研究商品的消費市場。據陳樂一、路寧濤等2010年所作的《我國電影消費問卷調查分析報告》,電影消費群體中18~35年齡段的人數最多,比例高達73.51%。可以明顯地看出青年人是電影市場的消費主體。從這個意義上講,對市場細分,針對特定群體的觀影需求進行電影創作,抓住最具觀影可能的觀眾心理,就能夠把他們吸引進影院,從而抓住票房。此外,《致青春》檔期安排在最佳的時間——五一假期,女主角名字“鄭微”也與導演“趙薇”有著若干通聯之處。加上娛樂圈曾經熱炒一時的“趙薇陳坤失和”事件以及陳坤所言趙薇聲稱“要抓住所有的宣傳點”等事件,雖不可辨其真假,但這的確證明導演對影片市場是進行過完備的策劃和推廣了。
《致青春》中所展現的大學生活,是70末或80后所共同經歷過的,幾乎每一位70末或80后,都能夠在影片中尋找到自己彼時的生活狀態。這部分70末或80后,正逐步進入人生中壓力最大的階段,觀影成為他們主要的娛樂與消解生活壓力的手段。對逝去的青春生活的回憶、追悔、祭奠幾乎是所有70末或80后的心理共鳴。正如《中國經營報》記者朱耘在《〈致青春〉:用“酸澀青春”撬動億元票房》中提到的,電影是在“用文青符號元素建立品質和話題制高點;用懷舊青春情感元素猛攻龐大屌絲市場”。應該說,電影抓住了最大的市場觀眾的心理共鳴,用觀看電影的方式與影片、導演一起回顧了自己“已經逝去的青春歲月”。
商業模式的成功,是商業電影的現實基礎和現實意義,是優秀電影的重要評價指標之一。但電影的“商業——藝術”二元價值評價模式顯然告訴我們:真正優秀的電影必須在這兩個層面都經得起問詢和推敲。顯然,《致青春》在取得電影票房成功的背后,也難掩其故事模式陳舊、青春價值迷失的尷尬境地。
一、經典而陳舊的故事模式
因“文革”的影響,20世紀70年代出生的人群中,以1976年為界,1976年之前出生者與1976年之后(70年代末)出生者在教育環境、社會環境和成長潛能等方面均有所不同,就其成年后的群體表現來看,70末與80后有更多的相似之處,在社會群體研究中,很多將他們歸為類似研究對象。自本世紀以來,這個群體正遭受著有史以來最艱難的生存夾層,面臨著獨特的群體性生存焦慮。南開大學周志強教授在《東方早報》撰文《“80后”集體焦慮是社會轉型的代價》,指出“80后開始走出象牙塔,走向柴米油鹽醬醋茶的現實人生的時候,現實的壓力紛至沓來,種種改革的不良后果,幾乎都由80后這一代來承擔”。對于這個群體而言,這部能夠幫助他們回憶與祭奠剛剛逝去的無憂無慮的青春時代的電影,一定能夠極大地引起他們的興趣。
作為男女主角的陳孝正與鄭微的愛情自然是影片下大氣力進行敘述的內容。雖然他們戀愛的過程充滿了曲折甚至離奇,傷感中夾雜著幽默、苦澀中包含著甜蜜……但無論如何,它就是一部老掉牙的歡喜冤家匯,遵循著“不是冤家不聚頭”的敘事策略和“分—合—離”的敘事邏輯,夸張的情節和表演、搞笑的細節和對白以及對觀眾“如見故人”的觀影心理的滿足,是該部影片情節和故事安排的基本特點,從這個層面上講,這個故事真的毫無新意可言。導演似乎注意到了這一點,鄭微最后主動向初戀男友林靜去表白的情節安排,應該是刻意為之,目的就是為了打亂觀眾已經覺察到的陳、鄭二人“冤家匯”敘事節奏,卻不料又重新進入“林靜、鄭微”新的“合—分—合”邏輯中,演繹起新一輪的“冤家匯”。到最后又來個不了了之,沒有交代兩人感情的最終結局——甚至連結局的暗示也沒有設計,顯得有頭沒尾,牽強附會,或者說,為了曲折而曲折。與已經在商業電影的大路上漸行漸遠的前輩相比,趙薇在電影的情節把握、敘事調試、文化開掘上,還顯得較為稚嫩,基本上還停留在20世紀90年代《甲方已方》等電影的水平上。技法上主要使用“小人物、小故事及非主流敘事”,缺少“歷史人文向度……游離于具體的歷史語境及文化背景之外”①。當然,作為演員“大姐大”的趙薇,不過是導演行業的新兵,初戰即取得票房大捷確屬難能可貴。這也符合導演的成長都要經歷一個從“講故事”到“講思想、講文化”的轉變過程這一基本規律。
除了男女主人公外,《致青春》描寫了各式各樣的大學校園愛情,可以說,影片幾乎涵蓋了校園愛情的全部模式。以至于凡是經歷過大學生活的人,都能夠從中找到自己的影子,或者找到自己最熟悉的同學、朋友的影子——這對剛剛逝去青春年華的80后(含70末)來說,極具殺傷力:默默單戀從不敢表白的(張開),視優越的物質生活為愛情全部意義的(黎維娟),為自己愛戀的人甘心付出一切的(阮莞),爭風吃醋大打出手的(許開陽),雙雙失意者相互結合在一起組成家庭的(許開陽、曾毓),視愛情高于事業的(鄭微、阮莞),視事業高于愛情的(陳孝正)……懷舊情結是人類的情感本能,通過對已逝的美好時光的回顧,借以撫慰因對現實生活不滿而產生的焦慮,是觀影者最大的心理動因。
商業電影本來就不以離奇的敘事為己任,相反,它更希望向觀眾展示類型化的故事,目的就是讓觀眾在觀影過程中能夠獲取告知者的地位并進而幾乎本能地站在導演的立場上,這種觀影后的“滿足感”是讓觀眾對影片產生正向評價并自愿地擔任影片義務推銷員的有力武器。或者說,導演把握住了電影的市場消費主體,讓影片的各個要素都能夠緊扣消費者的消費心理,以求得心理共鳴,吸引觀眾。
二、“青春”價值的迷失
青春不是孤立存在的,成長必然是個過程,這個過程要伴隨著家長、教師、學校和社會的引導與教育,以及自身的思想行為不斷地完善與升華。但是,影片卻將“青春”的價值迷失在對父母形象的顛覆與懸置、對學校和教師形象的嘲諷與戲謔、對青春意義模式的莫名與消解中。
(一)對父母形象的顛覆與懸置
對父母形象的顛覆。影片講述了兩對父母的形象,一個是陳孝正寡居的母親,嚴厲而苛刻。這極大地影響了陳孝正的性格,使他內向、自卑、輸不起。另一對是林靜的父親和鄭微的母親,他們是以“奸夫淫婦”形象出現的。他們不但沒有給孩子們的青春歲月以積極的引導,使家庭教育意義空缺,更沒有給孩子們以積極的“正能量”青春示范。甚至從某種意義上講,他們反而給孩子們的青春正常發展造成了巨大的阻力和障礙。因為林靜看到父親與鄭微母親有私情的一幕,進而對愛情的美好產生懷疑甚至憤怒,促使他逃離了鄭微。盡管后來鄭微對林靜講“如果犧牲掉我的感情,能夠成全他們,我毫不吝惜……”但這種評價已經不再屬于青春期的觀點,也無法對應青春少年當時的思想狀態。從某種意義上講,這種情節的設計,有著濃濃的“父債子償”的味道。
對父母形象的懸置化處理。無論是陳孝正去世的父親還是寡居的母親,或是偷情的林靜的父親與鄭微的母親,在影片中均沒有設計臺詞,只有細節表情。這種片斷式的展示,導致人物形象本身符號意義大于實際意義,使其平面化、懸置化,無法構建起“父母”甚至“家庭”的完整形象,使主要人物的成長背景虛幻化、縹緲化,這直接動搖了“青春”的根基。
(二)對學校和教師形象的嘲諷與戲謔
對學校育人環境的嘲諷。宿管科的老師一邊批評學生,不允許他們使用電爐,一邊自己偷偷地從電鍋里撈出一個茶葉蛋。黎維娟形容女生公寓像“野獸出沒的叢林”,還說:“大學生活太令我失望了,太浪費生命了,寶貴的青春就這么糟蹋了。”朱小北被學校商店懷疑成“小偷”,這對處于青春期的青年人來說是“被踐踏了人格”。在青年學生人格和價值觀念形成的關鍵時刻,作為學校管理者,在處理這樣的事件時,卻采取輕描淡寫的態度,試圖毫無原則地“和稀泥”,使得青年大學生的青春更蒙上了一層悲憤的色彩。類似的故事,也許還有很多,但這絕對不是學校管理的主流,影片沒有設計任何“正面”的學校管理和服務人員的形象,這不得不說是一種遺憾。
對教師形象的戲謔。在電影看來,本應在學校承擔“教書”與“育人”功能的教師們,也沒有給學生樹立起自身應該具備的形象。曾毓的父親、以領導和教師形象出現的曾主任,被“青春”攻擊潰敗而失意退場:很顯然,曾主任要演唱的節奏舒緩的《北國之春》,與鄭微的一首動感十足的《紅日》對于青年大學生來講,接受和意義均不在同一層面上。把自行車搬進教室,并對學生進行“痞里痞氣”的“恐嚇”的李老師,在被遲到的學生欺騙愚弄的時候氣急敗壞:其“教師”形象也不光彩,亦被戲謔與嘲諷。
(三)對青春意義模式的消解
青春到底是什么樣的?要找出一個能被所有人都接受的價值與意義模式的確很難,這是一個極具個性色彩的字眼。但有一點可以確定,青春的內容不能只用愛情和友情來填充,青春的意義也不能只在愛情與友情的擁有與失去的過程中獲取,青春的價值模式也不能等同于愛情與友情的價值模式。真實,不是價值意義的終極目的。我們看到的“臟、亂”的學生宿舍,各種生活在游戲世界中的莘莘學子,坐擁權與利而肆意踐踏別人尊嚴的富二代與官二代,等等,這些或許在我們的大學青春歲月中被聽到過、見到過,甚至經歷過,電影在展現這些場景的時候,關注了真實,卻懸置了價值,這種沒有立場的自然主義式的展覽,毫無意義傾向的場景,可能會引起觀眾的共鳴性回憶,卻無法求得回顧性梳理與反思。類似女主人公“我們一起度過了,誰也不虧欠誰的,青春就是用來懷念的”空洞的解釋,無法回答青春的價值和意義到底魂歸何處。正如胡清、蔡海波在《新世紀以來中國內地青春電影思考》中指出的:“青春電影在多元化的投資方式下,也呈現出類型各異的風格特征,既有堅守者,又有回歸潮,更有追求商業娛樂效應的紛繁錯綜、碰撞交融,對內地青春電影的發展是有著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同時,也淡化了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青春電影所擁有的深刻文化意義和獨特個性。”
總之,從商業電影的運作模式和效果上講,趙薇導演的電影《致青春》是成功的。但是,這種成功,難掩其敘事手段不夠豐富的無奈,也不得不面對電影主題——“青春”的價值迷失的尷尬。
注釋:
① 王連峰:《〈一九四二〉:歷史語境中的人性諦視》,《電影文學》,2014年第1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