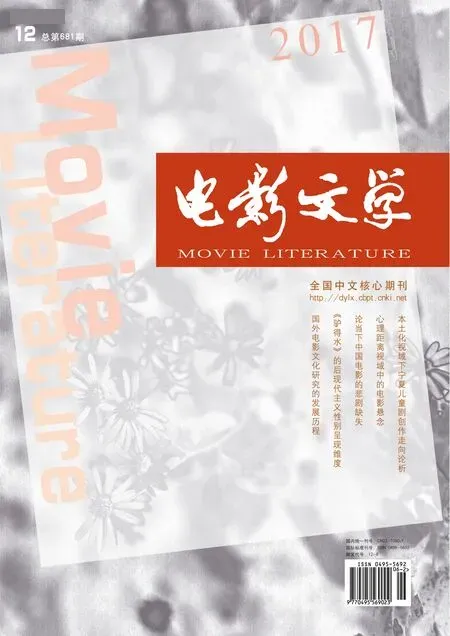《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的悲劇性解讀
蘭玉玲 (齊齊哈爾大學公共外語教研部,黑龍江 齊齊哈爾 161006)
李安是一位極具悲劇意識的導演,縱觀其電影,盡管它們背景、題材乃至文化指向各異,但其中幾乎都體現著某種悲劇精神。李安根據作家本·方丹(Ben Fountain)同名小說改編的電影《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BillyLynn’sLongHalftimeWalk,2016)亦不例外。盡管在影片上映前后,圍繞電影的討論基本上都圍繞李安大膽采用的,能給觀眾帶來空前清晰感、立體感的120幀技術展開,但在形式之外,《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的敘事也是值得進行解讀的。電影以比利·林恩在一場橄欖球比賽前后的數小時時間的活動給予了觀眾情感震撼,表達了導演的悲憫情懷。
從悲劇的深度而言,《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中依次存在三個層次的悲劇,分別是戰爭的殘酷、社會的無情以及人生的無奈。不難看出,隨著這三個層次的遞進,其所涉時空范圍便越大,能夠對悲劇感同身受的人便越多。
一、表層悲劇:戰爭的殘酷
只要對李安作品稍加了解就不難發現,無論是面對東西方題材,現實或奇幻、魔幻題材,李安都秉承著一種東方特有的節制與含蓄。其電影往往取材于他人的小說,而在對小說內容進行影像化的時候,李安總是采用一種“中性立場”,其隱藏在鏡頭背后的終極人文關懷往往需要觀眾自行品味。在張揚悲劇意識時亦是如此,李安并不會單純地為觀眾展示人生無邊的絕望與徹底的荒誕,使觀眾痛苦并不是李安的最終目的,啟發觀眾發現潛藏于哀傷、苦難之后的人性才是李安的目的。
就這一點而言,可以將《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中對戰爭場面的表現與同樣經典的《拯救大兵瑞恩》(1998)、《生于七月四日》(1989)進行對比,不難發現同樣是表現戰爭的殘酷,后二者選擇了對戰爭場面進行高度還原,如《拯救大兵瑞恩》以長達20分鐘的時間濃墨重彩地表現士兵在諾曼底登陸時相繼死去的場面,以為“大兵瑞恩是否值得被拯救”提供一個討論的背景。而《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中的戰爭場面卻并不宏大、血腥,也并無某種史詩性的厚重感,數個戰爭鏡頭是以閃回的方式出現的,而直接表現死亡的則只有兩處:一處是蘑菇班長的陣亡,一處則是一個與林恩近身肉搏的“圣戰者”的死去。這一來是與導演對戰爭性質理解的區別有關的(《拯救大兵瑞恩》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無疑是已被定性的,《生于七月四日》中的越戰在藝術創作領域中則通常是被否定的對象,而《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中的伊拉克戰爭則去今未遠,在美國乃至國際社會有著極大的爭議)。二來則是與導演的個人藝術偏好有關。與高度張揚愛國主義精神的《拯救大兵瑞恩》,以及具有明確反戰態度的《生于七月四日》不同,《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正好處于一個微妙的中間點。李安有意識地選擇了方丹這本表現美軍出兵伊拉克的小說,主人公因為這場尚未有清晰定義的戰爭而被置于一個微妙的境地:一方面,他們是國家的英雄,受到萬眾矚目的禮遇;另一方面,包括姐姐在內的親人則認為他們是“侵略者”。在李安的處理下,電影的主題是曖昧的,它既不是一部史蒂芬·斯皮爾伯格擅長的主旋律式電影,更不是一部純粹的反戰之作。
然而,盡管電影無意于指向反戰,但對于戰爭的殘酷性依然有著到位的揭示。這也是電影給予人悲劇感最為直觀的元素。首先是在槍林彈雨的戰場上,生死之隔就在須臾之間,蘑菇班長在行動前一個個地對士兵們說“我愛你”,正是預見到自己隨時有可能會失去生命。對于民眾來說,戰爭也同樣是殘酷的。電影中表現了美軍士兵在伊拉克居民家中搜查時婦女們撕心裂肺的哭喊和雙方在無法溝通情況下的敵意。而作為“入侵者”一方的家屬,林恩的家人也日夜生活在失去親人的擔憂中。其次,更為殘酷的是在戰場之外,大量士兵罹患了PTSD(創傷后壓力心理障礙癥)而無法適應社會。如在電影中,賽克斯在被舞臺的煙火嚇到以后情緒迅速激動起來,開始打推搡他的工作人員,在觀眾席上因為有觀眾輕佻地談起軍隊里的同性戀問題而將那名觀眾鎖喉致其昏厥等。戰爭帶來的創痛勢必在美國大面積、長時間地蔓延下去。
二、次層悲劇:社會的無情
《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中較戰爭更深一層的悲劇是根深蒂固的社會癥結。首先,展現著一種當下美國社會中的冷漠現象。B班的戰士們在橄欖球的現場茫然地被一群人指揮著,換軍裝,聽到某句歌詞的時候站在某個地點,然后立正不動一直到表演結束,等等。在嘈雜的比賽現場,戰士們全部無法理解導演的意圖,對這些交代左耳朵進右耳朵出,而導演也沒有解釋的耐心。林恩們成為塑像一般的表演道具,無論他們曾經怎樣出生入死,在這個時候他們實際上都是“真命天女”等明星的陪襯,是觀眾需要的激情、娛樂的一部分。在喧鬧的表演結束后,戰士們依然呆立在原地,各懷心事。林恩是想起了戰場時的悲慘景象,而戰友們則有的是激動于終于見到了碧昂斯等偶像。然而舞臺工人們因為只有九分鐘的裝臺時間,迅速與這群遲遲不肯離去的戰士起了沖突,兩邊都正情緒激動的小伙子很快就大打出手。在被保安拉開以后,舞臺工人選擇了在停車的卸貨區蹲守,在士兵們毫無防備的情況下再次沖出來,兩伙人又一次陷入纏斗之中,直到戴恩鳴槍示警,這一次斗毆才宣告結束。這是一個極具諷刺性的橋段,B班士兵在一個節目的時間內就從被邀請、被吹捧、被擁護的對象成為被遺棄、被圍毆的不受歡迎者。這兩種身份都不是士兵們主動選擇的。他們以一無所知的狀態來參加這一次球賽,又糊里糊涂地敗興而歸,并且在離開之后還要奔赴戰火紛飛的伊拉克。當舞臺工人在打架時說“這就是我們的兵”,言下之意便是這樣的軍人不值得納稅人供養時,B班士兵們的心中發出的聲音則是“這就是我們拼死保衛的人民”,雙方處于一種對立的位置,都認為對方辜負了自己的付出。
其次,對這種冷漠電影給出了答案,這是消費時代必然的產物。政治本身就是冷血的,戰爭在任何年代也都是殘酷的,但是在林恩所處的時代,他所經歷的冷漠無情在于這是一個幾乎一切都可以商品化的年代。在消費主義的影響下,人們抱有一種娛樂至上、利益至上的生活觀,而急促的生活節奏也致使人們只關心自己的情緒,這導致了一種扭曲。在林恩們前往球場時,組織他們的制片人就聲稱他們的故事將被著名導演拍成電影,他們將每人得到十萬美元,興奮的戰士們甚至已經計劃好了這筆錢的用途。然而就在球賽的短短幾十分鐘內,這個電影拍攝計劃就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制片人帶班長戴恩和作為主角存在的林恩去到投資方的包房里,告訴他們,第一,電影并不會展現整個B班;第二,他們每人只會得到5500美萬。這是重視戰友情義的戴恩和林恩無法接受的。而投資方奧格爾斯比先生則高傲地解釋道,他們曾經值得這筆錢,但是現在距離林恩勇救班長視頻在網絡上的火爆已經過去了兩個星期,對于好萊塢來說,兩個星期和兩年是沒有什么區別的,原本談好的巨星表示對這個題材沒有了興趣。換言之,林恩曾經的九死一生在消費主義時代下已經迅速地貶值了。
三、深層悲劇:人生的無奈
在對《斷背山》(BrokebackMountain,2005)進行總結時,李安曾經表示“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座斷背山”,以此來形容人生總有各種遺憾,人們有可能會因外在壓力和自我認同問題而阻礙自己得到幸福。由于李安在每一部電影中都流露出的“以小見大”的藝術追求,《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也同樣可以被引申為“每個人心中都有一次中場戰事”。
電影中最深層的悲劇在于,李安以林恩的故事揭示了人生的處處不自由,而人對這種不自由是無力抵抗的。首先,不自由體現在人選擇的有限上。林恩本人雖然身為以服從為天職的軍人,但是他并不是沒有選擇的。在電影中,林恩主要做了三個影響自己人生之路的選擇,以這三個選擇花費他考慮的時間排序,依次為:不顧自身安危營救蘑菇班長;拒絕了奧格爾斯比先生的無理要求;婉拒了姐姐請心理醫生幫助他開假醫療證明以避免再上戰場的懇求。從表面來看,林恩根據自己的意志支配了自己的命運,然而他最終依然無法平衡個人意識與時代洪流之間的沖突,“回歸戰場”僅僅是林恩所能夠做出的“最不壞”的選擇。最后踏上加長悍馬(在林恩的幻覺中,悍馬車成為戰車,車上坐著已經犧牲了的蘑菇班長)的林恩熱淚盈眶,戰友們一個個對他說“我愛你”,但此時林恩并沒有因為自己的選擇而獲得平靜和堅定,相反,他依然是惶惶不安的。林恩代表了有如塵埃的蕓蕓眾生,幾乎每一個個體都無法主宰自己的命運,而只能被各種外在因素裹挾著走完自己的人生。
其次,不自由還體現在人與人之間的難以互相理解上。在電影中,年僅19歲的林恩是一個高度孤獨的個體,林恩身邊的人沒有一個能給予他共情、理解和歸屬感。他出場時的定位是國民英雄,然而他卻厭惡因為“人生中最糟糕的一天”給他換來榮譽,這些榮譽反復提醒著他那段痛苦的回憶。廣大群眾熱愛在鏡頭前、聚光燈下的這群英雄,與其說是真心實意地尊敬他們,倒不如說是一種獲取愛國感、正直感的自我滿足(在電影中有一個蒙太奇鏡頭是人們在近距離接觸林恩的時候實際上對林恩談論的都是自己,如“我也曾經穿過制服”等),這種對他人熱愛的滿足的代價是林恩將自己置于人間地獄中;而最在乎林恩生命的姐姐,也即林恩參軍的直接關系人,則旗幟鮮明地反對林恩參加這場戰爭,她想保全弟弟的生命以及“純潔”;而即使是林恩最后選擇的以戴恩為代表的、和林恩生死與共的戰友們,實際上也并不能理解林恩,當林恩試探性地詢問戴恩有沒有想過退伍時,得到的是戴恩義正詞嚴的呵斥。
與拉拉隊員菲姍的一段短暫的情緣是林恩在這場“中場戰事”中邂逅的唯一美好,菲姍的存在也確實動搖了林恩繼續軍旅生涯的信念,然而這僅有的美好也很快被打破。在兩人告別時,林恩坦承他曾經想帶菲姍私奔。而菲姍的第一反應是“你不是要回戰場嗎,你是授勛英雄啊!”這徹底地斷絕了林恩最后一絲利用假醫療證明遠離戰場的念頭。這一刻的林恩明白,菲姍所愛的,僅僅是比利“授勛英雄”的光環而非他本人,菲姍從來沒有真正打算與他廝守,兩人所擁有的也僅僅是一面之緣帶來的好感,是與愛無關的。最后林恩的一句對姐姐半開玩笑、半認真的“我可能要以處男之身死去了”流露出他對這段實際已經無疾而終的感情的絕望。
綜上,李安的跨文化背景成為其遴選劇本的寶藏,而李安本人敏感思辨的心智則是其創作的源泉,其電影往往以大悲無言的姿態,表現著現實的質感以及生活的凌厲。其新作《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在以高清的120幀技術吸引著人們眼球的同時,也在敘事上清晰地洞察著人性和社會的細微之處,傳遞出悲劇美。李安匠心獨運地在電影中表現了戰爭、當代消費社會以及人生三個層面的悲劇,而在使觀眾感到遺憾與悲傷的同時,李安又不忘促使觀眾體味主人公的自省與救贖。可以說,以《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為切入點來觀照李安電影的悲劇感,是兼具現實意義與審美意義的。